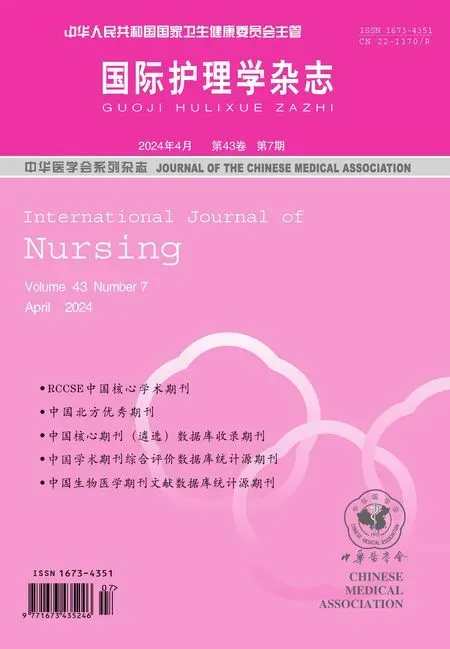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預期性悲傷的影響因素及中介效應檢驗
黃思明 江錦芳 蔣婷 謝金芹
廣西醫(y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南寧 530021
兒童癌癥負擔是全球癌癥負擔的重要部分〔1〕,而中國在全球兒童癌癥負擔中占比較大〔2〕。規(guī)律、長程、系統(tǒng)的治療是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所要承受的過程,一系列的治療副反應,如認知功能障礙、代謝和內分泌異常、骨毒性反應、心臟損傷和社會/心理不良反應等〔3〕使得兒童和青少年癌癥父母在照護患兒的過程中不僅要承受著沉重的治療負擔,還需要不斷對現(xiàn)實情況進行評估和預期,對家庭角色和功能進行重新調配〔4-5〕,這種感知到的強烈喪失感及難以解脫的壓力所形成的悲傷體驗被稱為預期性悲傷〔6〕,預期性悲傷反映了照顧者在不同臨終軌跡中的悲傷體驗〔7〕。當照顧者為父母時,盡管預期性悲傷理論上是一種自然過程,但實際面對這個過程時卻是艱難的〔8-9〕,較高水平的悲傷體驗不僅可導致照顧者情緒崩塌,還可能會對患者后續(xù)的治療及護理產生負面的影響,因此重點關注兒童和青少年人癌癥父母的預期性悲傷是有必要的。目前已有研究表明照顧者預期性悲傷與應對方式、焦慮抑郁和照顧者負擔存在密切相關關系〔9-11〕。應對策略是照顧者負擔的重要預測因素〔12〕,焦慮抑郁與照顧者負擔可能相互依存〔13〕,抑郁狀態(tài)可預測潛在的悲傷狀況〔14-15〕。此外,研究證實照顧者負擔是預期性悲傷的中介因素〔16〕。而預期性悲傷的具體發(fā)展路徑有待進一步探討。Stroebe等〔17〕構建的預測喪親結局的綜合風險因素框架包括了應對策略、個人因素、人際因素等預測因素,是有效識別癌癥照顧者預期性悲傷的理論模型〔18〕。因此本研究擬探討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預期性悲傷影響因素并基于該綜合風險框架理論探討其發(fā)展路徑機制,以期為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的預期性悲傷的個體化干預提高有效的指導方向。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樣本量估計依據預期性悲傷量表條目數(shù)的5~10倍計算,并考慮10%-20%的樣本流失,確定樣本量至少為165份。2022年1~8月采用便利抽樣法選取廣西醫(y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化療科185例住院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經病理學檢查確診為癌癥的兒童和青少年患者;②患者年齡<20歲;③患者住院期間主要照顧者為父親或母親;④調查對象知情同意,自愿參加。排除標準:患者父母存在讀寫障礙或認知障礙。
1.2 研究方法
1.2.1調查工具
1.2.1.1一般資料調查表 由研究者基于文獻回顧后自行編制,主要內容包括父母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居住地、職業(yè)狀態(tài)、健康狀況、子女狀況、家庭月收入、宗教信仰、性格,患者年齡、醫(yī)療付費方式、確診時間等。
1.2.1.2預期性悲傷量表(Anticipatory Grief Scale,AG) 由美國華盛頓國家兒童醫(yī)學中心研究員Theut〔19〕研制,主要用于評估癌癥患者家屬預期性悲傷的感知程度。本研究采用我國學者辛大君〔20〕于2016年進行跨文化調適后的中文版AG。總分范圍為27~135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家屬預期性悲傷程度越重。中文版AG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 α系數(shù)為0.896,分半信度系數(shù)為0.872。本研究中該量表Cronbach α系數(shù)為0.852。
1.2.1.3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采用解亞寧〔21〕在Folkman和Lararu研發(fā)的應對方式清單的基礎上針對中國國情修訂的量表,該量表包含積極應對(Positive Coping,PC)和消極應對(Negative Coping,NC )2個維度。本研究中該量表積極應對維度的Cronbach α系數(shù)為0809,消極應對維度的Cronbach α系數(shù)為0.731。
1.2.1.4照顧者負擔量表(Zarit Caregiver Burden Interview,ZBI) 由Zarit等開發(fā)并由王烈等〔22〕對其進行漢化及修訂的主觀量表,該量表主要包含個人負擔和責任負擔2個維度總分范圍為0~88分,得分越高,表明照顧者負擔程度越重。中文版ZBI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 α系數(shù)為0.87。本研究中該量表Cronbach α系數(shù)為0.855。
1.2.1.5醫(yī)院焦慮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 由Zigmond等〔23〕開發(fā)的用于心理自我評估的量表,研究表明該量表在癌癥患者及家屬中群中有良好的信效度〔24〕。該量表包含焦慮和抑郁兩個維度得分越高,表明焦慮抑郁程度越重。本研究中該量表總體Cronbach α系數(shù)為0.833。
1.2.2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通過面對面直接招募研究對象,由經過培訓的課題成員向參與調查者發(fā)放宣傳材料,進行面對面的調查問卷,所有調查對象均知情同意。
1.3 統(tǒng)計學方法
數(shù)據資料采用SPSS 26.0和 PROCESS v4.0插件進行處理和分析。應用Harman單因素法〔25〕進行共同方差檢驗;采用獨立樣t檢驗、方差分析、Pearson相關性分析探索預期性悲傷的影響因素;運用PROCESS插件中的Model4和Model6(以應對方式為自變量、照顧者負擔和焦慮抑郁為中介變量、預期性悲傷為因變量構建中介模型),假設模型檢驗通過Bootstrap法(重復抽樣5 000次)計算中介效應95%置信區(qū)間進行檢驗,當置信區(qū)間不包含零時則認為中介效應顯著〔26〕。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結果顯示共有23個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個因子解釋比例為20.24%,因此可認為研究樣本數(shù)據所致的共同偏差不構成明顯的影響。
2.2 不同特征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預期性悲傷得分情況
本研究共納入185名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參與調查,調查對象的預期性悲傷平均得分為(86.57±15.33)分,不同照顧者角色、年齡、婚姻狀況、職業(yè)狀態(tài)、家庭收入及患兒病程的預期性悲傷得分比較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P<0.05)。見表1。

表1 不同特征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預期性悲傷得分情況
2.3 應對方式、焦慮抑郁、照顧者負擔及預期性悲傷的得分情況及其相關性分析
185例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的積極應對總分為(19.47±6.26)分、消極應對總分為(12.56±4.36)分、焦慮抑郁總分為(20.92±7.08)分、照顧者負擔總分為(27.43±11.80)分、預期性悲傷總分為(86.57±15.33)分。預期性悲傷與積極應對、消極應對、焦慮抑郁及照顧者負擔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均呈顯著相關(P<0.01),其相關系數(shù)見表2。

表2 應對方式、焦慮抑郁、照顧者負擔及預期性悲傷相關性分析(γ值)
2.4 照顧者負擔和焦慮抑郁的多重中介效應檢驗
多重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不同模型的中介效應顯著,積極應對與消極應對在預期性悲傷中的總效應值分別為-1.002 6(P<0.05)和1.376 3(P<0.05);直接效應值分別為-0.253 0(P<0.05)和0.308 5(P<0.05);總間接效應值分別為-0.769 6(P<0.05)和1.067 8(P<0.05),占總效應的75.26%和77.58%。這提示控制照顧者負擔和焦慮抑郁中介因子后,應對方式仍對預期性悲傷產生作用。見表3。

表3 照顧者負擔和焦慮抑郁在應對方式與預期性悲傷間的中介效應分析
2.4.1照顧者負擔和焦慮抑郁在應對方式與預期性悲傷中的并行中介效應檢驗 并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積極應對方式下的照顧者負擔和焦慮抑郁的中介效應占比相當,分別為37.72%和37.54%,且兩條中介路徑之間的效應檢驗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提示兩條中介路徑對預期性悲傷的影響無明顯差異。消極應對方式下的照顧者負擔和焦慮抑郁的中介效應占比分別為49.57%和28.02%,且兩條中介路徑之間的效應檢驗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提示照顧者負擔比焦慮抑郁更能影響消極應對的預期性悲傷的作用。
2.4.2照顧者負擔和焦慮抑郁在應對方式與預期性悲傷中的鏈式中介效應檢驗 鏈式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優(yōu)先控制照顧者負擔中介效應后,積極應對與預期性悲傷間的路徑系數(shù)存在顯著性(β=0.300 0,P<0.05),而消極應對與預期性悲傷間的路徑系數(shù)則不再顯著(β=0.081 5,P>0.05),這提示若能有效控制照顧者負擔,可阻斷焦慮抑郁在消極應對與預期性悲傷間的中介效應;而優(yōu)先控制焦慮抑郁中介效應后,積極應對與預期性悲傷間的路徑系數(shù)不存在顯著性(β=-0.061 0,P>0.05),而消極應對與預期性悲傷間的路徑系數(shù)存在顯著(β=0.239 1,P<0.05),這提示若能有效控制焦慮抑郁,可阻斷照顧者負擔在積極應對與預期性悲傷間的中介效應。
3 討論
3.1 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預期性悲傷水平較高
本研究結果顯示成年癌癥患者父母預期性悲傷平均得分較高 ,與晚期癌癥患者護理人員預期性悲傷水平相似〔11,27-28〕,但高于認知障礙患者主要照顧者的預期性悲傷水平〔29-30〕,這可能與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對癌癥的醫(yī)療風險感知水平較高有關〔31〕。此外兒童和青少年癌癥疾病發(fā)展進程快,臨床表現(xiàn)較為隱匿以及一系列的治療副反應等特征也可能加重父母預期性悲傷水平。
3.2 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預期性悲傷影響因素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照顧者角色、年齡、婚姻狀況、職業(yè)狀態(tài)、家庭收入及患兒病程的預期性悲傷得分比較差異有顯著性。年輕母親、患者父母婚姻關系差、工作不穩(wěn)定、家庭經濟收入低等是預期性悲傷的重要影響因素,醫(yī)護人員應對存在以上特征的照顧者預以悲傷心理關注。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預期性悲傷與焦慮抑郁及照顧者負擔顯著相關,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10〕。于偉等的研究表明照顧者負擔可介導積極應對對預期性悲傷的影響〔32〕,但消極應對對預期性悲傷的具體機制卻是未知的,本研究則在此基礎上做了更進一步的探討,并剖析不同的應對方式對預期性悲傷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表明照顧者負擔、焦慮抑郁可獨立或多重介導應對方式在預期性悲傷中的作用。應對方式通過照顧者負擔及焦慮抑郁影響患兒父母預期性悲傷的發(fā)展,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在預期性悲傷中的總間接效應占比分別為75.26%和77.58%。負擔水平較重、焦慮抑郁水平較高的照顧者承受著較高水平的悲傷體驗且傾向于采取消極應對方式,這可能是因為依賴情緒介導的應對策略難以有效控制不良心理狀況的發(fā)展〔33〕。難以預期的照料負擔、反復治療造成的經濟負擔、社會角色的變化等還可加劇焦慮抑郁程度〔34〕。
3.3 兒童和青少年癌癥患者父母預期性悲傷中介效應分析
并行中介模型路徑顯示不同應對方式干預的中介效應結果存在較大差異。積極應對下照顧者負擔和焦慮抑郁介導的兩個路徑中介效應相當,而消極應對下照顧者負擔介導的中介效應比焦慮抑郁大接近一倍。此外,照顧者負擔介導的積極應對對預期性悲傷的影響和焦慮抑郁介導的積極應對預期性悲傷的影響無明顯差異;照顧者負擔介導的消極應對對預期性悲傷的影響比焦慮抑郁介導的積極應對預期性悲傷的影響大。鏈式中介模型結果顯示優(yōu)先有效控制照顧者負擔時可阻斷焦慮抑郁在消極應對在預期性悲傷間的中介作用,優(yōu)先有效控制焦慮抑郁時可阻斷照顧者負擔在積極應對在預期性悲傷間的中介作用,這與Yu W等〔32〕的研究結果方向基本一致,這提示了應對方式的不同可能是影響兒童和青少年癌癥父母心理狀況的前提影響因素,有必要對針對不同的應對方式而采取個性化干預措施。在臨床實踐中我們需要對傾向于采用消極應對方式的父母給予更多的關注,注意其照顧負擔的具體內容并有效指導或協(xié)助減負的措施;對而對于更傾向于采用積極應對策略的父母則應更加關注其焦慮抑郁水平,深入了解其精神需求,及時發(fā)現(xiàn)不良情緒,保持積極的能動性。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