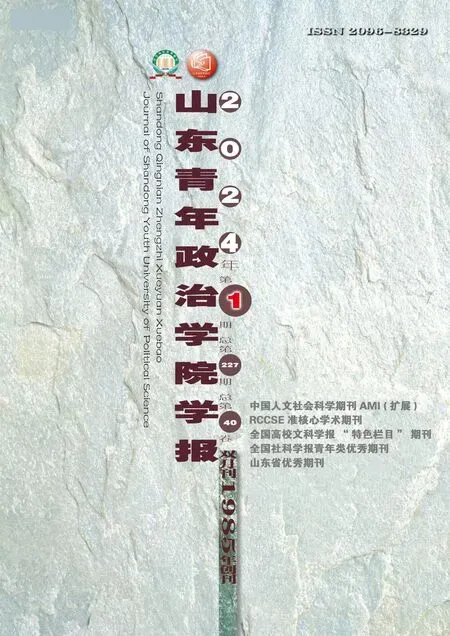以“大人之學(xué)”分判朱王之學(xué)
魏子欽
(安徽大學(xué) 哲學(xué)學(xué)院,合肥 230039)
作為“初學(xué)入德之門(mén)”與“孔氏之遺書(shū)”的《大學(xué)》,(1)朱熹:《四書(shū)章句集注》,中華書(shū)局,2010,第1頁(yè)。經(jīng)過(guò)朱子的詮釋,曾在宋明之際大放異彩。王陽(yáng)明早年也曾深究朱子所注之《大學(xué)》,并借其“格物”思想而格竹,但七日未見(jiàn)竹理,遂致重疾。直到龍場(chǎng)悟道,陽(yáng)明乃嘆“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2)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1031頁(yè)。于是,陽(yáng)明批評(píng)朱子“析心與理為二矣。”(3)同上書(shū),第41頁(yè)。不過(guò),朱子后學(xué)也以敗壞人心,禍亂朝綱為罪,批判陽(yáng)明之學(xué)是陽(yáng)儒陰釋,荼毒人心。按照梁?jiǎn)⒊呐卸?面對(duì)明朝覆滅,清初學(xué)者的“王學(xué)反動(dòng),其第一步則返于程朱。”(4)梁?jiǎn)⒊骸吨袊?guó)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東方出版社,2004,第110頁(yè)。正如張履祥言:“姚江著書(shū)立說(shuō),無(wú)一語(yǔ)不是驕吝之私所發(fā)。”(5)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中華書(shū)局,2002,第1173頁(yè)。有“清朝理學(xué)儒臣第一”之稱(chēng)的陸隴其,亦撰《學(xué)術(shù)辨》《松陽(yáng)講義》等著作專(zhuān)批王學(xué)。由此,朱王之學(xué)糾纏在學(xué)術(shù)與政治之間,影響后世對(duì)朱子、陽(yáng)明之學(xué)的客觀(guān)理解。從朱、王注《大學(xué)》看,朱子、陽(yáng)明注《大學(xué)》皆由“大學(xué)者,大人之學(xué)也”起,但二者卻存在明顯差異。有鑒于此,本文借朱子、陽(yáng)明對(duì)“大人之學(xué)”的闡釋,以“大人者”(學(xué)習(xí)主體)、“大學(xué)之教”(學(xué)習(xí)內(nèi)容)、“大學(xué)之道”(學(xué)習(xí)目標(biāo))掀開(kāi)遮蔽朱子、陽(yáng)明注《大學(xué)》用意之紗。
一、“何為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與“天地萬(wàn)物一體者”
朱子、陽(yáng)明在詮釋《大學(xué)》之時(shí),都曾對(duì)學(xué)習(xí)《大學(xué)》的主體作出界定。朱子認(rèn)為“大人之學(xué)”的主體是指“大人”,與其相對(duì)的是“小子”,即“大學(xué)者,大人之學(xué)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xué),有大人之學(xué)。(6)朱熹:《朱子全書(shū)》,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691頁(yè)。陽(yáng)明在《大學(xué)問(wèn)》中指出:“大人者,以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者也。”(7)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823頁(yè)。盡管陽(yáng)明認(rèn)為“大人之學(xué)”的主體是“大人”,但陽(yáng)明對(duì)“大人”的理解與朱子對(duì)“大人”的理解存在明顯不同,這是因?yàn)橹熳优c陽(yáng)明對(duì)“大人”的詮釋立場(chǎng)存在差異。
朱子對(duì)“大人”的詮釋,是站在古代教育階段設(shè)計(jì)的角度進(jìn)行論述的,并對(duì)受教育者何時(shí)學(xué)習(xí)“大學(xué)”與何時(shí)學(xué)習(xí)“小學(xué)”作出進(jìn)一步說(shuō)明。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xué),而教之以灑掃、應(yīng)對(duì)、進(jìn)退之節(jié),禮樂(lè)、射御、書(shū)數(shù)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xué)。(8)朱熹:《四書(shū)章句集注》,中華書(shū)局,2010,第2頁(yè)。
“小學(xué)”的學(xué)習(xí)主體是“小子”。“小子”是指到了八歲、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的子弟。這些“小子”進(jìn)入“小學(xué)”之后,開(kāi)始學(xué)習(xí)“小學(xué)”的具體知識(shí),如灑掃應(yīng)對(duì)等禮儀規(guī)范、禮樂(lè)書(shū)數(shù)等知識(shí)文化。“大學(xué)”的學(xué)習(xí)主體是指完成“小學(xué)”后立志成為“大人”的這批學(xué)子。這批學(xué)子是指“十有五年”從天子之元子到凡民之俊秀的優(yōu)秀群體,他們不僅是從“小學(xué)”選拔出來(lái)的人才精英,也是被社會(huì)寄予厚望的一批學(xué)子。所以,他們?cè)谕瓿伞靶W(xué)”的學(xué)習(xí)任務(wù)后,進(jìn)入“大學(xué)”所學(xué)的主要內(nèi)容便是蘊(yùn)含在“小學(xué)”之中的深層義理。朱子講:“古者小學(xué)已自養(yǎng)得小兒子這里定,已自是圣賢坯璞了,但未有圣賢許多知見(jiàn)。及其長(zhǎng)也,令入大學(xué),使之格物、致知,長(zhǎng)許多知見(jiàn)。”(9)朱熹撰,黎靖德編《朱子語(yǔ)類(lèi)》,中華書(shū)局,2020,第135頁(yè)。朱子對(duì)“大學(xué)”與“小學(xué)”的學(xué)習(xí)主體的討論,首先考慮到受教育者的身心、年齡等發(fā)展階段與社會(huì)階層問(wèn)題。朱子也告訴立志成為“大人”的“小子”,只有“于小學(xué)存養(yǎng)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xué),只就上面點(diǎn)化出些精彩。”(10)同上書(shū),第136頁(yè)。
因此,朱子對(duì)“大人”的概念界定,是以“大德”闡釋“大人”。他認(rèn)為“大人”乃是“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11)朱熹:《四書(shū)章句集注》,中華書(shū)局,第267頁(yè)。換言之,“大人”必是有大德之人,有此大德者須正己為先,不可好逸惡勞、斤斤計(jì)較,畏縮在個(gè)人的利害得失之間。換言之,大人者須先正己,但亦要向外擴(kuò)充而正物,不能正物,也非大人。故而,朱子以《周易》闡釋“大人”,認(rèn)為“大人”是以“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jiàn)龍?jiān)谔?天下文明’者。”(12)同上書(shū),第332頁(yè)。可見(jiàn),朱子對(duì)“大人”的闡釋,不僅使“大人”包含德盛大化的道德屬性,也包含正己正物的政治屬性,使“大人”并不是僅僅停留在個(gè)人的修養(yǎng)層面,而是告訴人們真正的“大人”一定要在社會(huì)中實(shí)現(xiàn)自我價(jià)值。這也正如朱子所言:“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wú)偽之本然。”(13)同上書(shū),第272頁(yè)。故朱子之“大人”,乃是從其大體而論,其德廣盛與天,其志通達(dá)天下,其業(yè)安定萬(wàn)民,大人可斷天下之疑,敦厚崇禮,開(kāi)物成務(wù)。
與朱子所理解不同的是,陽(yáng)明認(rèn)為的“大人”并非朱子認(rèn)為的大德之人、正己正物者,而是能與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者。而且,陽(yáng)明認(rèn)為對(duì)“大人”相對(duì)應(yīng)的主體,也不再是朱子認(rèn)為教育階段設(shè)計(jì)中的“小子”,而是不能與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的“小人”,即“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14)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823頁(yè)。陽(yáng)明以“萬(wàn)物一體”為判定標(biāo)準(zhǔn)對(duì)“大人”與“小人”作出區(qū)分,認(rèn)為“小人”在形骸上亦有人我之別,而大人卻能與萬(wàn)物皆為一體,能夠以“一體之仁”體知到親親仁民而愛(ài)物,如孩提入井之憂(yōu)、草折瓦裂之惜。在此基礎(chǔ)上,陽(yáng)明也指出,不是體驗(yàn)到“萬(wàn)物一體”就是“大人”,而是體驗(yàn)到“萬(wàn)物一體”的那一刻才是“大人”。所以,只要“大人”一旦墮落到私欲之界,“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15)同上。
對(duì)于“大人”的理解,朱子與陽(yáng)明不僅在詮釋立場(chǎng)出現(xiàn)分歧,也在概念界定存在差異。所以,面對(duì)“大人”的詮釋內(nèi)容問(wèn)題,朱子與陽(yáng)明也就出現(xiàn)更為明顯的分歧。朱子認(rèn)為學(xué)習(xí)“大學(xué)”需要從“小學(xué)”入手。“小學(xué)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guī)矩做去。大學(xué)是發(fā)明此事之理。”(16)朱熹撰,黎靖德編《朱子語(yǔ)類(lèi)》,中華書(shū)局,2020,第136頁(yè)。朱子認(rèn)為小學(xué)與大學(xué)的關(guān)系,是理之所以然與理之所當(dāng)然的關(guān)系。不過(guò)有人問(wèn)朱子:“大學(xué)與小學(xué),不是截然為二。小學(xué)是學(xué)其事,大學(xué)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17)同上。這是說(shuō),盡管提問(wèn)者知道大學(xué)與小學(xué)不是分割的關(guān)系,但還是基于兩者學(xué)習(xí)內(nèi)容而產(chǎn)生疑惑:即雖然知道小學(xué)是學(xué)事,大學(xué)是學(xué)事中之理,但是卻對(duì)大學(xué)與小學(xué)的如何關(guān)聯(lián)問(wèn)題產(chǎn)生疑惑。朱子指出,大學(xué)與小學(xué)的學(xué)習(xí)內(nèi)容“只是一個(gè)事。小學(xué)是學(xué)事親,學(xué)事長(zhǎng),且直理會(huì)那事。大學(xué)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zhǎng)是如何。”(18)朱熹撰,黎靖德編《朱子語(yǔ)類(lèi)》,中華書(shū)局,2020,第136頁(yè)。也就是說(shuō),只有做到了“小學(xué)”,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細(xì)致的“大學(xué)”學(xué)習(xí),才能努力讓自己學(xué)成“大人”。
面對(duì)“大人”如何學(xué)習(xí)“大人之學(xué)”的問(wèn)題,陽(yáng)明提出人人皆可學(xué)習(xí)大人之學(xué),人人皆可成圣的主張,即“所以謂之圣,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圣。”(19)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29頁(yè)。只是,按陽(yáng)明之義,如果說(shuō)萬(wàn)物一體就是人我之間便無(wú)分別、亦無(wú)貴賤的話(huà),那么也就正如徐愛(ài)的疑惑那樣,就會(huì)出現(xiàn)《大學(xué)》為什么又說(shuō)個(gè)厚薄的疑問(wèn)。對(duì)此,陽(yáng)明答復(fù)到: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ài)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wú)所不忍矣。《大學(xué)》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20)同上書(shū),第100頁(yè)。
依《大學(xué)》所言之“薄”與“厚”而論,似與陽(yáng)明之萬(wàn)物一體發(fā)生齟齬。但按照陽(yáng)明的觀(guān)點(diǎn)而論,如果非要在兩件事物中選擇一種,那么此時(shí)一定會(huì)有厚薄之別、主次之分。他認(rèn)為,在《大學(xué)》中,道理本身確實(shí)有厚薄之分。其中的厚薄是指良知上的自然條理,是對(duì)道德和倫理的追求和理解。具體來(lái)說(shuō),在面對(duì)自己和親人時(shí),立志成為大人者不能存在厚薄之分,應(yīng)該同樣地對(duì)待自己和親人,不偏袒地對(duì)待每個(gè)人。只有當(dāng)立志成為大人者能夠以仁愛(ài)之心對(duì)待他人,做到得饒人處且饒人,做到“此處可忍,更無(wú)所不忍”。故而面對(duì)道理的薄與厚,陽(yáng)明認(rèn)為應(yīng)以“萬(wàn)物一體”為判斷依據(jù),即孰厚孰薄需落在“良知”上作出價(jià)值選擇。
朱子受“慶元黨錮”之禍,導(dǎo)致其學(xué)在當(dāng)世備受打擊,如他對(duì)“大人”的詮釋立場(chǎng)、概念界定、詮釋內(nèi)容并未受到當(dāng)時(shí)世人的廣泛學(xué)習(xí)與支持,僅是在《四書(shū)章句集注》等著作中明述“大人之學(xué)”。直到淳祐元年(1241)以后,宋理宗手詔下令以朱子從祀孔廟,淳祐四年(1244),南宋倡導(dǎo)程朱理學(xué),全尚理學(xué),使得《四書(shū)章句集注》備受重視而依此為言道標(biāo)準(zhǔn),后又為官方讀本、科舉考試的根本依據(jù)。到了明代,直到王陽(yáng)明的心學(xué)出現(xiàn),朱子學(xué)的一統(tǒng)天下地位開(kāi)始被撼動(dòng),同時(shí)也撼動(dòng)朱子對(duì)《大學(xué)》“大人之學(xué)”的理學(xué)闡釋。
朱子、陽(yáng)明注解《大學(xué)》“大人”的主體判斷上存在差異。朱子站在古代教育階段設(shè)計(jì)的詮釋立場(chǎng)上,認(rèn)為大人是“有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并對(duì)受教育者進(jìn)入小學(xué)、大學(xué)的學(xué)習(xí)條件設(shè)置年齡、身份、社會(huì)階層的各種條件,依此揭示出“大人”的詮釋內(nèi)容,挺立中國(guó)古代知識(shí)分子的人文精神。陽(yáng)明以“萬(wàn)物一體”為詮釋立場(chǎng),依此區(qū)別大人與小人,認(rèn)為小人是“形骸而分爾我者”,大人是“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者”,“大人”的詮釋內(nèi)容則是指人人皆可學(xué)大人之學(xué),人人皆可成圣。盡管朱子、陽(yáng)明之學(xué)各有特性,但朱子、陽(yáng)明著力闡發(fā)“大人者”的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大人”須真切把握“大人之教”。
二、“大學(xué)之教”:“格物窮理”與“致良知”
盡管朱子、陽(yáng)明對(duì)“大人”的理解存在不同,從詮釋理路看,朱子、陽(yáng)明同樣是從對(duì)學(xué)習(xí)主體的概念界定,推演出對(duì)“大人之學(xué)”的學(xué)習(xí)內(nèi)容的系統(tǒng)分析。只是,由于兩人的詮釋立場(chǎng)的不同,導(dǎo)致他們對(duì)“大人”的理解難以保持一致,使得兩人在“大學(xué)之教”即“大人”的學(xué)習(xí)內(nèi)容上,呈現(xiàn)不同的安排與主張。
面對(duì)“大學(xué)之教”的內(nèi)容安排問(wèn)題,朱子以為“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后王宮、國(guó)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xué)。”(21)朱熹:《四書(shū)章句集注》,中華書(shū)局,2010,第1頁(yè)。對(duì)此,朱子分大、小之學(xué),以為欲為“大人者”須學(xué)“大人之學(xué)”,學(xué)“大人之學(xué)”必讀“大學(xué)之書(shū)”,效驗(yàn)“古之大學(xué)所以教人之法”(22)同上書(shū),第2頁(yè)。。對(duì)此,朱子指出“大學(xué)之書(shū)”重在“格物”。朱子指出:“《大學(xué)》是圣門(mén)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xué)》最初用功處。”(23)朱熹:《朱子全書(shū)》,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772頁(yè)。
朱子特重“格物”,到王陽(yáng)明這里,盡管陽(yáng)明一生極少注釋儒家經(jīng)典,但陽(yáng)明也在《答羅整庵少宰書(shū)》中說(shuō)過(guò):“大學(xué)古本乃孔門(mén)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bǔ)輯之。”(24)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70頁(yè)。可見(jiàn),陽(yáng)明不滿(mǎn)朱子以“格物”補(bǔ)《大學(xué)》,他要恢復(fù)《大學(xué)》古本之義,故而拒斥朱子分經(jīng)傳、重章句、做補(bǔ)傳的方法。而且,據(jù)《年譜》記載:(陽(yáng)明)“疑朱子大學(xué)章句非圣門(mén)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圣人之學(xué)本簡(jiǎn)易明白。其書(shū)止為一篇,原無(wú)經(jīng)傳之分。格致本于誠(chéng)意,原無(wú)缺傳可以補(bǔ)處。以誠(chéng)意為主而為致知格物之功。”(25)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1054頁(yè)。陽(yáng)明認(rèn)為《大學(xué)》要旨是“誠(chéng)意”,“誠(chéng)意”才是踐行“格物”實(shí)現(xiàn)目的。對(duì)此,黃宗羲指出朱子、陽(yáng)明在“格物”與“誠(chéng)意”之間的各自側(cè)重。“朱子之解《大學(xué)》也,先格致而后授之以誠(chéng)意;(陽(yáng)明)先生之解《大學(xué)》也,即格致為誠(chéng)意。”(26)黃宗羲編《明儒學(xué)案》,沈芝盈點(diǎn)校,中華書(shū)局,1985,第7頁(yè)。所以,在“格物”與“誠(chéng)意”之間,陽(yáng)明以“誠(chéng)意”為先,朱子則是以“格物”為首,足見(jiàn)兩人對(duì)“大人之教”內(nèi)容設(shè)置的理解差異。
朱子與陽(yáng)明之所以對(duì)“大學(xué)之教”有不同的理解,是因?yàn)槎怂媾R的經(jīng)典詮釋困境不同。朱子認(rèn)為學(xué)習(xí)“大學(xué)之書(shū)”重在“格物窮理”,其原因在于朱子不滿(mǎn)漢唐經(jīng)學(xué)家對(duì)《大學(xué)》一書(shū)的注釋。東漢鄭玄說(shuō):“名曰《大學(xué)》者,以其記博學(xué)可以為政也。”(27)孔穎達(dá)疏,鄭玄注《禮記正義》,中華書(shū)局,第1592頁(yè)。之所以稱(chēng)為《大學(xué)》,是因?yàn)榇髮W(xué)一書(shū)教人廣博而治平天下。唐代孔穎達(dá)疏解鄭玄之說(shuō):“此《大學(xué)》之篇,論學(xué)成之事,能治其國(guó),章明其德于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chéng)意為始。”(28)同上。孔穎達(dá)認(rèn)為《大學(xué)》主旨是為學(xué)治國(guó),此以明德為本,誠(chéng)意工夫?yàn)槭肌V熳硬粷M(mǎn)鄭玄注解《禮記·大學(xué)》原文順序有問(wèn)題,故而重新對(duì)《大學(xué)》重做修訂,將《大學(xué)》分為“經(jīng)一章”與“傳十章”兩部分。另外,朱子也否定漢唐經(jīng)學(xué)家講《大學(xué)》從“誠(chéng)意”為先的看法,認(rèn)為《大學(xué)》古本存在闕文,于是取程子之義做補(bǔ),作《格物致知傳》,將“格物”傳、“致知”傳放在“此謂知本”后,列于“誠(chéng)意”傳之前,強(qiáng)調(diào)“格物窮理”而后才是“誠(chéng)意”,突出“格物窮理”在“大人之教”中的重要。
陽(yáng)明則不滿(mǎn)朱子注釋的“格物致知”。“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29)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41頁(yè)。陽(yáng)明認(rèn)為朱子對(duì)事事物物上求一定理,易使心放而使之,出現(xiàn)心與理為二、知與行相分離的局面。所以,陽(yáng)明不認(rèn)同以“敬”詮釋“即物格物”的朱子學(xué)。“如新本(指朱子《大學(xué)章句》)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wú)著落處,須用添個(gè)敬字方牽扯得向身心上來(lái),然終是沒(méi)有根源。”(30)同上書(shū),第36頁(yè)。陽(yáng)明認(rèn)為須“以誠(chéng)意為主,而為致知格物之工,故不須添一敬字。”(31)同上書(shū),第1032頁(yè)。
除以上問(wèn)題外,朱子與陽(yáng)明也對(duì)“大人之教”的具體主張作出說(shuō)明。朱子講“格物窮理”,認(rèn)為“格物窮理”的涵蓋范圍是天下事事物物,任何事物皆可被格。朱子言:“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wú)不到也。”(32)朱熹:《四書(shū)章句集注》,中華書(shū)局,2010,第5頁(yè)。盡管“格物窮理”面向一切事物,在培養(yǎng)“大人者”的立場(chǎng)上,朱子強(qiáng)調(diào)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33)朱熹:《四書(shū)章句集注》,中華書(shū)局,2010,第2頁(yè)。教欲為“大人”者。這是由“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34)同上書(shū),第267頁(yè)的身份條件決定的。如果是社會(huì)中一般的普通人,他們的“格物窮理”可以停留在“小學(xué)”,即灑掃庭除,但大人不僅要修養(yǎng)自身,也要治理天下,既要為學(xué),亦要為政。因此,要想成為“大人”就不能僅限于自我修養(yǎng),也要正己正人,這就需要學(xué)習(xí)“窮理、正心、修己、安人”(35)同上書(shū),第2頁(yè)。之道,“是以大學(xué)始教,必使學(xué)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36)同上書(shū),第8頁(yè)。
陽(yáng)明則認(rèn)為“格物”之“物”并未獨(dú)立于心之外,所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37)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1070頁(yè)。也強(qiáng)調(diào)“理”也未獨(dú)立于心之外,所謂“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fā)之于親則為孝,發(fā)之于君則為忠……千變?nèi)f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fā)于吾之一心。”可見(jiàn),陽(yáng)明對(duì)“格物”“窮理”的理解,不再如朱子般以“敬”詮釋,而是認(rèn)為“敬”本身就來(lái)源于心,無(wú)須再外求一個(gè)“敬”字,一切如“敬”般之道理皆可收攝于心、皆可落在心上。所以,陽(yáng)明說(shuō):“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為一者也。”(38)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1089頁(yè)。與朱子不同的是,陽(yáng)明強(qiáng)調(diào)的是“致良知”。“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謂充廣其知識(shí)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39)同上書(shū),第826頁(yè)。陽(yáng)明認(rèn)為“致良知”乃原取于《大學(xué)》古本之義,非朱子歧出之學(xué)。“致良知”既推擴(kuò)良知使其發(fā)展達(dá)至極處,又是指操存良知、為善去惡的道德實(shí)踐。“致良知”發(fā)揮人的內(nèi)在主體性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40)同上書(shū),第1089頁(yè)。,使事事物物皆見(jiàn)得天理。陽(yáng)明認(rèn)為“致良知”不似朱子“格物窮理”般僅留駐擴(kuò)充知識(shí)之義上。所以,“致良知”同樣面向一切事物,但卻不再似朱子以知識(shí)束人手腳,而是以人人皆有之良心推擴(kuò)于外物。在培養(yǎng)“大人”的立場(chǎng)上,陽(yáng)明強(qiáng)調(diào)“大人者”乃“天地萬(wàn)物一體者”,高揚(yáng)“致良知”之學(xué),主張人人皆可學(xué)“大人之教”。
另外,陽(yáng)明也注意到,大人能呈現(xiàn)與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的結(jié)果、可以把握“大人之教”,并非是受到外在強(qiáng)加規(guī)范的“他律”,而是在于自識(shí)“一體之仁”使之流行遍布。陽(yáng)明說(shuō):“故夫?yàn)榇笕酥畬W(xué)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復(fù)其天地萬(wàn)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41)同上書(shū),第823頁(yè)。陽(yáng)明認(rèn)為,之所以大人能夠成為大人,乃是由大人的內(nèi)在之仁不斷擴(kuò)充而呈現(xiàn)。具體而言,孟子所謂“人乍見(jiàn)孺子將入于井”,瞬間生發(fā)的“怵惕惻隱之心”,這是陽(yáng)明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的“良知”。擴(kuò)而充之,如同大人者見(jiàn)草木猶有生意,見(jiàn)草木摧折而必有憫恤,瓦石毀壞必有顧惜,即是吾人之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與草木而為一體。陽(yáng)明高揚(yáng)“致良知”,認(rèn)為要想成為“大人”,“大人之教”就不能是朱子的“窮理、正心、修己、安人”,而應(yīng)是以“大人者”自識(shí)“一體之仁”實(shí)現(xiàn)“萬(wàn)物一體”。
關(guān)于朱子與陽(yáng)明對(duì)“大人之學(xué)”中“大人之教”(學(xué)習(xí)內(nèi)容)的理解,后世學(xué)者看法各異。唐君毅以為,朱子、陽(yáng)明論“格物致知之教”各有其美:“陽(yáng)明之說(shuō)不同于朱子者,則在朱子之格物窮理,皆由人之知其所不知者,以開(kāi)出;而陽(yáng)明之致良知,則由人之知其所已知者,以開(kāi)出。”(42)唐君毅:《中國(guó)哲學(xué)原論·導(dǎo)論篇》,臺(tái)灣學(xué)生書(shū)局,1986,第349頁(yè)。馮友蘭先生則指出,朱子、陽(yáng)明論《大學(xué)》皆有缺失:“《格物補(bǔ)傳》由‘窮物理’轉(zhuǎn)入‘窮人理’,所以顯得兩橛。心學(xué)專(zhuān)講‘窮人理’,所以顯得直截。”(43)馮友蘭:《中國(guó)哲學(xué)史新編》下冊(cè),人民出版社,2007,第202頁(yè)。馮達(dá)文先生曾指出:
朱子所講的“知”與陽(yáng)明所講的“知”,在內(nèi)容上即有差別,朱子廣泛涉及外在之“物”與“理”,而陽(yáng)明僅限于“德”;朱子既以外在之“物”與“理”為所知者,則他所面對(duì)的問(wèn)題,為殊相與共相之關(guān)系問(wèn)題,此為知識(shí)論的基本問(wèn)題,陽(yáng)明所面對(duì)的問(wèn)題,其實(shí)為如何成德之“行”的問(wèn)題,此實(shí)為信仰的問(wèn)題。(44)馮達(dá)文:《從朱子與陽(yáng)明之<大學(xué)>疏解看中國(guó)的詮釋學(xué)》,黃俊杰編《東亞儒者的<四書(shū)>詮釋》,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234頁(yè)。
唐君毅先生側(cè)重于朱子、陽(yáng)明論“格物致知”的特色,馮友蘭先生則重在解析心學(xué)與理學(xué)的流弊,馮達(dá)文先生是以“知”為標(biāo)準(zhǔn),分判朱王的知行觀(guān)。但以“大人之學(xué)”而觀(guān),朱王之學(xué)呈現(xiàn)出學(xué)習(xí)“大人之學(xué)”的兩種詮釋進(jìn)路也值得注意。朱子強(qiáng)調(diào)“格物窮理”,“大人之學(xué)”是學(xué)習(xí)“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陽(yáng)明則高揚(yáng)“致良知”,認(rèn)為“大人之學(xué)”是自識(shí)“一體之仁”,認(rèn)為只有大人者去除人欲之蔽,才能復(fù)明其德,揭示天地萬(wàn)物一體之本然。但無(wú)論朱王之學(xué)如何分庭抗禮,兩者皆是十字打開(kāi)“大人之學(xué)”,使“大人”通向“正人正己者”或是“與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者”,即“大人”通過(guò)“大人之教”向“大學(xué)之道”無(wú)限敞開(kāi)。
三、“大學(xué)之道”:“修己治人”與“中國(guó)一人”
朱子、陽(yáng)明對(duì)《大學(xué)》的經(jīng)典詮釋,最終都落在學(xué)習(xí)目標(biāo)即“大學(xué)之道”:“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這涉及朱子、陽(yáng)明的終極關(guān)懷問(wèn)題。朱子言:“大學(xué)一書(shū),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shí)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wú)益也。”(45)朱熹撰,黎靖德編《朱子語(yǔ)類(lèi)》,中華書(shū)局,2020,第267頁(yè)。讀《大學(xué)》需沉潛涵泳,逐字咀嚼,契入此書(shū)血脈,切不可只讀個(gè)“空殼子”。這就間接指出,《大學(xué)》一書(shū)在綱領(lǐng)上看,也確實(shí)具備“空殼子”的特征。正如牟宗三先生言:“《大學(xué)》只是一個(gè)‘空殼子’,其自身不能決定內(nèi)圣之學(xué)之本質(zhì)。”(46)牟宗三:《心體與性體》,正中書(shū)局,1985,第424頁(yè)。
正是因?yàn)椤洞髮W(xué)》只列出三綱領(lǐng)、八條目的實(shí)踐綱領(lǐng),“只說(shuō)一個(gè)當(dāng)然,而未說(shuō)出其所以然,在內(nèi)圣之學(xué)之義理方向上為不確定者,究往哪里走,其自身不能決定”,(47)同上書(shū),第18頁(yè)。故而出現(xiàn)朱子、陽(yáng)明兩種不同的講法。然而,朱子、陽(yáng)明對(duì)《大學(xué)》這“空殼子”的經(jīng)典詮釋,并不局限于書(shū)齋,而是促使他們?cè)凇翱諝ぷ印敝幸宰晕覂r(jià)值為文化生命內(nèi)核向宇宙、世界、人生投射終極關(guān)懷與實(shí)踐思考,即西方詮釋學(xué)所謂“解釋者必須恢復(fù)和發(fā)現(xiàn)的,不是作者的個(gè)性與世界觀(guān),而是支配著文本的基本關(guān)注點(diǎn)——亦即文本力圖回答并不斷向它的解釋者提出的問(wèn)題”(48)戴維·E·林格:《編者導(dǎo)言》,載高達(dá)美《哲學(xué)解釋學(xué)》,夏鎮(zhèn)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2頁(yè)。。朱子與陽(yáng)明面對(duì)《大學(xué)》文本對(duì)它作出的經(jīng)典詮釋,無(wú)不是關(guān)聯(lián)著他們各自提出的問(wèn)題,而這一問(wèn)題,落實(shí)在推行“大人之學(xué)”上,則表現(xiàn)在“大學(xué)之道”的踐行問(wèn)題上。
朱子回顧一生,自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shū),先須通此書(shū),方可讀他書(shū)。”(49)黎靖德編《朱子語(yǔ)類(lèi)》,中華書(shū)局,2020,第275頁(yè)。認(rèn)為“大學(xué)之道”可使“國(guó)家化民成俗,學(xué)者修己治人”。陽(yáng)明則指出“大學(xué)之教”可使“天下猶一家,中國(guó)猶一人”。這是因?yàn)?陽(yáng)明認(rèn)為“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wú)外內(nèi)遠(yuǎn)近”,但又因?yàn)槌霈F(xiàn)“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的問(wèn)題,圣人擔(dān)憂(yōu)此局面惡化,于是“推其天地萬(wàn)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fù)其心體之同然。”(50)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50頁(yè)。故而,為傳續(xù)各自心中的古代圣哲之真意,朱子、陽(yáng)明分別以理學(xué)與心學(xué)詮釋《大學(xué)》“大學(xué)之道”的“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
朱子以“氣質(zhì)之性”詮釋“大學(xué)之道”。在《經(jīng)筵講義》中,朱子曾指出“氣稟”的現(xiàn)實(shí)性、“變化氣質(zhì)”的必要性。“臣(朱子)竊謂天道流行,發(fā)育萬(wàn)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wú)所資乎陰陽(yáng)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lèi)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51)朱熹:《朱子全書(shū)》,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692-695頁(yè)。朱子從天道論闡釋人的生成過(guò)程,指明“氣稟”的現(xiàn)實(shí)束縛一面,朱子強(qiáng)調(diào)以“變化氣質(zhì)”實(shí)現(xiàn)“明明德”,認(rèn)為“明徳”乃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眛,以具眾理而應(yīng)萬(wàn)事者。”(52)朱熹:《四書(shū)章句集注》,中華書(shū)局,2010,第4頁(yè)。故而,朱子主張“學(xué)者當(dāng)因其所發(fā)而遂明之,以復(fù)其初也”(53)同上。,以“變化氣質(zhì)”使舊民能夠自明其德,成為“新民”。
與朱子不同的是,陽(yáng)明是以“萬(wàn)物一體”詮釋“大學(xué)之道”。“蓋其心學(xué)純明,而有以全其萬(wàn)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dá),而無(wú)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陽(yáng)明又言:“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wú)外內(nèi)遠(yuǎn)近;凡有血?dú)?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yǎng)之,以遂其萬(wàn)物一體之念。”(54)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51頁(yè)。陽(yáng)明從萬(wàn)物一體論闡釋人己、物我一體的道理,指明萬(wàn)物一體的重要。進(jìn)而,又以體用關(guān)系之“體”闡釋“大學(xué)之道”中“明明德”的核心地位。
首先,“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wàn)物一體之體也。”(55)同上書(shū),第823頁(yè)。
陽(yáng)明認(rèn)為:“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gè)‘明明德。’”(56)同上書(shū),第23頁(yè)。其中,“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57)同上書(shū),第824頁(yè)。所以,“明德”意味著“良知”,當(dāng)“良知”未發(fā)之時(shí),本身未受私欲遮蔽,靈昭不昧,它就只是“至善”,待“至善之發(fā)見(jiàn)”時(shí),作為“心之本體”,它就會(huì)成為主宰善惡是非的意念。“明明德”是通過(guò)去除人欲之私重新回返到“人心一點(diǎn)靈明”,以立根工夫呈現(xiàn)良知本來(lái)面貌,目的是為了呈現(xiàn)“明德”還原“良知”。緊接著,若“只說(shuō)‘明明德’,而不說(shuō)‘親民’,便似老、佛。”(58)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824頁(yè)。談“明明德”一定要與“親民”相連。只是在兩者之間,亦是如“種樹(shù)者必培其根”(59)同上書(shū),第30頁(yè)。一樣,須以“明明德”的立根工夫?yàn)橄取?/p>
其次,“親民者,達(dá)其天地萬(wàn)物一體之用也。”(60)同上書(shū),第823頁(yè)。
陽(yáng)明以體用關(guān)系之“用”闡釋“大學(xué)之道”中“親民”的關(guān)鍵作用。其實(shí),陽(yáng)明對(duì)“親民”的認(rèn)識(shí)是立足對(duì)朱子以“新民”闡釋“親民”的觀(guān)點(diǎn)進(jìn)行批評(píng)、改正的。朱子根據(jù)《盤(pán)銘》《康誥》《大甲》“新”字,認(rèn)為“親民”是“新民”之義,指出“新者,革其舊之謂也。”(61)朱熹:《四書(shū)章句集注》,中華書(shū)局,2010,第4頁(yè)。由于人們受到氣質(zhì)之性的拘束,所以,只有所學(xué)之人進(jìn)行變化氣質(zhì),才能復(fù)其明明德,進(jìn)而推以及人,便能除去自身舊染之污,成為自新之民。對(duì)此,陽(yáng)明否定朱子“新民”的講法,通過(guò)援引《論》《孟》《尚書(shū)》論證“親民”的合理與合法。在面對(duì)“新民”與“親民”之別,徐愛(ài)曾針對(duì)此問(wèn)題請(qǐng)教陽(yáng)明: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其足為據(jù)?‘作’字卻與‘親’字相對(duì),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guó)平天下’處,皆于‘新’字無(wú)發(fā)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lè)其樂(lè)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lèi),皆是‘親’字意。”(62)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2頁(yè)。
朱子與陽(yáng)明各自站在理學(xué)與心學(xué)的立場(chǎng)分別以“新”“親”闡釋“親民”。其中,朱子是以“氣質(zhì)變化”解釋“親民”之“自新”;陽(yáng)明則是以“萬(wàn)物一體”解釋“親民”之“一體”。按陽(yáng)明的觀(guān)點(diǎn)看,“親民”的實(shí)現(xiàn)源于“致良知”的完成,使“良知”由吾人之心泛出,并在恰當(dāng)時(shí)機(jī)向外界流動(dòng),即以其“一體之仁”擴(kuò)充到孝敬父母之“孝”,友愛(ài)兄長(zhǎng)之“弟”。進(jìn)而,隨著吾人“良知”的自致工夫與達(dá)至極致,實(shí)現(xiàn)“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良知擴(kuò)充。可見(jiàn),“親民”在陽(yáng)明的眼中是立根工夫的外化與實(shí)踐。換言之,人人皆可以實(shí)現(xiàn)的“親民”,是實(shí)現(xiàn)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的實(shí)踐門(mén)路。
朱子與陽(yáng)明對(duì)“大學(xué)之道”中“止于至善”解釋的也不同。朱子以為“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dāng)然之極也。”(63)朱熹:《四書(shū)章句集注》,中華書(shū)局,2010,第4頁(yè)。朱子認(rèn)為“止于至善”,是說(shuō)認(rèn)識(shí)并完成事物最高之理,始終如一的踐行保持不變。陽(yáng)明則認(rèn)為“止于至善”是“至善者性也,性元無(wú)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fù)其本然而已。”(64)王守仁:《王陽(yáng)明集》,中華書(shū)局,2016,第24頁(yè)。“止于至善”是指通過(guò)“致良知”時(shí)刻保任吾人之良知,讓良知呈現(xiàn)本來(lái)面貌,復(fù)其本然。
至于“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朱子、陽(yáng)明均認(rèn)為此三者乃“大學(xué)”之綱領(lǐng)。但朱子視“三綱八目”為不同節(jié)目,如“明德、親民,便是節(jié)目;止于至善,便是規(guī)模之大”,從理學(xué)進(jìn)路出發(fā),認(rèn)為“大學(xué)之道”是實(shí)現(xiàn)由復(fù)其自性的“明明德”,到使之自新的“新民”,再到“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的學(xué)習(xí)目標(biāo)。朱子將“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關(guān)系認(rèn)定為層層遞進(jìn),形成“次第”工夫體系。陽(yáng)明則認(rèn)為“明明德”是“萬(wàn)物一體”之“體”,“親民”是“萬(wàn)物一體”之“用”,“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兩乎?”(65)同上書(shū),第825頁(yè)。陽(yáng)明以體用關(guān)系詮釋“明明德”與“親民”,認(rèn)為其最終歸宿在“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明明德、親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xué)。”(66)同上書(shū),第824頁(yè)。王陽(yáng)明從心學(xué)進(jìn)路出發(fā),以“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者為一事之體、用、極處,形成“立根”的心學(xué)工夫。
朱子、陽(yáng)明對(duì)“大學(xué)之道”的詮釋,形成“次第”的理學(xué)工夫與“立根”的心學(xué)工夫。錢(qián)穆先生曾指出,陽(yáng)明重成色輕分兩,不能“于成色分兩上一并用心”(67)錢(qián)穆:《湖上閑思錄》,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0,第30頁(yè)。。因此,“陽(yáng)明良知學(xué),實(shí)在也只是一種小學(xué),即小人之學(xué)”,“晦翁的格物窮理之學(xué),始是大學(xué),即大人之學(xué)”(68)同上書(shū),第30-31頁(yè)。。對(duì)于造成陽(yáng)明學(xué)淪為“小學(xué)”的內(nèi)在原因,這是在于陽(yáng)明骨子里沿襲宋明理學(xué)講學(xué)大傳統(tǒng),“總是看不起子路子貢冉有公西華,一心只想學(xué)顏淵仲弓。他們雖也說(shuō)即事即心,卻不知擇術(shù),便盡在眼前日常瑣碎上用工。一轉(zhuǎn)便轉(zhuǎn)入渺茫處。”(69)錢(qián)穆:《湖上閑思錄》,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0,第31頁(yè)。
盡管錢(qián)先生高舉朱子學(xué),以朱子學(xué)的詮釋立場(chǎng)評(píng)價(jià)陽(yáng)明學(xué),但如果從“善”與“至善”的遞進(jìn)關(guān)系言,陽(yáng)明對(duì)“大學(xué)之道”的詮釋進(jìn)路,也是無(wú)法實(shí)現(xiàn)朱子學(xué)般的層層上達(dá)。這是由于陽(yáng)明學(xué)的“萬(wàn)物一體”之自身特性所決定。陽(yáng)明對(duì)“大學(xué)之道”的追求,是以“立根”工夫追求“天下猶一家,中國(guó)猶一人”。朱子認(rèn)為“大學(xué)之道”應(yīng)是以“次第”工夫?qū)崿F(xiàn)“國(guó)家化民成俗,學(xué)者修己治人”。盡管朱子陽(yáng)明對(duì)“大學(xué)之道”的詮釋存在各種分歧,但二人的“大人之學(xué)”均立足于儒家心性論闡釋“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三綱領(lǐng)”,使“大人之學(xué)”在儒家心性之海中全幅展開(kāi)而一路高揚(yáng)。
四、結(jié)語(yǔ)
朱子、陽(yáng)明注《大學(xué)》皆由“大人之學(xué)”而起,從主體、進(jìn)路、目標(biāo)的詮釋面向看,二人闡釋的“大人之學(xué)”存在分歧,但在儒家心性之學(xué)的映照下,朱子、陽(yáng)明之學(xué)亦有共通之處:朱子、陽(yáng)明均是順著“大人”—“大學(xué)之教”—“大學(xué)之道”而一路發(fā)揮之。而且,朱子、陽(yáng)明的“大人之學(xué)”在儒學(xué)基本問(wèn)題上也具有一致看法:即作為一個(gè)人,該如何認(rèn)識(shí)自我、如何實(shí)踐自我、如何實(shí)現(xiàn)自我。對(duì)此,用牟宗三先生的意思來(lái)表達(dá),則是說(shuō)無(wú)論是朱子還是陽(yáng)明,他們均是借《大學(xué)》這一“空殼子”,使道德主體在儒家經(jīng)典中獲得神圣體驗(yàn)與通體光輝,將經(jīng)典世界與現(xiàn)實(shí)世界融為一體,以“道德的理想主義”開(kāi)出“立千年之人極”。
作為“空殼子”的《大學(xué)》,既容納朱子、陽(yáng)明以“次第”工夫與“立根”工夫展開(kāi)的經(jīng)典詮釋,也包含朱子、陽(yáng)明以“格物窮理”與“致良知”開(kāi)啟的理論圖式。朱子、陽(yáng)明對(duì)“大人之學(xué)”的闡釋,不僅反映兩者建構(gòu)哲學(xué)體系的學(xué)理思考,也揭示兩者重塑精神世界的心性實(shí)踐。總之,朱子、陽(yáng)明以此身生命守護(hù)、踐行、開(kāi)拓“大人之學(xué)”的詮釋活動(dòng),不僅對(duì)儒家經(jīng)典詮釋學(xué)的現(xiàn)代建構(gòu)與發(fā)展具有模范作用,也對(duì)新時(shí)代中國(guó)特色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的思想體系建構(gòu)具有一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