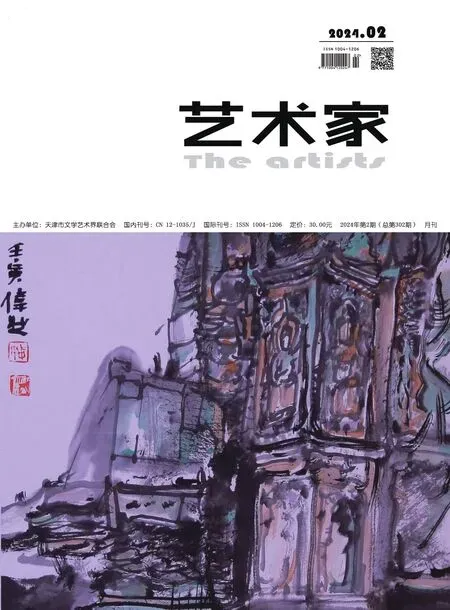杜甫仁科早期電影中的定格鏡頭研究
□吳貴軍
杜甫仁科(1894—1956)是著名電影導演。杜甫仁科的電影創作具有獨特的詩意風格,他一生都致力于“詩電影”美學的倡導和探索,并將這種創作理念在電影創作中得以實踐。杜甫仁科的電影創作和美學觀念對世界電影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詩意敘事結構方面的影響更大。
一、杜甫仁科早期電影定格鏡頭概述
定格鏡頭是以靜止畫面多印若干格,造成動作“凝結”的效果。定格鏡頭作為一種特殊的鏡頭語言,具有非常多的特征及功能。杜甫仁科一生共執導影片十六部,其中大多數都有定格鏡頭的運用,但主要集中在《外交信使袋》《兵工廠》《大地》《伊萬》四部電影中。本文主要圍繞這四部電影展開討論。
二、杜甫仁科早期電影定格鏡頭的特征
(一)定格鏡頭的外部特征
1.整體性、有機地布局
杜甫仁科電影的定格鏡頭在影片中的分布有某些規律,多分布于電影首尾兩端,中間基本沒有。《外交信使袋》的定格鏡頭集中在影片的00:15:30 之前及01:00:05 之后,《兵工廠》集中在00:17:43 之前及01:00:08 之后。電影的矛盾沖突主要集中在影片的中部,所以減緩節奏的定格鏡頭就“被迫”安置在影片的首尾。《伊萬》和《大地》情況不同,定格鏡頭散布在影片各處。因為這兩部影片的定格鏡頭數量過多(分別約20 個、40 個),所以無法在影片首尾兩端相對狹小的時空中密集展示。可見定格鏡頭是根據劇情節奏、矛盾沖突進行整體性有機布局的。
2.非沖突場景中出現
杜甫仁科在創作中善于利用運動鏡頭及定格鏡頭的不同特質,在敘事上發揮鏡頭的不同功能。定格鏡頭會明顯淡化矛盾沖突,所以常用于非沖突甚至是非敘事的場景。平淡敘事不意味著一定采用定格鏡頭,日常生活中靜止和劇烈沖突兩種狀態之間存在過渡地帶,而杜甫仁科卻偏偏鐘愛在非沖突情況下選擇定格鏡頭,足以表明定格鏡頭在杜甫仁科眼中不僅僅承擔敘事功能。
3.串聯、重復的形式出現
在杜甫仁科電影中相同的定格鏡頭串聯甚至重復,這種情況比較多見。定格鏡頭可以強化電影的鏡頭表現力及藝術感染力。《兵工廠》、《大地》(如圖1)、《伊萬》都有大量串聯的定格鏡頭。而定格鏡頭重復的情況相對較少,如《大地》00:02:23-00:02:29、00:02:46-00:02:55 兩處,00:47:07-00:47:31、00:47:38-00:47:55 及00:48:03-00:48:13 三處。

圖1 《大地》六個定格鏡頭串聯
通常,鏡頭的定格可以起到強化拍攝對象的作用,定格鏡頭的串聯甚至重復,可以實現強化基礎上的再強化。但在杜甫仁科電影中,串聯或重復的定格鏡頭內被拍攝對象往往未被強化,這些角色像是隨機選取的拍攝對象。這說明杜甫仁科關注的是拍攝效果(形式),而不是拍攝對象(內容)。
4.定格—小活動—大活動模式
杜甫仁科執導的故事片基本遵循傳統的發生—發展—高潮—結局的敘事模式,在發生和結局階段的定格鏡頭較多,當情節線朝向發展、高潮進行時,定格鏡頭逐漸減少直至消失,同時人物的動作傾向于由靜止到小幅度動作,直到大幅度動作。
5.定格鏡頭的打破
杜甫仁科利用多種手段來終結定格鏡頭,包括其他鏡頭進入、內部元素運動、光線進入、字幕植入等。其他鏡頭進入就是另一個鏡頭開始,實現對前一個定格鏡頭的終結。定格鏡頭要求鏡頭內所有元素均處于靜止狀態,鏡頭內部元素的運動可以打破鏡頭的定格狀態。光線進入這種終結定格鏡頭的手法在杜甫仁科電影中非常少見。《伊萬》在00:20:31 處利用一束光打破之前的定格鏡頭(如圖2)。利用字幕連接鏡頭是無聲電影時期比較常見的一種創作技巧,在杜甫仁科的電影中被廣泛采用。

圖2 《伊萬》利用一束光打破定格鏡頭
(二)定格鏡頭的內部特征
1.畫面元素簡單
定格鏡頭要求鏡頭內的各要素均處于靜止狀態。鏡頭內元素的數量越多就越難以維持這種定格狀態,所以定格鏡頭要求畫面元素簡單。杜甫仁科電影中的定格鏡頭基本都是單個的人物,很少多個人在一個畫面內,這樣就保證了鏡頭內的元素穩定性。
2.角色的表演
杜甫仁科電影定格鏡頭中的人物往往處于某個姿勢的靜態,這顯然違背生活中人很少處于靜止狀態這一常識。《兵工廠》00:01:02-00:01:16、00:01:54-00:02:06 都是一個女人低著頭做沉思狀(如圖3),00:01:32-00:01:44 是男人和女人躺在前行車上的近景鏡頭。過多的由靜止元素構成的定格鏡頭也產生了欣賞上的間離效果,最終觀眾從認知上判斷這是在“表演”。定格鏡頭介導的間離效果可以起到淡化敘事的作用,弱化電影事件發生的具體時空語境。

圖3 《兵工廠》女人低頭沉思狀
3.符合生活邏輯
杜甫仁科在創作定格鏡頭時,也會顧及生活邏輯。比如,在《外交信使袋》(00:04:23-00:04:31)中由于戶外下著大雨,視線受限,所以女人需要長時間透過玻璃窗觀看,此處的定格鏡頭符合日常生活經驗(如圖4)。同樣在《外交信使袋》00:12:37-00:12:42,《兵工廠》00:04:41-00:04:50、00:05:27-00:05:34,《伊萬》00:34:46-00:35:51 等處的定格鏡頭都考慮到了生活常識。

圖4 《外交信使袋》的定格鏡頭符合日常生活經驗
(三)慢鏡頭
杜甫仁科電影中的慢鏡頭可以寬泛地認定它們是定格鏡頭的衍生品。早期電影時期,導演一般采用低于現在的24 畫格拍攝,導致鏡頭內人物的運動比現實中要快,杜甫仁科卻有意利用慢鏡頭來達到某種效果。《茲韋尼戈拉》00:00:55-00:01:52 處有一個慢鏡頭,這種“慢”可以深化主題,表達情感及美感。《兵工廠》00:04:50-00:05:27 處慢鏡頭表現了民眾生活的痛苦和內心的絕望,強化了作品的戲劇性。
三、杜甫仁科早期電影定格鏡頭的功能
(一)淡化敘事或不參與敘事
杜甫仁科拍攝的定格鏡頭減緩了影片的敘事節奏。另外,由于畫面內人物經常是隨機選擇的而不充當影片的重要角色,所以定格鏡頭弱化了影片的故事情節。
(二)營造氣氛
杜甫仁科是一位善于營造影片氛圍的導演。《外交信使袋》在00:15:23-00:15:30 處的近景中,敵特展示自己外套上的胸章,鏡頭定格營造威懾對手、尖銳對抗的氛圍。同樣在《外交信使袋》的01:05:12-01:05:42 處三個特寫的定格鏡頭聯用,表現特務與水兵勢不兩立的對峙局面(如圖5)。

圖5 《外交信使袋》三個特寫的定格鏡頭聯用
(三)延緩節奏與增強戲劇張力
《米丘林》00:22:14-00:22:26、00:40:34-00:40:41處鏡頭節奏舒緩,符合角色的心理狀態。《伊萬》(00:12:39-00:13:10)三個定格鏡頭串聯,形成節奏上的拖沓(如圖6)。定格鏡頭的串聯或重復不僅延緩節奏,而且造成一種情勢,推動矛盾沖突的發展,增強影片的戲劇張力。

圖6 《伊萬》三個串聯定格鏡頭
(四)“白描”式地塑造人物形象
杜甫仁科電影定格鏡頭內的角色淡化了對人物形象的塑造,鏡頭的定格在效果上類似白描的手法。隨著聲音及色彩的出現,電影的逼真性和紀實功能得到極大的豐富和發展,所以對人物塑造的方法在杜甫仁科后期的電影中發生了變化。
(五)表現主題
定格鏡頭內與敘事無關的人物同其他事物共同構成畫面元素時,鏡頭可以表達某種意義。《兵工廠》(00:01:02-00:01:16、00:01:54-00:02:06)通過兩個串聯的定格鏡頭表現戰爭下人們的悲哀。《解放》00:05:11-00:05:18:母親抱著孩子站在戰爭的廢墟旁邊凝視。《烏克蘭之戰》00:01:40-00:01:44:女性站在親友的墓碑前;00:01:44-00:01:48:母親懷抱孩子坐在殘垣斷壁前,都同樣起到對戰爭控訴的作用(如圖7)。

圖7 《烏克蘭之戰》的定格鏡頭
(六)增加儀式感、雕塑感
電影《大地》的00:04:00-00:04:10:三個人物每個人物一個定格鏡頭。00:08:42-00:09:06:四個人物每個人物一個定格鏡頭。這么多的人物定格鏡頭排列在一起,觀眾的心中會油然而生宗教般的儀式感和神像般的雕塑感(如圖8)。

圖8 《大地》的人物定格鏡頭
四、杜甫仁科早期電影定格鏡頭的美學價值
(一)由定格通向形式
畫面靜止原本會產生攝影效果,由于畫面滲透進了導演的創作意圖,所以破壞了攝影的透明性,使定格鏡頭具有了內部張力,這樣一來,形式也就有了某種“意味”。杜甫仁科的定格鏡頭表層上看是一種無關敘事的無意義的“形式”,本質上密切關涉敘事以及導演想要達到的某種詩意風格。大量定格鏡頭正體現了杜甫仁科創作理念的一致性。
(二)由靜態通向詩意
杜甫仁科的定格鏡頭某種意義上沖破了經典蒙太奇語言的羈絆,形成了一種“情調”,也就是抵達了一種對敘事無視的自在自為的“詩意”境界。定格鏡頭滲透出的詩意具有燦爛的感性,凌駕于具有起承轉合的理性敘事。
杜甫仁科作為“詩電影”美學的倡導者和探索者,對蘇聯詩電影的理論及實踐均產生了很大影響。杜甫仁科在他的電影創作中利用定格鏡頭創造了電影的詩意敘事結構,營造了影片的整體“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