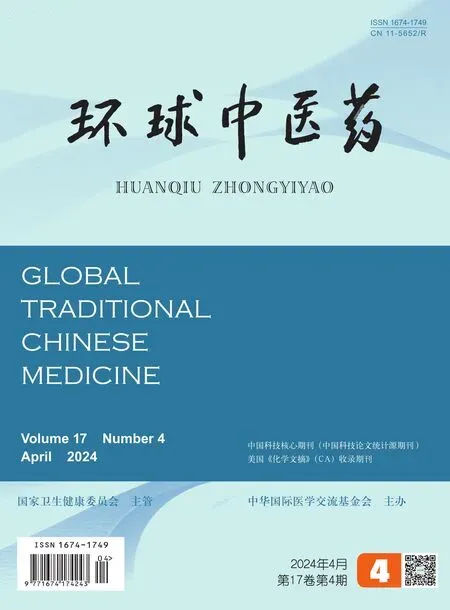從調和臟腑平衡等五種平衡辨治功能性胃腸病
李佳睿 朱煒楷 李吉彥 王政芃 代露 卓成婷 劉雨莎 戴孟君 沈會
功能性胃腸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FGIDs)是一組根據胃腸道癥狀分類的疾病,其以無器質性病變,但具有功能性改變的消化道癥狀為特征[1]。據報道,FGIDs病人在我國消化內科門診及住院病人之中,占總體病人的比例高達2/5~3/5[2]。
中醫自古以來多求一“衡”,治病遣方多遵一“衡”。從天地陰陽之衡,順其以人,得“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之健態。此論脾胃,即為中焦,故從中焦之衡論治。以“衡”愈疾之思想基于《黃帝內經》之中的“調平求和”“糾偏調衡”,且清代醫家吳鞠通亦提出“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之說。故結合中焦臟腑易相反相成的特征,為應對脾胃的復雜病機,衍生出和調臟腑、調達寒熱、消補并施、升降相因、燥濕相濟等一系列消長平衡之法。眾多醫家以“治中焦如衡”為指導思想,穩中焦與他臟之衡,固中焦之間多因素之衡。針對復雜失衡病機,采用辨證論治,因人而異的診療措施,可在臨床取得確切療效。
1 五種平衡觀指導辨證治療FGIDs
1.1 五種平衡觀的提出是中焦治衡的重要具象
《黃帝內經》開篇“提挈天地,把握陰陽”,指出萬物分陰陽,陰陽衡則萬物和。衡之思想由此廣而傳之。脾胃屬中焦,其含五衡。《素問·舉痛論篇》云:“百病生于氣也。”[3]氣之運動以機相稱,脾胃氣機多以升降為要,脾胃病生于氣機升降失衡。《醫宗必讀·醫論圖說》中云“氣血者,人之所賴以生者也”,脾胃亦賴之。津液與氣血可相互轉化,共筑脾胃活動之物質基礎。脾喜潤而胃喜燥,津液輸布失常則潤燥失衡。寒熱為陰陽的具體表現,陰陽失調為寒熱錯雜的基本病機[4]。脾胃之寒熱陰陽相反相成,稍有偏頗,易呈寒熱失衡之變。虛實之分,可與寒熱之性共賦脾胃病邪。脾胃為樞,與全身多臟腑協同合作,參與調節全身氣機升降出入、水液代謝、氣血生成及運化等多種重要生理活動。筆者由此提出脾胃與臟腑之衡以及脾胃之寒熱、虛實、升降、燥濕五衡之觀。脾胃病的產生多與上述五種平衡被打破有關,若能恢復平衡則脾胃病可得痊愈。
1.2 五種平衡觀為解決FGIDs難題的重要指導思想
FGIDs的產生,多因中焦失和,全身各臟腑之間配合紊亂,產生寒熱、虛實、升降、燥濕的一方偏頗,終成失衡之變。故臨床施治,需抓其偏頗,以消其因。早在張仲景時期,便有通過寒熱、虛實、升降、燥濕四衡論治中焦脾胃疾病的論述。劉國強教授[5]指出“治中焦如衡”應為糾正陰陽水火寒熱偏頗之法。路志正教授[6]則針對脾胃病以失衡之機,提出圓機活法調脾胃,佐證臨床多以衡調脾胃。
FGIDs無明確中醫病名,一般根據癥狀將其劃分進入中醫各個疾病范疇。FGIDs的病位在脾、胃、小腸、大腸,與肝、肺密切相關。FGIDs輻射中醫疾病面之廣,病位涵蓋之多,為其診治增加了難度。正因臟腑各有其性,臟腑之間各有其衡,故臟腑失衡,疾病乃生。因而治之,必抓其“衡”,使中焦臟腑之間回歸至相制相和的平衡狀態。唐旭東教授[7]則立足于臟腑平衡,提出“調中復衡法”以治療FGIDs的癥狀重疊現象。
2 以調和臟腑治其變,歸其衡
2.1 疏達肝木以助脾胃
肝主疏瀉,協調脾胃之氣的升降條達。疏泄得法,則升降之衡、納排之衡皆得以促進,全身臟腑之衡更以穩定。《血證論·臟腑病機論》中述:“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設肝之清陽不升,則不能疏泄水谷,滲泄中滿之癥,在所不免。”提示肝失疏瀉可出現脾不升清之證,甚則出現中氣下陷。除脾之外,肝失疏泄亦可影響胃氣降濁。以上病機變化均可屬木強橫逆犯土而致中焦失司,即肝與脾胃臟腑失衡之象,謂之“木乘土”。
調和肝脾之衡為治療FGIDs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法則。張仲景所提“四逆散”為肝脾不和之祖方,而后世逍遙散及柴胡疏肝散皆于此基礎上改之。四逆散于《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所言“少陰病,四逆”,為肝氣郁滯而致陽氣不達四末之“陽氣郁”,且其中所論或然證中所述腹中痛、瀉利下重等均可由肝氣疏泄失常,木來乘土所致,故其方之根本在于調和肝脾、疏肝和胃,以達平衡之態。王惠臨等[8]研究發現四逆散中有效成分直接作用于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號轉導轉錄激活因子3等相關靶點,并通過腫瘤壞死因子、MAPK及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等信號通路,多靶點調節胃腸功能,從而發揮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作用。姬莉等[9]則以多中心、隨機、雙盲研究證明疏肝健脾方之臨床療效佳,更是說明肝脾之衡在治療FGIDs的臨床應用中的關鍵作用。
怡情疏解亦是調暢肝氣之必須,對于肝胃不和所致失衡狀態起到緩解與預防作用。一方面,情志以臟腑精氣為物質基礎,故其為五臟精氣的表象反應,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所言“肝在志為怒……脾在志為思”。另一方面,情緒變化亦影響臟腑活動,如大怒傷肝,思慮傷脾。故暴怒之后,出現肝木驟強,橫逆脾土,常以抑木扶土、息平肝怒為主要治法。除此之外,情志抑郁,肝氣郁結,致脾胃氣機失調,常以疏肝解郁、和調肝脾為主要治法。故從情志而述,所用諸法,皆以復二臟之衡為要。羅馬IV指南中“腦—腸軸”的提出及對心理因素的重視,皆為調暢情志之法的證實。牛學恩教授[10]常以調節肝脾之組方論治功能性胃腸病伴抑郁。衛拂曉等[11]研究得出,逍遙散通過減少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6等炎癥因子釋放及山柰酚抑制一氧化氮降解等機制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取得確切療效。
2.2 宣降肺氣以助脾胃
脾為生氣之源,肺為主氣之樞,二者相互為要,維生氣之衡,保升降之衡,更護臟腑之衡。如《素問·經脈別論篇》所言[12]:“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肺氣宣降如常,則脾精得升,糟粕得下。清不得宣,可顯“清氣在下,則生飧瀉”之象,濁不得降,則氣機壅滯,腑氣不通。肺脾之間氣之衡可影響所司水液之衡。肺氣充而脾運佳,大腸得潤,納排則衡。肺失宣降,布津失調,則無水行舟,無便以下。肺主皮毛,其主腠理為肺氣宣出之門路,邪襲閉之,亦可見肺與脾胃之衡已破之象。以上皆可證《醫經精義》中“理大便必須調肺氣也”[13]。
歷代醫家皆重視調肺脾二臟,調其所掌之衡,故多用此法治功能性胃腸病中所見排便不調。張仲景于《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所提“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開創“逆流挽舟法”之先河。其中一味葛根既解表透邪,使腠理得開,肺氣宣發功能得以恢復,又鼓動太陰清氣上行,亦從標本雙側調達陽明里氣失調之下利。喻佳言所創人參敗毒散亦受此所啟。脾胃虛弱亦可致大便失調,《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參苓白術散則治之。其在益氣健脾,滲濕止瀉之時,加入砂仁理氣,配以桔梗引入肺經,調節肺氣宣降以更調脾胃,肺氣得宣,脾胃得運,則濕邪自除。單兆偉教授[14]參透此方中奧妙所在,善用葛根、桔梗等宣肺升清之品,治療慢性泄瀉[15]及腹瀉型腸激惹綜合征[16],臨床常得確效。
胃腑失和,糟粕不下之治法仍循調肺氣宣降,以達納排平衡之法。張仲景所擬麻子仁丸中所用杏仁,開宣肺氣,調達氣機;后吳鞠通所創宣白承氣湯中仍貫徹此法,方中杏仁、瓜蔞皆作用于肺,一宣一降,疏達氣機。肺宣降之衡,促肺宣腑降之衡。國醫大師許潤三[17]以麻黃湯加減治療慢性便秘,方選麻黃湯意為通調肺氣,其中麻黃配杏仁,宣降有序,布散津液,助大腸傳導之功。又有劉啟泉教授[18]善用紫菀,辛開而柔潤,杏仁利肺氣而潤腸燥,桔梗引經,載諸藥上行,以上三味宣開肺氣,通降腑氣,故用以治療功能性便秘伴有咳嗽、胸部憋悶等肺部癥狀。現有學者研究腸道微生物對遠端器官的影響,并提出“肺—腸軸”概念[19],這也側面認證了肺與脾胃腸腑的密切關系。
3 以調達寒熱治其變,歸其衡
脾為太陰濕土,主屬陰;胃為陽明燥土,主屬陽。人生而稟賦相異,加之所受邪氣性質亦有不同,故脾胃病難以單從寒病、熱病對其進行論述,故治脾胃應守寒熱之衡,以寒中夾熱、熱中帶寒的寒熱錯雜之象以論治。所闡述的脾胃病之寒熱區別及夾雜之癥,至《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下利……谷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硬而滿,干嘔心煩不得安”的進一步闡述得知寒熱錯雜之象的基本表現,皆可看出眾多醫家覺脾胃病之復雜本性,并致力于辨其寒熱,守其所衡而治之。
調達寒熱以治衡,從古至今皆為治療脾胃病的治則。張仲景在《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中指出“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嘔而腸鳴,心下痞者”,皆以半夏瀉心湯治之。方中所用藥物寒熱溫涼四性皆用,酸苦甘辛咸五味具齊,更是為求一衡,此可謂寒熱平調基礎方。現臨床醫療仍遵寒熱之衡為治療功能性胃腸病之法。唐旭東教授[20]以寒熱為綱,運用此方化裁,起同調復衡之效。《關于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醫結合診療共識意見》中提出,寒熱錯雜所致消化不良以胃脘痞滿或疼痛、胃脘部嘈雜不適及胃脘部喜溫怕涼為主癥,并自覺胃脘部灼熱,伴有噯氣,口干口苦,晨起尤甚,腹冷腸鳴或便溏等其他癥狀,方予半夏瀉心湯加減[21]。更有靳玉秋等[22]在動物實驗中發現半夏瀉心湯抑制肌球蛋白輕鏈激酶通路,可修復受損十二指腸黏膜,同時此方激活前列腺素E2-環磷酸腺苷通路,以維持腸粘膜完整。這便深入機制闡述了半夏瀉心湯改善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原因。
4 以消補并施治其變,歸其衡
《素問·太陰陽明論篇》:“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脾胃皆應此,故脾病多虛而胃病多實。故天地之間,陰陽虛實以衡為順,亦人體臟腑之間,消補虛實以衡為常。所知脾胃病多呈虛實夾雜之特性,為維其穩態,故調其虛實。脾主運化,以氣為依,以陽為生,故其病之,多以氣虛陽虛為主,致運化無力,生水濕內停、瘀血阻滯;胃主納運,屬腑陽明,以火為肆,故其病之,實象多見,以火熱之邪內蘊,或食積不化為主,但實邪久停,耗氣傷津,則陽明腑實后可顯氣陰兩虛之象。國醫大師路志正[23]更是提出“納化常”作為治療脾胃病的核心思想之一。單兆偉教授[24]亦訴調理脾胃不離消補。
為守其衡,或歷代泛而之論脾胃所病,而或現世精為解FGIDs,皆以虛實之衡為要,遣方以消補同施為用。李東垣在《內外傷辨惑論》中提出枳術丸,為中焦消補兼施之劑。后因丸者緩也,將水易丸,更符脾胃之性。其中白術益氣健脾配以枳實行氣,以白術倍枳實,顯補大于消之效。后世醫家于此,創枳實消痞丸,功效以消大于補著稱。觀其如今,單國順等[25]研究發現,枳術丸對提高食欲,改善功能性消化不良有較好療效。枳實消痞丸亦可聯合胃腸動力藥,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26]及功能性便秘[27]。由此析之,虛實夾雜之病機為脾胃病之常態,故予消補兼施劑固其平衡以治之。
5 以升降相因治其變,歸其衡

維護中焦氣機升降平衡理論在指導臨床治療功能性胃腸病效果確切。胃腑本降,而擾其所衡,于上呃逆、嘔吐,于中心下嘈雜、胃脘部脹滿甚則疼痛不適,于下則大便難下。歷代醫家喜用小半夏湯治胃氣上逆之呃逆。小半夏湯出自《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第十七》“嘔家本渴……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此為痰飲內阻于心下,胃失和降所致,于呃逆之胃氣上逆可謂異病同治。觀如今之證,于己百教授[30]在其治療一患者因慪氣并喝下涼茶后出現頑固性呃逆,以小半夏湯加味(半夏、生姜、砂仁、荔枝核、白酒)熏吸并內服,數日后痊愈。除小半夏湯,臨床亦有他方可解脾胃升降失司。2016年《胃痛中醫診療專家共識意見》指出脾胃升降失調而致胃氣壅滯型胃痛,多表現為脹痛、餐后尤甚,并伴有納呆噯氣等其他癥狀,以理氣和胃止痛為主要治法,方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香蘇散加減[31]。
6 以燥濕并濟治其變,歸其衡
脾喜燥惡濕,主運化水濕,胃喜潤惡燥,主通降下行。故《臨證指南醫案·卷二》中指出:“脾胃體用各異……以脾喜剛燥,胃喜柔潤也。”二者相互為用,共司燥濕之衡。脾胃燥濕相濟,則津液得運,寒熱自調。脾胃之衡被破,即一病而另一不可制之,則病由之顯。《素問·至真要大論篇》:“諸濕腫滿皆屬于脾。”若脾陽不足,則運化不能,水濕內停,而胃不燥之,則泄瀉、納呆、嘔吐。若胃火上炎,則中焦火動,氣逆上沖,而脾不潤之,則胃中嘈雜、惡心吞酸、多食易饑、口臭心煩等癥。《醫學正傳·嘔吐》有云:“有胃熱而吐者……有脾濕太甚,不能運化精微,致清痰留飲郁滯上中二焦,時時惡心吐清水者。”
FGIDs所應之證,燥濕失衡于臨床極為常見,故古今醫家皆研究何以維持脾胃之間燥濕平衡,何以潤燥而不礙脾運,祛濕而不傷胃陰[32]。醫家于此提出“脾陰”之重要概念,潤燥祛濕得法脾胃活動如常。張仲景于《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中云:“趺陽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澀相摶,大便則硬,其脾為約,麻子仁丸主之。”此方所治為“脾約”之證,因火熱聚于胃腸,脾土受其約束,顯胃強脾弱,失其所衡之態。脾亦無法受胃所傳水谷精微,故所顯脾陰虛之象[33]。現有臨床研究為證明麻子仁丸是功能性便秘的有效藥物提供了高質量證據[34]。又有研究明確麻子仁丸中藥復方活性成分的作用靶點及相關通路,以解釋麻子仁丸調節胃腸平衡,并對功能性便秘有重要臨床作用[35]。
7 結語
本文立于中醫角度,辨治FGIDs。因脾胃之寒熱、氣機、燥濕、虛實以及與他臟配合之特性皆相反相成,互為制衡。其中一方偏頗,或太過或不及,均可導致脾胃之間或臟腑之間“衡”再遭破。故欲治脾胃之病,必求于“衡”。吳鞠通所述“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極好概括此種思想。故本文以“治中焦如衡”為主要治則,將何為衡,何為治衡具體闡述,其中之“衡”涉及臟腑平衡、寒熱平衡、虛實平衡、升降平衡以及燥濕平衡。但目前對FGIDs的認知仍有未解之處,且其病程較長,病情復雜,病癥多變。本文僅從一元一組進行闡述,但臨床之中,衡為動態之衡,衡為多元之衡,衡為機體之大衡。故對FGIDs的治療應從整體出發究其病機,辨其病癥。抓其主因,治其偏頗,但不忘錯雜之他因,以方加減相合之形式,以藥物佐使之能效,使脾胃之內、臟腑之間多衡同時皆處“衡”位,使人之整體處于動態平衡之狀態。臨床之上,中西醫結合治療是更為符合現代臨床診療模式的體系,從兩種理論,同一目標,治中焦之衡。并且,更多地發掘中藥治療功能性胃腸病的具體機制,為中醫科學地以“衡”論治功能性胃腸病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