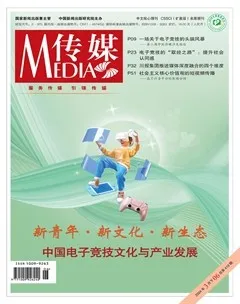延安時期《中國文化》在文化領(lǐng)域的歷史貢獻(xiàn)
徐雁紅
摘要:《中國文化》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延安時期創(chuàng)辦的重要刊物,該刊物通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民主主義文化、文化“民族形式”和文化抗戰(zhàn)等諸多方面的宣傳,讓新民主主義文化深入人心,堅定了全民抗戰(zhàn)的信心和決心,對改變根據(jù)地文化落后面貌起到了積極作用。雖然從創(chuàng)刊到停刊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時間,但其在宣傳先進(jìn)文化、抵制錯誤思潮以及繁榮根據(jù)地文化上,都作出了突出貢獻(xiàn)。
關(guān)鍵詞:《中國文化》 延安時期 文化繁榮
報刊是進(jìn)行宣傳、引導(dǎo)社會輿論的重要陣地。抗戰(zhàn)時期,報刊的地位尤為突出。延安是抗戰(zhàn)時期黨中央所在地、全國諸多青年心之所往的圣地。為了宣傳黨的政策主張,引導(dǎo)輿論,激發(fā)起全國軍民的抗日救國的熱情、信心和意志,也為了繁榮延安這一偏僻窮困、文化匱乏的地方的文化,抗戰(zhàn)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在延安創(chuàng)辦了很多報刊,有人們熟知的《解放日報》《邊區(qū)群眾報》《新文字報》《救亡報》等報紙,以及《共產(chǎn)黨人》《八路軍軍政雜志》《中國青年》等雜志,還有《中國文化》等。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下,延安學(xué)界發(fā)表了一系列有關(guān)中國民族文化、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重要論述,當(dāng)時的《中國文化》成為傳播我黨文化理論和文化政策的重要載體。
一、延安《中國文化》創(chuàng)刊始末
在黨中央進(jìn)駐延安之前,延安及其周邊地區(qū)文化十分匱乏。1935年7月,新聞工作者范長江作為《大公報》的特約通訊員,前往西北地區(qū)進(jìn)行了一次深入的考察。他在對陜北地區(qū)教育普及情況的報道中明確指出,陜北地區(qū)的教育水平相當(dāng)落后,當(dāng)?shù)馗鱾€縣一所中學(xué)都沒有,高級小學(xué)是當(dāng)?shù)匚ㄒ坏慕逃龍鏊T诳谷諔?zhàn)爭爆發(fā)前夕,陜甘寧邊區(qū)一共只有120所小學(xué),其中延安農(nóng)村僅有7所小學(xué)共70多名學(xué)生,華池縣更是一所小學(xué)都沒有。當(dāng)?shù)厝罕姷淖R字率僅有1%,人們的文化生活極度貧乏。毛澤東對此曾表示,“中華蘇維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許多偉大驚人的事業(yè),但在文藝創(chuàng)作方面,我們干得很少”。因此,黨中央認(rèn)為急需加強(qiáng)對根據(jù)地人民群眾的文化宣傳和文化教育,努力改變當(dāng)?shù)匚幕瘶O度落后的不利局面。
與此同時,隨著日本侵略者“三個月滅亡中國”的陰謀破產(chǎn),其不得不調(diào)整侵華戰(zhàn)略。這一時期,日本加快了對中國的文化滲透和侵略,比如加快掠奪中國文化成果,并大肆攻擊破壞中國思想文化傳統(tǒng)。同時,通過在淪陷區(qū)實行奴化教育,對淪陷區(qū)人民群眾實施思想和文化壓制。1940年,日本軍部制定的“對華思想指導(dǎo)要領(lǐng)”中,明確提出“使中國人民的思想統(tǒng)一于大東亞共榮圈”構(gòu)想,重點是驅(qū)逐和消滅共產(chǎn)主義思想。
國民黨政府方面一是面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誘降,二是這一時期其自身也出現(xiàn)了政治倒退、文化和思想專制加深的趨勢。國民黨政府設(shè)立了一系列機(jī)構(gòu)來加強(qiáng)文化控制,并發(fā)布了許多壓制進(jìn)步文化團(tuán)體活動的限制性法規(guī)。同時,抗戰(zhàn)時期全國上下彌漫著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國民黨利用普通大眾的愛國熱情,大力宣揚中國封建道德觀來壓制“五四運動”精神。
在這種錯綜復(fù)雜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我國文化思想領(lǐng)域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混亂。為了樹立正確的文化導(dǎo)向,從思想層面形成最廣泛的共識,爭取抗戰(zhàn)勝利的早日到來,處在延安的黨中央深刻意識到加強(qiáng)文化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39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wù)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延安的文化界需要與外界建立更緊密的聯(lián)系。在當(dāng)年召開的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上,選舉張聞天擔(dān)任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并提議創(chuàng)辦《中國文化》。隨后在1940年1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qū)文化協(xié)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任命艾思奇領(lǐng)導(dǎo)《中國文化》的創(chuàng)刊和主編工作。1940年2月15日,《中國文化》正式創(chuàng)刊發(fā)行。該刊從1940年2月創(chuàng)刊到1941年8月停刊,共出版15期。雖然該刊存在時間較短,但是其在短期內(nèi)密集刊登了一系列主題鮮明的文章,為厘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脈絡(luò)、宣揚馬克思主義思想乃至繁榮根據(jù)地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xiàn)。
二、延安《中國文化》文化宣傳的主要內(nèi)容
《中國文化》以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為指引,針對延安乃至全國的文化狀況,力圖堵漏補缺、糾偏正誤、規(guī)正方向,內(nèi)容聚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民主主義文化和文化“民族形式”等重要議題,大力宣傳我黨的文化理論和文化政策,其文化宣傳的內(nèi)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宣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出現(xiàn)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jīng)歷了一段漫長的演變和發(fā)展過程。早在我黨建立之初,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從多個視角對五四時期以來的新文化運動進(jìn)行審視和總結(jié),并進(jìn)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步探索。1938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強(qiáng)調(diào),“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理論……我們應(yīng)該把他們的理論當(dāng)作行動的指南,我們不僅要了解他們基于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jīng)驗得出的一般規(guī)律的結(jié)論,而且要學(xué)習(xí)他們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這一號召激發(fā)了延安學(xué)界深入學(xué)習(x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熱情。隨后,《中國文化》陸續(xù)刊登了延安學(xué)界學(xué)者創(chuàng)作或翻譯的一系列馬列主義哲學(xué)著作,例如楊松翻譯的《黑格爾的哲學(xué)》和默涵翻譯的《黑格爾與康德》兩篇文章,全面介紹了黑格爾和康德的德國古典主義哲學(xué)思想,是人們了解和認(rèn)識馬克思主義產(chǎn)生的哲學(xué)背景的重要參考著作。楊松的《列寧論中國》、張仲實的《怎樣研究〈資本論〉》和蕭三的《列寧論文化與藝術(shù)》等,在馬列主義哲學(xué)思想的宣揚和普及方面也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中國文化》主編艾思奇也撰寫了《哲學(xué)是什么》《論地理的統(tǒng)一》等一系列哲學(xué)性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對辯證法、對立統(tǒng)一和質(zhì)量互變等重要哲學(xué)概念和理論進(jìn)行了深入探討。總之,延安的《中國文化》成為當(dāng)時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宣傳陣地,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進(jìn)程。
2.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宣傳。“新民主主義”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先進(jìn)思想的重大理論成果的創(chuàng)新。在《中國文化》第一期就刊登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毛澤東在文章中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概念。毛澤東將新民主主義文化定義為“無產(chǎn)階級領(lǐng)導(dǎo)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強(qiáng)調(diào)它既非資產(chǎn)階級文化,也異于社會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進(jìn)一步描述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三個核心特質(zhì),即“民族的、科學(xué)的、大眾的”。其中,“民族的”是指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倡導(dǎo)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尊嚴(yán),具有民族特色;“科學(xué)的”是指反對封建主義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追求客觀真理;“大眾的”是指這種文化要服務(wù)于廣大工農(nóng)勞苦大眾,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隨后,張聞天也在《中國文化》發(fā)表了名為《抗戰(zhàn)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與今后任務(wù)》的文章,對新民主主義文化進(jìn)行了更加詳細(xì)的探討,將其描述為“民族的、民主的、科學(xué)的、大眾的”文化。毛澤東和張聞天的文章在新民主主義文化問題認(rèn)識上略有差異,這反映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在初期形成過程中的多樣性。毛澤東的文章聚焦于政治、經(jīng)濟(jì)與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而張聞天的文章更注重抗戰(zhàn)時期的文化問題和政策。
3.對文化“民族形式”的宣傳。抗戰(zhàn)時期,我國文化領(lǐng)域非常熱衷于探討“民族形式”的議題。當(dāng)時學(xué)界對于如何處理和評價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形式,在新的民族形式構(gòu)建中所扮演的角色看法不一。一種觀點認(rèn)為中國的民間文藝是民族形式的核心,因為它深受廣大民眾的普遍喜愛。然而,另一種觀點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民間文藝深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不能作為新時期新文化的表達(dá)形式。針對這些多元化的觀點,《中國文化》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對這個議題進(jìn)行了深入探討。延安的文化精英們強(qiáng)調(diào),只有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文化,才能在國際舞臺上站穩(wěn)腳跟。因此,在建立新文化的過程中,借鑒和利用民族文化的傳統(tǒng)形式是至關(guān)重要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盲目接受舊有形式。在利用這些傳統(tǒng)文化形式時,應(yīng)保持批判性和發(fā)展性的視角。周揚提出,形式是由內(nèi)容決定的,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形式是對長期封建社會的反映,不能不加區(qū)分地視為高等藝術(shù)。對于舊形式,必須以批判的態(tài)度進(jìn)行改造,因為它們往往帶有時代的局限性。茅盾則進(jìn)一步提出,舊形式中的某些特點實際上是封建社會的產(chǎn)物,并非中國特有,因此不能作為民族形式的基礎(chǔ)。他認(rèn)為,把這些形式誤認(rèn)為“民族的”,并試圖在其基礎(chǔ)上建立新的民族形式是荒謬可笑的。《中國文化》對“民族形式”的廣泛討論,厘清了新時期文化藝術(shù)怎樣更好地服務(wù)于政治和人民大眾這一關(guān)鍵問題。
三、《中國文化》在文化領(lǐng)域的貢獻(xiàn)
《中國文化》致力于文化建設(shè),立足陜甘寧邊區(qū)而放眼全國,致力于傳揚先進(jìn)文化、抵制錯誤思潮、繁榮根據(jù)地文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民主主義文化、文化“民族形式”、文化抗戰(zhàn)的宣傳,不僅對陜甘寧邊區(qū),而且對全國,不僅對抗戰(zhàn)時期,而且對之后的各個歷史時期,均在文化領(lǐng)域作出了突出貢獻(xiàn)。
1.使新民主主義文化深入人心。新民主主義文化這一概念,為毛澤東同志提出。毛澤東同志當(dāng)時有針對性地寫出《新民主主義論》,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這個科學(xué)概念,賦予中華文化以新的生機(jī)和活力,為的是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把我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zhuǎn)為社會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xué)的大眾的文化。
新民主主義文化經(jīng)過延安學(xué)界的廣泛討論和《中國文化》的宣傳,逐漸形成了一種能夠代表中國文化未來出路的成熟的根本性文化主張。新民主主義文化引導(dǎo)著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方向,并隨著革命的洪流成為主導(dǎo)中國文化進(jìn)程的核心主張。在《中國文化》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宣傳影響下,大量文化從業(yè)者受到新民主主義的啟發(fā)和感染,以飽滿的激情投身于根據(jù)地的文化建設(shè)事業(yè)中來。他們以新民主主義為指導(dǎo),以新民主主義文化倡導(dǎo)的“民族的、科學(xué)的、大眾的”為出發(fā)點,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中去,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大眾化、通俗化的文藝作品,歌頌了新時代下的新事物和新文化,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2.堅定了全民抗戰(zhàn)的信心和決心。在抗戰(zhàn)期間,文化抗戰(zhàn)被賦予了一種特殊的戰(zhàn)略地位,如果將抗戰(zhàn)時期的軍事動員、政治動員、經(jīng)濟(jì)動員等比作人體的五官和四肢,那么文化抗戰(zhàn)就是“人體中的血液”,因為文化抗戰(zhàn)起著調(diào)配和聯(lián)動其他領(lǐng)域抗戰(zhàn)的關(guān)鍵作用。在黨中央的號召下,根據(jù)地的廣大文化藝術(shù)工作者們紛紛積極行動起來,他們以筆為戎、揮斥方遒,在《中國文化》上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一大批小說文學(xué)、革命繪畫和音樂戲劇作品,不僅歌頌了中國軍民的偉大抗戰(zhàn)精神,同時也對日本侵略者的邪惡罪行進(jìn)行了無情揭露。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化》,發(fā)表了歐陽山的《抗戰(zhàn)以來的中國小說》、李伯釗的《敵后文藝運動概況》、葉生的《抗戰(zhàn)以來的歷史學(xué)》等文化抗戰(zhàn)評論性文章,這些文章不僅具有深遠(yuǎn)的文化價值,而且為文化抗戰(zhàn)的發(fā)展提供了具體的理念指導(dǎo)。此外,雜志還發(fā)表了何其芳、蕭三、艾青等人的詩歌,丁玲、劉白羽等人的小說,以及荒煤、黃鋼等人的報告。這些多樣化的文學(xué)作品從思想層面喚醒了根據(jù)地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日熱情,激勵了前線的抗日將士,鞏固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同時也無情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行徑。通過這些作品,文化在抗戰(zhàn)時期成為一種強(qiáng)大的武器,它以其獨特的戰(zhàn)斗方式增強(qiáng)了人民的抗戰(zhàn)信念和意志,為抗戰(zhàn)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3.塑造了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氛圍。百廢待興的抗戰(zhàn)時期,《中國文化》卻獨樹一幟,成為引領(lǐng)根據(jù)地乃至全國文化變革的一個重要思想文化陣地。《中國文化》不僅刊登哲學(xué)、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文章,而且還刊登了中國古代史、藝術(shù)史、民族史、經(jīng)學(xué)史等多個領(lǐng)域的大量文章。比如范文瀾的《關(guān)于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克夫的《關(guān)于藝術(shù)的起源問題》、葉蠖生的《從安陽發(fā)掘成果中所見殷墟時代社會形態(tài)之研究》等,這些文章成為日后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學(xué)術(shù)成果。尤其是郭沫若在《中國文化》上發(fā)表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文,引發(fā)了范文瀾、尹達(dá)、謝華、葉蠖生等人的廣泛討論,為中國歷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突出貢獻(xiàn)。《中國文化》通過刊登這些學(xué)術(shù)文章,營造出一種開放包容的思想文化交流環(huán)境,激發(fā)了一大批學(xué)者們的創(chuàng)造力。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不僅對我國的學(xué)術(shù)研究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而且也對陜甘寧這樣的敵后根據(jù)地的文化發(fā)展產(chǎn)生了本質(zhì)影響。
綜上所述,在這些文章的影響下,陜甘寧根據(jù)地的文化不再是一個封閉和單一的系統(tǒng),而是成為一個多元、包容和充滿活力的熱土。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根據(jù)地人民群眾的文化素養(yǎng)得到了提升,全國各地的廣大學(xué)者和青年人奔赴延安,使延安這個過去的文化荒漠,搖身一變成為無數(shù)青年人心中的思想和文化圣地。
作者單位 河北師范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
本文系2022年度河北省高校黨建研究課題“高校‘課程思政創(chuàng)新實踐研究”(項目編號:GXDJ2022B26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xiàn)
[1]孫書瑤.延安時期毛澤東對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戰(zhàn)略思考及其現(xiàn)實啟示[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xué),2019.
[2]葉靜.延安時期中國文化精神研究[D].沈陽:沈陽理工大學(xué),2018.
[3]張從容,李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70年來,中國文化發(fā)展路徑和發(fā)展現(xiàn)狀研究[J].大連大學(xué)學(xué)報,2016(02).
[4]齊衛(wèi)平,周穎秋.延安時期《中國文化》若干問題的研究[J].中國延安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2013(03).
【編輯:陳強(qiá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