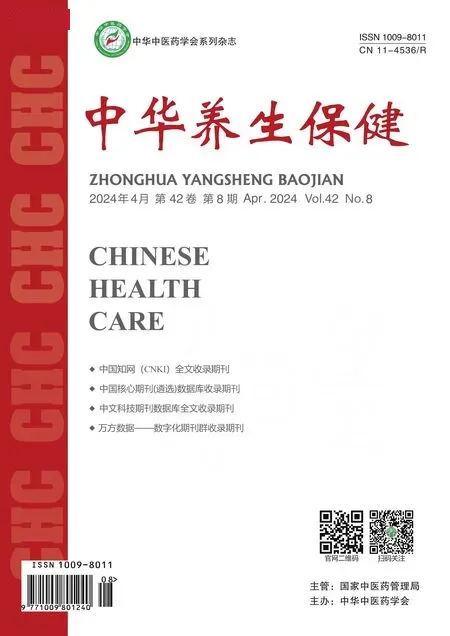伴MELF生長方式的子宮內膜樣癌臨床病理特征及免疫表型的研究
韓 莉 謝玉汶
(新疆巴州人民醫院病理科,新疆 巴州,841000)
子宮內膜樣癌在女性生殖系統惡性腫瘤的發病率中長期位居前3,占女性生殖道惡性腫瘤的1/3左右,占女性惡性腫瘤總數的1/10左右[1-2]。尚不明確子宮內膜樣癌的具體發病機制,病因包括遺傳、環境、激素變化,雌激素的靶器官是子宮內膜,當體內性激素表達發生變化時,可導致子宮內膜樣癌的發生[3-4]。低級別的內膜樣癌預后總體好于高級別,但也有5.0%~18.0%低級別的子宮內膜樣癌復發、轉移[5-6]。伴MELF生長方式的子宮內膜樣癌為子宮內膜樣腺癌的一種浸潤方式,表現為微囊性、伸長、碎片狀等,多在低級別子宮內膜樣癌中出現,患者預后相對比較差[7]。本文具體探討與分析了伴MELF生長方式的子宮內膜樣癌臨床病理特征及免疫表型的特征,希望為明確伴MELF生長方式的子宮內膜樣癌的發生機制提供參考,也為早期預防子宮內膜樣癌發生提供參考,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13年9月—2019年1月于新疆巴州人民醫院行子宮全切除+雙側附件切除+盆腔淋巴清掃術且隨訪成功的72例子宮內膜樣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患者自愿參與本次課題研究;本研究得到了新疆巴州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病理診斷為子宮內膜樣癌(所有切片均經兩位高年資病理醫師確診);②患者年齡30~75歲;③病理檢查前未接受靶向治療、放療、化療等的患者;④臨床與隨訪資料完整。
排除標準:①合并高危傳染性疾病者;②合并有凝血功能障礙的患者;③合并其他部位腫瘤者;④調查期間死亡者;⑤病理獲取標本不合格者;⑥在檢查過程中依從性不佳的患者;⑦妊娠與哺乳期婦女;⑧合并有先天性免疫功能障礙的患者;⑨合并有心臟、肝臟、腎臟異常的患者。
1.3 免疫組化檢測
收集所有患者的病理組織標本,制成標準化的病理切片,免疫組織化學染色采用羅氏全自動免疫組織化學儀(Ventana Bench Mark XT),抗體包括孕激素受體(PR)、雌激素受體(ER)、P16、細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Ki-67等。
1.4 觀察指標
(1)結果判讀。陽性表達部位出現棕黃色顆粒為陽性表達,其中ER、PR、Ki-67定位于細胞核,CK定位于細胞質。(2)調查與記錄所有患者的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絕經狀態等。同時調查與記錄所有患者的病理特征,包括病理分級、淋巴脈管間質浸潤、淋巴結轉移等。(3)所有患者都進行隨訪,調查與記錄患者的預后情況,包括有無出現腫瘤轉移與腫瘤復發等。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4.0分析數據,計量資料如受教育年限符合正態分布,以()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如免疫組化指標陽性率用[n(%)]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伴MELF生長方式的子宮內膜樣癌發生情況
在72例患者中,病理診斷為不伴MELF生長方式的子宮內膜樣癌(不伴MELF浸潤組)占83.3%(60/72);伴MELF生長方式的子宮內膜樣癌(伴MELF浸潤組)占16.7%(12/72)。
2.2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在72例患者中,伴MELF浸潤組的身體質量指數、受教育年限等與不伴MELF浸潤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伴MELF浸潤組的年齡、絕經狀態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 n(%)/()]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 n(%)/()]
一般資料不伴MELF浸潤組(n=60)伴MELF浸潤組(n=12)χ2/tP身體質量指數(kg/m2)20.17±0.6820.26±0.51 0.434 0.666受教育年限(年)15.79±1.1515.59±2.09 0.322 0.753年齡(歲)56.03±2.5867.44±3.5813.067<0.001絕經狀態(絕經前/絕經后)29/312/10 4.090 0.043
2.3 兩組病理特征比較
在72例患者中,伴MELF浸潤組的病理分級、淋巴脈管間質浸潤、淋巴結轉移等與不伴MELF浸潤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病理特征比較 (%)
2.4 鏡下特征
MELF浸潤灶位于緊鄰腫瘤主體的組織或深肌層中(以碎片狀腺體浸潤、微囊型腺體、拉長腺體浸潤為特點)。出現大量以中性粒細胞為主的炎癥細胞,伴隨有纖維黏液樣基質反應(詳細情況見圖1),腺腔內可見脫落的上皮細胞,呈碎片狀,伴隨有胞質豐富(詳細情況見圖2),癌細胞排列成細長或者破碎成小簇狀分布(詳細情況見圖3)。

圖1 40倍 MELF浸潤灶遠離腫瘤主體

圖2 100倍 碎片狀腺體

圖3 400倍 纖維黏液樣基質反應

圖4 100倍 淋巴結轉移灶不明顯
2.5 兩組免疫組化表達陽性率比較
伴MELF浸潤組中,ER(詳細情況見圖5)、PR、Ki-67、P16(詳細情況見圖6)陽性表達率分別為8.33%(1/12)、16.67%(2/12)、91.67%(11/12)、100.00%(12/12);CK呈彌漫性棕黃色強陽性表達(見圖7),陽性表達率為100.00%(12/12)。

圖5 ER陰性 400倍

圖6 P16陽性 40倍

圖7 CK陽性 100倍
不伴MELF浸潤組中,ER、PR、Ki-67、P16、CK呈棕黃色強陽性表達,陽性表達率均為100.00%(60/60)。
在淋巴脈管間質浸潤和淋巴結轉移(詳細情況見圖8)組織中,CK也均呈棕黃色強陽性表達,陽性表達率均為100.00%,詳細數據見表3。

圖8 淋巴結中CK陽性 100倍

表3 兩組免疫組化表達陽性率比較 [n(%)]
2.6 預后比較
對所有患者均進行隨訪,隨訪時間為9~60個月,平均隨訪時間為(31.40±4.02)個月,患者都生存且不帶瘤,隨訪期內患者都無出現腫瘤轉移與腫瘤復發情況。
3 討論
伴MELF生長方式的子宮內膜樣癌多出現于低級別子宮內膜樣癌中,預后相對較差[8]。MELF這種浸潤模式通常伴隨纖維黏液樣的間質反應及中性粒細胞浸潤、嗜酸性粒細胞浸潤等,癌成分中包含單個或成簇的腫瘤細胞,這些細胞常胞質豐富或具有嗜酸性[9-10]。本研究結果顯示,在72例患者中,病理診斷為伴MELF生長方式的子宮內膜樣癌12例,占16.7%(12/72);伴MELF浸潤組的身體質量指數、受教育年限等與不伴MELF浸潤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伴MELF浸潤組的年齡、絕經狀態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伴MELF生長方式的子宮內膜樣癌占比較高,但是通過臨床一般資料比較難以診斷鑒別。
子宮內膜癌容易發生淋巴結轉移,低級別患者的淋巴結轉移發生率較低,為5.0%~18.0%,而伴MELF生長方式患者盆腔淋巴結轉移的發生率平均為24.2%[11]。淋巴脈管間隙浸潤是經過組織學確認,兩層血管內皮組織之間出現惡性細胞。原發癌灶形成后,腫瘤的脈管隨之生成,脫落的腫瘤細胞進入脈管系統形成癌栓,隨體循環與血液循環等播散至全身其他器官。淋巴脈管間隙浸潤是影響子宮內膜癌患者預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存在MELF浸潤模式的患者淋巴脈管間隙浸潤的發生率較高[12]。有研究發現,伴MELF生長方式患者淋巴脈管間隙浸潤的發生率為97.4%,不伴MELF生長方式為5.3%,可能的原因是MELF浸潤多發生于深肌層,其中豐富的淋巴管及血管使之更易發生淋巴脈管間隙浸潤[13-14]。本研究結果顯示,在72例患者中,伴MELF浸潤組的病理分級、淋巴脈管間質浸潤、淋巴結轉移等與不伴MELF浸潤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特別是在無MELF浸潤的子宮內膜樣腺癌中,淋巴結轉移灶多呈現癌巢結構;在伴有MELF浸潤的子宮內膜樣腺癌中,淋巴結轉移灶可出現于淋巴濾泡內,多呈為孤立細胞結果,容易與組織細胞混淆[15]。有研究顯示,MELF浸潤腺體經常浸潤在子宮深肌層,其鏡下形態與淋巴管及血管類似,易與淋巴管及血管異常形成的腔隙難以鑒別,容易出現漏診情況[16-17]。
隨著醫學的發展,MELF浸潤模式分析進展比較大,但是關于其浸潤模式的生物學機制與信號傳導途經還不明確。不過MELF浸潤模式與免疫表型特征有相關性,比如MELF浸潤模式多伴隨有E-cadherin、雌孕激素受體、Ki-67表達缺失,而fascin、CK7、CKl9和P16表達上調,認為伴MELF生長方式可能代表了類似于上皮一間質轉化(EMT)的活化模式[18]。本研究結果顯示,伴MELF浸潤組中,ER、PR、Ki-67、P16、CK陽性表達率分別為8.33%、16.67%、91.67%、100.00%、100.00%。伴MELF浸潤組中,ER、PR、Ki-67、P16、CK呈棕黃色強陽性表達,陽性表達率均為100.00%。對所有患者均進行隨訪,隨訪時間為9~60個月,平均隨訪時間為(31.40±4.02)個月,患者都生存且不帶瘤,隨訪期內患者都無出現腫瘤轉移與腫瘤復發情況,可能與數量少、隨訪時間短有關。當前有研究發現,MELF浸潤中P16陽性時,伴隨有Ki-67陰性,可使得腫瘤細胞的生長發生阻滯,但是不影響患者的總生存率和無病生存率[19-20]。由于本次課題研究下撥的經費比較少,本次研究調查人數過少,分析指標比較少,也沒有納入健康人群與良性疾病人群進行比較分析,觀察也有待延長,后續研究中將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MELF浸潤在子宮內膜樣癌中比較常見,多伴隨有淋巴脈管間質浸潤、淋巴結轉移,ER與PR表達陽性率顯著降低,所以應該提高對伴MELF生長方式子宮內膜樣腺癌浸潤腺體的認識,工作中應仔細辨別是否存在MELF浸潤,減少漏診才能正確評估浸潤深度及淋巴結轉移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