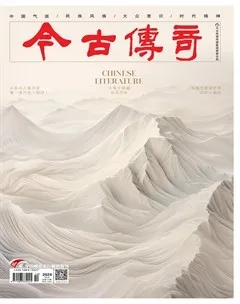將疼痛化為詩歌的心跳
詩人進入詩歌的方式多種多樣,沒有統一的模式,有以聽覺進入的,有以視覺進入的,有以嗅覺進入的,有以味覺進入的,有以觸覺進入的……以何種感官方式進入應該是因人而異的,即使是同一位詩人,他進入詩歌的方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更何況還有第六感官(直覺或伏覺之類)。但不少詩人和讀者認為,詩歌要寫出詩人內心的疼痛,給人疼痛感,甚至有人直言,沒有疼痛感的詩歌不是好詩歌。能將詩歌寫出疼痛感,已經成為不少詩人的追求。疼痛感,源自拉丁語中的“傷害”,是引發疼痛的刺激從受創部位或者病灶部位發出并傳導至中樞神經、使人產生疼痛感知的過程,這是一種生理上的觸覺反應。而詩歌的疼痛感主要還是心理或者精神上的反應,它源于詩人對生活的深切體驗與感知,詩人將它寫入詩中并藝術地呈現出來,然后傳導給讀者。著名詩人蔣楠在《“詩歌之鄉”與“疼痛之上”》中說:“我堅持認為,有什么樣的‘痛感,就有什么樣的思想和語言,在詩寫者的筆端流淌。”讀了詩人章洪波發表在本期的詩歌,我產生了一種明顯的疼痛感:一是其每一首詩歌幾乎都用到“疼痛”(或相近)一詞,二是其詩歌的意蘊都與疼痛有關。他的詩歌疼痛點究竟在哪里?他是如何表現這種疼痛感的?下面以詩歌文本為例,來具體分析一下。
《像一道閃電》的疼痛點在于人生的無常與生活的不易。詩歌以其獨特的語言和深邃的意象,向我們展示一個人在疾行于山間時的復雜心情。詩人用閃電般的比喻,表達內心的幸福、疼痛、光芒和愛。“把自己走成了/一朵烏云”,形象地描繪了人在行走中的孤獨和沉重。烏云象征著內心的憂慮和困擾,而行走則象征著人生的旅程。詩人通過這種比喻,表達了人在行走中內心的復雜情感。“偶爾,穿出一兩只小動物/與他對視,又匆匆走開”,表面上是寫動物,實際是寫人,寫生活,寫人與自然的微妙關系。對視是短暫的,留下來的是相互關注,同時人性、詩性的一些美好也體現出來了。“多像一些親人忙于/生計,只用眼神道別/牽掛,祝福……”則表達了詩人對親人的思念和牽掛,以及對人生無奈的感慨。“疾行于山間。他知道還會遇到/很多熟悉的事物”,這一句承上啟下,向讀者表明他在生活中不斷地遇見并不斷地感悟。最后,“但他必須像一道閃電……交出……”是全詩的高潮,詩人用祈使的語氣和形象的比喻來表達內心的幸福、疼痛、光芒和愛。閃電象征著瞬間的美麗和力量,也象征著對未來的期待和希望。詩人通過這一比喻,表達了對未來的憧憬和對生命的熱愛。詩中人物在“大雨將至”時的疾行過程,實際上就是人生的過程,需要我們不斷面對生活的挑戰和變化,同時也要付出生命中的美好和力量。
《被落日追趕的人》的疼痛點是人生的磨難與短暫。通過對主人公被風、雨、閃電、雷聲追趕,以及被落日追趕的描繪,展現了人生的苦難與掙扎,以及在困境中尋找希望和歸宿的主題。詩中的“他”其實就是詩人自己,不用第一人稱是為了敘述更客觀、更理性。詩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堅韌不拔的人,他經歷了種種磨難,但卻從未放棄。他的內心世界充滿對生活的渴望和對未來的期待。開頭兩行,“體內的風聲”與“殘缺的青春”相關聯,表明他曾經擁有過美好的青春歲月,但因為種種原因,它們已經殘缺不全。他試圖“趕在暮色降臨前”交出內心諸如月光、燈火、潮聲和浪花等一切美好,表達他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詩中的比喻和象征手法也十分出色。落日、流水等意象,不僅描繪了主人公所處的環境,也暗示他的內心世界。這些意象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人感受到了主人公的孤獨和無助。最后兩個“是不是……”,詩人運用疑問的口吻,引導讀者一起思考人生:當落日追趕一個人時才會覺得余生不多、遺憾似群山飛來;當生命遇到困境時,不要放棄希望,而要勇敢地面對一切,努力尋找屬于自己的美好。無論何時何地,家都是我們最溫暖的港灣。這里的家更多是指我們內心的歸宿感,是詩人內心精神的棲居地。這首詩表現了對生命的深刻感悟和對未來的熱情期待。
《東魯山》的疼痛點是失去親人的傷痛和對他們的懷念之苦。詩中的東魯山,坐西朝東,仿佛是人間的“風水寶地”,其實它是一塊墓地,“住著我的親人”,它的魅力在于它的靜謐與溫情,同時也因為它能“救贖”我們曾經救贖過的一切。第二節中的兩個“救贖”,將生與死、愛與恨、過去與現在、自然與人生融合在一起,透露出一種深沉的人生思考。每一份痛苦,每一份經歷,都成為詩人成長的力量源泉,從而構成一幅人生的多面鏡。“父母去,人生只剩歸途”,東魯山是親人的安眠之地,也是詩人內心唯一的情感依托。清明掃墓,是“我”和親人溝通、交流的特殊方式,也是“我”彌補親人的唯一方式。在“我”眼中,東魯山就像是一座精神的山,它可以洗滌過去,甚至改變著現在,麥子和高粱不見了,只見墓碑。在“我”看來,東魯山是高于草木花朵的。這里沒有物質的喧囂和爭奪,有的是溫熱的土地和寧靜的山谷。詩人的這份寧靜是經歷了風風雨雨、酸甜苦辣之后才獲得的。這里“住著”親人,“他們的名字緊挨著名字”,仿佛“在塵世取暖”并相互“問候”。然而,東魯山也“拒絕”麥子和高粱的生長,只生長“悲傷”,這里的“悲傷”是對親人的懷念,也是自我救贖的一種力量。東魯山不僅是人間的風水寶地,也是“我”心靈上的一片凈土。詩人的表達方式樸素而真摯,字里行間充滿了情感的力量。
《父親的鋼筆》的疼痛點是父親的“英雄氣短”。這支鋼筆是父親留給“我”的一件精神財富,它靜靜地躺在“殘舊”的筆盒里,現在可能已經壞了,寫不出文字了。但詩人睹物思人,仿佛看到一位“遲暮的英雄”。詩人通過描繪父親使用過的鋼筆,以及那些被他寫過的事物,以物喻人,傳遞了對父親的敬仰和懷念。首先,詩人在開篇就通過生動形象的比喻,將父親用過的鋼筆比作一位遲暮的英雄,這種形象化的表達方式讓讀者能夠更好地感受到詩人的情感。同時,詩中也運用“塵埃”這一意象,進一步強化鋼筆的“殘舊”和“落寞”之感。其次,詩人通過描述那些被父親寫過的事物“已成為歷史/成為殘缺和疼痛”,詩人將父親的手跡與歷史、殘缺和疼痛聯系在一起,表達對過去歲月的感慨和對父親的敬仰之情。最后,詩人又想象如果拿起鋼筆寫下現實,“那些虛構的/美好,將蕩然無存”,這里詩人以鋼筆作為引子,對過去與現在進行對比反思,體現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和對父愛的珍視。
《馬頭琴》是一首充滿情感和深度的作品,其疼痛點是馬作為生命的消逝。它通過馬頭琴這一藝術形式,將馬的堅韌、隱忍、熱烈和奔放等特質表現得淋漓盡致。這首詩不僅是對馬的贊美,更是對生命的憑吊。首先,詩中的描述讓人感受到馬的堅強和高貴。當一匹馬應聲倒地,它的頭顱被雕刻成馬頭琴,這個過程既體現馬的堅韌不拔,也體現馬的無私奉獻。接著,詩人進一步強調馬的骨骼和精神內核,將其融入馬頭琴中,象征著生命的精髓和內在力量。在馬頭琴的演奏中,詩歌通過生動的比喻和想象,將聲音賦予了生命和情感。那些豎起耳朵的動物和人,那些垂下頭顱的草木,雖然都感受到了馬頭琴的魅力,但方向感是截然不同的,動物抬頭是對琴聲的聆聽和共振,而植物垂下頭顱是對琴聲的感知和緬懷,通過對比產生一種情感張力,進而生發出生命的悲憫力量。在詩的結尾,詩人用“馬頭琴啊!其實你是一匹馬的/靈魂”來總結全詩,將馬頭琴與馬的靈魂緊密相連,強調了馬頭琴所蘊含的生命意義和精神力量。同時,詩人也提出一個問題——“誰能喚醒一個人內心的蒼涼/和波瀾壯闊的悲痛”?這個問題既是對生命的思考,也是對人類的關懷,喚起人們對生命的敬畏和珍愛。
另外幾首詩也是有疼痛點的。“誰能比它更鋒利,更輕易就劃開我與故鄉/久治不愈的疼”,《七月的敘述詞》的疼痛點是遠離田野的疼痛。“請允許我說出愛,久藏于內心的/紅撲撲的愛”,《請允許我說出……》的疼痛點是愛而不得的落寞與苦悶。“仿佛暮色一合攏,父親就將/離我而去”,《催眠術》的疼痛點是父親走得太匆忙的遺憾。“像一株植物,遺忘在夕陽的背影里”,《需要一場雨水》的疼痛點是生命缺乏愛的滋潤。“它是一個人內心的/燈盞,被風提著/在旅途中,明明滅滅”,《低處的陽光》的疼痛點是底層對“陽光”的渴求。“它落下的/重量,足夠壓住塵世一切的/輕浮、荒蕪和絕望”,《汗水的重量》的疼痛點是勞動的艱辛。“它把一個人輕輕摁進春色里/仿佛把幸福和疼痛,摁進/生活的骨肉里”,《三月的風》的疼痛點是青春易逝與人生無奈。“它羞澀的歌聲/把月光下的子夜,捻得又細又長”,《子夜的小村》的疼痛點是思念之苦。詩人將這些疼痛點,通過語言的多姿多彩和結構的起承轉合等手段藝術地表現出來,也引發讀者閱讀的疼痛感。章洪波認為好的詩歌要“有血,有肉,有骨頭”,因而他的詩歌注重構思的精巧、語言的錘煉和內涵的厚實,特別講究修辭手法的出新出彩。
章洪波從小熱愛文學,學生時代深受艾青、徐志摩、戴望舒、北島、鄭愁予等詩人的影響,在多種文學樣式中獨愛詩歌,他喜歡詩歌的語言、哲思以及直抵人心的力量。章洪波詩歌的疼痛感來源于自己的生命體驗和生活感知,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現實的警覺與批判,并不是子虛烏有、空穴來風,它是有真摯的情感基礎的。疼痛是他詩歌的詞根,更是他詩歌的心跳。“疼痛”一詞在他的詩歌里出現的頻率較多,這恐怕與他成長的經歷、經受的生活密切相關。據了解,他比同齡人經歷過更多的風雨、苦難和傷痛,過早地體會了人情冷暖、愛恨情仇、生離死別,但恰恰是這一點讓他更透徹地感悟人生,更深情地熱愛生活。當然,一首詩光有疼痛感是不夠的,他的詩中更有幸福、期許、甜蜜、憂傷,與真切的體驗交織在一起,使主題更加豐盈、飽滿。他說:“幸福并疼痛著,讓我在塵世時刻保持冷靜的思考,穿透一些事物的表相,看清它的本質。我并不因疼痛而厭惡生活,相反更愛生活。”在堅韌的人生歷練和自覺的詩歌實踐中,他正在不斷探索,以日臻成熟的審美追求力爭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疼痛詩學。
李漢超 湖北應城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應城市作家協會主席。已出版詩集《歲月無塵》《大地之燈》和詩評集《詩海逐浪》《靜下心來讀好詩》《荊楚詩韻》等11部。
(責任編輯 蔣茜 7405021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