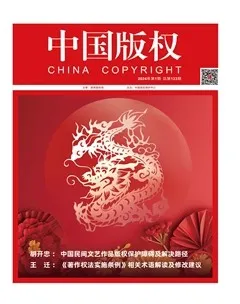文學角色的版權保護:以“金庸訴江南案”為例
劉銀良
關鍵詞:文學角色;版權;同人作品;本作品一般讀者
一、問題的提出
文學作品是指基本以文字為主要表達工具的作品。自從人類發明文字以來,文學作品就成為承載文化或文明的重要載體。文學作品既可以紀實,亦可以虛構,并且紀實作品中又可有虛構,虛構作品中亦可有紀實。文學角色是指文學作品所塑造的角色。與之對應的是由藝術作品塑造的藝術角色,如卡通、繪畫、攝影或視聽作品中的角色。一般而言,藝術角色有確切的形象,可構成著作權法下的美術作品或攝影作品(包括視聽作品的靜止畫面),其版權保護并非難題。文學角色主要是由文字描述,通常認為比較抽象,并且因不同讀者有不同理解而有多樣性,因此其版權保護是富有爭議性的難題,不僅法院的判決不同,研究者亦見仁見智。再加上文學角色的借用通常又與同人作品交織,更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與爭議性。
本文試圖解析小說等虛構文學作品的角色版權保護問題,這也是司法實踐中矛盾與糾紛多發的領域。通常認為文學作品有角色(人物)、故事(情節)和環境三要素。其中,環境是指故事發生的歷史背景、場所或場景等,一般在故事中敘述,或者可直接納為故事要素。因此,本文將主要關注文學作品的角色與故事兩要素,它們可構成作品的實質部分。近年來相繼發生的“瓊瑤訴于正案”和“金庸訴江南案”所關注的重點恰好分別是故事與角色的版權保護。“瓊瑤訴于正案”已對故事(情節)的版權保護進行了論述,人們對此基本沒有爭議。本文將不再單獨涉及對故事的可版權性論述,而主要利用“金庸訴江南案”對角色的可版權性問題進行探究。金庸先生“秉承深厚的文化傳統,運用廣博的歷史與文化知識,利用高超的文學敘事方式,通過傳奇的故事情節,塑造了大批性格鮮明的武俠角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有趣的江湖故事構成獨特的武俠作品集合,成為映射中國傳統文化乃至現實的武俠世界。”金庸作品尤其是與該案件相關的部分亦構成本文的論證基礎。
二、著作權法下的“角色”與“表達”
和所有著作權法難題一樣,文學角色的版權保護問題亦須回歸至著作權法的基本原則和法律教義才可能得到合理解決。著作權法的基本原則是保護表達而不保護思想。要探究文學角色的版權保護,須厘清的根本問題是如何界定文學角色的著作權法地位——具體而言,文學角色到底是表達還是思想?或者說,文學角色是否可能成為著作權法下的表達從而獲得版權保護?
(一)文學角色解析
既然角色與故事是文學敘事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構成作品的實質部分,那么文學作品也就不可能離開角色與故事,這是作品和角色以及故事的關系。進一步地,須探究角色與故事的關系。一方面,除對環境的描述外,故事基本是角色的行為集合,沒有角色不可能有故事,也不可能構成作品。另一方面,角色亦須故事支撐才可能得以塑造或表現,即角色的由來、經歷、命運及其性格、品質等特征,除作者的直接或間接敘述外,仍須經該角色的行為或不同角色的行為或矛盾沖突才可能加以展現并得以塑造,繼而得到讀者認知并獲得其積極或消極評價。這意味著,角色與故事互為支撐與依存,沒有角色就沒有故事,沒有故事也就沒有角色。角色與故事有機結合,共同完成作品的敘事或表達,兩者亦共同構成作品。
因此,不僅角色與故事不可分,角色、故事與作品亦不可分。在著作權法意義上,既然版權保護原創性的作品,那么就須保護具有原創性的作品構成,即角色與故事。如果說版權保護原創性的作品,但卻不保護構成其實質部分的原創性的角色或故事,或者僅保護原創性的故事,卻不保護原創性的角色,就顯然有內在的邏輯沖突。符合邏輯的推論是,既然著作權法保護原創性的作品,那么它也須保護構成作品實質部分的角色,前提是該角色屬于著作權法下的“表達”。
對角色與故事互依關系的強調,并不能推翻兩種作品元素相互獨立的地位,否則就沒有必要強調其是不同的表達元素。在“金庸訴江南案”中,一審法院在論證角色不能獲得版權保護時,認為被告作品《此間的少年》沒有將故事情節建立在原告作品基礎上,基本沒有提及或重述原告作品的情節,而是在不同的時代與空間背景下重新創作作品,被告并未侵害原告的版權。這顯然是用作品的故事元素否證其角色元素,在邏輯上并不當然成立。
(二)“角色”何時成為“表達”
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角色何時成為表達從而可獲得版權保護。鑒于角色涵義的廣泛性,它既可能僅有抽象的“思想”含義,也可能具體化為“表達”,因此針對該問題的答案只能是著作權法下的文學角色既可能是思想也可能是表達,而究竟是思想還是表達只有在具體情形或案件中才可能界定。在“金庸訴江南案”中,二審法院即廣州知識產權法院認為,文學作品的表達既包括直觀的文字呈現,也包括作品的結構、情節安排等內容表現。就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事件的發生、發展和先后順序,角色的設置、交互作用和發展,作品的結構安排、場景設計和故事推進等,“已經充分描述、能夠具體到形成一個內部各元素存在強烈邏輯聯系的結構”,該情節就已脫離思想的范疇,屬于表達。該論證邏輯對于角色的認定也基本適用。
與藝術角色相比,人們一般認為文字描述多屬抽象,文學角色因而具有抽象性,也難以獲得版權保護。在“金庸訴江南案”中,二審法院認為,文字描述的角色形象通常無法直接獲得讀者視覺感知。“囿于語言文字的抽象性,無論作者如何工于描述,縱有生花妙筆,但人物角色的整體形象或者說各個組成方面仍然難免存在模糊之處。”讀者雖然可以感知角色的容貌,但這畢竟不如視聽角色、卡通角色形象那么“直觀、固定”,角色的具體容貌還得讀者“腦補”。該認識雖然對于角色的“容貌”可能部分適用,但整體而言卻難以成立,因為就角色的整體形象塑造而言,文字作品可能遠勝于視聽作品。即便對于“容貌”來說也是如此,因為角色的容貌除了長相外還有氣質呈現。例如,似乎沒有演員可以呈現蕭峰的內涵、形象與氣質,無論裹頭巾還是披頭散發都是如此。由金庸作品改編的影視劇拍了又拍,除極少數外,大多數影視形象難以讓人留下深刻記憶,其命運也多如云煙,而金庸小說的角色形象一旦在讀者心目中固定,就可能始終生動如初。
認為文學角色抽象或模糊的認識,可能有先入為主的偏見。事實上,對于習慣文字閱讀的讀者(而非主要觀看影視劇的觀眾)來說,文字可能要比圖形、畫面、面部表情或肢體語言等非文字表達因素有更為強烈而持久的穿透力與塑造力,對于具有高超文字表達能力和敘事能力的作者如金庸而言更是如此。如《天龍八部》敘述兩位主角在無錫松鶴樓匿名斗酒的過程,情節離奇,栩栩如生,“六脈神劍”的排酒路線清晰如見,遠非影視作品所能描述。“凌波微步”更是如此。而在故事被敘述的同時,角色的形象也變得具體而生動,斷非“抽象”所能概括。這意味著,文學作品可有更為廣泛、具體、驚心動魄或波瀾壯闊的表達,所塑造的角色亦可成為讀者心目中鮮活且持久的形象。
從作品傳播角度看,是讀者或觀眾的參與才使作品的傳播得以完成。“金庸訴江南案”的二審法院認為,閱讀是主觀與客觀交互作用的過程,讀者會不自覺地將自身對事物的認知和情感偏好等代入故事和人物,最終讀者心目中的角色形象各不相同,正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或言之,對很多讀者而言,文學作品有更大的想象空間,有助于讀者代入作品。因此,文學作品對于角色的塑造,可以遠比視聽作品對角色的塑造更為全面、深入、細膩和長久。這意味著,文學角色不一定抽象和難以把握,它可能非常具體,也可能持久地停留在讀者心目中。
文學作品基本是通過故事情節或矛盾沖突塑造角色,角色與故事的交融即可完成作品的敘事與表達。反過來講,作品之所以成為作品,在于有角色與故事的支撐,缺少任何一種元素作品都不完整。例如,如果沒有蕭峰,《天龍八部》的故事就難以講述,不僅胡漢恩仇無所承載,多數故事情節也將黯然失色。角色與故事的結合不僅塑造了角色、講述了故事,還可構成作品的實質內容,使作品及其角色與故事皆體現原創性,從而奠定其可版權性基礎。所以對文學作品而言,角色處于中心地位或至少與故事并駕齊驅。由此角度看,當原創性的角色構成作品不可或缺的實質內容時,角色就成為作品的表達,從而可獲得版權保護。并且,在角色的各要素中尤以具有原創性和文化涵義的名字最為重要,它是角色所有內容的承載,角色的特征、關系、經歷等最終都聚集和體現在角色名稱上,被讀者感知與認知。
三、角色成為“表達”的判斷
(一)判斷標準及其統一性
在司法實踐中,美國聯邦法院分別提出“角色被充分獨特地描述”和“被講述的故事”兩個判斷標準。聯邦第二巡回法院在尼克爾斯( Nichols)案中不僅提出“抽象測試法”,還提出“角色被充分獨特地描述標準”。版權保護不能僅限于字面文本,否則抄襲者就可能因其無關緊要的改變而逃脫責任。當越來越多的細節被略去后,作品就可能呈現不同抽象模式,最抽象的可能就是關于作品是何種主題的陳述,此時也許僅剩作品標題。在思想與表達的分界線一邊,可能就是版權保護不能延及的思想,它不受版權保護。角色和故事情節是作品的實質部分,但不能認為它們僅是作品的部分就不重要,“骨骼盡管只是身體的一部分,但它貫穿并支撐著身體。”由于角色與故事貫穿并支撐作品整體,所以不能忽略其保護。當然,角色又分兩類。莎士比亞戲劇的主角就可能是表達而受到保護,但一般角色可能僅是講述故事的工具,就可能落入思想的范疇而不受版權保護。角色是否受保護的界線就是看該角色是否被描述為“獨特的角色”:如果是,角色就屬表達,應該受到版權保護。但如果角色僅被蒼白地而非充分地描述,就可能是角色原型,屬概念范疇,不能受到版權保護,即使該角色原型是由原告最先創作也是如此,因為作品原型并不包含原創性的內容。因此,角色越不能得到塑造,就越不受版權保護,這是作者不能使角色成為獨特角色而應承擔的后果。在華納(Warner)案中,聯邦第九巡回法院提出“被講述的故事標準”:角色可以構成被講述的故事(the story being told);但角色如果只是講述故事的棋子,就不在版權保護范圍內。
在DC Comics案中,聯邦第九巡回法院總結并結合了兩個標準。版權保護不僅適用于整部作品,還適用于作品中“足夠獨特”或“特別獨特”的角色。基于此前判決,法院提出三要素測試標準以測試漫畫或視聽角色是否可獲得版權保護:角色應具有“物理的和概念的品質”;角色被充分描述,且在系列作品中具有可識別的一致性;角色須“特別獨特”且包括一些獨特表達元素。具有鮮明特征的007詹姆斯·邦德就符合版權保護條件,而輕描淡寫的角色僅可能是敘述故事的工具,既不值得版權保護,也難以獲得版權保護,如一般的魔術師。大眾角色也不滿足要求,不能獲得版權保護。
該標準雖然是針對藝術角色提出,但對文學角色判斷也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其中包括“角色的獨特性”和“被充分描述”。如在Klinger案中,第七巡回法院強調,角色越模糊,越不完整,就越不可能獲得版權保護,但如果角色有特定的名字、物理特征或其他特征,就可能獲得版權保護,如神探福爾摩斯及其助手華生。
雖然研究者多認為“角色被充分獨特地描述”和“被講述的故事”是兩個標準,且后者更為嚴格,但若結合上述角色與故事的關系或可發現,兩個標準實質一致,皆要求角色被充分描述,以至于成為獨特的角色或被講述的故事,并因而構成作品的表達。事實上,在上述尼克爾斯(Nichols)案中這兩個標準都被提出過:法院一方面強調角色須被充分獨特地描述,另一方面又說如果角色僅是敘事的工具就不受版權保護。這意味著,如果角色沒有被充分獨特地描述,沒有成為被講述的故事,就可能僅是大眾角色。除有限的外部特征或客觀特征(如名字、出身等)外,角色只能以故事加以合理描述或塑造,所以在角色被故事描述的同時,故事亦被講述,兩標準具有內在的統一性。DC Comics案對此有充分說明:“獨特的角色”就是原創性的角色,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角色原型”或“大眾角色”,即不具有獨特個性或沒有被充分描述的角色,其本身亦不構成被講述的故事,而僅可能是講述故事的工具或棋子。相應地,作者只能針對其原創性的角色主張和享有版權,對于角色原型或大眾角色不可主張版權。
(二)判斷標準的適用
尼克爾斯(Nichols)案提出的“抽象測試法”是判斷思想與表達的基本方法。可利用該方法以及上述兩判斷標準分析金庸小說中的角色描述。在金庸多部作品中有“丐幫幫主”的角色,蕭峰、洪七公、黃蓉都曾做過,但作品對其余幾屆幫主并未充分描述,有些甚至只是簡單提及,此時該角色就可能僅屬敘事工具。針對丐幫幫主的角色,如果作者添加了其他經歷或特征,如“本非漢人”“武功高強”“被逼與漢人為敵”等,仍可能屬思想的范疇,而不構成表達,因為此時該角色仍沒有被充分描述,仍不具有獨特個性。當角色在松鶴樓匿名登場,丐幫幫主“喬峰”的形象瞬間引起讀者興趣。隨著故事展開,傳奇的情節越來越豐富,蕭峰早已不是角色原型或敘事工具,而逐漸成為金庸武俠世界最悲壯的豪俠人物。在其出場前就有“南慕容,北喬峰”的江湖傳言,在其身世逐漸披露后,“雖萬千人吾往矣”“燕云十八飛騎,奔騰如虎風煙舉”,胡漢恩仇的歷史舊怨最終由掃地僧了結。蕭峰“塞外牛羊空許約”,以一己身軀,“教單于折箭,六軍辟易”。在故事演進中,故事越來越豐富,矛盾越來越激化,蕭峰的形象被充分描述,使之具有鮮明個性,以至于提到蕭峰,一般讀者心目中就會涌現出豪杰乃至“天龍”形象。而作為角色名字“蕭峰”所代表的,不僅是其外表、性格及人物關系,更是他斷崖式的人生經歷及其悲歡、無奈與無助。蕭峰作為主角,在其行為與個性被充分描述的同時,故事亦隨之展開,角色與故事交織而構成作品的表達,使作品及其角色與故事皆有很高的原創性。
金庸作品的其他主角乃至較多配角也是如此,皆是在被充分描述的同時也構成相應的江湖敘事。角色被充分描述就會使角色的獨特個性得以塑造,而描述越充分,角色的獨特個性就越顯著。金庸無疑是塑造角色的頂尖高手,無論是持續兩部作品的郭靖或黃蓉,還是出場即隱去的人物如風清揚或掃地僧,其形象與特征皆躍然紙上。當然,金庸作品中的大眾角色也比比皆是,如杏子林中結打狗陣的丐幫弟子或黑木崖上歌功頌德的翩翩少年。這些大眾角色沒有更多的行為或特征,甚至沒有被提及名字,他們顯然只是敘事的棋子或工具,不可能屬于表達并享有版權保護。
質言之,作品對角色的獨特個性描述越充分,角色就越可能構成表達。無論是根據獨特個性被充分描述標準還是被講述的故事標準,金庸作品充分描述的眾多武俠角色,包括角色名字、性格特征、人物關系或江湖經歷,多屬具有獨特個性的角色,呈現較高的原創性,有其內在的生命力,斷非“抽象”所能概括,而應屬作品的表達并受到版權保護。無論在文學創作的意義上,還是在著作權法意義上,都顯然不能再把此等角色界定為“思想”的范疇。具有原創性并可能獲得版權保護的角色需滿足兩個條件,即“獨特的角色”和“被充分描述”,而“獨特的角色”是“被充分描述”的結果。因此可把二者合并為“被充分描述的獨特角色”。角色在被充分描述的同時,亦可構成“被講述的故事”。此時角色就可構成表達,獲得版權保護。進一步地,就角色的塑造與保護而言,角色的名字最重要,因為其所有的經歷與品質最終都會聚集在名字上。
“金庸訴江南案”的二審法院似乎也認可上述兩個標準的統一性。法院認為,當人物形象的各要素在作品中獲得充分而獨特的描述并由此成為故事內容時,或者說當人物形象的描述包括了外部形象特征和內在個性特征,且刻畫足夠充分、清晰、具體時,就可獲得版權保護,包括郭靖、黃蓉、喬峰等60多個角色的人物群像,無論人物名稱、性格特征或人物關系等都體現了原告的選擇與安排,可被認定為“已經充分描述、足夠具體到形成一個內部各元素存在強烈邏輯聯系的結構”,屬著作權法下的表達,可獲得版權保護。
四、角色的版權范疇界定與侵權判定
(一)本作品一般讀者
角色是否被充分獨特地描述或者是否構成被講述的故事,具體的判斷標準就是看該角色是否具有充分獨特的個性。在被不斷描述的過程中,角色一旦具有獨特的個性,就在作品中成為有生命力的主體,其行為也便構成故事,成為作品的表達。角色是否被充分描述為具有獨特的個性,或者是否構成被講述的故事,皆應在“作品”的框架下進行判斷,因為角色是在作品中被描述,也是在作品中擁有原始的生命力。這意味著,在具體的糾紛判定或裁決中,研究者或裁判者不應脫離該角色存在于其中的作品去判斷角色是否構成表達或僅屬抽象的思想,否則就可能缺乏判斷的語境。
如上所述,文學作品需要讀者的想象或代人才可完成作品的閱讀,而讀者的認知又具有多樣性,所謂每個讀者心目中都有一個哈姆雷特。然而,即便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他們仍是角色哈姆雷特,此即多樣性認知下的共通性或一致性。當然,讀者心目中的多樣性或一致性,皆有賴于作者對于角色獨特個性的充分描述。例如,金庸小說的讀者對于蕭峰、郭靖或黃蓉等角色的感受可能就沒有哈姆雷特般的多樣性,這也是金庸塑造角色能力的高超之處。
為減少不同讀者、研究者或裁判者的認知差異,本文主張,對于角色是否被充分描述為具有獨特的個性或構成被講述的故事以及被告作品是否借用了原告作品的角色,可引入“本作品一般讀者”作為相對客觀的判斷者。作為一種法律擬制,其可與專利法中的“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或商標法中的“(本商品)一般消費者”相對應。例如,對于金庸作品的角色是否被充分描述為具有獨特的個性或構成被講述的故事,須由金庸作品的一般讀者作為判斷主體,而非從未讀過金庸小說的人,甚至也不應是僅看過金庸影視劇而未讀過金庸小說的人,因為除了極少數例外,金庸影視劇的觀看效果可能不及對小說的閱讀,表演者也不可能準確呈現或全部呈現金庸小說對角色的刻畫。正如要讓從來不看瓊瑤劇或于正劇的人判斷于正的電視劇是否抄襲了瓊瑤的電視劇可能不知所云一樣,要判斷金庸小說對角色的描述,也只能是金庸小說的一般讀者。“本作品一般讀者”的引入旨在使判斷客觀化,可望有助于判斷角色是否構成作品的表達以及是否被借用。
(二)角色的版權范疇界定
依據著作權法,版權的范疇僅延及作品的獨創性部分,非作者獨創性的表達屬于公有領域,可為人們自由使用。文學角色的版權范疇當然亦須遵循著作權法的基本原則與規范,即作者就其角色所享有的版權僅延及角色的獨創性部分,不具獨創性的角色原型以及僅屬于思想范疇的概念或要素,不屬于作者版權的范疇。
對于金庸武俠世界燦若群星的武俠角色而言,除去真實歷史人物如丘處機、張三豐等外,其余多數是具有獨特個性的角色,基本屬作者原創。諸多角色的原創性不僅反映在姓名的獨特性方面(既有文化內涵又無造作之感),更體現在其各自的特征、人物關系以及傳奇的江湖經歷等方面。用上述標準來說,金庸小說的眾多角色的獨特個性在被充分描述的同時,亦構成被講述的故事,而角色與故事的結合構成獨具特色的金庸武俠世界敘事和金庸作品表達。如果研究者或裁判者認可版權保護須延及作品的原創性內容,那么符合邏輯的推論只能是版權保護可延及金庸武俠世界眾多被充分描述且具有獨特個性的角色。
從思想與表達二分法看,角色的版權保護也僅能覆蓋角色的原創性表達部分,不能延及角色內涵的思想。那么何為角色的表達或思想,就可借由抽象測試法予以理解。具體的角色如蕭峰及其故事顯然是作品不可或缺的實質內容,屬版權保護的表達。針對搭便車者在其作品中僅使用“蕭峰(喬峰)”的名字(以及相應的人物關系),而未使用與蕭峰相關的故事,不少研究者以及“金庸訴江南案”的一審法院認為其未使用金庸作品的表達。此種理解似乎沒有認識到角色的名字在角色塑造以及相應的故事講述中占據絕對中心的位置——如上所述,作品中所有關于蕭峰的品質、人物關系及其大是大非的江湖經歷的描述最終都匯集在名字之下,角色的名字相當于該角色描述的集合體,未經許可的使用當然屬于對原作品表達的使用。因此,即使周星馳為拍攝電影《功夫》而簡單使用“楊過”與“小龍女”的名字就須經過金庸許可且支付費用。
隨著角色內容不斷抽象,在某層次,角色就可能由表達成為思想,也不再受版權保護,當然此時它也可能不再是具有獨特個性的角色,而成為角色原型或大眾角色乃至抽象的概念。例如,當“蕭峰”的名字隱去(這是最關鍵的,否則不可能抽象化),角色逐漸抽象化,就可能成為“身世曾經成謎、身負胡漢恩仇、最終自絕身亡的契丹豪杰”,此時就可能成為思想而非表達,當然此時他也不再是《天龍八部》主角.而可能成為任何武俠小說乃至校園文學的角色原型,包括被告在內的作者當然可以使用。缺乏獨特個性的角色本身就處于公有領域,不屬于著作權范疇,如眾多丐幫弟子或黑木崖教眾。所以,也并非金庸作品中的任何事物都屬其權利范疇。如在《笑傲江湖》中出現的《葵花寶典》就難以成為版權或其他知識產權客體。“華山論劍”和“襄陽之戰”也僅是部分情節的概稱,其本身亦應屬公有領域。
角色姓名影響其在著作權法下的排他性例證,可包括《天龍八部》的“掃地僧”和《笑傲江湖》的“江南四友”。掃地僧可能是金庸武俠世界功夫最高的人物,若神龍乍現,且精通佛法,但卻沒有名字,只被作者稱為“掃地僧”。雖然在作品或文學的維度上,這更符合作者“無相”的本意,但在著作權法意義上,他所擁有的排他性不免受到影響。雖然皆屬世外高人,在作品中現身即隱身,但就其版權保護程度而言,角色“掃地僧”擁有的排他性應該不如“風清揚”。“江南四友”雖然皆由其江湖綽號加以指代也不免受到影響,以至于“金庸訴江南案”的一審法院都沒有注意到其中的“禿筆翁”亦由被告借用。這說明,角色姓名對于角色塑造具有重要意義,可獲得讀者最直接的認知。如果角色姓名有特別涵義,亦可增加其原創性,如具有沖盈對照涵義的“令狐沖”與“任盈盈”,具有遠山與高峰疊加涵義的“蕭遠山”與“蕭峰”。
(三)角色侵權判定
既然被充分描述的具有獨特個性的角色屬于作品的表達并享有版權,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認定他人是否侵犯角色版權。“瓊瑤訴于正案”雖然也涉及對角色的借鑒(至少沒有使用角色的名字),但更多是借用故事,對其構成侵權人們較少爭議。“金庸訴江南案”則主要借用角色,但人們對其是否構成侵權多有爭議。這主要是因為研究者或裁判者沒有認識到角色亦是作品的實質部分。甚至在有些情形下,角色比故事更重要,因為角色是故事的主體與支撐,而故事是角色的行為集合,讀者對于故事的感受或感悟可能匯集為對角色的認識與感受,并且這些認識與感受最終都匯集在角色名字中。由此而言,《此間的少年》直接借用或盜用數十個金庸小說的重要角色,要比《宮鎖連城》借用瓊瑤電視劇《梅花烙》的故事,所侵犯的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都要嚴重得多。在任何國家,無論其是否有版權制度,亦無論是基于道德還是法律,都似乎沒有作者敢以如此廣泛的方式大規模盜用他人多部作品的數十個主要角色。
無論如何,對于他人作品充分描述的具有獨特個性的角色的借用或盜用,可構成對他人作品表達的使用,從而侵犯他人的版權。“金庸訴江南案”的二審法院認為被告作品的絕大多數人物名稱皆來自原告小說,因此認定被告抄襲原告作品的人物名稱與形象的行為屬著作權法下的剽竊,侵犯了原告的版權,應承擔侵權責任,但卻沒有判決被告停止侵權,而是決定被告可通過支付版稅的方式繼續出版侵權作品。本文認為,二審法院較為準確地界定了被告的侵權性質,但未判決被告停止侵權值得商榷——法院真能夠保證被告作品繼續出版的社會收益能夠超越原告作品以及社會公眾所可能受到的消極影響嗎?
五、角色保護與同人作品
角色的版權保護通常涉及同人作品是否侵犯版權等問題。正如角色是否享有版權保護沒有當然的答案一樣,同人作品是否侵犯版權也沒有當然的答案,因為同人作品的創作既可能侵犯版權,也可能不侵權,需在個案中具體分析,并非同人作品就當然具有免責事由。
同人作品基本屬原作品的改編作品或演繹作品。基于同人作品與原作品的關系,本文認為,從作品的要素即角色與故事出發,可把同人作品分為“角色同人”“故事同人”“角色與故事同人”三類。角色同人是指在后作品延續使用一部或多部在先作品的角色(以及相關的角色特征與人物關系等),但基本不延續原有故事,《此間的少年》就是此類。故事同人基本延續或模仿在先作品的故事,但可能不會直接使用其角色或僅使用其中較少的角色,《宮鎖連城》近于此類。更為常見的類別是同時延續使用在先作品的角色與故事的同人作品,如對原作品的續寫或改寫。無論同人作品分幾種類型,它在著作權法下都不可能被特殊對待,而只能利用著作權法的基本原則與法律規范加以判斷。
具體而言,需看同人作品的創作是否涉及在先版權。如果不涉及,就可能屬自由創作或自由使用而不侵權。不涉及版權的情形既包括針對已超過版權保護期的作品的同人,也包括針對尚在版權保護期但卻不屬于版權保護范疇的作品元素的同人。如果涉及在先版權,則須進一步判斷是否屬合理使用,其中包括轉換性使用,如是亦可能不侵權,否則就可能侵權。例如,在涉及歌曲“The Pretty Woman”的糾紛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被告對于原告作品的使用屬于批評性質的轉換性使用,不構成侵權。在《飄>(Gone with the Wind)與《斯風已逝》(The Wind Done Gone)的糾紛案中,聯邦第十一巡回法院認為,后者對于前者的使用屬戲仿性質,因而不侵權。也有研究者認為《此間的少年》對于金庸作品角色名稱的借用具有轉化性使用特征,并認為美國聯邦法院把轉換性使用限于批評或評論目的實屬狹隘。這可能誤解了美國版權法下的轉換性使用標準或合理使用制度。
須防范在缺乏著作權法基礎的前提下將同人作品視為侵權例外。研究者使用了多種概念或理論,試圖論證《此間的少年》對于金庸小說眾多角色的使用為正當。如認為從作品中剝離的角色名稱、性格特征和角色關系難有獨創性,如果同人作品僅使用在先作品的角色而不使用其故事,就僅可能屬標識性使用,不侵犯版權。該觀點為“金庸訴江南案”一審法院所借鑒。類似的觀點認為這屬“空殼”式借用,雙方作品不存在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相似。還有研究者認為,被告作品是在不同場景使用金庸作品的人物,所以不能認為其利用了金庸作品的角色。如果確如研究者所稱在平行時空的同人作品不侵犯版權,那么他人是否亦可在虛構的“西夏大學”或“桃花島大學”再讓這些角色來次穿越?研究者不宜用其片面理解的著作權法去割裂文學世界,否則將不利于激勵文學藝術創作。
當然,無論“蕭峰”還是“郭靖”,其名字均非禁忌,亦非金庸的財產(構成其作品表達的角色名字才是)。后來者當然可以通過獨立創作的方式創作或使用“蕭峰”等角色的名字,但卻不可盜用金庸作品的表達。是否屬金庸作品的表達,其一般讀者當然可以容易判斷。當被告同時使用金庸作品數十個角色名字的時候,獨立創作的可能性就不再存在,唯一的解釋就是搭便車式地借用或盜用。后來者也當然可以通過戲仿等形式對金庸作品進行批評或評論,這是再創作者的自由與權利。只有互相尊重各自的權利,社會文化才可能得以持續創新與發展。
綜上,金庸小說構筑了絢麗多姿的武俠文化世界,讓“成年人的童話”有所寄托。《此間的少年》直接盜用金庸武俠世界各具獨特個性的角色名稱及人物關系等,意圖吸引讀者注意力,純屬為搭便車目的之抄襲或剽竊行為。被告最好別在借用他人作品栩栩如生的角色時覺著“好玩”,而在被訴時又主張這些角色屬于“思想”——角色不總是“思想”,還可以是著作權法保護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