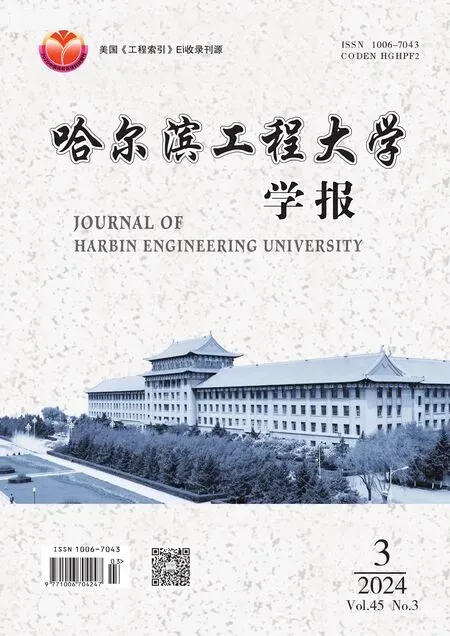并列切角方柱風致干擾效應的大渦模擬研究
李方慧, 張智博, 張特, 范佳紅, 尚靖淳
(黑龍江大學 建筑工程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隨著建筑物的密集程度增加,建筑間的干擾問題日益突出。此類問題導致建筑表面風壓分布變化,進而影響圍護結構的安全性甚至導致結構整體破壞。英國渡橋電廠下游冷卻塔破壞[1]和美國漢考克大樓圍護結構脫落[2]均由風干擾效應產生,可見對建筑間的風壓干擾效應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早期的風荷載研究主要基于單體建筑為研究對象[3-8],逐步擴展為多建筑間的干擾效應研究。Gu[9]對不同排列下建筑的風壓干擾效應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并列工況的放大效應尤其嚴重。謝壯寧[10]、朱劍波[11]、劉慕廣[12]、Mara[13]基于高頻測力天平風洞試驗,歸納2個高層建筑不同空間位置下的氣動干擾效應,并總結出建筑干擾包絡圖與干擾因子規律曲線。Yu等[14-16]系統對比了2棟不同高度的高層建筑間的扭轉干擾效應和加速度干擾效應,發現高度比為1.0和1.5時,受擾建筑的基底彎矩增大作用最顯著。Hui[17-18]分析了方形建筑與矩形建筑(長寬比為3)間的干擾效應,結果顯示方形建筑的平均和脈動扭矩可分別達到單體狀態的3倍和1.6倍,建筑角部的最小極值壓力比單體方柱高40%。Yan[19-20]采用計算流體力(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數值模擬方法,對城市中心高層雙塔間的風荷載、風致振動和氣動干擾效應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基于剛度映射算法的高層建筑風效應及舒適度評估分析框架。
針對方形與矩形建筑間的干擾效應,國內外學者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對切角截面建筑考慮較少,而實際工程中,切角處理的建筑并不少見。文獻[21]表明,切角能夠大幅改善結構的氣動性能。當切角率為10%時,建筑橫風向和順風向的風致位移響應能減少35%左右[22-23]。采用切角處理的建筑周圍分離渦的數量、形態及其尺寸均發生了明顯改變[24],進一步導致建筑間的氣動干擾效應和風壓干擾效應存在差異[25-27]。基于此,本文采用大渦模擬方法,對均勻流場下的三維方柱進行網格收斂性分析和模擬方法的驗證,并基于切角方柱的氣動力系數與風壓分布特征,分析不同間距下并列雙切角方柱的氣動力系數變化特點和干擾因子分布規律。
1 大渦模擬及數據處理方法
1.1 大渦模擬
在結構抗風研究中,流體被視為黏性不可壓縮,假定過濾過程和求導過程可以互換,將N-S方程做過濾,得到大渦模擬的控制方程為:
(1)
(2)

本文采用Dynamic Smagorinsky亞格子模型:
(3)

1.2 計算域及網格劃分
計算域及模型尺寸見圖1,方柱邊長為L=0.1 m,豎向高度為4L,切角對應直角邊長D=λL,λ=0.1。計算域大小為40L(流向x)×(20L+B)(展向y)×4L(豎向z),B為兩方柱中心間距。網格采用非均勻結構化網格,采用加密處理的近壁面網格如圖2所示,最小網格高度為5×10-4L,網格總數控制在150萬~200萬。計算域邊界條件如圖3所示,入口為速度入口(velocity-inlet),采用風速為U0的均勻來流;出口為壓力出口(pressure-outlet);上、下表面以及兩側面均采用對稱邊界條件(symmetry)模擬自由滑移壁面;方柱表面采用無滑移壁面(wall)。壓力速度耦合采用SIMPLEC法求解,動量方程采用二階精度的離散格式。

圖1 計算域尺寸Fig.1 Computational domain size

圖2 近壁面網格劃分Fig.2 Near-wall mesh generation

圖3 計算域網格及邊界條件Fig.3 Computational domain grid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1.3 數據處理方法
為了便于結果對比,對文中出現的表面風壓、升力和阻力均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4)
(5)
(6)

采用峰值因子法估算各測點的極值風壓系數:
(7)
式中:σp為測點風壓系數的標準差;g為峰值因子。
對于峰值因子的取值,在GB 50009-2012《建筑結構荷載規范》中,假設結構滿足高斯分布,建議g取2.5,置信率可達99.38%。但實際上,結構存在非高斯區域,在滿足規范所要求的保證率下,峰值因子取值會增大。本文采用觀察極值法和全概率迭代法結合計算峰值因子,置信率為99.50%。
為了更直觀地表示方柱間的干擾效應,根據風壓分布情況將方柱每個立面分為9個區域,切角從A~D編號,如圖4所示。采用各區域測點極值風壓系數的最大值作為各區域的極值風壓系數,引入塊干擾因子BIF0來描述方柱的干擾大小:

圖4 測點布置與立面分塊Fig.4 Sketch of tapping location and blocking region of facade
(8)

考慮到由于切角測點分布較少,采用BIF0并不能準確的描述角部干擾的分布規律,進一步采用測點風壓系數干擾因子IF0進行分析:
(9)

2 網格收斂性分析與結果驗證


表1 網格收斂性分析與結果對比Table 1 Analysis of grid convergence and comparison of results
為了進一步驗證Case3網格的精確性,對比Case3模擬結果與文獻[7-8]結果的平均風壓系數(圖5)和脈動風壓系數(圖6)曲線,模擬結果與文獻結果的2種曲線吻合。

圖5 平均風壓系數比較Fig.5 Comparison of average wind pressure coefficients

圖6 脈動風壓系數比較Fig.6 Comparison of fluctuating wind pressure coefficients
數值模擬的平均風壓系數與文獻值最大偏差不超過3%,對于脈動風壓系數來說,本文對迎風面和背風面的模擬結果與文獻結果相差不超過5%,但方柱側立面的模擬結果平均值與文獻[8]試驗值相比大13%,產生這些差距的原因是因為數值模擬是在理想條件下進行的分析,而在試驗過程中,會有影響試驗結果的因素,如模型縮尺比、入流風場的精度等。綜合上述的對比結果,整體的大渦模擬結果能夠比較精確地反應方柱的各項氣動力數值和風壓結果,表明本文的網格模型與參數取值具有良好的精確性和可靠性。
3 干擾效應的結果與討論
3.1 氣動干擾效應
圖7給出了方柱1和方柱2的氣動力系數隨間距比的變化曲線,由圖7可見:

圖7 氣動力系數隨間距比的變化曲線Fig.7 Aerodynamic coefficients vary with spacing ratio
1)當1.2≤B/L<2.5時,兩方柱的平均阻力系數無規律波動且數值相差較大,說明此時流場仍然處于偏流狀態。B/L=1.5時,兩方柱系數差值最大,達到18%,間距比接近2.5時,系數趨于單體值。當2.5≤B/L≤8.0時,兩方柱的平均阻力系數基本相同,與單方柱的值相比偏離程度不超過2%。
2)當1.2≤B/L<2.5時,兩方柱的脈動升力系數逐漸增大并趨近于單方柱的值,脈動升力系數表現為減小效應。當2.5≤B/L<6.0時,兩方柱的脈動升力系數先減小后增大,最小值為0.22,出現在B/L=4.0處,脈動升力系數依然為減小效應。當6.0≤B/L≤8.0時,雙方柱脈動升力系數趨近于單方柱的值,最大誤差為3%。總體來看,兩方柱的脈動升力系數相差很小,變化規律一致。
3.2 流場分布
為了更直觀地分析流場分布特點,圖8給出了典型間距比下雙切角方柱的流場分布圖。當B/L=1.2時,2個切角方柱后壁面各出現一個貼近壁面的小尺度渦,尾流通過間隙形成一個大尺度渦,旋渦脫落后隨尾流逐漸消失,小尺度渦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切角的存在使剪切流變窄,剪切流遇到大尺度渦后產生回流,使渦旋更貼近壁面,此時處于偏流狀態。當B/L=1.5時,后流場大尺度渦消失,轉變為小尺度渦的脫落,流場中可以明顯觀察到小尺度渦有融合為大尺度渦的趨勢,流場向穩態轉變。當B/L≥2.0時,尾流狀態轉為對稱渦,2個方柱的后流場互相干擾減小。

圖8 不同間距下流場分布Fig.8 Flow field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spacing
3.3 并列切角方柱的風壓干擾效應
由于并列雙切角方柱沿流向的對稱性,將方柱1考慮為施擾建筑,方柱2為受擾建筑,方柱1與方柱2間的位置關系見圖1。
3.3.1 相鄰立面(左立面)
方柱2的左立面即施擾建筑的相鄰立面,左立面隨距離的干擾因子(IF0)分布如圖9和圖10所示。當B/L=1.2時,左立面平均風壓IF0值和極值風壓IF0值最大分別為1.01和0.73,整體表現為減小效應,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切角的存在,增強了流體再附性,流體再附導致立面受到的風壓力變大,進而減弱了立面的負風壓(表現為風吸力),最終表現出減小效應。當B/L=1.5時,由于間距比的增加,流場干擾能力下降,切角的流體再附效果減弱,干擾效應呈明顯的放大效應,此時平均風壓IF0取最大值為3.31,極值風壓IF0最大值為2.39。當1.5≤B/L<6.0時,平均風壓IF0值呈現明顯的規律分布,從立面迎風側(立面右側)到背風側(立面左側),干擾因子逐漸減小,極值風壓IF0值規律與平均風壓IF0值規律相似,各間距比下IF0最大值均位于立面迎風側。當6.0≤B/L≤8.0時,平均風壓IF0值與極值風壓IF0值緩慢減小,當B/L=8.0時,兩切角方柱相鄰立面仍然存在28%的放大干擾效應。

圖9 左立面平均風壓系數干擾因子Fig.9 IF0 contours for average wind pressure coefficients

圖10 左立面極值風壓系數干擾因子分布Fig.10 IF0 contours for extreme wind pressure coefficients
3.3.2 右立面、迎風面和背風面
對于方柱的其他立面,采用塊干擾因子(BIF0)描述立面不同區域的干擾大小,圖11給出了3個立面不同間距下塊干擾因子的分布情況。當B/L=1.2時,迎風面BIF0值分塊變化,左側編號為1、4、7的區域表現為放大效應,位于1號區域,放大效應最大為45%,右側3、6區域與背風面和右立面均表現為減小效應,其中右立面BIF0值最小,僅為0.74。當B/L=1.5時,3個立面的干擾效應均達到峰值,其中迎風面與背風面靠近左立面(相鄰立面)的一側BIF0值最大,均達到2.00以上。當B/L≥2.5時,各區域BIF0值變化幅度較小,并逐漸趨近于1。


圖11 各立面塊干擾因子分布Fig.11 BIF0 contours of windward facade, leeward facade
3.3.3 切角
基于方柱各立面的干擾結果,相鄰立面與迎風面和背風面的相臨側干擾效應更明顯,因此對位于兩方柱相鄰側上的切角C和切角D的干擾效應進行研究,圖12為兩切角的極值風壓IF0值隨高度(標高見圖4)的分布結果。當B/L=1.2時,2個切角表現為明顯的減小效應,切角D干擾因子為負,與單體切角方柱相比,此處由風吸力轉變為風壓力,這是由于2個方柱距離過近,風在進入峽谷(兩方柱間的縫隙)時相互作用,產生風壓力,改變了切角處的受力情況。這也解釋了迎風面相鄰側的放大效應產生原因。當B/L=1.5時,前流場處的切角D仍然表現減小效應,但干擾因子由負變正,說明此時兩方柱的相互作用減弱,相互作用產生的風壓力并不足以抵消風吸力,因此表現為正值減小效應,隨著后續距離的增加,這種相互作用逐漸消失。后流場切角C表現為明顯的放大效應,干擾因子最大值為2.58,出現在切角頂部區域。當B/L≥4.0時,干擾因子隨間距的增大不再變化,切角處的干擾逐漸消失。

圖12 不同標高下切角干擾因子分布Fig.12 IF0 on chamfered corners at different elevations
4 結論
1) 并列方柱的氣動干擾效應對切角的變化很敏感。與標準方柱相比,切角方柱的氣動力系數有顯著減小。當1.5≤B/L<2.5時,兩方柱的平均阻力系數呈放大效應,脈動升力系數呈減小效應。當2.5≤B/L≤8.0時,兩方柱的平均阻力系數與單體值偏離幅度不超過2%,脈動升力系數先減小后增大,B/L=4.0時取最小值為0.22。
2) 切角會改變小間距并列方柱的風壓干擾效應。當B/L=1.2時,由于風在峽谷入口壁面處相互作用,產生了風壓力,風壓力與建筑各立面和切角受力疊加,迎風面相鄰側正壓疊加表現為放大效應,其余立面與切角均為減小效應,其中切角D干擾因子為負值,表現為風壓力。由于本文在切角處的測點布置不夠多,所以切角處風壓變化情況以及變化機理仍然有待進一步試驗研究。
3) 切角產生的干擾效應在相鄰壁面影響更廣,當B/L=1.5時,受擾方柱的干擾因子取得最大值2.58,位于相鄰側后流場的切角C上。當B/L≥4.0時,除左立面外的其他立面與切角的干擾效應趨于消失,左立面仍然存在較大的干擾效應。當B/L=8.0時,兩方柱相鄰立面仍然存在28%的干擾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