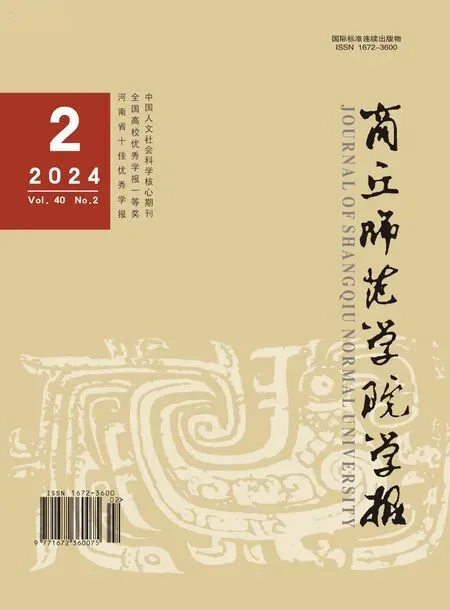隱喻認知視域下《老子》中的“象”
張 弓 也
(蘭州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730013)
隱喻認知依據喬治·萊考夫和馬克·約翰遜的理論劃分為本體隱喻(ontological metaphor)、結構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和方位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1]7—29。當今對《老子》的研究中也有學者引入了這種方法,如林國敬[2]、毛春洲[3]等,已經證明了該方法的可行性。但由于語言差異以及思維核心的差異,根植于西方思維的隱喻認知在分析典籍原文時往往會產生新的焦點,在超越傳統解讀的同時難以進行宏觀上的把握,或對于原有的概念產生新的解釋與老子原意相差較大,因此使用隱喻認知分析《老子》需要我們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重新構筑自己的認知思維。有學者指出中國傳統思維模式應該集中于“象”,故而提出意象思維,其定義為:“在徹底開放而不破壞事物所呈現象之自然整體性的前提下,對事物進行概括,探索事物整體規律的思維。”[4]63或者:“思維主體將物象或擬象(符號、概念、模型等)作為思維工具,運用直覺、比喻、象征、聯想、類推、頓悟等方法,來表達對世界認識的一種思維方式。”[5]18若以“象”取代“隱喻”并為其賦予更加豐富的內涵,或可以更近一步地理解《老子》。解讀《老子》的一大難題在于語言,王樹人指出,傳統典籍不僅具有豐富的原創哲思,更有一種“詩化”的語言表達,這種表達方式是超越文字與感覺的,西方哲思從胡塞爾到梅洛也遵從著這一過程[6]。這種思路發展至隱喻認知,幾乎逼近語言表達的極限,是故隱喻認知代表著認知學在語言層面高峰之一。故本文借用隱喻認知的分類方法,將《老子》中的“象”分別與本體隱喻、結構隱喻以及方位隱喻進行對比歸類,考慮到胡壯麟已然指出萊考夫等人所建立的隱喻認知體系有所局限[7]85—100,且中國傳統文化其根系在于對“時間”的把握,因此還應在“空間”層面加入“過程”,力求進一步理解《老子》中出現的概念及其對“道”的分析。
一、本體隱喻中的“象”:對本體的不同表述途徑
“隱喻”原本屬于修辭方法,在認知學發展的過程中,前代學者敏銳地察覺到人們在表述、理解的過程中不自覺地用一件熟悉的事物來描述另一件不熟悉的事物,故將這一過程命名為隱喻認知。值得注意的是,隱喻認知作為認知過程而言并不完整。換句話說,隱喻認知必須建立在“已知”的基礎之上,這種“已知”可以是對以往熟悉事物的感官經驗,也可以是邏輯推導的思想經驗。但顯然隱喻認知跳過了收集信息的步驟,如視聽觸覺亦或是宗教中的超人體悟,這就導致了隱喻認知的局限性。其次,在個體面對一個無法找到相似物的新事物時是無法通過隱喻認知的手段來進行理解的。《老子》中的“象”卻根于體悟,這是必須注意的。更進一步說,部分“象”從本質上更改了認知渠道,將感受與體悟發展到極限,即《老子》中所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8]134“虛極”“靜篤”即人作為個體的一種極限狀態,“觀”即為此刻的認知渠道,通過這種“虛靜”的極限狀態去閱讀宇宙本質。
本體隱喻本身僅是語言層面的表達,語言可以包括圖像、文字甚至是行為,但“表達”并不是針對“本體”所進行的探索,其本質是利用離散的物體或物質來解構人們的經驗,并對被解構的經驗進行指稱、范疇化、量化,再以邏輯推理作為串聯而完成的。本體隱喻其形式為通過包含“本體”的語言,以隱喻的手段讓接受者理解“本體”當前的狀態,如:“一番話打開了我的心門。”以“打開門”這一動作進行隱喻,描述主體“我”在情緒、精神方面的變化,使人更加清晰地理解主體“我”的狀態。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本體隱喻是對于“人”這一概念的充分理解。這似乎與世界本質有一定的差距,但本體隱喻作為方法論,在以海德格爾至伽達默爾發展出的語言世界中進行運用時,“世界”即是“本體”,所有的經驗都將對其進行描述,通過對經驗的梳理使“世界”的規律清晰化,從而達到接近真理的目的。“人”與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具有同一性,如海德格爾所說:“人(此在)在本質上總是它的可能性,所以這個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選擇’自己本身,獲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說絕非獲得自身而只是‘貌似’獲得自身。”[9]49“人”是“此在”(dasein)的,這是海德格爾對于“本體”的批判,更是一種超越,在其設計之中“本體”將無法把“人”排出,甚至在歷史的跨度中與“人”合為一體。這種思路顯然受到了約克的影響,用其原話表述則更為直觀:“對自身的思考并不指向一個抽象的我而是指向我自身的全幅;這種思考發現我是從歷史學上規定的,正如物理學認識到我是從宇宙論上規定的。我是歷史,一如我是自然的。”[9]453也正是在這種表達之中,本體隱喻超越了靜態的空間,在時間中獲得表達。
而在本體隱喻視域下,《老子》所構建的“象”是認知過程中的重要部分。主體通過感覺與體悟進行“取象”,之后通過對獲得的經驗進行抽象化,從而獲得某一“象”,如《老子》中不斷強調的“道”。在認知的過程中,對于宇宙本質的探求是無法回避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本體隱喻以“象”的形式得以發展。其特點為:首先,作為本體的映射,其目的在于反映本體的全部特征而非某一部分的特征;其次,本體隱喻以語言進行表達,但所構成 “象”的內涵是基于時間的,因此其表達的其實是一個事物及其永恒運動的狀態。而書中作為本體隱喻下的“象”,“道”這一概念往往被看成是自然存在的某種實體[10]。隱喻認知與傳統文化所表達的內涵仍有些許的差別,如前文所言,最為明顯的是概念獲取的路徑。
以隱喻認知而言,“本體”必須作為論述的內容,必須在語言中展現出來。“道”之本意為大地上的道路,而在《老子》中引申為具有不同層次的本體,按照陳鼓應的論述,至少具備“構成世界的本體”“世界運動的動力”“世界運動的規律”“人類社會的規律”[11]2—13四重含義,對應的隱喻表達也有相應的變化。在作為“世界本體”的“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描述為第四章:“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8]90在本章之中,老子全力勾畫出具有虛空、深邃、幽微、源頭四個特性的“道體”。原文“道沖”一句中“沖”古字為“盅”,訓虛。《說文》也強調“盅,器虛也”[12]212,即點名“道體”虛空的狀態,而這種描述由于其僅具備形容詞性的意味,無法直觀,故在第五章用“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8]93進行再次說明。“橐龠”即為風箱,通過抽取現實生活中可見之物的特性,同時說明“道體”的空虛以及在虛空狀態下的“道”本身的運動。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顯,當“橐龠”確定了以后,對于具體實在之物的探求必然涉及個體經驗,老工匠與年輕學徒對于“橐龠”的理解一定大不相同,這種不同這將導致個體在理解“道”時產生差別。同時,隱喻認知因使用個體熟悉的事物代替不熟悉的事物,使得個體在認知過程中逐漸產生已經掌握未知事物的偏差感而不能自知,最終導致認知的偏差。如《莊子》中論述的“庖丁解牛”一事,庖丁認為其所應用的為“道”而非技術,并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詳細描述。而結合《知北游》一篇中黃帝所言“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13]185之語,可見庖丁并不能稱為真正的得“道”者,楊立華在其書中同樣指出《莊子》之中“無言者”才是至德者[14]2。
老子通過對于宇宙的認知而提出“道”這一“象”,與一般的隱喻認知結構相比,沒有“喻體”的參與,而是轉化成了一種體悟與理解,即原文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8]73之語。從此處分離出傳統典籍無法用隱喻認知解讀的第一個局限,即對文字的處理。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到東方的老子,都承認語言的局限性,認為通過語言完全表述某件事物是不可能的。同時,人是有限的,因此不需要去理解完全無限的世界,而是在“人”的水平上達到自身的極限即可。即《莊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13]28對于“人”而言,其極限是具有多個方面的,隱喻認知所追求的正是語言表達的極限。《老子》不同,它體現著中國傳統哲學中所認識到宇宙的無限性和對語言束縛性的超越。
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言: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15]571
本段的核心在于論述“言”“象”“意”三者的關系,王弼強調“言”的作用就是對“象”進行形容,而“言”與“象”的最終目的是“意”。這也就意味著不能拋棄“言”或者“象”,亦不能執著于“言”或者“象”的形式,想要充分理解“意”,那么超越“言”與“象”都是必然的。雖然本段以《周易》為論述對象,但實際上《老子》同樣是“意”產生“象”,再通過“象”產生“言”,因此也同樣適用。前文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也正是如此,“道”字是否指“道路”此時已不再重要,它的“象”已經變成了世界本質與規律的映射,而拋開映射的形式剩下的即為“道”背后的“意”。如此一來,整部《老子》對于“道”的描述從“感受”開始而終于“文字”,而讀者由“文字”開始直抵“體悟”,最大限度地跨越了文字的影響,這是隱喻認知所不能達到的,只有在此基礎上將“道”作為“象”來考慮方能有如此結果。
二、結構隱喻中的“象”:不同領域中的相通之處
所謂結構隱喻,即在認知過程中以具體結構形容抽象結構,而結構便意味著事物中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組成,如醫學中的“君臣佐使”正是將方劑的藥物結構比附為國家的政權結構,又如描述辯論賽的輸家“潰不成軍”,正是借助了戰爭的結構取代辯論本身的結構。結構隱喻可以解讀《老子》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描述本體的“象”與描述時間的“象”通過結構隱喻在語言中得以表達,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名詞性的如“水”等實體結構,與結構隱喻有著高度一致性。在《老子》中,“水”涵蓋了老子對于宇宙、社會以及個人修養等不同層面的表達,如第四章中的“沖”“淵”“湛”最初都被用來形容“水”的特性[3]。“沖”原寫作“沖”,合并“沖”和“衝”。“沖,從水從中”[12]547,本義為水流搖晃沖刷,《說文》“沖,涌搖也”[12]547,引申為沖虛、沖和等,用于形容水上下翻涌和左右蕩漾之狀。“淵,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皃。淵,淵或省水。”[12]550后引申出“深”意,此處指“道”的深邃玄妙。“湛,沒也。從水甚聲。”[12]556其本意為清澈透明,此處用于描述“道”幽隱不顯的樣子。“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8]102“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8]308“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8]339這幾句可以看作是個人修養與治國理政的最高要求,即要求個體在日常處事之中或者國家在外交關系中要謙和、寬厚、不爭以及守靜。在“水”的隱喻解讀中,老子之“道”具有了濃重的向下、向內的意味。這對于個體以及國家而言,只是存在于理想環境中的理想狀態而非現實。同時,“水”體現“道”的三個特性為“利萬物”“不爭”“處眾人之所惡”。作為本體的“道”是否可以“處眾人之所惡”呢?并非如此。“所惡”并非指嫌惡具體環境,而是指想要立即擺脫的階段,“水”居于下是為了更好的積蓄力量,而“利萬物”作為“水”之本性需要在力量達到一定程度才能體現。《莊子》有言“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13]2,滴水難以發揮潤澤功能。而后文中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若以“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來解釋,則將“不能勝”的原因歸結于“柔弱”,表面上似乎符合道家守柔守靜的傳統,但所表達的情感過于消極,更與后文中“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相矛盾。若以“柔弱”為積蓄之表現,則“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是最終結果。
《老子》中某些結構隱喻的“象”具有形容詞的特性,如“自然”“樸”等,因其并不具備實體,結構隱喻難以直接對其進行分析,只能通過其他類似的“過程”進行理解。
“自然”是《老子》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書中具有不同的內涵,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作為宇宙的本體、作為個體所處的環境以及自然而然的狀態。“自然”一詞既可以當作具有實體的名詞指代,又可以看作沒有實體的形容。其名詞性的表達如原文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8]164此處之“自然”指的正是自然界本身,如以結構隱喻來進行分析,則“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一句以風雨的狀態來對比人事的變遷,對自然界賦予人格,“飄風”和“驟雨”成為“自然”有目的性的去完成的某種活動,那么依據邏輯進行判斷,則人事與風雨同樣不可長久。將人與風雨同構化在某種程度上回避了兩者的差異,但究其實質,人與自然只能相通而不能相同。以“象”觀之,則自然、風雨以及天地都為具體的“象”并且具有其獨特內涵,明確不同事物的獨立性,“自然”作為動因推動整個世界從風雨至無風無雨,而個體在“自然”的推動下隨之運動,故以“而況于人乎”進行總結。與結構隱喻相比,《老子》更加在意事物的過程和運動。凸顯出過程的重要性,是老子描述“道”時更加常見的手段。其形容詞性的表達如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8]169
上文中“自然”并不存在一個具體實指,而是僅僅用于形容“道”的特性。這種情況下強行使用結構隱喻去統一“自然”的含義,則會導致額外出現一個“自然”喻體,但又缺少對這一喻體的解釋與定義,最終陷入迷惑。因此在《老子》之中,“自然”必須作為一個獨特的符號來對待。它同時含有名詞性與形容詞性,并且同時指代外界的環境以及“自然而然”這一屬性。這雖然部分程度上復雜化了“自然”一詞,增加了其理解的難度,但只有這樣才能充分打破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屏障,將流動性賦予“自然”,才能使其逐漸進入個體的實際生活。
老子對于“樸”非常重視,常用作“圣人”的人格追求[16]或者“道”的美好特性。如形容古時行道之士的“敦兮其若樸”[8]129,又如第十九章的“見素抱樸,少思寡欲,絕學無憂”[8]147。“樸”本義指沒有雕琢的木材,此處引申為一種質樸的品性,具體而言是主體行為和心態上的清靜無為。而通過這種純粹、厚重的品質,進一步引申出“樸”的豐富內涵。作為“道”的代名詞,“樸”代表完整無缺的自然的本體存在。第二十八章:“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圣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8]183從“人”的維度來看,只有做到“知其榮,守其辱”,才能夠“為天下谷”;如是,“常德乃足,復歸于樸”[17]。本句使用三段描述來形容“道”的特性,首先從個體層面說明了具體的行為要求;第二層由“行為”上升至“德行”,這是個人層面的升華;第三層將充足飽滿的“德行”回歸于“樸”,此時不能再簡單地以“樸實”來理解,而應該認為“樸”表達著一切事物的自然狀態,雖然在此時“樸”與“道”的界限仍然存在,但是對于個體來說,它們不再是分離的事物。在這種情況下“樸”與“道”之間就體現為有形與無形、外在與內在、形而下與形而上的融合與轉化[18]。而在第三十二章的“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8]198之中,以王弼本的句讀方法來解釋,則“樸雖小”作為一個整體對“道”形容,“樸”很細微卻沒有人能夠使其臣服。“樸”成為獨立的個體。故應按陳鼓應的說法,將之句讀為“道常無名、樸”,將“無名”與“樸”進行并列同作為“道”的特性。“道”作為“雖小,天下莫能臣”的主語,這樣文意順暢,也不會增加另外的實體[8]198。在第三十七章中:“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8]212老子以“無名之樸”對“道”進行代替,這將使個體達到“不欲”的境界,而最終達到“安定”的狀態。萬物有名,因名而顯,樸卻是無名,無名是最素樸的狀態。以樸指道,而不直言道,其效果是將道的無名突顯出來[19]。這說明“樸”反映的是“道”由形而上的抽象意蘊向下進行落實的結果,直接落實在個體身上即為對事物本然狀態的追求,不輕易的去雕琢或改變事物的本色,也就不再對自己進行矯揉造作的裝飾,消解人為的一切雕飾和社會習性。如此一來,自然就可以達到“不欲”的狀態,當具體的行動達到了此種狀態,則精神境界就多了上升至“靜”的可能性。如此觀之,“樸”不僅是老子對于個體理想人格的期望,更是個體與“道”相合的起始點,這樣就將個體的“修行”之路不斷地深化與延伸,并且使每一階段都有了確定的目標,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在面對名詞性的概念如“水”時,結構隱喻通過借用已知事物的“結構”,對未知的“道”作進一步的解釋;但在面對如“自然”“樸”此類形容詞性的概念時,隱喻認知則有較大的限制。但將“自然”“樸”等作為“象”來看待并用結構隱喻的思路加以分析,則可以超越具體結構的限制,使解讀者充分理解其含義。
三、方位隱喻的“象”及其局限:空間與時間的不同
在概念隱喻中,一部分始源域的內容來自于人體本身,當個體通過“具身性”[20]將環境產生的影響轉化為一種邏輯上的概念之后,認知過程就完成了。對于方位隱喻而言,其本質是將人體所感受到的上下、內外、前后、左右等空間方位代入抽象的理解之中,這些概念源自身體,故不會因文化的差別而發生變化,《老子》之中同樣如此,如“上善若水”,老子之本意在于強調“水”所具有的“德行”,但并沒有使用一般意義上的褒義詞,而是采用了方位詞“上”。依照隱喻理論,個體常常因“上”相關的動作如抬頭、起身、登山等建立優勢,并在思維中逐漸將其與倫理概念結合,因此產生抽象概念的價值評判,在文中即對于“水”之“德行”產生的近似高山仰止的理解。與之相對的如第三章中:“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8]121此處“下”同樣不再作為方位的表達,而是作為對于“寵”這一情況的評價。而與“上”“下”相比,“左”“右”“內”“外”其具身性較低,與文化的整體影響關系較大,如《老子》第三十一章“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以及后文“吉事尚左,兇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8]195所表達的含義即為以君子之德行而論,日常生活以“左”為尊貴而軍事活動中則以“右”為尊貴,其原因在于在“吉事”中“左”是尊貴的,而“兇事”中“右”為尊貴,軍事活動屬于“兇事”,故使用了與日常相反的標準。但對比當時的歷史則又有所不同,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 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21]2443依照前文觀之,藺、廉二人之官位問題當不屬于“兇”事,但仍以“右”為尊。對于此種問題,學界觀點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其一為“左”“右”的尊卑受到陰陽哲學的影響,發生著頻繁的變化[22];其二為“尊左”“尊右”觀念錯雜流行,后發展為普遍流行的“尊右”觀念[23];其三為“尊左”“尊右”在歷史中并存,因其應用的環境不同表現也不同[24]。這一點對于我們討論隱喻認知極為關鍵,之所以形成這種狀況,是因為傳統社會有著復雜的政治、環境、民俗習慣等,僅僅以具身性來概括,則不足以完全反映先秦時期的實際情況。《老子》一書中的相似問題則并不能完全以方位隱喻進行討論,原因在于,書中的“象”針對的不僅是空間關系,更是包含主體在內的宏觀變化,故《老子》更加重視“過程”。當要對本體的運動或者演化進行描述時,語言難以全方位地表達其內容,因此借用日常的某些經驗。如《老子》全書中涉及的三個非常重要的“象”:誕生于“道”形成過程中的“生”與“反”,“人”追求“道”的過程中產生的“觀”。如果說以“道”為主體的“生”是從形而上向形而下的落實,那么以人為主體的“觀”則是從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超越,兩者相互呼應,過程為“反”。若以隱喻認知來進行分析,則無法找到相應的始源域對其進行映射,也就無法充分展示其內涵。
對比方位隱喻的應用與《老子》的表達,可以發現中西方思維的巨大差異。以隱喻認知而言,無論是始源域還是目標域,其討論的始終是靜止之物,并在整個思維過程中,不斷嘗試將其從空間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存在。這種方式確實使得所關注的問題更加具體與突出,但同樣正是因為這種獨立性,使得事物與主體之間的聯系減弱甚至斷裂。而在《老子》一書中,多將一個完整的過程歸納為某種“象”,時間的發展是其基礎。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結果的重要性,但增強了事物之間的聯系,甚至可以說,正是通過這些事物之間的聯系充分地反映了背后的本質規律。
四、結語
在《老子》的解讀中,隱喻認知已經成為較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但并不能完全適用。借由喬治·萊考夫和馬克·約翰遜所建立的隱喻認知學分類體系,將《老子》一書在本體隱喻、結構隱喻與方位隱喻三個層面進行解讀。通過具體內容可以發現,本體隱喻本身并不是針對宇宙本質的討論,但在“語言世界”中作為一條探知真理的途徑是非常恰當的,而《老子》中作為宇宙本質的“道”,相對于本體隱喻而言具有更加明確的目的性。對于結構隱喻而言,在名詞性的概念如“水”之中,可以獲得良好的理解效果,但在面對如“自然”“樸”此類形容詞性的概念時,隱喻認知卻難以做到完全的解構,必須借助概念的實體來進行表達,從而淡化了同一概念前后出現的程度和層次。對于方位隱喻而言,因其基于空間產生,能夠將所研究的事物剝離而得到更加清晰具體的結果,但《老子》中許多概念基于時間產生,因此“過程”同樣重要。以“象”而言,通過本體隱喻所認識的“道”難以用語言加以具體描述,故需要借助“結構”或“方位”如“水”“自然”“上”“下”等來間接理解。“結構”賦予“道”框架,“方位”賦予“道”性質,二者被“過程”所串聯,從而將“道”轉變為具體的圖式,有利于對“道”的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