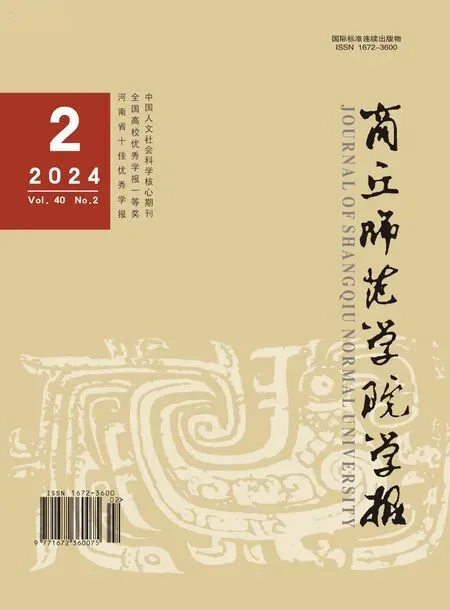天授者何?章學誠的神秘體驗與性情論闡發
王 際 灃
(山東大學 儒學高等研究院,山東 濟南 260100)
章學誠所處時期是乾嘉考據學的鼎盛時期。乾嘉考據學被民國學者視為一種最接近科學的研究方法,但由于其過度傾向于科學的客觀實證主義,以至于削弱了學者本人在研究中的直覺的發揮,導致學者為考據所役,異化為考據工具。在這一背景下,章學誠力倡性情論,希望在為學之中抒發學者個人的性情,以重立學者本身的主體性,還學者以“人”的尊嚴,體現出從“智識主義”向“人本主義”的轉變。
對于章學誠的性情論的研究,早期有錢穆發其緒,認為章學誠以性情與考據學風氣相抗衡,來闡發經世致用之學[1]441—445。余英時以柯林武德與章學誠作比較研究,指出其思想中的相似之處,認為章學誠繼承并發揮了中國史學傳統中的人文精神,重視學人的思想性[2]234—282。章益國將章學誠的“史德”說從客觀主義的解釋中解放出來,認為“史德”并非單純指歷史學家的求實精神,而是立足于“個人知識”層面,恰與客觀主義相對[3]。以上研究均注重章學誠的性情論,并以西方歷史學與之作對比研究,以更好地闡述章氏學問。但其中仍遺存兩個問題,一是章學誠通過怎樣的論述方式將主觀的性情提升到與客觀的考據足以相提并論的地位?二是性情一詞一直以來都呈現合體的狀態,若將其分開處理,性與情之間的關系是什么?章學誠又是如何處理這二者之間的關系?
章學誠以自己早年的“天授”經歷為例談性情的重要性。這些回憶多是章學誠感于后事而回憶前事,頗類于“倒放電影”的敘述模式,因此如果將其簡單地看作章學誠早年生活的真實呈現,難免有失偏頗。這些對于往事的回憶更像是一面鏡子,透過這些對于往事的回憶可以倒映出章學誠回憶時的個人心境,并且解讀一些章學誠留下的言外之意。倪德衛認為,章學誠的記憶世界與他的文學世界已經混為一談,難以完全分辯真假了[4]16。在對章學誠對早年的回憶文本的閱讀中可發現,章學誠對早年的回憶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自我修飾,并且不同回憶之間有著較大的變動,足可見章學誠回憶時的個人心境極大地影響到了回憶的呈現。最令人好奇的是,章學誠的回憶中涉及“天授”這一神秘體驗。透過這一體驗,可一窺章學誠對性情的態度。
一、記憶世界中的“天授”經歷
章學誠對于自己少年時的回憶散見于他三十至五十余歲時寫作的多篇文章中,這些經歷對于章學誠的性格及治學有著極重的塑造作用。章學誠在《家書二》及《家書三》之中提到自己早年曾經有一段神奇的“天授”經歷:
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而人乃擬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5]817
又十五六歲時,嘗取《左傳》刪節事實。祖父見之,乃謂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吾于是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體例,遂若天授神詣,竟成絕業。祖父當時,亦詫為教吾之時,初意不及此也。[5]819
這兩封家書中的內容可歸結為二。第一,章學誠對于自己在史學上的成就非常自信,認為自己堪與劉知幾相比,與劉知幾各得其趣但不盲從于劉,這一成就的原因被章學誠歸于“天授”。第二,章學誠在十五六歲時將《左傳》改寫為紀傳體史書,命名為《東周書》,章學誠認為此書堪稱“絕業”,是“天授神詣”的成果。章學誠于家書中兩次提到“天授”經歷,足見這一經歷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這一“天授”說極為神秘,帶有禪宗之中“頓悟”的影子,甚至可類于“神跡”這樣的超自然現象,是一種“神秘體驗”。由于其中的神秘性,這一“天授”的說法也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金毓黻在《中國史學史》中說:“章氏又自謂,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其自負為何如,觀其所自述者,奚以異焉,此所以前后曠然相接,為史家不祧之宗也。”[6]310倉修良對“天授”經歷評價說:“章學誠后來屢屢說自己對于史學,‘似有天授’。其實并不盡然。他對史學的情有獨鐘,與其父親的家教也是分不開的。……可見,章學誠后來所以能在史學上獨有建樹,又能在讀書中識其大體,觀古人立言之宗旨,而不囿于破碎支離的訓詁,這些都與家學淵源有一定關系,并非全在‘天授’。”[7]38—39
金毓黻認為,章學誠的“天授”經歷的說法并非出自原創,而是與劉知幾的早年回憶有著相似之處,認為章學誠為人自負,在談回憶時有效仿劉知幾之舉。倉修良對“天授”一類的超自然的說法表示懷疑,認為章學誠在年輕時取得如此成就,其依靠的不是“天授”的力量,而是依靠家學傳授。長年的耳濡目染為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章學誠才能在史學上獲得如此大的成就,與“天授”關系不大。從以上兩位學者的分析可見,他們對于“天授”的說法都表示懷疑,認為章學誠的“天授”說更像是自抬身價,通過“天授”的說法來抬高自己在史學上的成就,認為“天授”一詞并無特殊含義在其中。
縱觀章學誠的早年回憶,可發現,章學誠有一段回憶與“天授”經歷的回憶非常類似,但是明顯這段經歷帶給章學誠的不是“天授”般的歡喜,而是一種極強的挫敗感。在《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中,章學誠回憶道:“年十五六,在應城。……日夜鈔錄春秋內外傳,及衰周戰國子史。輒復以意區分。編為紀表志傳,凡百余卷。……時從破簍檢得向所叢編,則疏漏抵牾,甚可嗤笑。”[5]799
章學誠在這封信中同樣提到了自己在十五六歲的時候編寫《東周書》一事,但極為明顯的是,章學誠在這封信中認為自己編寫《東周書》一事只是在浪費時間,并且認為自己耗費三年心血編寫的《東周書》錯誤百出,不值一提,與上文自信滿滿的“天授”經歷形成鮮明對比。為何其中會出現這樣的反差?
《與族孫汝楠論學書》創作于乾隆三十一年(1768),章學誠29歲之時;《家書》創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章學誠54歲之時。從29歲到54歲這二十余年的歲月之中,勢必是因為章學誠的思想有所改變,所以他才會對十五六歲這段編寫《東周書》的經歷的認識有所改變。因此不能簡單地將章學誠的“天授”經歷看作是一種超自然體驗或者是章學誠自抬身價的做法,而應透過章學誠對這段回憶的改寫來一窺章學誠背后的思想。“天授”經歷對于章學誠來說,更像是經歷了二十余年的學習與感悟后所形成的一整套新的思想體系的一個縮影,因此如何給予“天授”經歷以新的解釋,對于理解章學誠本人的思想也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二、個人體驗下的“天授性情”說
針對“天授”的解釋,除金毓黻、倉修良等學者的說法外,其實最容易讓人聯想到的是禪宗的“頓悟”說或者王陽明的“龍場悟道”,這兩種體驗具有突發性、獨特性、不確定性及情緒性等特征。章學誠早年并不聰慧甚至近于愚鈍,對于這樣一個“椎魯”的少年來說,突然在史學上獲得成就,只能依靠“頓悟”,類似于民間所說的“開竅”。關于王陽明的“龍場悟道”的經歷,《王陽明年譜》中記載:“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注疏若相抵牾,恒往來于心,而著《五經臆說》。”[8]507《年譜》中所載王陽明“龍場悟道”之過程,其實也有些類似于“天授”的過程,即領悟的結果多是突然出現在腦中,然后以自身所學知識去一一印證。以王陽明的經歷對比,可將章學誠的“天授”經歷理解為學習過程中的“頓悟”體驗。
章學誠曾經提到了另外一人的“頓悟”,這一“頓悟”的體驗者是戴震。章學誠記述此事如下:“觀前輩自述生平得力,其自矜者,多故為高深,如戴東原言:‘一夕而悟古文之道,明日信筆而書,便出左國史漢之上。’”[5]823這并非是章學誠第一次提及此事,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所寫就的《書朱陸篇后》中,章學誠亦提到此事:“(戴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生平不解為古文辭。后忽欲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復思之,廢寢忘食數日,一夕忽然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為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遠出左國史漢之上。”[5]133
前后兩次提到戴震的“頓悟”經歷,可見章學誠對戴震“頓悟”一事記憶之深刻,以至于多年不忘。戴震的“頓悟”經歷可簡單概括為戴震原先對古文辭并不擅長亦無進行系統的學習,但有一天戴震突然對古文辭產生了興趣,于是進行學習,在一夜之間便有所成就,其文章的功力不下于《左傳》《史記》等名著。戴震雖然于古文上也有用功,但他在對外表述中卻削弱了自己在古文學習上付出的努力,將古文學習一事簡單化,更突出一種“頓悟”的說法。
關于戴震學習古文一事,在《戴東原先生年譜》中載:“先生少時學為古文,摘取王板《史記》中十篇。首《項羽本紀》,有《信陵君列傳》《貨殖傳》,其他題記憶不清。皆密密細字評其結構、用意、用筆之妙。”[9]490從《年譜》中可見戴震研讀古文之勤,這被記述下來的努力還只是冰山一角,可見戴震所付出的努力不止于此。戴震勤讀古書并且多加揣測古人寫作的手法,最終才得以在古文上做出一番成就。
戴震當時如何在章學誠面前談說學習古文一事已不可知,但在章學誠筆下,章學誠有意突出了戴震學習古文的“頓悟”過程而忽視了戴震學習古文的用功之勤。在《書朱陸篇后》中,戴震說自己是有“廢寢忘食”的學習過程,經過了學習之后才在古文上有所成。但在《家書六》中,章學誠刪去了戴震學習古文“廢寢忘食數日”的說法,直接說戴震是“一夕而成”,突出了戴震學習古文的“頓悟”體驗而忽略了戴震在古文學習上的積累。章學誠用極為辛辣的筆調嘲諷戴震,認為戴震之言“使人一望知其荒謬,不足患也”[5]823。簡單地說,章學誠認為戴震在吹牛,是在故意抬高自己身價,因此說出這種荒謬之言,顯示出章學誠對戴震的對抗之意。
關于章學誠與戴震交鋒一事,前人的討論已經頗多。章學誠既欣賞戴震的學問,又將戴震視為自己學術生涯中的“假想敵”,處處針對戴震。從此處可見,章學誠非常反對戴震將做學問一事視為輕飄飄的“頓悟”而忽視其中艱苦困難的學習過程。章學誠刻意突出戴震本人的天資很高,可能能夠達到“頓悟”的效果,但大部分學人并無這等學力,戴震輕巧的說法只會給后來的學子帶來困擾。因此從此處看,章學誠認為“頓悟”一事雖有可能會出現于個人身上,但對個人天分要求極高,對大部分人,尤其是類似于章學誠這樣的“椎魯”之人來說,“頓悟”是不可靠的,章學誠對“頓悟”是呈批評態度的。因此不能將“頓悟”視為章學誠心中的“天授”過程,章學誠心中的“天授”應另有所指。
章學誠作《家書》時已經54歲。五十余歲是章學誠學術創作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其“文史通義”的思想體系基本確立。章學誠是一個極具體系的學者,其思想往往是貫通于其全部作品乃至書信之中,因此可采用一種結構主義的態度去看待章學誠的思想。在談“天授”一說時,亦應立足于章學誠整體的思想體系來談。
“天授”一詞,可將其擴充為“天授某物于人”,其中牽涉三者,分別是“天”“某物”與“人”,因此關于“天授”的探討,實際上可將其轉換為天人關系的探討,即在這一過程中,“天”將何物授予“人”?
章學誠將自己歸屬為浙東學派的學術系譜之中,并將浙東學派的治學特點歸結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所謂“性命”者,即“天人性命”之學,取于《中庸》中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探討天人關系的學問。章學誠認為探討天人關系,需要從史出發進行探討,因此只要集中于對章學誠史學觀念上的探討,便可從中一窺章學誠對天人關系的看法,這其中隱含著章學誠化德性于學問的想法。
《史德》篇中言:“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5]265章學誠認為,處理天人關系的關鍵在于“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句話由于涉及“史德”這一關鍵概念的探討,因此多為史學家留意。有史學家引西方史學理論為用,將“天”解釋為“客觀性”,將“人”解釋為“主觀性”,認為這句話的含義是指在史學研究上要盡可能地做到客觀以避免主觀干擾。此說可見于何炳松,“我認為就是他所說的‘天人之際’完全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歷史上的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何炳松將《史德》中的這句話解為“應該純用客觀主義去觀察一切事物的真相,不應該參雜絲毫主觀的成見”[10]15。這種帶有濃厚蘭克史學意味的解讀方式一直被史學界所認同。細細檢查這句話便會發現,這種解讀方式是有一定問題的,因為它并不符合中國傳統式的解讀。
章益國提出,章學誠的“史意”概念具有一個默會維度,并且在章學誠的史學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章益國進一步將這一默會維度解釋為“一定程度上史不能‘言’的。與其把‘史意’想象成某個對象——像一個物體一樣可以拿出來放在你面前、你可說可指的東西——不如理解成‘章學誠在以言史意的那樣一種方式談論史學’”[11]。簡單地說,章益國認為在章學誠的思想體系之中存在著一種神秘的意會傾向,這一傾向導致章學誠所傳達出來的意思只能“意盡”,不能“言傳”,即“言不盡意”,因此獲得這一知識的方法只有通過感悟去領會章學誠的意圖,而不能通過具體的語言將其表示出來。
鄧志峰針對章益國的默會知識的說法,進一步提出“知識體系”的說法,認為存在著一套公共知識,是大家不言而明的[12]。這種知識自成一套體系,這種體系中的很多概念都是傳統學者從小耳濡目染的,因此無需多言便可領會其中想要表達的意圖,對于章學誠的解讀,應盡可能貼近章學誠的思想背景,將一些默會的知識與時代知識相連接,這樣才能更好地領會章學誠的思想。因此應以中國式的知識結構去看待章學誠潛藏的意圖,而不是專以西方式的知識結構去比附章學誠的意圖。在這一視角下,用客觀與主觀來區分天人便出現其內在的問題。
以客觀與主觀來解釋“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在關系上是申天以曲人,用章學誠的話來說,即“盡其客觀而不益于主觀”,體現一種天人相分,甚至是天人相對的關系。在這一觀念下,應是去消滅人以伸張天,這一觀念并不符合傳統中國的天人合一的觀念。如余英時言,“章氏史德治說于史學中重天人之變……毋使一己偏私之見(人)損害歷史的‘大道之公’(天)!”[2]257因此從傳統文化的角度看,章學誠必不可能提出天人相對的觀念,因此將天解釋為歷史書寫的客觀性也失之偏頗。
從章學誠的總體思想看,“天”更好的解釋應是“天性”,切合于章學誠思想中的性情論,即“盡其天性而不益以人也”。在章學誠的思想體系中,“性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錢穆稱之為“實齋論為學從入必本性情”[1]445。章學誠認為“情本于性”,情是從性中而來。而關于性的來源,章學誠并沒有很直接地道出,如在《答沈楓墀論學》中言:“人生難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學者不自知也。”[5]712人沒有精通一切的天才,必須要近于“天”才能在學業上有所收獲,但大部分學者并不了解此事。此處章學誠提到“近天”的概念,與“天授”說有相似之處。這里的“天”,明顯不能解釋為客觀性,將“天”解釋為“天性”明顯更接近于章學誠的本意,即學者應去尋找符合自己天性的學問方向,才能獲得成功。孔穎達將“性情”解釋為“性者天生之質,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13]24,即將“性”視為“天質”,章學誠認為“性”是一種天生之物。
在《質性》中,章學誠亦探討了“性”的來源。章學誠認為,“性”來自于天地之氣灌注于人身上而形成,氣有陰陽之分,因此人的天性亦有不同。《質性》篇中言:“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為陰陽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滲陰,中于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為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5]179天地間存在一股氣,這一氣落到個人身上,“繼之者善,成之者性”[5]94,呈現或陰或陽的天性,順遂著符合自己天性的方向治學將事半功倍。因此“性”的來源是天地之氣,這一氣是先于人而存在的,人生下來就具有天性。在有關“天人合一”的解釋中,人性即天道。天道、人道與人性之間具有統一性。章學誠認為,道生氣,氣灌注于每個人的身上形成天性,因此天性是人生而具有的而非后天形成的。因為天性是生而就有的,天性無法轉變,因此學者為學應依據個人天性治學而不能違背個人的天性。“天”與“性”是一致的,因此章學誠談到的“天授”“天質”“近天”等概念的“天”,指的不是他物,正是“天性”。
從以上分析可見,章學誠極其重視天性這一概念,甚至將其提升至與“天”一樣的高度,在文章中多用“天”以代指“天性”,甚至以浮夸的“天授”說法來代指“天性”,原因何在?章學誠的目的正在于拔高“天性”的地位,以提醒學者為學應順隨“天性”而非被風氣所裹挾。這一認識的產生是基于章學誠寶貴的生命體驗而非簡單的紙上談兵。
在兒童之時,學子尚未受到外界風氣影響,因此在學習之中較為自由,可以尋找到符合自己天性的學術方向,此時是極為重要的認識自己天性的時期。在《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中,章學誠談道:“人之性情才質,必有所近,童子塾時,知識初啟,蓋往往以無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后讀書作文,與夫游思廣覽,亦時時有會焉,又習而不察焉。此即道之見端,而充之可以垂弗達者。”[5]710在童子塾時,學子常會有無心之得,這一得極為重要,因為它往往是學子獲得的第一次學問符合天性的感受。但大部分人對這一獲得并不重視或根本就無意識,因此常違逆自己的天性而為風氣所裹挾。章學誠在這封信中所談的這一經歷,正是他本人的生命經歷。章學誠在少年學習時曾經也茫然無措,并不清楚自己應從事什么方向的學習,出現了埃里克森所說的“同一性危機”,即青少年時代出現的對前途的迷茫及認同危機,青少年常會以一種叛逆的情緒來表現自己面臨的“同一性危機”。章學誠當時表現得像現在的青春期叛逆少年一樣,他厭惡功課,熱愛游玩及廣泛的課外活動。在功課上,他的表現是“性絕騃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5]823。在課堂之外,他去騎馬、游玩、呼朋引伴。他的精力十分旺盛,在文章、歷史等方面均有涉獵。正是在這種廣泛的涉獵之中,章學誠逐漸化解了他的“同一性危機”,確立了以歷史為未來的治學方向,章學誠認為自己十五六歲時的筆記“其識之卓越,則有至今不能易者”[5]823。章學誠將歷史視為合乎他天性的治學方向,事實證明也是如此。
章學誠在自己的文章中有“天授”“天倪”“近天”“天質”等說法,這些說法中的“天”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神靈性或自然性的天,而應理解為人的天性,即天授性于人,將“性”比之于天賜之物,實際上抬高了“性”的地位。章學誠對天性的發現,來自于他對“人倫日用”的觀察,即發現學者各有自身所長之處,如果違逆自身天性去治學,將會事倍功半。但對于這一天性的來源,章學誠無法作出有效的解釋,因此只能將其歸為陰陽之氣灌注于人而形成。章學誠的根本用意在于呼吁學者治學順隨天性而不必順隨于風氣,體現出章學誠對治學應契合個人天性的重視。
三、“性”與“學”之間的情感張力
在章學誠的建構下,“性”被拔高到了一個極高的地位,是天賦予人的重要之物。章學誠如此強調性情,是為與當時盛行的考據風氣相抗衡,因此在考據學學者眼中章學誠被視為“學力不足”的“異端”。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中言:“蓋實齋識有余而學不足,才又遠遜。……其短則讀書魯莽,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變,汎持一切高論,憑臆進退,矜己自封,好為立異,架空虛無實之言,動以道眇宗旨壓人,而不知己陷于學究云霧之識。”[14]1047余嘉錫亦于《書章實齋遺書后》言:“章實齋文史通義深思卓識,固有過人之處,所惜讀書未博,故立言不能無失。”[15]578李慈銘與余嘉錫共同指出,章學誠的缺點在于讀書不多,學力不精,以至于錯誤頻出。但是他們認為章學誠有新論,并且論有所得,可謂超越常人,這是章學誠的“高明”之處。
章學誠本身在學力上難以與博聞強識的考據學者相比,因此在這些學者眼中,章學誠難免與“束書不觀”的心學學者有幾分相似之處,即好發新議但不博于學,性情論正是章學誠提出的新論之一。錢穆指出,章學誠的性情論淵源于王陽明的“拔本塞源”論,更是加強了章學誠與心學之間的聯系。一方面面對著被歸入“反智識主義”的危機之中,一方面仍囿于考據學嚴謹治學的風氣影響,章學誠如何在“學”與“性”之間把握一種微妙的平衡,盡其天性而又不忽視治學,憑借性情論與考據風氣相抗衡?
首先,性情論要與考據風氣抗衡,它最終的落腳點應在學上,即將自己歸入到“智識主義”的范疇之中,以學言事而非空言著述。其次,性情多連用,甚至出現以性蔽情的情況,情的重要性被忽視。但性與情總歸是兩種不同概念,常被章學誠分開使用,“性”“情”“學”之間的關系亦值得探討。
《說林》中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于人為,非謂虛誑欺罔之偽也。”[5]227章學誠此語,是為荀子的“化性而起偽”進行辯護。荀子的“化性起偽”說常被人理解為“欺誑”,即偽裝自己的天性以適應社會。章學誠認為這一理解是錯誤的,荀子的意思是天性是不能完全依靠的,因此必須要經過學問的打磨之后才能表現出真正的對人有益的天性。這引出章學誠對天性與學力之間的關系的看法,天性雖有,但獨木難支,只有經過學力打磨之后才能有所成。
學力與天性之間呈現兩種關系,一是通過為學可以發現自己的天性,二是通過為學可以砥礪天性。《博約中》篇中言:“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5]117人生下來各自具有天性,但是人初學之時,并不明白自己的天性幾何,因此應該通過學問的磨礪來發現自己的天性。這一天性呈現為先驗的心理結構,只有在個體的經驗之中才能具體捕捉到這一心理結構。在發現自己的天性之后學者進一步學習,學問會和天性契合產生“情”,可類比為學者創作時的主觀性。
朱熹在談論性情時,常以“性本情用”“性靜情動”為分,錢鍾書總結為“性不得其平而為情”。如果用此種觀點帶入章學誠之言,即是在為學中遇到與自己天性相合的內容,天性會因此波動而產生情。這一情既是創作時的激情,亦是創作時的靈感。情對于學者為學是極為重要的。雖然情重要,但情本身是一種沖動的產物,極易受到外物的影響而偏離它原本的方向。為減少外物對情的影響,也需要學的幫助,“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5]179。
對于章學誠的“性”“情”“學”之間的關系可簡單下一個判斷:天性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種特質,但是天性是無形的,無法捉摸的,因此天性需要通過學才得以發現。在學的過程中,學力會與個人的天性發生碰撞,使得天性發生激蕩,其產物便是情。情由于是一種情緒化的產物,其本身會受到外物的影響,因此同樣需要以相當的學力去培育,讓其穩固。因此章學誠雖然強調性情的重要性,但是并未因為性情而忽視學的重要性,這與束書不觀的心學形成對比。章學誠與考據學學者雖分屬“尊德性”與“道問學”兩脈,但隱約之中,章學誠依然受到考據學影響,主張在學的基礎上闡發性情說。
章學誠的將人的天性分為“高明”與“沉潛”兩種,分別對應著“尊德性”與“道問學”,其體現在“學”上的表現是“撰述”和“記注”。章學誠認為自己屬于“尊德性”這一脈,考據學者屬于“道問學”這一脈。在天性方面,“高明”與“沉潛”相對,即文史之學與考據之學平分天下,各有各的天性,就天性而言并無高下之分。但在章學誠的心中存在著一個觀點,以“沉潛”為天性的考據學只是單向與學接觸,難以與學產生雙向互動,因此難以產生學者之情,情是“高明”天性特有之物。在章學誠看來,他的文史之學能與考據之學分庭抗禮的原因在于他的文史校讎之學是一種有情之學,而考據之學是一種無情之學。在“性”與“學”之間產生巨大張力的正是“情”。
考據學的特征在于嚴格而精密的訓詁考據,這一方法需要學者秉持嚴謹的態度,不作帶有自我感情的義理上的發揮。后世學者如胡適、傅斯年等人對這一考據學的方法十分崇敬,認為它合于科學的方法,具有科學的精神。所謂“確有科學的精神”,按照傅斯年之意,即“史的觀念之進步,在于由主觀的哲學及倫理價值論變做客觀的史料學”[16]326,“斷斷不可把我們的主觀價值放進去”[16]45。這一精神是考據學方法與蘭克史學的合流,即盡可能排斥學術的主觀性,以發揮學術的客觀性,求一完全客觀的史學。這一史學看重對史料的搜尋與積累的工夫,要求學者不對史料作自我的見解,只將史料進行比較,學者在其中幾無發揮的余地,而成為史料比較的工具。綜上來看,考據學的方法中雖有學者的“天性”,但排斥學者的“情”在其中,“情”即主觀性,考據學的方法是堅決排斥主觀性。
章學誠對于排斥學者本人之情,只重視文本以至于將學者異化為文本的奴隸的考據學非常反對,因此屢屢出言譏諷。在《與邵二云書》中,章學誠稱考據學為“竹頭木屑之偽學”,并說:“故以學問為銅,文章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為道也,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5]676章學誠此話實則針對考據學鼻祖顧炎武的“采銅于山”論而發,從源頭上出發抨擊考據學。章學誠認為,以顧炎武等為首的考據學家雖然做到了搜集一手資料,不盲目抄襲前人,但他們的工作也僅僅到搜集材料為止。搜集材料不涉及學者之情,因此是一種機械性的、工具性的工作,不帶有學者的主觀性在其中。章學誠認為這種無主觀性的作品,僅僅是一種累積,類似于搬運沙石,真正的學術應該是有“情”在其中的。
章學誠關于融情于學的看法,在具體的歷史書寫的實踐中有多種表達,其中如“筆削”“別裁”“家言”“別識心裁”“一家之言”等。“筆削”來自于孔子,“一家之言”來自于司馬遷,“別識心裁”來自于章學誠,其表達的都是如何以學者的“情”來著史。其中的關系為,史學家如何通過“筆削”或“別裁”的方式著史以成就“一家之言”。
章學誠推崇“筆削”之義,尤其推崇《春秋》與《新唐書》。如果按照嚴格的史料標準來看,《春秋》與《新唐書》并不合格,因為其中多有記載上的錯誤與沖突。但章學誠卻對這兩本書予以褒獎,甚至認為《新唐書》一書“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5]946。
《答客問上》中特言“筆削”的含義:筆削之義,不僅事具本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5]252
筆削的重點在于對于史料的選取工作之上,應根據自己的想法來選擇史料并對史料進行剪裁,以此成書,在這一剪裁過程中不必拘泥于前人的體例,只要是符合自己的想法就好。這一想法,章學誠又稱之為“意之所在”或者“獨斷一心”。通過自己的想法得以成書的作品便可稱之為“一家之言”或“家言”。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不在于史料的搜集,而在于著史者著史時的想法,即“意”或“心”。“意”或“心”可指代著史者的主觀性,因此與“情”也有相同之處。“撰述”與“記注”的區別由此分明,二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在于有沒有學者的“情”灌輸其中。有情之學是撰述,無情之學是記注。“高明”與“沉潛”兩種天性本身并無高低,但在學上的體現卻因為“情”的存在而有高下之見。這反映了章學誠想要舒張學者的性情,避免學者成為考據學的工具。
與章學誠同時代的學者如焦循與袁枚等人,亦主張為學應發揮個人的“情”。章學誠曾經親眼目睹孫星衍、焦循、袁枚等人的爭論,而爭論的焦點在于考據是否屬于著作。袁枚看來,考據是形下之器,因此不足稱著作。孫星衍則認為考據本身就是著作。袁枚論事的立足點亦集中于情上,但袁枚談情是談詩人之情,與章學誠融情于學的做法相比顯得狹窄。袁枚認為:“夫水火,性也;其波流光焰,則情也。人能沃其流而揚其光,其有益于水火也大矣。”[17]396袁枚認為情出于性,這一點與章學誠相近,但章學誠常視袁枚為論敵,多出言譏諷。章學誠雖然主張學問應談“情”,但是“情”需要以豐厚的學識以發揮,而非空中樓閣。袁枚論情,在章學誠看來則有幾分空談的意味在其中,這是章學誠所不能容忍的。
焦循對于袁枚與孫星衍的說法都持有異議,焦循認為治經學的關鍵在于“性靈”。這一“性靈”的說法,與章學誠的“性情”的說法相映成趣。焦循認為,做經學研究必須要具有“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關于“性靈”的重要性,焦循認為“學經者博覽眾說而自得其性靈,上也;執于一家以和之,以廢百家,唯陳言之先入,而不能自出其性靈,下也”[18]213。焦循看來,經學學者能夠在多學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性情來進行創作,著作是上等的;如果僅僅模仿古人而壓抑自身性情,著作是下等的。焦循此處的“性靈”說,更類似于一種創新性的說法,即認為學者做經學考據應有創新而非照搬前人。焦循此說將經學分為“高明”與“沉潛”兩種天性,并對其進行高下之分,其與章學誠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綜上,乾嘉考據學過度注重客觀層面的知識梳理而忽略了主觀層面的學者發揮,學者淪為考據的工具,導致學者被“工具化”,成為“百科全書”或“字典”。章學誠對這種風氣表示不滿,認為學術應體現學者本人的性情。因此章學誠提出人具有天性,天性經學發現并由學培養,天性與學激發出情,情會予學者以靈感和啟發,幫助學者完成著述工作,成“一家之言”。
四、小結
性情論是章學誠思想體系中的重點,也是章學誠用以對抗乾嘉考據學的最為重要的武器。學必與學者本人的性情相關聯,只有這樣,才成學問,而非死記硬背的人型參考書,如錢鍾書言:“大學問家的學問跟他整個的性情陶融為一片,不僅有豐富的數量,還添上個別的性質;每一個瑣細的事實,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養,長了神經和脈絡。”[19]78—79學問與學者個人的性情融匯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學必本性情”。
章學誠談性情,多以性情二字連用,但細究可發現,章學誠將性情分為“性”和“情”分別闡釋,認為人具有天生之性與后天之情的區分。章學誠通過自己的切身經歷,認為“性”來自于“天授”,這一“天授”說帶有神秘色彩,從而將“性”的地位大大提高,凸顯出“性”在為學中的重要性。
章學誠將人的天性分為“高明”與“沉潛”,二者在“學”上的表現則為“撰述”與“記注”,“撰述”與“記注”的最大區別就是其中是否含有學者的“情”的發揮,有情之學為撰述,無情之學為記注。“情”由“性”而生,但“情”不能脫離“學”而獨立存在。因此,“情”通過“學”與“性”的互動關系而被學者發現,同時又會在“學”上給作者以啟發,成就“一家之言”。
章學誠對“性情”的發現與袁枚、焦循等人的“情”“性靈”說相映成趣,其背后反映的是乾嘉學者在考據學風氣的裹挾下的反思、部分學者對于學者個人主觀性發揮的日益重視。這批學者不想讓學術變成一種沒有人的學術,因此力主闡發學者本人的主觀性,這一重視學者本體性的反思形成對乾嘉考據學的一種延伸與思考,也促進了學術的進一步發展。
章學誠的性情論雖然在當時的考據學風氣下應者寥寥,但到民國時,由于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風氣傳入,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為學必本性情。胡適于《愛國運動與求學》一文中言:“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認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發展,這便是你對國家應盡的責任。”[20]5顧頡剛在青年時期曾治各科學術,散漫而無目的,直到后來才確定以歷史為研究方向,并坦言“最合我的性情的學問乃是史學”[21]53。章學誠與胡適、顧頡剛等人,一舊一新之間,竟發生了時空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