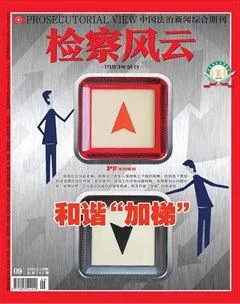盧梭:沒能成為“承攬訴訟人”之后的人生
馬嵐熙

讓·雅克·盧梭盧梭是一個飽受流浪生活和潦倒體驗折磨的人。他后來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張,很大程度上因其青年時期苦難經歷的影響。
讓·雅克·盧梭的故居有好幾處,其中一處位于巴黎北郊的蒙莫朗西小鎮。此處距離巴黎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小鎮偏遠。盧梭的故居就在馬路邊上,是一棟不大的二層小樓。當年盧梭就住在這里,故居門前的馬路現在被命名為“盧梭路”。后來,當地政府把隔壁的另一座小樓一起開辟為盧梭博物館。盧梭故居屋后是一個不大的花園。花園里有兩排高大的老樹,遠處則是低矮的圍籬、教堂鐘樓和廣袤的鄉野。
日內瓦少年從法律事務所出走
盧梭渴望打破等級差異,并在《社會契約論》中寫下他的心愿:“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因此既沒有主人,也沒有奴隸。”1712年6月28日,盧梭出生在日內瓦。然而他的母親卻在產后死去。盧梭自幼便背負上了罪惡感。他在《懺悔錄》中寫道:“我的出生使母親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也是我無數不幸中的第一個不幸。”他的父親是一位粗通文字的鐘表匠,外祖父倒是一位博學的牧師,所以家里藏書甚多。父親在工作的時候,七八歲的盧梭便在旁邊讀小說和歷史故事給父親聽。然而這樣相依為命的日子并沒有過多久。十歲那年,父親跟一個叫高濟埃的法國陸軍上尉發生了一場糾紛。糾紛中,盧梭的父親把高濟埃的鼻子打出了血,而高濟埃則誣告盧梭的父親持劍行兇。雙方訴上法庭。高濟埃要求法庭判盧梭的父親入獄。根據日內瓦的法律,斗毆者互有過失時,可以要求一同入獄,共受處罰。盧梭的父親提出了這項要求,法庭卻作出了偏袒高濟埃的判決,要求盧梭的父親離開日內瓦。
這場變故使十歲的盧梭在失去母愛之后,又失去了父親的庇護,只能去舅舅貝納爾家中寄居。舅舅希望盧梭繼續做一名鐘表匠,或者進城去學習法律或神學,成為一名律師或牧師。13歲那年,盧梭按照家人設計好的法律之路,被送到了本城法院書記官馬斯隆那里,在他手下學習“承攬訴訟人”的行當。依照舅舅的說法,那將是一個非常有前途的職業。名義上是法院書記官,卻負責接洽形形色色的原告被告,給他們法律建議,并“適當地”收取費用——有時這便成為當事人接觸和賄賂法官的托詞。盧梭在《懺悔錄》中寫道:“我對‘承攬訴訟人這個雅號討厭透了……不想用卑鄙手段去發財。天天干這種業務真是枯燥乏味,令人難以容忍,加上工作時間又長,還得和奴才一樣任人驅使,我心里就更不高興了。我每次走進事務所大門的時候,總是懷著憎惡的心情。”
馬斯隆也很不滿意盧梭,經常罵他懶惰,蠢笨,像一頭驢。不久盧梭就被趕出了那家事務所,開始了長達13年的流浪生活。流浪青年盧梭遭遇冷遇、白眼,也得到許多幫助,甚至有過離奇的愛情邂逅。一路上他看到橫行鄉里的稅吏和被稱為“酒耗子”的地方治安官們橫征暴斂,不禁為農民的貧苦和社會的不公感到憤慨。這些觀感和他童年所受的不幸,亦成為他未來致力于探討人類不平等根源的動力。對于人民所遭受痛苦的同情和對壓迫者所抱的不可遏止的痛恨,就從這里萌芽。1742年,30歲的盧梭來到了巴黎。在這里,他結識了狄德羅、伏爾泰和其他的啟蒙巨子,并很快嶄露頭角,進入了另一種生活。
在職場遭遇不公的使館秘書
在他31歲那年,在一位夫人的推薦下,盧梭前往威尼斯使館擔任大使的助手。這位名為蒙太居的大使先生,既不會口授文件,也不會自己寫,屯積下大批公文等著盧梭幫忙處理。盧梭憑借出色的學識和流暢的文筆,很快處理好了,還掌握了威尼斯人的密函讀寫技術。不到一個星期,他就把密函全部譯寫出來,提供給蒙太居大使參考。盧梭得到大使的賞識,不久就獲得了一個響亮的正式頭銜——威尼斯法國大使館秘書。
盧梭很細心,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把屬于他基本職責范圍內的事都辦得很有條理。不管是大使還是任何別人,對他的工作都從來沒有指出過一點疏漏之處。當大使回國述職時,盧梭還自己處理過幾次外事糾紛,都可謂“有理、有據、有節”。展現出色外交才干的盧梭,獲得了法國宮廷的贊譽,卻也同時激發了大使蒙太居的嫉妒。盧梭越是盡職盡忠,就越遭受大使的無端指責。但是大使又不能辭退盧梭,因為很難找到像他這樣能干的秘書。雙方的關系僵到極點,在這種情況下,盧梭決定離開使館返回巴黎。然而蒙太居竟然不顧體統,給參議院寫了一個備忘錄,要求逮捕盧梭。回到巴黎的盧梭雖然未遭逮捕,卻也遭到了宮廷的訓斥。雖然威尼斯方面給予了他充分的好評,盧梭也拿出了無可辯駁的證據,但他卻得不到任何公平的對待。這段經歷,在32歲盧梭的心里種下的仇恨是深刻的。他開始反思和聲討這種不公的社會制度。
參加征文比賽成名的法國憲法之父
1749年,好友狄德羅因言獲罪,被關入范賽納監獄。盧梭等人為營救他而四處奔走,并每周都去看望他一次。從市區到監獄有好幾里路。盧梭手頭拮據,只能步行去看望狄德羅。他隨身帶著一本書,以便走累時消遣。這一天,他帶了一本《法蘭西信使》雜志,在路上邊走邊讀,突然看到第戎學院的有獎征文公告:《科學和藝術的進步是否有利于敦風化俗》。一看到這個題目,盧梭頭腦中那些長期孕育的許許多多富有生氣的思想潮水般地涌來。
據說,當日盧梭躺在一棵樹下,靈感洶涌,他寫出了大段大段假托古人法布里修斯的論述。在這篇文章中,盧梭并沒有就藝術談藝術,而是將視野投向宏大的人類歷史。在他看來,人造的不平等的階級世界要回到最初的美好狀態,就要打碎早已腐壞變質的不公秩序。一年后,這篇由名不見經傳的前任使館秘書投來的論文,竟然獲得了第戎學院征文的頭獎。論文使他一舉成名。但是,性情孤傲的盧梭并沒有因此而混跡于上流社會,他仍是靠抄樂譜度日。1755年,第戎學院再次征文,盧梭以《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應征。這篇論文解剖了人類歷史文明的過程,從經濟和政治上挖掘出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將社會的貧困和罪惡歸因于私有制的建立。這些理論的種子,早在他童年遭遇不幸、青年目睹冷暖和職場親歷不公時已經埋下。兩年后,這部著作在荷蘭出版后震動了歐洲。各個沙龍都在討論“人類歷史的起源”。但此時,盧梭孤僻古怪、敏感偏激的性格再次發作,巴黎城市的喧囂、上流沙龍里的明爭暗斗,讓他萌生退隱的念頭,甚至與多年的好友狄德羅鬧翻。
于是,1756年,盧梭離開巴黎,搬到了蒙莫朗西。在那里,他過著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盧梭在這個隱居之地生活了6年。1762年6月8日的夜里,盧梭被人從睡夢中叫醒。一位朋友派人前來通知他,巴黎最高法院即將于次日下令查禁他那部在10多天前開始發售的《愛彌兒》,并要逮捕作者。第二天,盧梭不得不匆匆搬離蒙莫朗西,逃亡到日內瓦。而家鄉日內瓦也不安全。那里的議會因那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而對他恨之入骨。不久,日內瓦也下令燒毀他的書,并在巴黎通緝令下達的第九天,也下令通緝他了。兩份通緝令傳遍歐洲。他只得逃往伯爾尼邦治下的一個小島圣皮埃爾島。然而不久,伯爾尼邦也下了驅逐令,要他馬上離境。盧梭只得繼續流亡。1764年9月,盧梭接到一封來自科西嘉的信,邀請他去該國擔任制定憲法的工作。這個消息很快傳遍歐洲,他的政敵抓住把柄,立即發表攻擊。盧梭卻毫不避嫌,回信稱因為“眼前障礙重重”和身體“不適宜海上行程”而無法前往,但對于這項事業熱忱不減,并“大包大攬”地代擬了一部憲法——這部憲法在30余年后,亦成為法國革命的綱領之一。
最終,逃亡生活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健康。1778年7月2日,盧梭去世。艱難不幸的一生終結后,他的理念才由法國大革命得以實現。應該說,盧梭的法律思想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法國大革命的靈魂。與此同時,盧梭提出的許多法律思想,也在1791年憲法中得到了落實。為此,他被稱為“法國憲法之父”。他的靈柩被共和國政府遷進了巴黎市中心的先賢祠,并且在葬詞里寫道:“我們向盧梭致敬,我們的再生——我們的道德、風俗、法律、 觀念、習俗所發生的一切幸運變化,都歸功于他。”
編輯:薛華? ?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