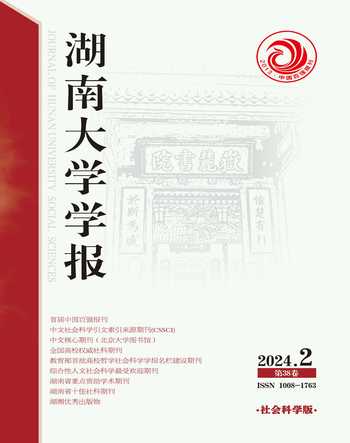經學儒學關系論
黃開國
[摘要] 由于四部分類法與經學始于漢武帝獨尊儒術說的影響,在經學與儒學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學為子學,非經學的認識。孔子開創的儒學是闡發五經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學,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不過是先秦漢初儒學發展的結果,經學與儒學的本質完全相同,四部分類法的以儒學歸于子部不能成立,說明儒學與經學都是闡發五經元典常道的學說,二者不存在經子之分。
[關鍵詞] 經學;儒學;本質
[中圖分類號]? B2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8-1763(2024)02-0025-06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Classics and Confucianism
HUANG kaiguo
(School of Philosoph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610068,China)
Abstract:Because the four-part classification and Confucian classics began with the influence of Emperor Wudis exclusive respect for Confucianism,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has been used as a sub-study, which is a non-Confucian understanding. The Confucianism initiated by Confucius is the Confucianism of the gentleman, and Dr. Emperor Wu of Han's Liwujing is only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re-Qin and early Han Dynasties, the essence of classics and Confucianism is exactly the same, and they are both the theories of expounding and inheriting the five classics and the Common Dao.
Key words: Confucian classics; Confucianism; essence
經學與儒學的關系問題,是一個至今依然值得探討的問題。傳統的四部分類法以經學、儒學分屬經部與子部,現代有關經學史的論著都以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為經學的開端,以孔子開創的儒學為諸子百家之一,而在經學研究中流行儒學為子學,經學高于儒學的觀念。其實,孔子開創的儒學與五經博士之學都是傳承詮釋五經元典的學說,不能因儒學與五經博士之學出現時間的先后,更不能據四部分類法,將五經博士之學與儒學分屬兩個不同層次的部類。
一孔子開創的儒學
要正確說明儒學與經學的關系,就得追根溯源,對孔子開創的儒學有準確的認識。孔子開創儒學是一個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但以儒學稱呼孔子開創的學派是否準確?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孔子開創的儒學?卻是一個至今需要認真反思的問題。
自孔子開創儒學,對儒學作出說明的是西漢的劉安、司馬談與東漢的班固。《淮南子·要略》說:“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1]709劉安是從孔子的開創來講儒學,所以,著重從孔子對周公禮樂文化的繼承來講儒學的形成。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是這樣評說儒學的:“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通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2]3289西漢言六藝,并不是指周秦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學,而是指經學典籍的五經。無論是《淮南子》的所謂“修其篇籍”,還是《論六家要旨》的以“六藝為法”,都特別重視儒學對五經的依存關系。
對儒學的最經典說明,出自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3]1728雖然儒學并不一定出于司徒,但關于游文六經、宗師仲尼云云,無疑是對儒學精神實質、學派特點的最為全面而準確的說明。其中五經的經典文本是儒學成立的根本,是整個儒學發展依賴的根據;五經的精神是以仁義為核心的圣人之道,而堯、舜、文、武是五經精神的人化,孔子則是儒學開創者。離開五經的經典,所謂留意仁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皆無蹤可尋。儒學的成立有賴于五經,五經是儒學開宗立派的根本,而五經的最終確立是孔子刪定五經。五經同時也是經學建立的根本,因為經學是闡發五經元典的學說。肯定孔子刪定五經,儒學以詮釋五經為宗,經學是詮釋五經的學說,就得承認五經的確立,儒學的開創,經學的開端,三者是同一的。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指出,孔子著六經,才有經學的開辟,這雖然帶有迷信孔子的成分,但確實道出五經的確立、經學的開辟、儒學的創立同一這一基本事實。細品司馬談與班固論儒學的話,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司馬談卒于公元前110年,是立五經博士之后的24年,看到了西漢五經博士之學的興旺,“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通其禮”,絕不是先秦漢初的儒學,而只能是立五經博士、獨尊儒術之后才可能出現的現象。班固游文六經、留意仁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的論述,不也完全適用于評說五經博士的經學嗎?完全可以說司馬談、班固對儒學的論說,實際上講的是西漢經學。
儒之名,兩見于《周禮》。關于儒的本義,前輩大師們多有考辨。先有章太炎的《原儒》,隨后出現胡適的《說儒》,馮友蘭著《原儒墨》,錢穆作《駁胡適之〈說儒〉》,郭沫若撰《駁〈說儒〉》,大師們以深邃博厚的學識,對儒的本義、源起和儒學的內容等作出了各自的精湛解說。《原道》第二輯發表陳來的《說說儒——古今原儒說及其研究反省》,后來居上,不僅對歷代原儒、說儒的得失進行了有充分理據的公允評析,還通過翔實的考辨,得出“前孔子時代的儒可能是對六藝有專門知識者”的結論。這一結論是有說服力的。
但以儒稱呼孔子開創的儒學,并不能反映儒學的本質特點。《論語·雍也第六》載,孔子曾告誡子夏:“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說明春秋不僅有儒,而且有君子小人的分野。小人儒是指以六藝討生活之儒,君子儒指以闡發五經常道為己任之儒。孔子最有時代意義與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并不在早年以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為教,而是在晚年刪定五經,及其用以教育弟子。孔門評價弟子的賢與不賢的主要標準,就是看是否知曉、踐行五經的精神,孔子開創的儒學對后世最重要深遠的歷史影響正在于此。正是因為孔子的刪定五經,確立了經學的元典五經,經學才得以開端形成,儒家學派才能夠建立。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意義,往往要在許多年之后才會被認識,孔子審定五經、以五經為教的意義,并沒有被當時的人們充分認識,當時人們更多地注意到孔子創立的學派與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歷史聯系,而將“儒”的名稱冠于孔子開創的學派。若從孔子的最重要文化貢獻在審定五經,以五經為教而論,用儒這個名稱來稱謂孔子開創的學派顯然是名不副實,沒有抓住孔子開創儒學的本質所在。盡管用儒的名稱稱呼孔子開創的學派是不準確的,但由于當時還沒有發明能夠準確描述孔子所開創的學派的名詞,就只能接受這一約定俗成的稱呼。可是,孔子本人對這一稱呼是不滿意的,于是才提出“君子儒”與“小人儒”之辯,以標明自己所創立的學派與先前之儒的區別。
對何為君子儒,何為小人儒,《論語注疏》是從明道與矜名來分解的,君子儒追求的是圣人之道,而小人儒則以名利為追求;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是從天理人欲之辯來分解的:“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4]88代表漢學的《注疏》與代表宋學的《集注》的解說,表現了漢學、宋學各自的理論特色,都在一定程度上合于孔子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名言,有一定的根據。但孔子以義利分君子小人,只是對君子小人的原則說明。具體到“儒”,僅僅拘泥于原則性的說明,是遠遠不夠的。這兩種解釋并沒有準確說明君子儒與小人儒的本義,但君子儒相關的義、天理,皆為經學常道的內容,所以,漢學、宋學的解釋又都暗合于孔子的君子儒、小人儒之義。
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所載歷代學者關于君子儒、小人儒的解釋,多數都肯定君子儒是與道德精神相關的人格。如劉逢祿《論語述何》,以“賢則識其大者”釋君子儒;《集解》以“明道”釋君子儒[5]450-451。這些對君子儒的詮釋,雖然沒有點明君子儒以傳授五經為務,但這些說法都與五經有關,因為儒學的明道之道只能是仁義之道,為己之學即成人之學,識之大者也只能是仁義之道的為己之學,而這些說法都是五經精神的體現。歷代多數學者的詮釋都旨在說明,孔子所說君子儒的本質在重道德,而道德就是五經的仁義精神,君子儒自然應該指傳授五經、講求仁義之道的儒者,而不是依憑六藝討生活的小人儒。
孔子以君子儒、小人儒之別告誡子夏,就是希望他不要做以六藝討生活的小人儒,而要做以五經的傳授為己任的君子儒。子夏以文學著稱,故孔子將這一希望寄托在子夏身上,子夏的確也沒有辜負孔子的厚望,相傳子夏著有《子夏易傳》等傳經的著作,并在弟子中重視五經的傳授,是七十子中對經學的傳承貢獻最大的弟子,因而經學史上有子夏傳經之說。子夏在孔門四科中以文學著稱,這里所說的文學不是現代意義的文獻,而是與經學相關的文學,漢人以文學為經學的別稱,就是對孔子四科之一的文學與經學關系的最權威說明。以傳承五經為務,是孔子所說君子儒的真諦。后世真儒、大儒、鴻儒與假儒、陋儒、腐儒之辨,都應該從孔子所說的君子儒、小人儒之別來解釋。
承認君子儒以傳授五經為業,就得承認儒學是傳授詮釋五經的經學。固然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術“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3]1746,但只有儒家才是唯一“游文于六經之中”[3]1728的學術。從學派意義說,儒家雖然可以稱為諸子百家之學,但從學術的實質而論,儒學又與諸子百家其他學派有重大區別,儒家與經學的學術本質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以闡發五經常道為宗。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夠解釋為什么漢武帝實行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不是以其他學說為官方法定之學,而且儒術獨尊能夠延續二千余年;也才可以說明為什么先秦到漢初儒學家的著作,如《論語》《孟子》《孝經》《禮記》,及其先秦漢初儒學家詮釋五經的《公羊傳》《穀梁傳》《左傳》《毛詩》,后來都被列入十三經,《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也成為四書學的經典;孔子弟子及其后學詮釋五經的著作,如《子夏易傳》《尚書大傳》《韓詩外傳》等,都在四部分類中被列為經部,成為經學的重要文獻。后來即使是所謂漢學代表人物董仲舒與宋學的代表人物朱熹,他們都沒有被列入十三經或四書序列的經典著作,《四書章句集注》被官方列為學官,也只是對四書的集注,而非四書本身。事實說明,先秦漢初儒學為經學發展做出的貢獻,是后來任何一個經學時期都無法相比的,這個時期是經學史上最為光輝的階段。
二五經博士之學
自孔子開創儒學,從先秦到西漢初年都無經學的概念,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后才有經學概念的出現。《史記》一書,無經學一詞。經學一詞最早出現在《漢書》中,共有12次。
具體出現的次數為《宣帝紀》《賈鄒枚路傳》《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翟方進傳》各1次,《儒林傳》2次,《匡張孔馬傳》6次。《兒寬傳》載:“及(張)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3]3332這是經學一詞的最早出現。自此以后,西漢言經學皆指五經博士之學,如長安令楊興推薦匡衡時,稱贊他“經學絕倫”[3]3592等。《后漢書》中經學一詞出現25處,都用于指稱研習五經的經學家或相關學說,無一異義。這表明出現在漢代的經學一詞,是用來稱呼五經博士之學的專有名詞。
經有法則、法典、經典、常道等義,先秦就有天經地義的說法。而天是漢代哲學的最高范疇,漢人以經學來稱謂五經博士之學,表現了對五經博士之學的尊崇。用經學一詞指稱五經博士之學,帶有將五經博士之學置于天經地義高度的哲學意義,也帶有以經學典籍為法典,以經學為圣人之道等含義。設立五經博士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巨變,經學一詞的出現,正是五經博士之學凌駕于其他學說之上法定地位的反映。漢代以后,人們都是以對五經元典的詮釋來言說經學,幾乎無人超出這一經學含義。
比較漢武帝以來的五經博士之學與先秦漢初的儒學,就會發現二者存在時間早晚先后的不同,民間的私學與政府的官學等諸多方面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先秦漢初的儒學只是諸子百家之一,可以與其他學派相互討論、批評甚至批判,但五經博士之學為法定的官方學說,只能信奉,不能懷疑,更不能批評;先秦漢初儒學與其他學派的論爭,主要是學派之爭,漢武帝以后與經學相歧的學說,就會被社會所排斥,甚至被視為非圣誣法的異端邪說。五經博士之學在漢代也成為讀書人入仕的唯一“敲門磚”,通經入仕,成為時尚,這與先秦漢初知識分子的入仕,法家、縱橫家、陰陽家出身的人物,往往更容易獲得高官厚祿形成鮮明對照。
如果由此認定先秦漢初的儒學與五經博士的經學是不同時代的學說,就不得不承認經學是開始于漢武帝,在這之前是無所謂經學的。但是,這只是對先秦漢初儒學與五經博士之學關系的片面認識,只看到漢武帝的五經博士之學與先前儒學的時代差異,而沒有看到二者學術本質的一致性,存在一脈相承的內在聯系。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本來就是先秦漢初儒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最初成為五經博士的學者全部都是漢初的儒學家。所以,司馬遷、班固追溯五經博士之學來源時,常常聯系先秦漢初的儒學大師為說,如《漢書·儒林傳》說:“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3]3593這說明五經博士之學不是儒學之外的另一種學說,而是先秦漢初儒學的繼續。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而制定的重大文化制度,是保證儒學獨尊,為經學發展作出制度保證,而不是對儒學本質的改變。孔子開創的儒學以傳承五經常道為使命,五經的常道經過先秦漢初儒學日新無已的發展,不僅到漢武帝時成為時代的顯學,而且已經深深影響到整個中華民族,成了中國人的文化精神的共識。漢初政治家、思想家總結秦亡的教訓,形成的馬上得之,不可能馬上治之的共識,更為漢武帝的立五經博士做好了直接的理論準備。歷史的風云際會,水到渠成,讓漢武帝實現了這一點。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被后人歸結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含有經學、儒學無本質區分,二者是同一學說的不同稱謂之意。《漢書·武帝紀》有“罷黜百家,表章六經”[3]2525之語,《漢書·董仲舒傳》中則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2524的表述,雖然沒有獨尊儒術一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連稱也出自蔡元培,但這一說法自出現以后就能夠被學者廣泛接受,并長期成為評論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的流行觀念,絕不是無道理的。因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語,從儒學的獨尊與百家的被抑黜的對立,說明了建立五經博士這一重大事件的歷史意義。《漢書》所說的“表彰六經”與“推明孔氏”,用的雖然不是“獨尊儒術”一語,但都與孔子開創的儒學有關,都是指儒學由私學變為官學。盡管罷黜百家不是禁絕諸子之學,但官方只認可儒學,只有儒學尊奉的五經才是官方認可的經典,通經才是讀書人入仕的門徑,在這個意義上說儒學獨尊是完全合乎歷史事實的。而儒學獨尊的制度表現就是官方設立五經博士之學,既然如此,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不過是將儒學由民間之學升為官方之學,只是儒學地位的改變,而不是儒學學術本質的變化就十分清楚了。
我們固然可以說五經博士之學是經學,卻不能據此認定經學開端于漢武帝。因為判定經學、儒學的標準,是學術的本質,而不在于是官方法定還是民間之學。從經學是闡發五經常道的學說來看,經學的開端應該以五經的確立為標準,而五經的確立是由孔子實現的,遠在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前。若以民間之學與官方法定的不同,將同一性質的學說認定一為儒學,一為經學——兩種不同學說,這還有什么學理可言。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后的所謂經學,與先秦漢初的所謂儒學,只存在是否為官方認可的區別,而不存在學術本質的差異。若追尋為什么儒學能夠獨尊,其余諸子之學沒有被官方承認的根源,顯然在于儒學的學術是以詮釋五經常道為宗,具有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價值取向的文化基因,而這正是經學的本質所在。
正因為漢武帝以來的經學與孔子開創的儒學精神實質、學術趣旨、價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史記》《漢書》也用經學一詞指稱先秦漢初的儒學,如《史記·儒林列傳》:“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圣人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漢興,然后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2]3592《儒林傳》是記敘五經傳授的經學師承,這里所謂經藝明顯是指先秦流傳下來的儒學,《漢書·儒林傳》也有相同的記敘。《漢書·賈鄒枚路傳》鄒陽說:“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3]2353以經學與辯知、奇節相對,說明鄒魯與齊楚、韓趙不同地域的文化特點,也是指先秦縉紳先生為載體的齊魯儒學。在《史記》《漢書》《后漢書》中,五經博士或著名的經學家常常被直接稱為儒或名儒、大儒,不絕于書。董仲舒是公認的公羊學大師,是公羊學博士,但劉歆稱董仲舒“為群儒首”[3]2526,班固稱董仲舒“為儒者宗”[3]1317,都是用儒之名,而不是經學之名,也就不難理解了。
正是因為漢武帝以來的經學與孔子開創的儒學是一脈相承,所以,深知這一點的司馬遷在記載漢武帝以來以五經博士之學為代表的經學時,用的是《儒林傳》的名稱。《史記·儒林傳》是以五經的經典為綱目,來記敘五經經師傳承的變化,也就是說《儒林傳》是經師經典傳授的記敘,是完完全全的經學記錄。如果說司馬遷著《史記》時用《儒林傳》之名,可能因為當時還無經學一詞,而采用權宜之計,那么班固生活的東漢,經學一詞已經成為稱呼五經博士之學的專門名詞,得以普遍流行,可是班固依然還是用《儒林傳》的名稱,這就只能說他們是以儒學經學本質同一的觀念在指導《儒林傳》寫作。而且這一現象一直到《清史稿》都因而不改,幾乎全都是用《儒林傳》來記述研治、傳授五經、四書的經學家,這不正是對漢武帝以來的歷代經學是先秦漢初儒學的歷史發展的認同嗎?從孔子開創儒學的先秦到近代,除了有班固所說“儒家”者流的經學與經學家,哪里還有什么另外的經學、經學家可言?而歷朝歷代史記的《藝文志》或《經籍志》及《四庫全書》所列的經學著作,無不是出自宗師仲尼的所謂儒學家之手。離開以傳經為業的儒學家,還能找出什么經學家?
只有元人著《宋史》,才在《儒林傳》外,設立《道學傳》,并置于《儒林傳》之前,來表彰周敦頤、程朱所謂道學,以為只有程朱之學才接續孔孟之道,這明顯受到韓愈道統說的影響。清代編著《明史》時,徐乾學、徐元文主張沿襲《宋史》,設立《理學傳》,但遭到黃宗羲的激烈反對。黃宗羲說:“夫十七史以來,只有《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為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為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正為允當。”[6]451黃宗羲明確講到《儒林傳》是“為傳經而設”,十七史無異,根本用不著在《儒林傳》之外去另設什么《道學傳》《理學傳》。所謂《儒林傳》“為傳經而設”,所傳只能是經學,既然是經學,以“儒林”為名,不正是以經學即儒學嗎?
若經學與儒學真是兩種不同的學說,在已經有了經學之名,特別是四部分類法已經出現,嚴格區分經子已經成為人們的常識的情況下,難道歷代的史學家還會不顧這一常識,還要以子的“儒”代經,犯下混淆經子的錯誤嗎?尤其是在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后,黃宗羲還敢以《儒林傳》為據,來理直氣壯地反對設置《理學傳》嗎?如果不是這樣,只能用司馬遷等歷代史學家與黃宗羲都深知經學儒學本質不二,漢武帝以來的經學,實際上就是先秦儒學的發展,二者并不存在本質的差別來解釋。可以說,在司馬遷與歷代學者那里都是以經學儒學本質同一,來處理所謂儒學家與經學傳承的關系,他們從沒有將經學與儒學分裂,看成兩種不同的學說。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儒學由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上升為官方認可的獨尊學說,五經成為法定的經典,帶有官方意識形態的色彩。在獨尊儒術的歷史背景下,經學僅僅成為“游文六經”的儒學家的專業,實際上就是儒家一家獨享,而其余諸子學派的人都被剝奪了詮釋經學經典的權利。對經學研究人員身份的限制,給經學的發展帶來了局限。但經學也因得到統治階層的官方支持,獲得了制度的保障與國家資源的扶持;而通經入仕的官方文化政策,使通經入仕成為知識分子晉升仕途最重要的手段,加之利祿的引誘,知識分子紛紛投入經學研習中,許多人皓首窮經,為經學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撐,并引發了經學學說的極度繁榮。班固在《漢書·儒林傳》中曾這樣評說西漢經學在利祿刺激下的興盛:“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3]2620經學在其后的發展中雖然有盛有衰,但被官方認可的統治地位,卻一直沒有被動搖。兩千年來,在利祿的引誘下,經學人才輩出,著作汗牛充棟、不可勝數,是其他任何學術都無法比擬的。
三四部分類法的經學儒學
無論是從孔子開創的儒學,還是漢武帝立的五經博士之學,所依據的經典都是經學元典的五經,就其精神實質而言都是闡發五經常道的學說,這是完全相同的。這本來是十分清楚的歷史事實,也是歷代史學家的共識。但由于歷史上長期流行經學始于漢武帝獨尊儒術的觀念,甚至在區分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時,有兩漢經學的專門術語,只以經學歸屬兩漢的學術,以儒學歸于先秦漢初的諸子學派,以及由此引起的相關誤解;加之人們將四部分類的圖書分類誤認為學術分類,使原本清楚的問題變得模糊不清,而有儒學為子學非經學觀念的普遍流行。
四部分類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產物。儒學獨尊的歷史變化,固然為經學的發展提供了官方的支持,但也使五經成為只能信仰,而不能懷疑,甚至不能模仿的經典。由此形成了唯經是從的尊經意識,使經學走向以注疏為主要形式的發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退化為注疏之學,從這個意義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后的經學主要表現為一種注疏之學。即使像朱熹這樣的一代宗師,也是通過“集注”的形式來表現他的四書學思想。這也是西漢以后兩千多年,經學著述再也沒有出現先秦漢初那樣多經典文本的原因。
注疏之學興盛的背后是尊經意識,表現在圖書分類上是四部分類法的出現。從《隋書·經籍志》開始,四部分類法就成為歷代整理圖書的不二法則。四部分類法以經史子集四部分列圖書,以經部置于第一的位置,表現出強烈的尊經意識。四部分類法本是圖書目錄學的劃分標準,但也具有劃分標準學術高低的意義,人們常常以四部分類法來分判學術思想的高低。以經學為第一層次,史學為第二層次,子學為第三層次,集部為第四層次,由此必然得出經學最高,史學次之,子學又其次,集部為最后的結論。
四部分類法在《四庫全書》中得到極致的發揮。《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規定經部的標準:“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7]1詁經即對五經的詮釋,但詁經之作,并不一定合于經學常道。而四部分類法的所謂詁經之作,主要是指注疏形式的著述。因此,只要是對四書五經的注疏,都被歸于經學,不過這樣的經學并非闡發五經元典常道意義的真正經學,而是以注疏形式為特點的經學。盡管注疏是經典詮釋的重要形式,也能夠對經學的常道作出一定的闡發,但過分強調注疏,甚至將注疏作為判定是否屬于經學的標準,那些對經學常道有深刻闡發的著作,因不具備注疏的形式,反而會被排斥在經學的范圍之外。
正是以注疏形式為經學著作的評定標準,在四部分類法中許多經部的著作,實際上并沒有多少價值可言。一個不入流的所謂學者,哪怕是毫無創新的著述,只是因為是對經典文本的注疏,就可以取得經的神圣地位,而被理所當然地列入經部,受到尊崇。而一個一流經學家不是注疏的著作,就被排除于經學之外。這就使經學走向庸俗化,也造成了四部分類法中的許多經學著作,反而沒有史部、子部乃至集部的某些著作更具常道價值的現象。
《四庫全書》的《子部總敘》關于子部的標準是:“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7]769按此標準,將儒學劃歸子部,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為儒學根本不是“自六經以外立說”的學說,而是唯一“游文于六經”的學派,其學術根本就在于經學六經的常道。《四庫全書》以儒學歸于諸子,根本是完全錯誤的。四部分類對儒學的錯誤定位,造成了歷史上孟子、荀子、董仲舒、張載、二程、朱熹、王陽明等儒學大師的著作,雖然對經學常道的闡發遠遠高于絕大多數注疏著述,但因沒有注疏的形式,都被排除在經部之外,置于子部,有的甚至被列在集部,如《王文成公全集》;甚至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四庫全書》也認為歸屬經部,“非其實”[7]244,但只作為經部的附錄而收入。當然,《孟子》一書后來被從子部改列為經部,甚至成為十三經之一,學術界說是由子升經,其實此說非也,《孟子》被列入經典不過是得到應有的認可,而不是什么由子升經,因為“自六經以外立說”的子,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成為經典的。早在漢代揚雄的《法言·君子》中,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揚雄以異于孔子的學說來判定諸子,明確反對將孟子列入諸子的范圍,其根據就在孟子不異于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圣人之道、經學常道都是含義相同的同義語。
四部分類法以經子分屬第一、三部類,固然根本原因在尊經意識,但也有一定的依據。漢武帝之后,經學作為官方的法定學說,具有至高無上的獨尊地位,沒有地位可與之匹敵的學術,加之經學著述宏富,故能夠獨立為一部。而儒學在先秦漢初都是作為諸子百家之一的學派而存在,漢代講經學之名,都是從五經博士而言,由此而言,以儒學列在子部,好像也有一定的歷史根據與理由。但圖書分類不能作為學術或學派區分的根據,因為學派與學術不是分裂的,而是合一的,特別是就儒學與經學的關系而論,更是如此。
從孔子創立儒學以來,特別是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以來,經學的存在與發展都是以歷代儒學家為載體的,沒有歷代儒學家對經典的詮釋發展,就無經學可言。而儒學就其精神實質而論,就是闡發五經元典的常道的學說,這是儒學得以成立的根據,儒學之為儒學的根本。沒有五經元典的常道,儒學就無安身立命之地;闡發五經元典常道學說的經學,又只能依賴于儒學學派而存在,離開儒學,經學就無依附的主體。只不過儒學偏重于學派之稱,經學偏重于學術的本質而言,就其實質而言并無區別。
現代經學研究中,受四部分類法的影響,一些學者強調儒學非經學,以經子分判經學儒學,而忽略二者本質的一致性。如果儒學只是與經學無關的子學,就無法說明儒學為什么能夠成為傳統文化的主干,儒術獨尊能夠通行兩千余年等經學儒學研究中諸多重大問題。只有認清儒學經學沒有本質區別,不可割裂為二,才能夠對為什么經學是中國文化的根與魂,儒學能夠成為傳統文化的主體,中國文化延續五千年等重大問題,作出合于歷史事實與理論說明的雙重證明。
[參考文獻]
[1]劉文典.淮南鴻烈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3.
[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6.
[5]程樹德.論語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3.
[6]黃宗羲.黃梨洲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59.
[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