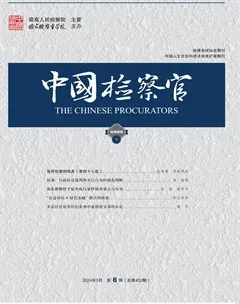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實行行為的 規范判斷
楊楊 朱廷華 張明達
摘 要:司法實務中缺少有效的枉法裁判認定規則,致使辦案人員習慣于將審判監督作為前置程序,由“錯案”結果追索法官是否故意“錯判”。事實上,枉法裁判實行行為的形式標準為民事、行政裁判違反事實或法律,實質標準則指向侵犯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保護法益。本罪的保護法益是司法公正,即國家審判機關的正當履職。行為是否對上述法益制造了現實危險,首先,須以事后查明的客觀事實為判斷素材;其次,因故意犯具有主觀驅動客觀的特殊行為結構,動機、目的等主觀意圖應當作為補充素材;最后,必須立足于行為當時,根據社會一般人的認知水平得出判斷結論。若涉案法官的動機傾向與行為方向一致,即可證明枉法裁判行為成立。
關鍵詞:枉法裁判 實行行為 判斷素材 判斷標準
一、枉法裁判的司法認定困局
[基本案情]2017年3月23日,吉林省東遼縣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東遼縣法院”)依法審理郭某貴與郭某興買賣合同糾紛一案。郭某貴的代理人李某巖與郭某興簽訂了林地林權轉讓協議書,但是該協議未約定合同價款,隨后李某巖與郭某興的親屬李某輝又簽訂了一份轉讓協議,約定該林地林權轉讓價款為600萬元,而在東遼縣林業局涉案林地產權變更備案登記的協議中約定轉讓價款為60萬。這樣,同一個林地林權的轉讓過程卻出現了三份價格不同的轉讓協議,其中60萬元和600萬元的轉讓協議均由李某巖和李某輝代簽。在林地林權過戶登記期間,郭某興曾向李某巖轉賬58萬元,李某巖為郭某興出具了借條。一審東遼縣法院判決李某巖與李某輝簽署的600萬元的轉讓協議有效,郭某興須支付剩余轉讓款542萬元。郭某興不服東遼縣法院判決,向吉林省遼源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遼源市中院”)提起上訴。李某巖之妻金某華為遼源市中院法警隊工勤人員,金某華堂兄金某巖為該院副院長。案件本應由法官趙某霞負責,但經金某華協調之后該案改為法官王某忠審理,并向王某忠暗示給予關照,在案件審理前,王某忠向金某巖表示“案子收到了”,金某巖暗示知道了。二審審判中,王某忠以超期舉證為由拒絕采納郭某興所提供的關于涉案林地林權的價格評估報告,維持了一審判決。事實上,涉案林地林權為李某巖、金某華所有,二人于2008年4月29日購入,并以郭某貴(金某華姨夫)名義登記備案,該案的實質是李某巖以合同糾紛之名行詐騙之實,最終李某巖犯詐騙罪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2017年9月1日遼源市中院審委會作出再審該案的裁定后,主審法官王某忠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16日吉林省遼源市西安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王某忠犯民事枉法裁判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王某忠不服向遼源市中院提起上訴,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定吉林省通化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通化市中院”)負責審理。2021年4月20日通化市中院駁回王某忠上訴維持原判。
上述案件在學界和實務界引發廣泛討論,有觀點認為該案不存在枉法裁判行為,僅是在行使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也有觀點認為該案判決結果正確,但釋法說理不夠充分,未能深入論證枉法裁判和自由裁量的區分。[1]上述歧見折射出司法實務中枉法裁判罪的適用困境,即辦案人員難以準確把握枉法裁判和自由裁量的界限。基于此,本文以行為的法益侵害性來界定枉法裁判罪的實行行為,并嘗試建構枉法裁判行為的規范化判斷體系,以期指引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在司法實務中的適用。
二、枉法裁判實行行為的界定邏輯
關于枉法裁判行為的判定,理論界存在主觀說、客觀說和職務義務說三種觀點:主觀說認為只要違背了法官對法律的信念就構成枉法裁判;客觀說認為只有違反實體法或程序法的規定才構成枉法裁判;職務義務說認為違背法官職業義務的行為屬于枉法行為。主觀說的標準不具有客觀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已經被理論和實務界所拋棄。職務義務說由于將道德義務納入考量范圍也難以成為判定枉法裁判行為的適用標準。客觀說得到我國部分學者的支持,因其具備高度可操作性的同時也符合結果無價值論的一貫主張。[2]事實上,裁判結果違背了程序法或實體法并不意味著法官必然枉法裁判。客觀說也僅是停留于形式判斷的層面,并未觸及枉法裁判行為的實質。
在司法實踐中,枉法裁判的認定方法與客觀說大體一致,往往將審判監督結果作為論證法官枉法裁判的主要依據,但王某忠案刑事一審判決作出在民事審判監督結果之前,彼時王某忠是否錯判尚未有定論,因此辦案單位釋法說理的難度較大,刑事二審裁定亦未能填補一審判決的論證缺陷。本文認為,枉法裁判實行行為的判斷必須兼有形式和實質兩個層次,形式特征在于民事、行政裁判違反事實或法律,實質特征則在于侵犯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保護法益。
(一)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保護法益
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法益對于實行行為的判斷具有方法論的意義。[3]對于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所保護法益有兩種觀點:單一法益說和復合法益說。單一法益說認為,本罪的保護法益是國家的司法公正。復合法益說認為除了司法公正外,還包括被害人的人身和財產權利。[4]本文贊同單一法益說,理由在于:首先,在1979年刑法中,司法工作人員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的枉法裁判行為與刑事審判活動中的徇私枉法行為統一規定在第188條[5],由此可知兩罪的保護法益應當具有一致性,而通說認為徇私枉法罪的保護法益正是國家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和司法公正[6];其次,依照刑法條文原意,若法官嚴重違反事實或法律從而引發社會公眾對于司法強烈質疑的,即使未能造成任何人身或財產損失,依然構成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最后,最高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中列舉的應予立案的情形中前三種屬于嚴重損害當事人利益,其余情形則側重于行為不法而與當事人權益并無直接關聯。
(二)枉法裁判法益侵害的判斷路徑
無論是客觀歸責理論中的制造法所不允許的危險,還是實行行為理論中行為的實行性判斷,二者都是從實質上判斷行為的法益侵害性。傳統理論對于這一問題的討論肇始于不能犯和未遂犯的區分,若行為缺乏對于法益的現實危險,則行為人屬于不能犯,否則屬于未遂犯。[7]本案中王某忠是否構成枉法裁判,實質判斷依據就是其作出的民事判決是否侵害本罪保護法益,即是否在民事審判中客觀、公正、平等地對待原被告雙方的勝訴權。判斷行為如何侵害法益,主要涉及兩種要素:一是判斷素材,即依據何種事實來作出判斷;二是判斷標準,即應根據何種知識標準得到結論。筆者認為,判斷王某忠是否違反司法中立,偏頗民事訴訟中的一方當事人,必須依托事后查明的全體事實,站在行為的當時,根據社會一般人的認知水平得出結論。
三、危險判斷素材:事后查明的全部主客觀事實
實行行為是行為人對于法規范的敵視態度的意思表達,其本質具有行為不法和結果不法的二元架構。[8]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是故意犯罪,故意犯中的行為人對于危險制造持積極立場,即客觀外在行為由主觀內在意志驅動。因此枉法裁判實行性的判斷,應該以事后查明的全部事實為素材,其中既包括外在客觀事實,也包括行為人的心理性事實,如犯罪動機、犯罪計劃、犯罪目的等。
(一)客觀事實是危險判斷的基礎素材
德日刑法學的主流觀點為“一般人+特別人”認知的事實模式,即危險判斷的基礎是社會之一般人在行為當時能夠認識到的事實,但當行為人的認識能力高于一般人時,判斷范圍隨之擴充至特別認識能力所及的事實。[9]例如,甲某日乘坐公交車時與乙發生爭執,甲揮拳擊打乙的面部,因乙患有嚴重心臟病當即死亡。依照上述觀點,若甲不知道乙患病,則該行為沒有對乙之生命法益制造法所不容許的危險;但若甲事先了解乙患有重疾,則甲屬于具備特殊之認識,甲之行為制造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但該學說的理論建構存在明顯不足:一是混淆了主觀和客觀的區分,危險事實獨立于人的主觀認識,主觀認識無法決定客觀危險是否存在[10];二是難以解釋為何當行為人的認識能力超出社會基準時,以行為人特別認知為準,而當行為人能力低于社會一般標準時仍然以社會一般人認知為準,該理論的不對稱性缺乏合理解釋。
事實上,客觀事實是判斷行為危險的基礎。危險是客觀的,客觀事實不會因為尚未被人主觀認知而不復存在,客觀性是行為所制造的危險的第一屬性。甲揮拳擊打的動作對乙的生命造成了現實危險,是因為其動作力度足以致使身患重病的乙產生死亡可能,而不在于甲是否認識到乙患有疾病。因此,客觀事實應當是危險判斷的基礎性素材,王某忠案事后已查明的客觀事實有:案涉林地林權雖然登記在郭某貴名下,但實際上為李某巖所有。郭某貴與郭某興之合同糾紛本質上是李某巖以虛假訴訟的方式實施詐騙,最后李某巖以詐騙罪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該林地林權買賣糾紛中存在三份買賣合同:無價款合同、60萬元的登記備案合同、600萬元的轉讓合同。其中無價款合同由李某巖和郭某興簽訂,后兩份均由李某巖和李某輝代簽。[11]該案訴爭焦點有二:一是原被告雙方之間是否存在買賣合同關系;二是若買賣合同關系成立,則林權轉讓價款以哪份合同的約定為準。針對上述分歧雙方當事人各自提供了有力證據,原告方有合同、過戶登記和李某巖的證詞,被告方亦有李某巖出具的借條和李某輝的證言。上述客觀事實構成了判斷王某忠是否枉法裁判的法律評價基礎。
(二)主觀判斷要素的邏輯證成
主觀因素對于行為危險是否具有影響力,這一問題歷來是學術論爭的焦點。客觀危險說在危險判斷素材的篩選中排斥主觀因素,認為實行行為的“危險”是純粹客觀、不摻加行為人主觀因素的。[12]除此之外理論界也存在認同主觀要素的觀點,認為危險不是已經發生的危害結果,而是法益侵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某種程度上可以等同于人們的“驚懼感”。在危險制造的過程中,行為人的主觀素材對于危險力的形成具有作用力。例如,甲以玩笑的心態持槍指向乙和甲以殺人復仇心態持槍指向乙,乙對兩者的恐懼感是不同的。之所以外觀一致的客觀持槍行為產生了不同的法益侵害危險,就在于行為背后的主觀內核存在差別。
客觀危險說的支持者認為上述示例混淆了行為可能和行為致損可能。具體來說,犯罪動機等主觀素材會升高行為人的行動概率,但與行為致損概率無涉。無論行為人持有何種主觀意圖,只要其揮刀傷人的動作方向、力度等客觀外在保持一致的話,則該行為均制造了同等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險,并未因行為人主觀目的、心理狀態的不同而發生變化。但是,犯罪并非孤立、單數的行為個體,往往體現為在意志支配下的行為組合,在故意犯罪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邏輯上對于同一個犯罪樣本進行重復考察,可以發現主觀因素對于犯罪能量的提升極為明顯,即行為人在犯罪動機、犯罪目的的驅使下,會由單行為升級為復行為、由輕行為升級為重行為。可見,客觀危險說是將刑法中的行為理解為純粹物理意義上的身體動作,而這一理解是簡單、機械、片面的,行為所制造的危險是主客觀因素共同驅動的。行為動機等主觀判斷素材對于認定王某忠是否枉法裁判具有重要指引功能。本案中可以發現王某忠有明顯的徇私動機。林地林權買賣糾紛實際上由李某巖一手策劃、操縱,李某巖之妻金某華通過溝通將該案分配給王某忠,王某忠與金某華身為副院長的堂兄金某巖的交流等細節,可以認定王某忠將該案當成“關系案”“人情案”來辦理,具有徇私枉法的動機。[13]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中僅具備枉法裁判的行為要件尚不足以定罪,還需行為人具有犯罪故意。本文認為故意作為主觀歸責要件,不屬于行為危險判斷的主觀素材。首先,危險判斷的主觀素材通常為行為人的心理性事實,而故意具有心理性和規范性雙重特性[14];其次,故意的心理性內容包含“明知”和“意欲”,而認知與行為危險無涉,意欲則可以被犯罪動機或目的所評價;最后,依照國內刑法通說對于故意的體系定位,故意屬于主觀歸責要素,而危險判斷之主觀素材則屬于不法判斷要素。[15]因此,不宜將故意認定為危險判斷的主觀要素,僅需將行為動機、行為目的納入事實素材即可。王某忠案之所以論爭不斷,關鍵之一就在于辦案人員將行為動機或行為目的視為與犯罪故意等同的歸責要素,但實際上前者屬于心理性事實,后者屬于規范構成概念,二者具有不同的內涵。刑事二審裁定中僅僅將王某忠的徇私動機作為推定犯罪故意的介質要素,忽略了其對于枉法裁判實行行為的不法認定功能,實際上弱化了行為動機的體系價值。
四、危險判斷的認知標準:社會一般人標準
不法行為所制造的危險并非物理學意義上的,而是規范視野中的危險,故此不應站在純粹自然科學的立場上判斷。[16]刑法作為對社會一般人的行為規范,為了實現刑法的規制機能,其內容必須符合一般人的認知能力。因此,危險的判斷標準應當是社會一般人所具有的知識水準。
(一)“一般人標準”的概念界定
該“一般人標準”并非全社會之平均認知水平,而是與行為人的社會角色、認知能力相當的群體的平均認知水準。對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而言,該罪名的規范對象為特定群體,即司法審判工作人員,此處的“一般人標準”等同于職業法官群體所具備的法律專業認知水準。因本案中王某忠為民事法官,這一標準具體可表現為:第一,熟悉民商事實體法規范和民事訴訟程序規則;第二,以人的視角而非上帝視角,該案實質是李某巖以合同糾紛之名而行詐騙之實,但這一事實的發掘依賴后續大量刑事偵查工作,身為二審民事法官的王某忠對此未能識別實屬正常。
(二)對王某忠民事裁判內容的全面檢視
適用上述認知標準審視全案事實,可以發現林權買賣關系存有重大疑點:其一是郭某貴與郭某興的林權買賣合同有效,則郭某貴收到所謂58萬元的“轉讓款”時應當為郭某興出具收據,但事實上在收到上述款項時卻是由李某巖為郭某興出具了欠條;其二是事后評估當時涉案林權價值230萬元,該價值與兩項約定的轉讓款(60萬、600萬)均差異巨大,不符合交易常理;其三是合同簽訂和過戶登記時雙方當事人均不在場,頗為反常。[17]針對上述林地林權買賣疑點,王某忠在郭某貴與郭某興買賣合同糾紛案件二審中裁判如下:
1.認定郭某貴和郭某興之間的林地林權轉讓合同關系有效。理由是:第一,在答辯中郭某興先是否認存在林權買賣合同關系,但是在看到郭某貴提出60萬元的林權買賣合同后轉而主張該60萬元的合同有效;第二,郭某興的合同無效抗辯屬于原被告對于該合同的理解不一致,郭某興應當以反訴的形式提出對該重大誤解的撤銷。
上述裁判實屬違法:第一,郭某興寄希望于即使敗訴也可按照60萬元承擔義務,以減少潛在的損失。但備位訴訟請求可以順次審理,備位事實主張則構成前后矛盾的反言。依照民事訴訟規則若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前后矛盾時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但王某忠卻規避了這一環節徑行將該主張定性為郭某興自認的事實[18];第二,王某忠回避了郭某興關于合同無效的抗辯。無效合同與可撤銷合同屬于合同效力瑕疵的不同類型,合同無效是自始無效、當然無效,并不需要以反訴的方式行使撤銷權。
2.認定600萬元價款合同為雙方真實意思表示。理由是:基于自認規則可以認定郭某興主動支付了58萬元的合同價款;另外,以超期舉證為由不予采納郭某興自行委托機構作出的林權、林地交易價格的鑒定報告。
上述裁判不當:第一,違反了自認規則。在證據認定規則中,自認規則僅適用于對己方不利的事實,郭某貴認為“58萬元是買方付款”明顯對其有利,不符合自認的適用條件[19];第二,對于超過舉證期限后提供的證據,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審理法官必須予以采納認定,而是授予了民事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王某忠的行為雖不合理,但仍在自由裁量的預期范圍內。
綜上,從民商事法官專業視角審視本案客觀事實,可以發現王某忠的裁判中違法審判與自由裁量相互交錯,但二者的行為方向具有一致性,均是對被告不利而對原告有利。另外從該案已查明的主觀事實判斷,王某忠具有徇私徇情的動機,其動機傾向性和行為指向性高度吻合。因此可以認定王某忠是出于偏袒原告的動機,違反證據規則選擇性認定事實,制造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判結果,其行為嚴重違背司法公正,屬于枉法裁判的實行行為。
五、結語
刑法以保護法益為旨歸。刑法中的實行行為是對法益產生現實危險的行為。實行行為的認定必須立足于客觀素材和主觀素材的結合,兼具形式判斷和實質判斷的雙重檢驗。枉法裁判行為的實行性在于司法工作人員未恪守審判中立,偏袒訴訟中的一方當事人。該實行性的判斷在于:應立足于裁定、判決作出的當時,依托事后查明的全部主客觀事實,以專業法律人的知識水平去檢視裁判全流程。當涉案法官的違法審判行為足以改變訴訟結果且具有明顯指向性時,則應充分挖掘其內在動機或目的,若違法審判方向與行為動機傾向一致,即可判定枉法裁判行為成立。
*吉林省遼源市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五級檢察官助理[136200]
**吉林省遼源市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136200]
***北京市平谷區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級法官助理[101200]
[1] 參見陳麗媛:《吉林法官王成忠羈押三年取保:無法接受對自己的有罪指控》,中國新聞周刊網http://www.inewsweek.cn/society/2020-09-07/10331.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4年2月17日。
[2] 參見張明楷、勞東燕、吳大偉:《司法工作人員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頁。
[3] 參見張明楷:《法益初論》,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183頁。
[4] 參見朱剛:《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諸問題研究》,《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5] 參見陳興良、劉樹德、王凱芳:《注釋刑法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283頁。
[6] 同前注[2],第150頁。
[7] 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54頁。
[8] 參見周光權:《行為無價值論之提倡》,《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5期。
[9] 參見何榮功:《論實行行為的危險及其判斷》,《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10] 參見陳璇:《刑法歸責原理的規范化展開》,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頁。
[11] 參見吉林省通化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18)吉05刑終198號。
[12] 參見崔志偉:《實行行為的“危險”與處罰未遂的實質根據——“修正的具體危險說”之提倡》,《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
[13] 參見吉林省遼源市西安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8)吉0403刑初1號。
[14] 參見曾文科:《犯罪故意概念中的“危害社會”:規范判斷與歸責機能》,《法學研究》2021年第5期。
[15] 參見張明楷:《論故意的體系地位》,《法商研究》2022年第2期。
[16] 參見陳璇:《論客觀歸責中危險的判斷方法——“以行為時全體客觀事實為基礎的一般人預測”之提倡》,《中國法學》2011年第3期。
[17] 同前注[11]。
[18] 參見紀格非:《民事訴訟禁反言原則的中國語境與困境》,《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
[19] 參見段文波:《我國民事自認的非約束性及其修正》,《法學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