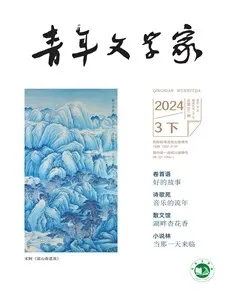作家朵拉研究綜述
何燕娜

朵拉,原名林月絲,祖籍福建惠安。她多年來在散文、微型小說、短篇小說、訪談錄等領域筆耕不輟,兼事繪畫,著述頗豐,在海外華文文壇享有盛譽。但目前,朵拉的文學創(chuàng)作并未在學界引起太多的關注,現(xiàn)有的評論文章也以印象式作品的鑒賞為主。在史料研究領域里,福建師范大學袁勇麟教授是世界華文文學中一位勤勞的“拾遺者”,孜孜不倦于“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叢書”的編撰,其于2017年出版的《朵拉研究資料》為朵拉文學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文基于文學史料學的學科視野,梳理朵拉文學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并將此納入對世界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的思考,由此實現(xiàn)對朵拉文學創(chuàng)作的整體考察。
一、文化尋根
以漢字作為共同文學語碼的世界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中,必定隱現(xiàn)著相互聯(lián)系的文化意識與審美意識,這幾乎已經(jīng)成為朵拉文學研究者們的共識,追尋已有的文學傳統(tǒng),為作家在世界文學之林中尋找可以安身立命之所在,是朵拉文學研究的重要目的。
(一)從作品意象觸摸精神“原鄉(xiāng)”
陳沁薇在2016年發(fā)表的碩士學位論文《朵拉小說創(chuàng)作論》中認為,朵拉的文學創(chuàng)作,習慣從日常生活的物象中提取一個有意味的意象來建構整篇小說。在朵拉文學的研究中,對作品中意象的關注早已不足為奇,這種觀察的目的除了以探討美學意義為旨歸之外,意在讓更多的讀者看到朵拉筆下這些古典意象背后的文化傳統(tǒng)。小說方面,有學者以朵拉的小說《來一杯中國茶》作為審視的對象,從“茶”這一意象的角度觀照朵拉在創(chuàng)作中無意識流露出的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事實上,“茶”作為意象在朵拉小說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曾麗琴的《花的修行—評朵拉的微型小說》和李樹枝的《試論朵拉微型小說的書寫愛情/愛情書寫—以〈有一首歌〉〈等待的咖啡〉〈別人的夢〉〈歲月的眼睛〉以及〈素色的母親〉為討論對象》中均有對朵拉小說所營造的“茶”意象的追尋。當然,對中國古典意象的找尋同樣出現(xiàn)在散文研究領域。朵拉的散文中“花”是一個反復出現(xiàn)的意象,也成為進入朵拉散文世界的重要通道。林宛瑩的《詩情花性兩相融》和荀忱忱、朱文斌的《一夜繁花—讀朵拉散文集〈給春天寫情書〉有感》中均經(jīng)由“花”的意象進入朵拉的情感世界。
(二)從寫作藝術追尋文學傳統(tǒng)
朵拉從不斷成長演變的中國文學中選擇了符合自身藝術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寫作技巧,不斷提升著自己的創(chuàng)作技藝。在小說研究方面,學者欽鴻在這方面有著較為敏銳的發(fā)現(xiàn),“朵拉對于小說藝術的探索,我以為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小說結(jié)構法的變化和演進”(《論朵拉的小說創(chuàng)作》),其中演變的基礎是對中華文學傳統(tǒng)手法的學習,具體包括明晰的情節(jié)線索、有意為之的矛盾、具體的環(huán)境描寫。《問情》是朵拉叩問文學世界法則的敲門磚,學者欽鴻正是以此為起點認為朵拉是在對中國文學不斷選擇和超越的過程中實現(xiàn)藝術成長的。而在散文研究方面,另一位學者陸衡在《是初次相遇,更是久別重逢—讀朵拉散文集〈給春天寫情書〉有感》中分析了朵拉對中國當代作家秦牧筆法的承繼與發(fā)展。可以說,思想性、知識性的文學書寫是中國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積極入世思想的重要表征。在這方面朵拉和秦牧都不過是蕓蕓中華文化書寫者中的一員,但就朵拉而言,她能跨越既有的空間距離和文化差異,一心執(zhí)著于此便值得欽佩。
在朵拉文學研究中,文化尋根的意味最鮮明地體現(xiàn)在趙艷的《馬華作家戴小華和朵拉的中華文化認同合論》這篇論文中。全文以較大的篇幅深入挖掘了朵拉作品中潛藏的東方倫理意識、傳統(tǒng)的審美境界、恪守回歸精神原鄉(xiāng)的創(chuàng)作傾向,并以比較分析的方式將朵拉視為馬華作家整體文化面貌的一面鏡子,由此對馬華文學的文化個性進行抽樣分析。這似乎預示著“文化尋根”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看似已經(jīng)不足為奇,但其實仍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學術生長點。
二、“宏”觀主題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世間的情感是最難以言說的,但朵拉用寥寥幾百字搭建起了獨特的言說空間,不求包羅萬象,但求入木三分。在這個情感空間中,微線條的散文、小說縱橫交織,愛情、親情、友情各種情愫水乳交融。學界對朵拉情感空間的探析形成了由點到面的結(jié)構形態(tài)。
(一)“點”的透視
如果說朵拉建構的這個情感空間是以文學的方式來承載自己對人世的點滴思考,那么愛情就是朵拉在這個空間里的一扇窗,此后慕名而來的評論家們紛紛打開這扇窗,以此來觀望朵拉的情感世界,尤其在小說方面。由福建師范大學袁勇麟教授收集出版的《朵拉研究資料》中,一共收錄了28篇朵拉小說的評論文章,其中直接以小說中的情愛書寫為探究對象的有16篇之多。可以說,朵拉小說中對愛情故事的關注已經(jīng)占了朵拉小說研究的半壁江山,甚至其他以現(xiàn)代人情感書寫為探究主旨的文章中,也離不開對愛情清醒的審視。其中的研究視角大致包括:從朵拉情愛小說創(chuàng)作機緣的探索出發(fā),看到現(xiàn)代都市人在物欲橫流的現(xiàn)代生活中蘊含的情感危機;從朵拉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把握中詮釋朵拉情愛書寫的慈悲情懷,在小說敘事風格的厘析中咀嚼愛情的韻味與苦澀;從朵拉苦心經(jīng)營的“愛情荒原”中發(fā)掘現(xiàn)代性憂思,以及對朵拉小說進行整體觀照后生發(fā)出對其愛情觀的暢想。
(二)“面”的觀照
朵拉的微型小說被譽為“掌上愛情”,在其文學創(chuàng)作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正是她筆下的愛情。但愛情、親情,甚至友情向來無法自顧自地呈現(xiàn),所以在愛情的場次里離不開親情的陪伴,親情的存在和延續(xù)也都離不開愛情的滋養(yǎng)。
在小說研究中,以與愛情密切相關的親情切入朵拉的情感世界可以獲得更為開闊的視野。袁勇麟教授在看到朵拉小說里溫情脈脈的家庭畫面的同時,也看到了朵拉敘事里那些人與人之間由于煩瑣生活產(chǎn)生的疏忽、誤解、埋怨、隔膜,這些是親情在現(xiàn)實生活中更為真實的一面。而在對朵拉的散文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論者們更是發(fā)現(xiàn)了除愛情、親情、友情之外的綿綿情意。目前,有不少直接將朵拉的情感書寫作為研究對象的評論文章,從諸多維度帶著我們別開生面地領略了朵拉筆下更加細膩的情感書寫。例如,故人昔事之情、人在旅途之情、關愛家人之情、品味美食之情、故土鄉(xiāng)思之情、中華文化之情、世間大愛之情,從中我們看到朵拉由“此在”到“彼往”,從精神到物質(zhì),將個體體驗與群體記憶融為一體,或強烈而深刻,或淡然而空凈,在記憶、當下、未來的多重想象中形成一種富有穿透力的召喚,召喚人們珍惜當下,關愛他人,用心生活。
三、“微”文學
一般來說,“微”是對朵拉微型小說中獨特敘事藝術的體認,但是綜合21世紀以來的論述,顯然朵拉的散文恰恰也同樣帶有這樣的“微”特色,舉凡談論愛情、捕捉思緒、感慨生活均輕微進入情感,不去關乎時代、置身宇宙,僅往來徜徉于自由、自我、自然之間。“微”觀進入朵拉的文學世界也成為朵拉研究中極為精彩的一筆。
首先作出整體性論述的典范的是曹惠民教授《“微”之四維—朵拉微型小說讀后》中對于朵拉微型小說的分析,從朵拉的“微言”中體味背后的大義,肯定其作為一個作家所具有的敏銳的洞察力以及巧妙的敘事策略,最后又不忘從讀者接受的視角對朵拉這種“微”觀敘事的效果進行檢驗,作為一種對作品從創(chuàng)作到讀者接受的整體性探析,以“微”這一視角成功進入朵拉文學。
(一)微之視角
首先,選擇一個既能容納作者千思萬緒又能被“蜷縮”在短短數(shù)百字的篇幅之中的題材是創(chuàng)作的關鍵。曹惠民教授在對朵拉小說的評論中認為,朵拉微型小說的取材正是來自作家對生命有意義的瞬間的捕捉。“微”的捕捉是第一步,在朵拉的筆下,日常生活中那些不為人所在意的細枝末節(jié),都仿佛被放到了顯微鏡下有了清晰的顯現(xiàn)。在散文方面,對朵拉選材角度加以討論也普遍存在。蘇永延在《澄江一道月分明—論朵拉的散文創(chuàng)作》中肯定了朵拉從日常瑣事中探索現(xiàn)代人內(nèi)心世界的寫作特色,正如他所分析的,在朵拉的散文中,牽引起一篇散文書寫的緣由往往是身邊的一朵花、一杯茶、一個貝殼這樣細微的物品。其次,對于從生活中發(fā)掘而來的這些點滴感想,如何實現(xiàn)在數(shù)百字的篇幅里妥帖布局甚至是比小說情節(jié)設置更為艱難的過程。也如陶然先生所說的:“要在有限的字數(shù)里完成一篇散文,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剪裁就顯得很重要。”(《不必把話說盡—序朵拉的〈自說自話〉》)而在蘇永延看來,朵拉所用的“剪裁”正是以小見大、由淺入深的表現(xiàn)方法,在生發(fā)感想的素材中選擇一個點,由此夾敘夾議地進行深刻闡釋,使思想的層次過渡不斷深化。
(二)微之藝術
微型小說本身就是一種精巧的藝術,如何在有限的文字中巧妙布局故事框架,交代故事線索,展現(xiàn)人物個性,傳達作者所思所想,這些對于研究者而言,天然帶有一種誘惑,這也成為朵拉研究中最為深入的一部分。研究焦點集中在對朵拉小說藝術結(jié)構的解析,其中作家如何進入小說,又以什么樣的形式結(jié)束小說成為重點論述的對象。首先,開門見山式地切入情節(jié)中心。姚朝文、戴冠青等學者認為朵拉筆下的故事從來不拖泥帶水,在一開始就迅速抓住讀者的眼球。關于小說的結(jié)尾,不少論者指出朵拉小說擅長以“歐·亨利式”結(jié)尾來完成小說最后的藝術突變。袁勇麟教授對這種突變藝術的效果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如果說,朵拉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最受重視的是小說的結(jié)構,在僅有幾篇論述朵拉散文藝術呈現(xiàn)的文章中,“空間藝術”成為關鍵詞。以趙小琪、何娟的《二元對應性的空間結(jié)構美學—論馬華作家朵拉〈聽風的聲音〉中的空間意識》為例,論文發(fā)掘出朵拉散文創(chuàng)作中是著眼過去與現(xiàn)實、自然與社會、精神與物質(zhì),由此揭示了朵拉散文中所呈現(xiàn)出的對應性空間,完成了對朵拉散文文本空間的探析。
(三)微之大義
無論小說還是散文,朵拉用筆都極為節(jié)儉,但這并不妨礙她對于人生哲理和生命體驗等深層次思想的探索。學者錢虹在《偶遇的真情與詩意—讀朵拉的兩本新著兼論其散文》中認為:“她(朵拉)的情感、情愫、情趣、情緒,乃至她的歡悅、她的痛楚,總之,她的喜怒哀樂、一顰一笑皆清清楚楚地凸現(xiàn)在這篇散文集中。”關于朵拉散文中的這種“天性”,與朵拉一直以來對“自由”的向往是密切相關的。胡德才在《朵拉散文的關鍵詞》中將“自由”稱為朵拉散文的關鍵詞之一,她在散文中告誡世人要擺脫世俗功利的誘惑,遠離日常瑣碎的困擾,使精神有所放松,收獲心靈的自由。這種“自由”之下就意味著作家“自我”的呈現(xiàn)。而關于這種“自我”的尋找又多次出現(xiàn)在論者的筆下,并從這種“自我”的背后發(fā)掘出朵拉對深層人生意蘊的探尋和對社會歷史的深度發(fā)掘,由此產(chǎn)生了人文意義上的生命關懷。蘇永延的《澄江一道月分明—論朵拉的散文創(chuàng)作》和李卓然、朱文斌的《最美不過情濃時—讀朵拉的散文集〈給春天寫情書〉》都對朵拉散文中“自我”背后的“大我”情懷進行了細致的評說。
應該說,作為一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不斷辛勤耕耘于文壇的女性作家,朵拉創(chuàng)作的“量”與她所獲得的關注是不成正比的,我們不能否認這與馬華文學研究大環(huán)境的冷清有關。因此本文認為,在這種多重邊緣的處境下,對朵拉的研究仍有許多亟待拓展的空間。從文化書寫層面上來看,對朵拉文學進行“文化尋根”的研究已經(jīng)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朵拉文學作為海外華文文學在地化書寫的典例,其文化特征卻一直被掩蓋,這對朵拉文學的研究來說是一種文化多樣性的缺失;從文化尋根的路徑來看,朵拉研究中對朵拉中國畫的文化表現(xiàn)的關注是缺位的,筆者認為這涉及的應該是跨文化研究工作開展的不足;從主題研究層面來看,對朵拉文學中情感世界的探究仍主要集中在愛情觀方面,事實上作為一個敏感多情的女作家,她投射在文字中的情感是多樣的。另外,對朵拉文學中朵拉小說的主題研究往往缺乏理論背景,多局限于就文本談文本的人物分析模式,而且僅在“女人的題材”“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這樣的研究視野中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女性作家獨有的敏感與細膩絕不應該成為一種僵化的標簽。最后,作為一位“用”情至深的“兩棲”作家,朵拉散文的敘事因素和小說的抒情個性顯然沒有得到關注,雖然這種涉及小說、散文的關聯(lián)性研究必然遭遇理論的困境,但是也不失為打破研究僵局而開辟的新鮮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