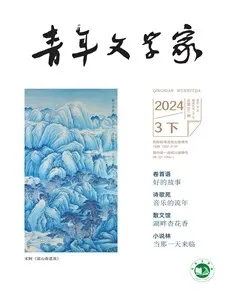從“二元對立”到“互生共融”:《幕間》的生態詩學
黃雪芹


作為現代主義作家的領軍人物,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 伍爾夫(1882—1941)的作品自出版以來,就引發了學界的持續關注,并產生了豐碩的成果。《幕間》(Between the Acts)是伍爾夫的最后一部作品,發表于1941年。學者們多從女性主義、現代主義等角度解讀該作品。近年來,隨著跨學科研究的興起,學者們開始從人類學與倫理學、空間政治批評、生態批判等角度對該作品進行考量。其中,空間政治批評和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起步較晚,屬于伍爾夫研究的后起之秀。
《幕間》完成于“二戰”爆發前夕。故事發生在1939年6月的某一天,描繪了英國某鄉村舉辦露天歷史劇表演的場景。小說以一天的時間為背景,展示了戰爭的陰影悄悄逼近時,鄉村的生活和動態。通過舞臺上的歷史劇表演,伍爾夫巧妙地揭示了人類歷史與社會變革之間的聯系,同時反映了人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共通性和變遷。小說凸顯了伍爾夫對時間、人類關系和社會現實的敏銳洞察力。在“一戰”的鐵蹄下,自然和人類文明已遭受不可逆轉的摧毀。而伍爾夫寫作《幕間》之際,西方社會正籠罩在“二戰”即將來臨的巨大陰影之下。在這部絕筆之作中,伍爾夫通過獨特的意識流敘事技巧,深入描繪人物內心世界,同時巧妙地運用隱喻和自然意象,展現了對戰爭背景下人類關系和社會狀況的深刻思考。
本文試從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分析《幕間》中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系,指出導致兩者之間的生態失衡關系的根源是父權中心和人類中心主義。伍爾夫通過揭示不對等的兩者關系,解構了傳統二元對立中心論,表達了作家對構建平等的兩性關系以及人與自然互生共融的和諧社會的渴求和生態詩學。
一、生態女性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一詞源于法國作家奧波尼的《女性主義或死亡》。美國女性主義理論家瓦爾·普拉姆伍德在《女性主義理論百科全書》的生態女性主義詞條中指出:“女性和其他屈從群體及自然,與男性精英階層及理性,兩者形成的二元論聯系,是理解西方文化殖民式根本屬性問題的關鍵。”知名生態女性主義學者格里塔·加德給出的生態女性主義概念:“生態女性主義不僅僅如其名所示,是關于女性主義與環境主義,或女性與自然的,還基于以下前提來討論環境惡化及社會不公等問題,即我們對待自然的方式與我們相互對待的方式密不可分。”國內知名學者金莉教授指出:“那種認可性別壓迫的意識形態同樣也認可了對于自然的壓迫。生態女權主義號召結束一切形式的壓迫,認為如果沒有解放自然的斗爭,任何解放女性或其他受壓迫群體的努力都是無濟于事的。”(《生態女權主義》)
盡管生態女性主義研究派別眾多,觀點各異,但在生態女性主義學者中存在一種基本共識:人類對自然的掌控與男性對女性的利用之間存在重要聯系,深入理解前者將有助于理解后者,反之亦然。換言之,人類對自然的支配建立在一種父權制度的世界觀之上,這一觀念奠定了女性被支配的正當性。因此,生態女性主義將關注點拓展到對各種壓迫和統治結構之間關系的考察。
二、《幕間》中人與自然的關系
人與自然有著不可分割、互生共存的緊密關系。然而,隨著工業化進程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自然逐漸成為人類奴役的對象。《幕間》的開篇即寫到自然遭受的創傷:“污水溝的選址是在羅馬路上。從飛機上仍然可以看到,非常明顯地看到英國人、羅馬人和伊麗莎白莊園留下的痕跡,以及耕種留下的痕跡,因為拿破侖戰爭期間,他們曾在那兒開墾山丘種小麥。”人類的斗爭和對土地的開發給大地帶來的傷痛尚未愈合,而“二戰”的來臨將不可避免地給土地和自然帶來毀滅性的創傷。在父權社會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呈現出男性對自然的壓迫和支配,而女性與自然之間則展現出更為親近融合的關系。
(一)男性與自然
《幕間》中男性與自然的關系,多是壓迫、暴力、支配。小說中父權制的代表人物奧利弗先生是英屬印度行政機構的退休公職人員,盡管已經退休,他仍然“像命令一支軍隊一樣”,喝令他的阿富汗獵犬蘇赫拉布,“讓其聽命于他”。在他的責罵下,獵犬乖乖地“向他認錯”,并“蜷縮到老人腳邊”。奧利弗先生總是用一股繩索套在獵犬的項圈上,不論走到哪里,他都牽著這個套索。套索是老奧利弗實現控制和支配的工具。奧利弗先生在書房看完報紙后昏昏欲睡,在夢境中他看到自己成了“一個戴著頭盔的年輕勇士”,雙手緊握著槍,想射殺一頭小公牛。奧利弗先生的兒子賈爾斯在演出中場休息準備去谷倉的路上時,遇到一條嘴里卡著一只蟾蜍并盤成圓環的橄欖綠色的蛇,蛇沒法兒吞下蟾蜍,蟾蜍也半死不活地卡在蛇嘴里。“一陣痙攣使蟾蜍的肋骨開始收縮,鮮血滲透出來”。賈爾斯“抬起腳,踩在它們身上”,“白色帆布的網球鞋上沾滿了黏糊糊的鮮血。這是他的發泄動作”。跟父親老奧利弗先生一樣,作為父權社會的男性強者,他將對自己和生活的不滿與怒火,肆意發泄到大自然中。
此外,在建造波因茨宅之時,為了躲避某些自然因素,節約馬力成本,男人們讓宅子面朝北建在山谷中,而不是朝向陽光充足的南面,“大自然提供了這個建房的場所,人們卻把宅子建在山谷里”。躲避大自然的結果是:“冬天的冷雨敲打著窗玻璃,寒風吹落一地落葉阻塞排水溝。”在18世紀的某個冬天,宅子甚至被積雪封鎖整整一個月,“樹木倒塌”。年老的斯威辛太太,只能在“每年冬天來臨時”,躲到黑斯廷斯居住。此外,由于不向陽導致的潮濕,書房的書本在冬天會發霉,而書房是“這棟宅子的心臟”,“書籍是‘靈魂的鏡子”。
(二)女性與自然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與自然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在《幕間》中,女性人物與自然呈現親近融合的關系。《幕間》中的曼雷薩太太從倫敦回到鄉下,觀看露天歷史劇表演。她“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就是大自然的野孩子”,她喜愛和大自然親近,會深更半夜在花園里散步,認為鄉村是“避風港灣”,是“繼倫敦之后第二個能讓她微笑的地方”。在這棟位于鄉下的波因茨宅,這個“大自然的野孩子”遠離了城市的喧囂和束縛,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開胸衣”,甚至想“在青草中打滾兒”。伊莎感到曼雷薩太太對于鄉村的喜愛非常“真實”。斯威辛太太一直盼望著能有一座自己的房子,這樣她就能“擁有自己的花園”。她居住的臥室掛著印花布的窗簾,“綠色的襯里給窗戶染上了淡淡的綠色”,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她最愛讀的書是《世界史綱》,常常陷入沉思和遐想,想象史前社會的大陸,滿是大自然的意象,比如禽龍、猛犸象、乳齒象。歷史劇導演拉特魯布女士選擇了戶外演出,將灌木叢作為更衣室,置身于大自然中。她認為這是“室外演出的最佳地點”,“草坪像劇場的地板那么平坦”,“周圍的樹木像柱子一樣護住舞臺”。大自然的元素貫穿了露天歷史劇的演出。
三、《幕間》中男性與女性的關系
《幕間》中男性與女性的關系,大體分為兄妹關系、夫妻關系、情人關系,大多充滿壓迫和矛盾。在兩性關系中,女性和自然一樣,處于他者的位置。
伊莎和丈夫賈爾斯的關系緊張。兩人因為在蘇格蘭釣魚而偶遇,“她的釣魚線纏結在一起了,她便放棄了,坐在一旁看他釣魚,看溪水從他雙腿間流過……然后她便愛上了他”。三十九歲的伊莎第一次出現在讀者面前時,穿著一件褪色的孔雀圖案的睡袍,一直在陪生病的兒子。她有著一頭濃密的頭發,卻因不打理而顯得凌亂。她雖然關注發型,但“從沒有燙過卷發或剪過短發”。伊莎是家庭主婦,依靠丈夫的工作來維持家庭開支,自己承擔了家務瑣事,她“討厭家務事,討厭占有欲,討厭母親的職責”,但只能默默忍受。公公跟她告狀,說她兒子是個愛哭的孩子,是個膽小鬼。她雖不高興,卻不敢反駁。她愛好文學,但怕被丈夫發現,隨手記下的文字和思想為了不讓丈夫生疑,“特意將它裝訂成賬簿的樣式”。而伊莎的丈夫賈爾斯在露天歷史劇時偶遇城里來的曼雷薩太太,便如影隨形地跟著獻殷勤,完全不理會伊莎的感受。在缺乏交流和壓抑的氛圍下,伊莎也在無意識地尋找婚姻外的精神寄托。“飽經風霜、沉默寡言、浪漫多情的鄉紳農場主”—羅伯特·海恩斯,總能讓她感受到神秘和熱情,在她眼里“那是愛”。在歷史劇演出的一整天,伊莎總是在搜尋海恩斯的身影,而她所能做的也就僅此而已。沒有感情溝通的婚姻已像無形的枷鎖牢牢把她綁定。伊莎是當時社會典型的女性縮影,扮演著父權社會下完美的“房中天使”形象。馬庫斯在《弗吉尼亞·伍爾夫女性主義新論》中提到:“女性的價值和天賦,不管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后天文化建構的,在男性主宰的男權社會中,都被邊緣化了。”
斯威辛太太的宗教信仰被哥哥取笑,當她說“恐怕要下雨,我們只能祈禱”時,哥哥說:“并且提供雨傘。”斯威辛太太臉紅了,因為哥哥“攻擊了她的信仰”。當她問“碰碰木頭”的起源是什么時,哥哥說是迷信。她又一次臉紅了,“她連自己輕輕的吸氣聲都能聽見,因為他又一次攻擊了她的信仰”。她雖然一直想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最終還是投奔哥哥。斯威辛太太回憶起小時候她“屁顛屁顛地跟在他身后去釣魚”,當哥哥讓她取下魚鉤上的魚時,她看到魚鰓里全是血,嚇得大叫,而哥哥對她低聲咆哮,訓斥她的膽小,而不是給予安慰。
賈爾斯對待家族女性的態度也多是消極的。在露西姑姑面前,“他出于本能,把自己的宿怨都歸罪于她,如同一個人把外衣掛在鉤上”。而碰到四十五歲風韻猶存的曼雷薩太太,他就像換了副面孔似的獻殷勤。他一方面生氣露西姑姑只會欣賞風景,但當曼雷薩太太說風景真漂亮時,他非但不生氣,還“窩著手掌又給她點了一根煙”。作為男性,賈爾斯和曼雷薩太太的曖昧不會給他帶來任何不良后果,正如妻子伊莎所說:“他的不忠一點兒影響都沒有—而她的不忠卻會有很大的影響。”由此可見,《幕間》中矛盾微妙的兩性關系,體現了精神層面的生態失衡。在父權制社會下,男性始終處于強者的位置,而女性與自然一樣,受到前者的壓制。
四、對構建互生共融美好社會的渴望
在《幕間》中,伍爾夫不僅指出了二元對立導致的兩性關系和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還通過女導演的露天歷史劇解構了傳統二元對立中心論,表達了作家對構建平等的兩性關系以及人與自然互生共融的和諧社會的渴求和生態詩學。評論家馬克·赫西指出,《幕間》是伍爾夫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證明,體現了作家對構建互生共融社會的渴望。“這就是這場露天劇的好處—它把人們聚集到一起。”熱愛自然、喜愛讀歷史書的斯威辛太太想象著“將一切融為一體:綿羊、奶牛、野草、樹木、我們自己—都融合成了一體”。
《幕間》的背景設在英國鄉村,伍爾夫對自然和鄉村的渴望以及回歸并非逃避,實際上是她對即將到來的戰爭對大自然的摧毀的批判。在小說的結尾,當眾人都散去,伊莎和賈爾斯“兩個人第一次單獨待著,他們沒有說話”。然而,在爭吵完后,“他們會擁抱,從那個擁抱可能會有另一個生命誕生”。融合與新生命,伍爾夫在她的謝幕之作中表明了她對互生共融社會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