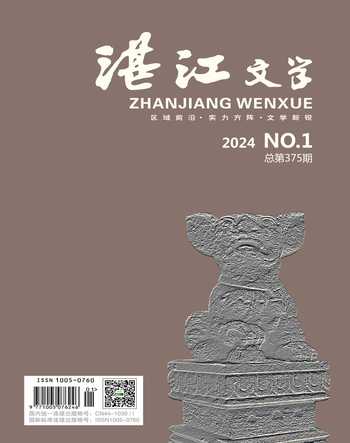午時深處的味道
符昆光
我一有空就到北橋公園走一走。唯有來到這里,我才覺得自己不是工作的奴隸。人來到這世上,總被一輪輪的人生游戲,弄得自己成不了自己。自由的靈魂、獨立的意志,永遠面臨循環往復的窘境。北橋公園有一種向上的原始動力,于無聲中一直陪伴著我,把它的惻隱之心全盤托給我。
北橋公園并沒有耀眼的美麗,實際上它只不過是一個占地一百多畝的小園子,上面長滿了雷州半島日常所見的各種樹木,如荔枝、龍眼、芒果、小葉榕、紫荊、木棉、鳳凰、椰樹等,甚至有好多叫不上名字的各種高高低低的灌木。十幾年前建設這座公園的時候,曾路過,是一片農田或荒地,被齊腰深的草叢湮沒。十年前我在海田買了辦公室,從那時候開始,北橋公園便走進了我的生活。那時候,可以說是我最忙碌、經事最多的時期,時間仿佛唯有在北橋公園才得到停歇。
在這里,青翠茂盛的樹林、草地、蟲鳴,還有閃光的水面、飛鳥,令我有了回歸大自然的情趣。在這里,我必定像野貓一樣舒展身體,讓每一條筋骨都徹底放松。樹葉釋放出來的新鮮空氣,在枝葉間吱吱作響,夢幻般閃爍著生命的生機。深深吸一口,是貪婪式的吸,能真切感受到神經細胞沸騰起來的旋渦,瞬間使整個身體回響著愉悅的音樂之聲,一身的清爽,靈魂如放飛的鴿子。在這里,唯有晌午最幽靜,能聽到落枝落葉清脆的聲音,我常常懷疑是有人故意為我添加了一點情趣。它是大自然的小調,鮮活而靈動,讓我心底有隱隱的閃亮。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它也是故意讓我注意它,像一本書一樣,讓我慢慢翻閱。別看我多半像若無其事的樣子,時不時,是突然間我能看到關于它的優秀品行。
園中央有個突起的小山包,頂部平坦,有幾塊死去的火山巖石。它們沉默,但依然高昂著頭顱,在表達什么,一直猜不透。
我喜歡在火山巖石上冥想,或坐或臥,也許周邊有竹林的原因,隱隱能感受到有風從遠處傳來,再傳到遠方去,就如《詩經》中“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有無限曼妙的美好,我屏息看著,宛若她的一呼一吸,讓我無從抗拒。我突然發現世界另外一個狀態,這可能是《道德經》里所謂的“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的浮現。
小山包上有七棵小葉榕。榕樹的生長速度快,最初的時候,有手臂般大,十多年間,一人抱不了。榕樹的氣根,長得最旺,如雨簾,向下懸垂,密密麻麻。沒有風時,一片幽靜,或說是老態龍鐘。有風時,顯現少婦的柔情,甚至是少女的羞羞答答。我對氣根懷有敬畏之心,它們一心從樹枝臂部噴出欲望,努力接近地面,然后扎根泥土里,不用七八年便長成強壯的樹樁,為家族的興旺提供更多的支撐點。它結的果粒特別多,人類不會碰它,然而卻是鳥類的美味。我常觀察鳥類的一舉一動,覓食時默不作聲,至少是輕聲細語,吃飽之后,嗖的一聲,揚長而去。我常想,人如果也有它們的簡單,是多么的瀟灑。
我百思不得其解,鳥喜歡吃榕樹的果子,它們為什么不在這幾棵樹上筑巢?難道鳥不懂得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嗎?我愛人曾說,鳥不在這里筑巢,肯定是樹上有蛇或其它天敵。她說她曾在一部紀錄片里見過蛇偷鳥蛋吃。
這么多年來,我們在北橋園從沒見過有蛇出沒,倒是見過樹蛙、蜈蚣、蝎子、黃蜂、甲蟲、毛毛蟲等。我愛人大王有一晚曾被一只蝸牛嚇著。這個背著螺旋形外殼的軟體動物,令人驚異,小時候我總是不得其解,蝸牛的肉體如何能鉆到一個小螺里,然后占為己有?在鄉下,在有露水的季節,在上學一路上,我常常看見蝸牛走在路邊,它走過的地方,分泌的黏液,總會留下一條濕痕,讓人確信它是一個能夠爬動的物體。
那天晚上,愛人的腳板差點踩在蝸牛上,如果不是燈光照在它渾圓的殼上,它肯定被壓碎。蝸牛嚇了大王,而她的尖叫聲也嚇了蝸牛,蝸牛一動不動,連觸角及頭迅速收縮到殼里。蝸牛喜歡晝伏夜出,可也不能走在水泥路上啊?這無異于在冒險。
自那晚之后,我才注意蝸牛,并且發現,它喜歡爬樹,特別喜歡高大挺拔的美麗木棉樹。美麗木棉樹干長滿圓錐狀尖刺,如果不細致觀察,一定會誤把蝸牛當成尖刺。
穿行在北橋公園的樹林里,我更喜歡于陽光下的樹林,這常常勾起我對童年的回憶。
我生活在林區,在松樹林或檸檬桉樹林里,陽光越大,松脂香或檸檬香越濃烈,整個樹林好像有成群仙女下凡的傳奇,仙氣飄飄,深深打動了我。我不得不張大眼睛,香味的廣闊,極其強悍,而當細嚼慢咽時,是溫柔,是優雅,特別是用手搓著樹葉,散發出奇異的香味留在手掌上整天不會消散時,我將看到夜里的夢,很細嫩,讓人精神飽滿。在花開時節,氣味濃郁,想壓都壓不住。蜜蜂蝴蝶涌動著激情,歡快地融入花海放縱自己,滿足自己,釀造的蜂蜜,纏繞著松脂的味道,檸檬的味道,極具感染力,柔美、浪漫,使人有超凡脫俗的感覺。
園里的樹比較多,自然形成一個小氧吧。我喜歡坐在石頭上抬頭看樹,看縫隙里的陽光。陽光透過樹枝樹葉的縫隙,溫柔、羞澀,投射到地面有飄逸之美,仿佛地上開了一朵花,我更相信她是天上下凡的小天使。有好幾次,剛好有一只繡眼鳥飛過來,停在光圈上,不停跳躍如在舞蹈。它小巧玲瓏,動作敏捷,頭部和翅膀是暗綠色、腹部白色,眼圈被白色絨毛環繞如玩偶,不喜歡都不行。在陽光照射下,如綠寶石熠熠生輝。它用圓圓的眼睛看著我,我平靜的心,濺起一片小水花。它就像一個誘餌,或是一劑滋補良藥,或者是上天為我打開的一道小天窗,在我人生不如意的時候,陽光變成一個開心果與我相依,然后又送來有如唐詩宋詞的繡眼鳥,用橡皮擦去我的孤獨與煩惱,她無盡的恩惠,撫慰我,喂養我,我不再是棄兒。
我曾經用手機抓拍了視頻,回放,卻始終找不到那種感覺。我又用鉛筆慢慢畫,也無法捕捉那個窄小而寬闊的歡喜,或許它只適合留在記憶里。
鳥喜歡在水面飛翔。但不是繡眼鳥,而是順著海溝飛過來的海鳥。
北橋公園有兩條海溝穿過。南邊的河叫南橋河,北邊的叫北橋河,北橋公園就在兩河交匯的夾角里。河的兩岸,都是用石欄桿所圍,長滿三角梅。像兩道紅色彩帶,幾乎是四季嫵媚,倒影映在河面,與紛擾喧囂的城市,形成鮮明的對比,它是鬧市的世外桃源。身置此景,人如果遇有再大的心事,也會被凈化,釋然。
河水沒有激流,因而河面大多數平靜如鏡,但對垂釣者,激情燃燒。這里自然是垂釣者的好去處。
垂釣者有老年人,有中年人,年輕人比較少,但幾乎是清一色的男士,這么多年來,還沒碰到女性。
我對垂釣也感興趣,奇怪的是,我從來沒想過要買一把魚竿。曾經有一個靠發射魚鏢射擊魚的中年人鼓動我也買一枚魚鏢,當時我也躍躍欲試。魚鏢是成套工具,好似一件袖珍兵器。一個橡皮筋彈弓,一個魚線輪。魚線纏在輪上,另一頭拴在魚鏢上。魚線輪固定在拿魚鏢的手腕上,魚鏢上有鉤,用鉤鉤住皮筋中間點,拉開皮筋,一放,魚鏢迅速飛出去,射向露出水面的魚。
而跟我談得來的孫老頭,對這種“釣法”不屑一顧,認為這種“釣法”沒有一點技術含量,他對此嗤之以鼻。
而釣魚效率最高。什么是釣魚呢?就是在線上扎上十多枚魚鉤,無餌。在線末尾的底部綁上一個小螺絲帽。魚竿一甩,嗖一聲,小螺絲帽帶著魚鉤飛出十幾二十米開外,沉到水底。然后用手慢慢搖繞線輪,線慢慢收。在收線過程中,如果有魚碰到任何一枚魚鉤,鋒利的魚鉤會鉤住魚嫩嫩的皮肉,一旦鉤上,想跑都跑不了。
這種“釣法”,簡直絕了,每次放鉤,極少會落空,不用一個時辰,能鉤上十斤八斤。孫老頭說,他們都偏離了釣魚的初衷。他還說天下垂釣者肯定都注重結果,然而更加注重過程,垂釣就是一種修煉。他說,面對微波蕩漾,持桿垂餌,身定如石,寡語如金,人與魚的博弈或游戲,充滿難以言傳的妙趣。
也許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就這個韻味吧。這是古代文人孤獨美的極致,而處于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每每覺得自己就是鉤上的那條魚,嘴里含著魚鉤,越掙扎越疼痛,越疼痛,越是徒勞的掙扎,就像生活中的自己,一天一天的衰敗,幾乎找不到生命存在的理由和價值,精神上接近鉤上那條絕望的魚,心里特別的痛。可我一直盯著鉤上的那條魚,我想挽回我的暗淡,我想我有更好的命運,這是多么的茅盾啊。鉤上的那條魚,也讓我從中反復琢磨這個娑婆世界,一個接一個的誘惑,一個接一個的困惑,一個接一個的坎,它們是冰冷的,也是溫熱的,它們是柔軟的,也是堅硬的,它們十分頑皮而任性,甚至如一只披著羊皮的狼的嗥叫,它們始終成為我的伙伴,攜著我的手。在夜間,我常常感覺到心底下隱隱的顫抖或疼痛。
我更加羨慕孫老頭了。
別看孫老頭平時少語,他釣魚的背景儼然是一塊石頭,而他告訴我,別人眼里的孤獨,是一種錯覺。如果不站水邊,如果手里沒有一把魚竿,其他人很難理解垂釣者的心景。他說,垂釣者期待魚碰到釣的一剎那,需要垂釣者敏銳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戰機,稍為不慎,就會讓魚兒溜走,這其中的享受,是不能用言語來表述。他每次見到我,一定遞來一支香煙,我說我不抽煙,他還是說,來一支吧。我只好接過,也抽起來。
他曾問我:“你知不知道這兩條河為什么叫南橋河和北橋河?”
我從來沒想過這一問題。我知道南橋在區政府門前,北橋在九二一路路口。是啊,河為什么以橋名來命名?
孫老頭得意地哈哈大笑。他說解放前南橋河叫南溪,不相信你看看南橋旁邊還存活著一家老賓館叫南溪賓館,唯有它對南溪不離不棄。而北橋河原來叫福建河,因北橋河流經福建村而得名。解放前,在海田一帶,全部是海,福建河的出海口就在北橋公園一公里遠的地方,名叫鴨乸港。鴨乸港不存在了,但名字還立在街頭的路牌上。鴨乸港見證了赤坎城區滄海桑田變遷。
說起赤坎的填海,我總是感慨萬端。如果不填海,赤坎的人文景觀是另一番圖景,但我敢肯定,絕對是威尼斯版,海在城中城在海中。
一談到這個話題,孫老頭就一言不語。我也只好盯著他釣魚。河面上,我看到幾條魚迅速閃過的身影,頭時而露水面,時而翹起尾巴,一擺,深潛水下,水面出現小小旋渦。
“嗖”一聲,孫老頭將魚鉤拋向河中央,魚鉤碰在水面,迅速鉆入水里,浮漂也沒入水中,就一秒,又從水里彈出水面。黃色浮漂,在水中擊起一圈圈漣漪。不一會漁線輕輕拉緊,浮漂向下沉并向左上移動,有魚吃鉤了,孫老頭像個年老的孩子,臉上蕩起一種深沉而顯得意的笑容。當孫老頭起線時,一條一斤多重的羅非魚在空中拼命掙扎,在陽光下如一曲荒野的挽歌,越過河面。相當于這條魚在世間最后一抹隱約的微光,反復在我的腦海再現。
海鳥看到了這一幕。它們在河面歡快地盤旋,它們的叫聲,有詩歌的穿透力,它們滑在水面的優雅,照樣有唐詩宋詞的風韻,一句話,海鳥給我某種啟示。我總覺得,此時的鳥類,這下子與人有了共同的語言。
北橋公園十年光陰,于人生來說是不短的歲月,至于二月的雨,三月的木棉花,五月的鳳凰花,六月的荔枝,八月的黃皮,臘月里的海鳥,沒有憂郁的神情,一路匆匆,奔流不息,從有影子,到無影,但每一次都是清晰可見,都是那么純真,并給人向往。看看,大自然的確沒有偏愛之心,它的活力全潛伏在物競天擇里。北橋公園為我提供了一個關于生命或生存的視角,也是大自然在歲月中延伸的動態,是歲月在時序里的長途跋涉,變得有節奏感,更具有美感,它的輕淡、柔和與大度,或它的無聊或有趣,不悲不喜,在無為中又無所不為地、一點點地沉浸進我的細胞,讓思想的困窘,煥發出另一種生活的態度。我深深地愛上這午時深處虛靜的時光。站在這里,我想起我過往的人生,及幻想未來的人生,北橋公園填充著我的想象。
“爭名于朝、爭利于市”已經泛濫成災,甚至成為常態,我常常問自己,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么?除了油鹽柴米愛恨情仇,生命本就是一段孤獨的旅途。人生起起伏伏,坎坎坷坷,一個人總會碰到心力交瘁的時候,渴望的總是不能實現,又很難坦然接受。無疑,北橋公園是人間的溫熱,是狂躁世界所需要的安靜,它讓我明白,它是躁動的主宰,它對我了如指掌,常常暗示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我曾多次懷想,我要是它身上一部分該多好。
是的,不可否認,北橋公園于我的人生,真的是“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任何時候有它在,我的內心都油然而生一種安寧、曠達之感。一天夜深人靜之時,我獨自一人坐在房間,突然間,北橋公園的智慧悄然而至,彪悍但不鋒芒畢露,它掛在我的腦門上,讓我久久地凝視。它是一曲交響樂,一片歡快和諧。不,它是暴風雨后那一縷溫暖的陽光,穿透烏云照在我蒼茫的大地,讓我走出迷茫。
我樂了,是打心窩兒的樂。這詩意般的風味,有嚼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