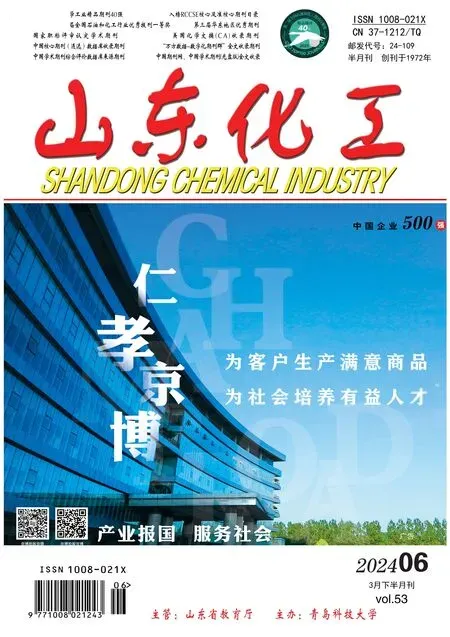重金屬污染水和土壤的生物修復技術研究進展
蔡長君,崔永峰,賈維平,丁蓉
(甘肅省武威生態環境監測中心,甘肅 武威 733000)
重金屬是一組來自地殼的天然元素。然而,工業排放、采礦和農業活動等人類活動會將重金屬釋放到環境中。在許多國家,由于無計劃的城市化、工業化、人口增長和管理政策不善,土壤、地下水和各種水體中的重金屬濃度都超過了可接受的限度,對人類食物鏈造成了隱性威脅。
目前已有多種創新技術用于修復土壤和水中的重金屬污染,如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1]。例如,已使用多種物理技術去除重金屬,如土壤清洗、吸附、光催化、膜過濾、顆粒活性炭和電動法。一般來說,這些方法相對耗時,且高度依賴于所研究的有毒金屬的物理化學特征。不過,最常用的重金屬修復化學方法包括離子交換法、絮凝法、混凝法和化學沉淀法。另一方面,高級氧化工藝涉及使用強氧化劑來分解和去除污染物。這些工藝可用于有機和無機污染物,包括重金屬和新出現的污染物。雖然這些方法能有效去除重金屬,但過量使用化學品會增加污泥和沉積物的處置難度,并增加二次污染的風險,這可能會限制其廣泛應用。
因此,生物修復(如基于植物和微生物的方法)被認為是利用潛在的微生物或植物物種將有害的金屬形式解毒為危害較小的狀態,從而修復受污染環境的有前途的技術之一[2]。其中,微生物生物修復被認為是一種可持續且廉價的策略,可用于消除水生環境(包括廢水處理)中的重金屬污染[3]。此外,利用微生物進行重金屬生物修復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中包括重金屬的不可生物降解性以及細菌有時會產生有害代謝物。值得注意的是,植物修復和微生物生物修復是兩種突出的綠色修復策略,由于具有多方面的優勢,包括生態友好、方便的原位方法及較低的使用成本,科研人員針對這兩種重金屬去除策略已經展開了大量的研究。總的來說,植物修復是一種用于改良受重金屬污染的土壤的強有力的綠色技術,它可能包括植物萃取、植物積累、植物穩定、植物溶解和植物降解等重要機制[4]。同樣,微生物生物修復以金屬生物吸附、生物累積、生物礦化、生物沉淀和生物浸出為主。納入新物種的植物積累劑、微生物生物修復與植物修復的合并,以及包括多組學在內的生物技術方法的應用,可以加速土壤和水生環境的可持續生物修復過程。
1 環境中重金屬的分布和毒性
1.1 重金屬的分布
在環境中,重金屬是自然存在的,但人類活動大大增加了重金屬的含量。鉛是一種常見的重金屬,在自然界中的含量相對較少,通過生產和處理電池、油漆和電子產品等工業產品釋放到環境中。制造業、采礦業和化石燃料的燃燒都是導致大氣中鉛含量持續上升的人類活動的例子[5]。水生環境中的鎘污染是由土壤和沉積物的吸收、工業廢物和地表徑流造成的。鎳和鉻是環境中天然存在的元素[5]。鉻有兩種氧化態:三價鉻和六價鉻。三價鉻是人類的重要營養物質,而六價鉻則是一種有害的致癌化合物。環境中鉻的含量因地點和鉻的具體形式而異。在某些地區,由于自然地質過程或文明的影響,鉻的濃度會升高[6]。
在巖石圈中,砷廣泛分布于巖石、土壤、水、空氣和生物體中。土壤和巖石中的砷濃度可從低于百萬分之一到數千萬分之一不等。錳是巖石圈中含量第12高的元素,豐度為0.1%[7]。錳存在于許多礦物中,包括輝綠巖、菱鐵礦和紅柱石。錳在環境中的豐度相對較高,不被視為稀有元素。然而,錳的濃度會因具體地點和來源而有很大差異。在有錳礦或冶煉廠的地區會發現高濃度的錳,接觸這些高濃度的錳會對人類和其他生物的健康產生負面影響[8]。汞是通過火山爆發、巖石風化和海洋脫氣自然產生的。人類活動(包括采礦、燃燒化石燃料和廢物處理)也會促進汞向環境中的釋放[9]。汞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包括元素汞、無機汞化合物和有機汞化合物。甲基汞是特別令人擔憂的一種汞,因為它可以在食物鏈中積累,并可能危害人類健康。鈷廣泛存在于環境中,用于制造合金。鈷大量存在于植物、土壤、巖石和水中。相當含量的鈷通常不會產生有害影響,但大規模的環境釋放可能會致命。銅通常存在于巖石、土壤、水和沉積物中。包括侵蝕、火山爆發和巖石風化在內的自然過程會將銅釋放到環境中,農業、工業生產和采礦等人類活動也會將銅釋放到環境中[10]。銅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包括元素銅、氧化銅和硫酸銅。植物和動物都需要銅作為養分,但環境中高濃度的銅會對某些生物產生毒性,并可能損害人類健康[11]。鋅的毒性受接觸類型和數量的影響。獲取鋅的兩種主要方式是冶煉和采礦,這兩種方式都會影響生態系統和生物體[12]。
1.2 重金屬對人類和植物的毒性效應
一般來說,重金屬可根據其在植物營養中的必要性分為植物必需元素和非必需元素。非必需金屬會對人類和植物的生理構成重大威脅,甚至可能致命[13]。簡而言之,重金屬是一種金屬元素,可能對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體有毒。主要毒性可能包括生殖系統畸形、腎功能障礙、呼吸困難、高血壓、細胞突變、肺癌和腹部損傷等。此外,重金屬離子還通過三種不同的方式導致植物死亡:它們從結合位點取代必要的陽離子;它們產生活性氧,產生氧化應激;它們直接與蛋白質上的羧基、組苷基和硫酰基結合,與蛋白質相互作用。
2 對土壤和水中的重金屬進行植物修復
植物修復是一種經典的綠色修復技術,利用潛在的超積累性植物物種(無論是原始形態還是轉基因物種)來治理重金屬污染。與當代物理和化學修復策略相比,這種修復技術易于原位應用,投入成本相對較低,因此在應對重金屬污染方面頗受歡迎。一般來說,超積累性植物可以耐受更高濃度的有毒金屬,并能從受污染的土壤中吸收大量的重金屬。一些證據表明,包括多年生植物、觀賞植物和某些竹類在內的各種植物物種對高濃度的重金屬具有耐受性。此外,一些水生大型植物、鹽生植物和鹽沼也是水生環境中的高積累植物,適合用于修復水道和廢水中的重金屬污染[14]。
2.1 植物修復重金屬當前進展
盡管利用具有吸附、固存和吸收潛力的植物物種對受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屬進行植物修復是一種正統的修復技術,但這種具有成本效益的綠色方法的可持續性仍是土壤和水環境中污染物(包括痕量金屬、農藥和相關新出現的污染物)環境修復領域的研究熱點。包括觀賞植物、鹽堿地、開花物種和草種在內的多樣化植物物種可作為積累汞的植物物種,用于原位和異位修復策略,以清理受汞污染的場地。
蕓苔屬植物能有效地萃取土壤中的大部分有毒痕量金屬,包括鎘(Cd)、鉻(Cr)、銅(Cu)、鎳(Ni)和鋅(Zn)[15]。所研究的重金屬被固著在蕓苔屬植物的嫩芽中,不會影響土壤肥力和結構聚集。不過,所研究植物物種的重金屬吸收能力取決于多個因素,包括植物生物量、土壤類型、污染程度、實驗階段和根圈相互作用。特別是超積累性植物物種的根部滲出物和土壤化學特征將影響重金屬吸附過程。與自然生長的煙草物種相比,轉基因煙草能在污染土壤中積累大量經測試的重金屬(如 Cd、Cu 和 Zn),這是因為轉基因煙草具有更好的根系和更大的生物量結構。
雖然傳統的植物修復技術作為一種基于植物的可持續緩解土壤中重金屬污染的修復技術已被廣泛報道,但將傳統的植物修復技術與土壤有機改良劑(如有機肥、生物炭、活性炭)結合使用,將擴大現有策略的規模和效率。此外,增加商業金屬螯合劑和表面活性劑將是增強正統植物修復重金屬污染土壤的有效選擇。
2.2 植物修復的基本機制
植物修復的基本步驟可能通過根-芽-葉吸收方法在植物生物量內進行維管運輸后,通過受測植物物種的根系進行植物積累。植物修復技術中采用的植物物種具有強大的根系結構和增強的生物量結構,同時對相對較高濃度的有毒痕量金屬具有超強的耐受能力。在抑制氧化還原有毒金屬產生的活性氧導致的植物脅迫過程中,超積累植物通過抗氧化系統或酶相互作用的強適應性驅動了一種常見的金屬脅迫機制。另一方面,非氧化還原有毒金屬則通過基因表達被耐受性植物物種的根系和芽系吸附[16]。
最常見和最廣泛探討的植物修復機制是“植物萃取或植物積累”,即從污染土壤中吸收 重金屬,然后將吸附或轉移的重金屬封存到嫩芽或生物質中。植物萃取過程的關鍵機制可以通過金屬螯合、細胞壁與被檢測金屬離子的結合以及由谷胱甘肽、植物螯合素、金屬硫蛋白等介導的金屬-生物質復合物的形成得到證實。然而,由于植物、土壤和環境的特定因素,植物萃取的具體機制千差萬別。因此,我們鼓勵在不同的環境條件(包括非生物不利脅迫)下,使用特定的金屬植物萃取劑對植物物種進行細致、單獨的研究,以探索特定的金屬修復機制。
下一個重要機制是“植物穩定”,即應用潛在的植物物種對重金屬進行穩定固著或固定,通過化學固著、根瘤層相互作用和根部滲出物的化學作用,顯著限制吸附的重金屬在污染場地的生物利用率和流動性。與植物萃取不同,植物穩定過程是通過無機配體沉淀、堿化以及與高分子物質絡合等方式限制吸附在土壤中的有毒金屬。通過在根瘤區添加有機改良劑或生物炭作為土壤填料,可實現植物穩定性的增強,而通過潛在植物物種根系的穩定固碳,可抑制重金屬在植物維管束系統中的遷移。在重金屬生物修復過程中,增強植物穩定性的關鍵觸發因素是土壤pH值、土壤有機質、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和根瘤滲出物。
2.3 植物物種可持續管理面臨的挑戰
利用自然生長的耐受有毒金屬的植物物種或基因工程植物物種進行植物修復是一種有效的修復策略,但修復處理后如何管理超積累植物和植物生物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受有毒金屬污染的植物生物質傳統上采用綜合管理策略進行處理,包括焚燒、露天傾倒、堆肥和熱解。在現有的植物生物質修復后處理管理中,采用熱處理策略(即焚燒和熱解)是為了將吸附的有毒金屬集中到熱處理后的固體部分(即黑炭或灰燼部分),而不是熱解過程中產生的液體和氣體部分。因此,仍需對高積累植物物種進行有效的后處理。
有毒金屬在原始植物物種中的超積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處理后的后期管理也很繁瑣。此外,被調查植物物種的根系在耕作層內是淺表的和有限的,導致重金屬不能被有效吸附并隨之向植物生物量轉移。根據以往的觀察,在使用自然生長的高積累性植物物種時,有毒金屬的固著和生物積累相對較低。因此,在田間規模的應用中,廣泛使用包括桉樹、竹子和觀賞植物在內的多年生植物物種是不可行的。尋找新的替代性高積累植物物種,如海洋鹽沼和路邊多年生木本物種,將是克服現有挑戰的一種選擇。同時,在實地應用有毒微量元素的植物修復過程中,成本效益和環境可持續性是面臨的挑戰。
3 對土壤和水中的重金屬進行微生物修復
微生物修復是一項創新技術,它利用多種潛在的生物制劑,主要是細菌、真菌、藻類、酵母、霉菌,在去除/解毒/轉化/中和重金屬負面影響的同時保護周圍環境,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17]。與一些廣泛用于緩解重金屬污染的物理化學方法不同,生物修復法由于其重金屬去除效率高、成本效益高、易于處理以及在受污染的土壤和水中隨時可用,因此具有一系列經濟可行性。在生物制劑中,微生物在重金屬生物修復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生物不僅有助于溶解重金屬,還能參與過渡金屬的氧化和還原。這項綠色技術利用微生物的新陳代謝能力來消除重金屬污染。特別是,這項技術旨在將高價有毒重金屬轉化為毒性較低的離子。許多微生物菌屬,包括節桿菌屬、褐藻屬、曲霉菌屬、氮青霉屬、芽孢桿菌屬、伯克霍爾德菌屬、鐮刀菌屬、黏菌屬、青霉菌屬、假單胞菌屬、根霉菌屬、鏈霉菌屬、鏈霉菌屬、硫桿菌屬、擔子菌屬和毛霉菌屬已被用于生物修復。值得注意的是,潛在微生物的應用一般不針對特定地點,而是既可用于土壤環境,也可用于水生環境。這些生物制劑具有較大的表面積與體積比、眾多的結合位點、較強的結合親和力以及其他獨特的特性,可提供較高的重金屬 清除效率。
3.1 重金屬污染的微生物修復機制
一般來說,大多數重金屬都被歸類為有毒物質,但潛在的生物有機體已進化出特定的抵抗機制和復雜的細胞內途徑,以利用、相互作用、適應和解毒重金屬,實現細胞再生。微生物修復可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包括解毒、生物吸附、降解、礦化以及從高毒性形式向低毒性形式的轉化,通過生物累積進行細胞內固存,通過沉淀以不溶性化合物的形式進行細胞外固存,以及產生可溶解和螯合導致瀝濾的金屬化合物的代謝物。此外,包括細菌、菌根和真菌在內的植物生長促進微生物也可能有助于重金屬的生物修復。在植物生長促進微生物中,細菌和菌根可以分泌生物活性分子,包括金屬螯合劑,從而促進生物吸附和生物累積過程。然而,一些益生菌和真菌可以加速微生物沉淀和生物表面活性劑介導的金屬離子釋放,從而實現痕量金屬污染的再生。然而,這些潛在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物的性質和效率以及重金屬的類型和濃度的影響[18]。
3.2 實驗室到現場的挑戰
對于微生物修復技術的設計、開發和實施而言,根據其修復潛力和基本過程選擇最佳細菌菌株至關重要。最近,基因工程和轉基因生物等不同的生物技術工具提高了生物修復技術的效率,然而,處理大量受污染的土地和廢水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工程生物的工業影響面臨若干障礙。此外,這些生物在野外的遺傳穩定性一直是人們猜測的話題。要使研究走上正軌,需要對生物修復機制有深入地了解。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強烈建議進一步研究生物工藝水平的發展,在工業和現場實施更快的操作程序,并對微生物進行元基因組操作。
4 結論
綜上所述,綜述了我們通過潛在植物物種(超積累物種)和細菌、真菌、藻類等微生物進行重金屬修復處理污染土壤和廢水的潛在機制的認識。然而,在清除受污染場地中的有毒金屬時,任何生物驅動因素的單獨應用都可能會限制其廣泛應用。因此,植物修復和微生物修復相結合的方法似乎可以提高重金屬修復的效果。特別是,生物炭、有機肥料和潛在的微生物也可以與植物修復相結合,為加強有毒金屬的生物修復提供奇妙的選擇。盡管傳統的植物修復法或微生物生物修復法是最有效的方法,但這一過程相當緩慢,而且由于性能不佳,可能無法實現完全修復。因此,建議進一步開展適應性和跨領域實驗,以確認可持續的修復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