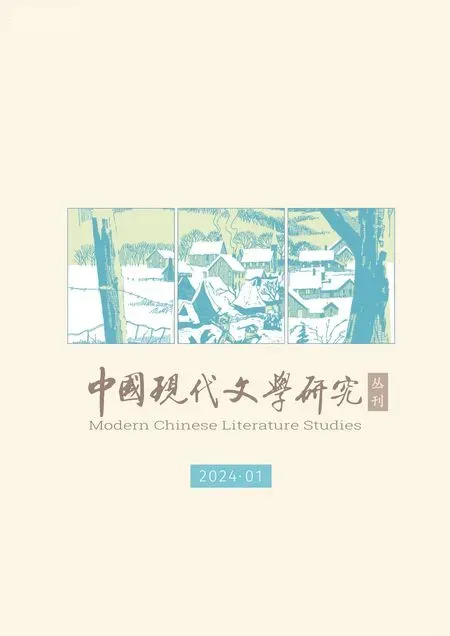《霞滿天》中的王蒙密碼※
段曉琳
內容提要:《霞滿天》是王蒙新近創作的小說文本,無論是對于王蒙的個人創作來說,還是對于中國新時代文學而言,《霞滿天》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王蒙在《霞滿天》中采取了小說的“回旋曲”寫法,在“回旋曲”中,王蒙埋藏下了許多“密碼”。首先,《霞滿天》以時間的回旋與視角的回旋實現了小說敘事的回旋,并在敘事的回旋中,以多層次疾病隱喻為中心形成了小說的雙重環形敘事結構。而且,《霞滿天》還通過作者的在場與虛構的暴露、時間的“錯置”與“重版”、多文本的嵌套與互文實現了小說虛構的回旋。正是在敘事的回旋與虛構的回旋中,王蒙借助雙重環形敘事結構和文本內外的互文,完成了一部關于女性、國族與人類的寓言,并將這寓言寫成了一部對女性、國家和民族、人類精神的贊歌。這是《霞滿天》中的王蒙“密碼”,它彰顯了王蒙小說創作的新時代文學品格。
2023年是“人民藝術家”王蒙從事文學創作70周年,在與共和國一同成長的文學生涯中,王蒙為中國當代文學貢獻了《青春萬歲》、《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活動變人形》、“季節系列”、《青狐》、《這邊風景》、《笑的風》、《猴兒與少年》等重要作品。其中2022年發表、2023年出版的《霞滿天》是王蒙新近創作的小說中引人注目的一部。無論是對于王蒙的個人創作來說,還是對于中國新時代文學而言,《霞滿天》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小說中所展現出的堅定的人民立場、強烈的家國情懷、宏闊的人類視野,以及以文化自信與民族自信講述中國故事的文學自覺彰顯了王蒙小說創作的新時代文學品格。
從文本細讀的角度來看,《霞滿天》是一部暗藏玄機的作品。這是一部小說的“回旋曲”,王蒙在小說的“回旋”中埋藏下了許多“密碼”。“回旋曲”寫法是王蒙所格外欣賞的一種寫法,它可以用于小說創作,也可以用于詩歌寫作。具有濃厚“李商隱情結”1趙思運:《王蒙舊體詩中的“李商隱情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2期。的王蒙,在詩論《李商隱的回旋曲(外二章)》中,曾重點解讀了李商隱的“回旋曲”寫法。王蒙認為李商隱的“詩之回旋”主要包括時間的回旋、視角的回旋與詩語的回旋三個方面:時間的回旋是指現在、未來、過去與現實、想象、回憶的彼此交織、相互轉化、互相影響乃至共時存在,它體現了“時間的多重性”;視角的回旋是指君與我、主與客角色視角的回旋轉換,這是一種虛擬的多層次復調對話狀態;而詩語的回旋則是指詩歌中字詞的重復現象,在這些有意義的重復中形成了詩的“張力與悲哀,懸念與期待,落空與落實”2王蒙:《李商隱的回旋曲(外二章)》,《讀書》2023年第2期。。王蒙認為正是通過時間的回旋、視角的回旋與詩語的回旋,李商隱完成了比音樂回旋還要回旋的詩之“回旋曲”。而王蒙的小說《霞滿天》中也存在著復雜的小說“回旋曲”,因此《霞滿天》與《李商隱的回旋曲(外二章)》可以作互文參照閱讀。首先,《霞滿天》同樣以時間的回旋與視角的回旋實現了小說敘事的回旋,并在敘事的回旋中,以多層次疾病隱喻為中心形成了小說的雙重環形敘事結構。其次,《霞滿天》還通過作者的在場與虛構的暴露、時間的“錯置”與“重版”、多文本的嵌套與互文實現了小說虛構的回旋。正是在敘事的回旋與虛構的回旋中,王蒙借助雙重環形敘事結構和文本內外的互文,完成了一部關于女性、國族與人類的寓言,并將這寓言寫成了一部對女性、國家和民族、人類精神的贊歌。這便是《霞滿天》中的王蒙“密碼”,它彰顯了王蒙小說創作的新時代文學品格。
一 敘事的回旋與疾病的隱喻
《霞滿天》的小說敘事結構嚴密而精巧,其總體小說敘事是一種雙重環形敘事結構。小說楔子和正題共同構成了從2020年代到2020年代的環形敘事,而小說正題部分以蔡霞為中心的敘事則構成由2012年到2012年的環形敘事。這種雙重環形敘事結構是通過視角的回旋、時間的回旋與敘事的回旋共同完成的。
具體來看,《霞滿天》由小說楔子部分開始敘事,楔子(第1—4章)由“我”(王蒙)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我”往事中的“日子”和幾個老友的故事片段。這看似碎片式的隨筆體記錄中卻暗含著兩條與時間有關的敘事線索。首先是時代線索。與共和國一同成長的王蒙,是一位擅長在個人史中講述國家史的作家。《霞滿天》的楔子在講述“我”三十歲、四十歲、四十歲后對“日子”的感受以及新疆“鐵胃人”老友、北京“沒情況兒”老鄉和某海濱城市“大舌頭”姜主席的故事時,王蒙借助“五七”干校、“愛國衛生”運動、“批林批孔”、出國移民夢以及市場經濟東風等標志性時間節點,在個人史的片段中折射出了國家發展史中的大時代變遷。楔子部分在看似隨意的散文式感慨中,將1950、1960、1970、1980、1990年代的個體往事與國家往事,按照時間順序予以了以點帶面、以小見大式的呈現。在這一敘事中,個體與時代、個人與國家緊密相連、同步向前。也正是時代線索的連續性,讓小說楔子與正題部分獲得了敘事上的連貫與氣韻上的相通。
其次是敘事時間線索。《霞滿天》的小說敘事是從當下2020年代(約2021年)的回溯式講述開始的,這個立足當下的敘事時間并沒有被王蒙明確點出,而是需要讀者在閱讀中自己推算出來。楔子中的“我”在三十多年前因病療養時認識了某海濱城市的姜主席,分別后不到一年,“我”就聽到了他投資期貨被騙、突然因病去世的消息。由于市場經濟的東風與“從未與聞的‘期貨’市場”在改革開放后的出現時間是1990年代初,那么距此三十年后的現在就是2020年代初,這說明《霞滿天》的小說敘事是從2020年代初開始的。在小說的結尾部分,小說敘事又回到了2020年代初:“二〇二一年,在‘霞滿天’院里,王蒙終于見到了九十五歲慶生的蔡霞‘院士’。”1王蒙:《霞滿天》,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66頁。也正是立足于當下的敘事才為王蒙提供了“王按”與“王評”的機會,讓“王蒙”得以直接參與敘事對話并做出了立足于當下的價值評判。
《霞滿天》的總體敘事(楔子+正題)是“我”(王蒙)在2020年代講述發生于2020年代的“我”與步小芹、蔡霞交往的故事。在這一敘事中,王蒙通過敘事視角的轉換與回旋,形成了小說敘事的三層嵌套:層次一,“我”講述“我”與步小芹、蔡霞相識相交的故事;層次二,在層次一的敘事中嵌入“我”聽步小芹講述和轉述蔡霞的故事;層次三,在層次二的敘事中嵌入蔡霞對其人生經歷的自述。這種敘事視角的回旋轉換在參差對照中形成了一種立體復調敘事,蔡霞、步小芹和王蒙(“我”)都對蔡霞的奇葩行為與傳奇經歷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并做出了價值判斷。
更重要的是,在小說主體(正題)部分,王蒙完成了以蔡霞為中心的從2012年到2012年的環形敘事。在這一環形敘事中,以疾病為核心,形成了多時間軸的多層次疾病隱喻敘事。
首先,時間軸一(第5—9章)的敘事是“我”聽步小芹講述蔡霞2012—2017年的故事。該時間段所覆蓋的核心事件是蔡霞入住霞滿天養老院后,因跌跤突然發作幻想性精神病。蔡霞的精神病是《霞滿天》中敘事節奏最慢的部分,也是小說中最精彩的部分,它是小說的題眼、心臟與靈魂。以這一精神病為中心的多層次疾病敘事要靠整部小說的環形敘事結構來完成。僅從時間軸一來看,它完整地講述了蔡霞入住霞滿天養老院、因跌跤而發作精神病,并依靠時間與音樂的治療而自愈的過程,其表層敘事即精神病的發病與療愈。但時間軸一的敘事中卻留下了許多“格格不入”的懸念。比如,當王蒙聽步小芹講述蔡霞的精神病經歷時,善于為休養員保密的步院長尚未告訴王蒙蔡霞的個體往事,但時間軸一的敘事卻已經在字里行間透露出蔡霞的精神病發作與其“此生遭遇過重大的不幸”密切相關。而且當蔡霞的精神病被時間與音樂所療愈后,時間軸一的敘事又專門提到了空間旅游的治療作用,盡管入住霞滿天后的蔡霞從未進行過旅游:“為什么提到了空間的旅游?也還少有誰知道情況。霞滿天,并沒有旅游業務,小步他們還不敢組織古稀耄耋群體的大空間活動。”1王蒙:《霞滿天》,第32頁。個體的不幸與空間的療愈這些突兀的懸念要到時間軸二的敘事來揭露和解決。
其次,時間軸二(第10—18章)的敘事是蔡霞在聽說王蒙想了解她的故事后,她向步小芹自述了其1926年至1996年的人生經歷。該時間段所覆蓋的核心事件是蔡霞初婚意外喪夫、再婚意外喪子、后遭丈夫與干閨女雙重背叛婚變離婚、離婚后開啟了國內外全球化旅行。時間軸二的表層線性敘事是蔡霞前70年的人生經歷,但其深層敘事卻構成了以“病毒-免疫”模式為核心的疾病隱喻敘事,其中“病毒-免疫”模式兼具敘事結構功能與隱喻結構功能。時間軸二中的蔡霞處于一種大喜大悲、禍福更替的極端人生狀態中,她人生中的重要機遇與幸福和重大不幸與災禍總是螺旋纏繞、交替出現。蔡霞遭遇一次次苦難突襲后所作出的種種應對恰似遭受了病毒侵襲的肌體進行的一次次免疫對抗。這個多次突襲與對抗的“病毒-免疫”過程本身構成了時間軸二的線性敘事結構。同時從蔡霞的個體人生經歷來看,這個“病毒-免疫”過程也構成了關于人生狀態的疾病隱喻結構,其內里是對人性弧光與堅毅品格的贊美:“荒唐的痛苦正像一種病毒,摧毀生命的紋理與系統,同時激活了生命的免疫力與修復功能。我明白了,我不可能更倒霉更悲劇了。已經到頭,已經封頂。我蔡霞反而堅定了一種信心。”1王蒙:《霞滿天》,第51、75頁。為了應對突襲而至、不得不全盤接受的災禍與苦難,蔡霞采取了種種有效措施來向外發泄和向內修行。她購買健身器材鍛煉身體,她排演話劇、用文藝充實自己,更重要的是她去新疆、西藏、云南、四川、甘肅、青海、布拉格、維也納、俄羅斯、北中南歐洲名城、突尼斯、尼日利亞、好望角、伊朗、埃及乃至南北極等地進行國內外全球化旅行。對于蔡霞而言,“空間”成為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與自我救贖手段。至此,時間軸一中的懸念得以解決,但王蒙同時又在時間軸二里埋下了更大的懸念,即蔡霞為何在2012年突然中止了全球化旅行(空間自療)而入住霞滿天養老院。這個懸念的揭曉與環形敘事的閉合則要在時間軸三里完成。
最后,時間軸三(第19—21章)的敘事是一種第三人稱全知敘事。2021年,在霞滿天養老院,王蒙終于見到了95歲的蔡霞,蔡霞在慶生攝影展上講述了她南北極旅行的故事。當王蒙問她為什么在2012年終止了全球化旅行時,蔡霞微笑不答,步小芹則小聲告訴王蒙,“二〇一二年初,中日友好醫院查體時候發現她的淋巴結有變化……”2王蒙:《霞滿天》,第51、75頁。這顯然是一種強暗示,正是突襲而至的更大災難、極有可能是癌癥的重大疾病迫使蔡霞停止了自我療救的空間旅行。因此,時間軸三的敘事仍是一種雙層敘事,其表層敘事是對王蒙與蔡霞故事結局的交代,而深層敘事則是對以蔡霞為中心的環形疾病敘事的完成。2012年既是小說正題部分疾病敘事的時間開端,也是小說主體疾病敘事的結尾,小說在完成全部敘事的同時,將蔡霞故事的結尾與開頭相連,形成了完美閉合的環形敘事結構。
而從以蔡霞為中心的完整環形疾病敘事結構來看,在時間軸一(2012—2017年)中同樣存在著雙層疾病敘事。時間軸一的表層敘事是關于蔡霞精神病發病-發展-自愈過程的完整敘事,而深層敘事則是關于“作為一種療愈方法的精神病”的敘事。蔡霞的精神病不僅是一種疾患,更是一種療愈方法。當歷經人生苦難的蔡霞再次遭受命運的重大突襲(罹患絕癥)時,她由外向式的空間自療,轉入了內向式的精神自療。“疾病是通過身體說出的話,是一種用來戲劇性地表達內心情狀的語言:是一種自我表達”1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頁。,蔡霞突然發作的自言自語、自戀自憐式的幻想性精神病是一種內向型的自我表達與“智能補償”。
結合時間軸三與時間軸二的敘事來重審時間軸一,會發現蔡霞發作的精神病不僅是療愈身體病變(癌變)的有效方法,也是療愈人生病變(苦難)的有效手段。發作精神病同樣是“病毒-免疫”模式下蔡霞應對命運突襲時所作出的免疫對抗。而歷經時間與音樂的自我療愈,從精神病中恢復過來的蔡霞,不但實現了身體的康復,還完成了人生境界的質的飛躍,她實現了由人境到圣境到佛境的提升。縱觀蔡霞的95歲人生,前30年(1926—1956年)是幸福的成長經歷與愛情生活,中間35年(1956—1991年)是災星噩運、禍福更替的極端人生苦難,而最后30年(1991—2021年)則是不屈不撓的決絕反抗與堅持到底的自我療救過程。當王蒙見到了95歲的霞滿天“院士”蔡霞時,他為蔡霞的超高齡美貌與神仙風度所折服。歷盡人生病變而又頑強自愈的蔡霞終于修煉到功德圓滿:“與天為徒,天人合一,莫得其偶,是為道樞。”2王蒙:《霞滿天》,第69頁。
由此,再來反觀由楔子和正題共同構成的雙重環形敘事結構,楔子部分其實與正題相似,其核心也是關于疾病/人生病變/苦難突襲的敘事。楔子中看似碎片式的關于王蒙(“我”)、“鐵胃人”、“沒情況兒”、姜主席等人生片段的隨筆式回憶,其共性內核都是如何應對人生病變(苦難突襲)這個問題。楔子中罹患咽喉病、口腔癌、頸椎病、心肌梗死等疾病的“他”和“他們”面對身體疾患、人生病變與命運突襲采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有的積極,有的消極,有的成功,也有的失敗甚至一敗涂地。“他們”的故事與正題中“她”(蔡霞)的故事共同構成了有意味的參差對照與疾病隱喻,在大小雙重環形敘事結構中共同揭示了《霞滿天》的小說主題:“不要怕偶然與突然的禍端,因為我們勇敢而且光明。”1王蒙:《后記:與日子一道》,《霞滿天》,第188頁。而這也正是小說題目“霞滿天”的內涵。
二 虛構的回旋與小說的寓言化
王蒙是一位言說欲極強的作家,這種強烈的言說欲不僅促使其小說語言經常處于一種汪洋恣肆、奔涌駁雜的語言流、詞語流狀態,還經常讓“王蒙”直接以對話者、旁觀者或敘事者的身份參與到小說敘事中,從而以“王蒙”的強在場感彰顯著作者對虛構的掌控與對小說的話語權。《霞滿天》就以“王蒙”的在場、作者的“破壁”與虛構本質的主動暴露彰顯著王蒙的強烈言說欲與對小說虛構的絕對掌控:“看官,以上是本小說的‘楔子’。您知道什么是‘楔子’嗎?……讀小說也是一樣,開個頭,對世道人情、生老病死感慨一番,顯示一下本小說的練達老到、博大精深,誰又能不‘聽評書掉淚,讀小說傷悲’?”2王蒙:《霞滿天》,第14、74頁。
除了作者的在場與虛構的直接暴露外,王蒙還在《霞滿天》中埋下了許多虛構的密碼。比如時間的“錯置”與“重版”。《霞滿天》是一部在“時間”上極其講究卻又極其“不嚴謹”的小說,與時間有關的“錯誤”總是過分明顯而又過于頻繁地出現于小說中,這是一種與虛構有關的有意味的時間形式。比如在第5章中,蔡霞2012年入住霞滿天時是76歲,但在第21章王蒙詢問蔡霞時卻說:“您為什么二〇一二年,在您八十六歲的時候停止了全球化旅行,變成霞滿天的‘院士’了呢?”3王蒙:《霞滿天》,第14、74頁。同一年發生的同一事件卻對應著兩個年齡點,這種時間上的“錯誤”提醒著讀者時間錯置的在場。比如第9章中,蔡霞在霞滿天春節聯歡晚會上用多國語言朗誦詩歌這一事件發生于2017年,但在第19章中,步小芹卻說蔡霞“自從二〇〇五年春節聯歡會上做了多種語言的朗誦以后,立刻被全院稱為院士”1王蒙:《霞滿天》,第66、40頁。,這不僅與第9章的時間線發生了沖突,更與第5章及第21章的小說敘事發生了邏輯悖反,因為在蔡霞故事的開篇與結局,她都是2012年才住進了霞滿天養老院,她根本不可能在2005年時就成為霞滿天的“院士”。再比如第13章中,薛逢春出軌干閨女小敏并致其未婚懷孕是在1988年,但在第17章中小敏生子卻發生于1991年秋天,一孕三年,這顯然不合邏輯也不符合常理。
總體來看,雖然與蔡霞相關的多個時間點因為數次出現的時間錯置而發生了時間線上的連鎖波動,但這些頻頻出現的時間錯置并沒有影響整體雙重環形敘事結構的閉合與完成。在有效的敘事中,重復必有意義,由于“在各種情形下,都有這樣一些重復,它們組成了作品的內在結構,同時這些重復還決定了作品與外部因素多樣化的關系”,因此“一部小說的闡釋,在一定程度上要通過注意諸如此類重復出現的現象來完成”。2J.希利斯·米勒:《小說與重復——七部英國小說》,王宏圖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這些反復出現的時間“錯誤”以時間的矛盾、邏輯的悖反與敘事的不自洽動搖了整部小說的真實性與可信力,強烈地彰顯了小說的虛構本質及其人物的隱喻性與符號性功能。為了提醒讀者時間“錯誤”的在場,王蒙不惜在敘事中直接揭露時間錯置與重版的可能:“是的,出嫁在一九五九年,似乎也可以說,同時是一九五六年,還同時是一九四五與一九四九年的重版,是時間的多重疊加……”3王蒙:《霞滿天》,第66、40頁。
此外,《霞滿天》中的文本嵌套與互文是更加隱晦的虛構回旋與虛構密碼。王蒙是一位善于在小說中嵌套文本的作家,依靠文本間的嵌套與互文,人物命運與小說主題往往能夠得到強化與加深。在《青狐》《笑的風》《猴兒與少年》等代表性小說中都存在著典型性的文本嵌套與互文,《笑的風》甚至在出版時以字體區別、變體引用等方式來強化文本間的嵌套性,這顯然也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但與以往作品對文本的直接嵌套不同,《霞滿天》中的文本互文以一種更隱蔽的密碼式線索存在。《霞滿天》在小說敘事中提到了王蒙的另外三部作品——《沒情況兒》《夜的眼》《初春回旋曲》。這三部小說的文本內容并沒有被直接嵌套于《霞滿天》中,但它們在《霞滿天》中的出現卻是一種強暗示,它給予了介入《霞滿天》文本的新線索,強烈地誘惑著讀者去發現《霞滿天》文本內外的互文。相較于《沒情況兒》和《夜的眼》,《初春回旋曲》在《霞滿天》中的地位顯然更高,它直接參與到了《霞滿天》的小說敘事與人物塑造之中:
九十五歲的蔡霞與八十七歲的王蒙見面,她笑著說:“我讀過你的《夜的眼》和《初春回旋曲》。”
“什么?回旋曲?”我一怔,一驚。
《初春回旋曲》一直在我心里,發表以后沒有一個人說起過它,以至于聽到蔡霞的話我想的是,好像有這么一篇東西,可是我好像還沒有寫過啊。
似有,似無,似真,似幻,似已經寫了發表了,似仍然只是個只有我知道的愿望。1王蒙:《霞滿天》,第74頁。
王蒙發表于《人民文學》1989年第3期的《初春回旋曲》是一部典型的元小說,它展現了小說虛構的不確定性與小說創作的正在進行時。《初春回旋曲》的開篇便充滿了“回旋”,小說在“我們”-“她”-“他”-“你”-“他”-“我們”-“我”-“你”的人稱回旋中,將小說的時間情境設定于一個有著慘白清冷月光的冬夜。就在這個“我”和“你”喝茶回憶往昔的冬夜里,“我”突然說起了一部1960年代寫的卻已丟失了的小說稿子。隨后,“我”便向“你”敘述小說稿的梗概,但“我”的敘述卻不是確定性的,而是在對小說的復述中加上許多不確定的“可能”。這種不確定性讓過去已完成卻未曾發表出來的小說進入到了“過去未完成時”,并在當下“我”的講述中重新進入了虛構的“現在正在進行時”。“我”所敘述的小說梗概成為該小說的第一種寫法,即現實主義寫法。隨后,在“我”與“你”的對話中,“我”分別在構思的假想中用階級斗爭的寫法、敵特偵察小說寫法、1980年代的身體寫作寫法、現代派與先鋒派寫法、等待戈多式的荒誕派寫法以及尋根小說式的新潮寫法等數次解構并重寫了這個圖書館管理員的故事。至此“我”的虛構想象被徹底放開,這部丟失的小說稿進入到了無限的虛構可能中。
《初春回旋曲》的小說敘事是一種雙層嵌套敘事:首先它的主體敘事是“我”與“你”的冬夜敘話,這是第一層敘事;在敘話中又嵌入了多種圖書館管理員的故事,這些小說中的小說、文本中的文本是第二層敘事。但當小說中“我”的文學想象進入無限虛構后,第二層敘事與第一層敘事發生了交叉混合。第二層敘事向第一層敘事的入侵,讓圖書館管理員的故事與“我”和“你”的故事在敘事上發生了嵌套融合。在雙層敘事相互入侵混合后,“我”敘述了這部舊日小說稿的結尾,由這個“不能保證這一切都是原文”的結尾來看,這部已完成卻未發表的小說其實是寫了一段已發生卻又從未開始的愛情。《初春回旋曲》作為一部小說中有小說的元小說,它以小說虛構的方式去回憶另一部已完成卻丟失了的小說,這種回憶性講述讓小說稿回到了最初始的存在狀態,即“回到了有待虛構有待生發的狀態”1曉華、汪政:《〈初春回旋曲〉斷評》,《文學自由談》1990年第1期。。而關于小說稿的虛構性敘事顯然是一種破壞性復述,它在不停的建構與解構中,讓回憶變成了虛構,讓小說的本真歷史文本在無限的想象與虛構中永遠地失落了。
顯然《初春回旋曲》與《霞滿天》之間構成了文本內外的強烈互文。在《初春回旋曲》中那部關于圖書館管理員等待姑娘的小說稿是一部已完成卻從未發表的小說,它以多種虛構的可能存在于文本嵌套的元小說敘事中,它的似完成又未完成、似存在又無法確定存在的虛構進行時與《初春回旋曲》本身的元小說敘事強化了小說的虛構性,讓“虛構”本身成為文本敘事的意義。而在《霞滿天》中,《初春回旋曲》就像那部丟失的小說稿一樣,它似乎早已存在卻又仿佛從未被寫過,它似乎早已經發表卻又好似只存在于王蒙的意愿之中。正像丟失的小說稿彰顯著《初春回旋曲》的虛構性,《初春回旋曲》也以虛構的回旋彰顯著《霞滿天》的虛構本質。《初春回旋曲》與《霞滿天》在“虛構”上實現了文本間的回旋互文共振。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楔子”部分也存在著類似的文本互文。《霞滿天》的“楔子”依靠回憶隨筆體敘事營造了一種類似于非虛構的敘事效果,但王蒙又巧妙地通過文本內外的互文,以強暗示動搖了非虛構敘事的真實性,暴露了小說的虛構內里。這部在“楔子”中具有強烈在場感與提示感的小說是《沒情況兒》。與《初春回旋曲》相似,王蒙發表于《人民文學》1988年第2期的《沒情況兒》同樣講述的是“我”和“你”的故事,小說的主體內容是“我”在一種類似于對話的獨語體敘事中講述“你”的故事與“你”的“沒情況兒”。這種獨語體敘事因為回憶的細節與個體的深情而充滿了可信的真實感,但《沒情況兒》的小說“緒言”卻在主體敘事開始之前就以小說家的強烈在場暴露了小說的虛構性:“創作,真是一件殘酷的事情。當你成為一個作家……這一切都是創作的啟示,創作的材料。”1王蒙:《沒情況兒》,《王蒙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頁。顯然,《沒情況兒》與《霞滿天》之間也構成了文本內外的強烈互文。《沒情況兒》的開篇“緒言”動搖了整部小說回憶式獨語體敘事的真實性與可信性,強化了小說的虛構性。而在《霞滿天》的“楔子”中,《沒情況兒》以關于虛構的強烈暗示,動搖了“楔子”回憶隨筆體非虛構敘事的真實性與可信性,強化了《霞滿天》的小說虛構性。
“虛構是文學的特權”2南帆:《虛擬、文學虛構與元宇宙》,《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5期。,縱觀王蒙70年的文學創作,其一直都是創造力與虛構力極強的作家。迷戀于小說“元宇宙”3王蒙:《寫小說是幸福的》,《小說評論》2023年第2期。的王蒙一直有意識地鍛煉自己的虛構力與想象力,即“虛構的能力要靠自個兒發展”4許婉霓:《春天的旋律 生活的密碼——“春天一堂課”側記》,《文藝報》2023年3月22日。。王蒙擅長以汪洋恣肆的語言與無拘無束的表達來進行縱橫捭闔、先鋒新銳的虛構,其內里則是對精神空間的極限拓展與極度放大:“我喜歡說的一句話是開拓精神空間,增益精神能力,包括想象力、聯想力、延伸力與重組及虛擬的能力。”5舒晉瑜:《為文進載,意猶未盡——王蒙創作70周年對談》,《中華讀書報》2023年1月18日。而《霞滿天》就是一部極其重視聯想、延伸、重組與虛擬的小說。《霞滿天》以作者的在場與虛構的暴露、時間的“錯置”與“重版”以及文本間的嵌套與互文形成了“虛構的回旋”與“虛構的在場”。《霞滿天》對小說虛構本質的有意暴露和對雙重環形敘事結構的刻意制造,均是在追求一種詩化寓言體小說效果:“王蒙從小就想寫這樣一篇作品,它是小說,它是詩,它是散文,它是寓言,它是神話,它是童話……”1王蒙:《霞滿天》,第33~34頁。顯然,王蒙想要寫作的是一種“文備眾體”的小說,而《霞滿天》就是一部典型的詩化寓言體小說,兼具“哲學的深邃”、“詩歌的激情”與“歷史的質感”2劉瓊:《王蒙中篇小說〈霞滿天〉:向汪洋恣肆的才華和不絕的創造力致敬》,《文藝報》2022年8月26日。。
結語:一部關于女性、國族與人類的寓言
王蒙的《霞滿天》以敘事的回旋與疾病的隱喻、虛構的回旋與小說的寓言化,在雙重環形敘事結構和文本內外的互文里,完成了一部關于女性、國族與人類的寓言。
首先,《霞滿天》是一部女性寓言,它是一部女性的贊歌。王蒙是一位善于書寫女性的男性作家,但《霞滿天》中的蔡霞不同于王蒙以往小說中的女性,“她”不是“我”的配角,更不是“他”的陪襯,“她”作為霞滿天中的塔尖院士,本身就構成了對“活著”與“生命力”的最高闡釋。
其次,《霞滿天》還是一部國族寓言,它是一部國家與民族的贊歌。縱觀王蒙70年的文學創作,其總是能夠在充分表達作家個體生命經驗的同時,將國家史、民族史與個人史同步融合,在個體的生命記錄中折射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發展史。與蔡霞困難重重、艱難非常的人生經歷相似,中國與中華民族也在歷史發展與民族復興中經歷了種種磨難、重重困難。因此,蔡霞性格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典型性格,“而是我們經歷的歷史滄桑在民族性格中的集體沉淀”3郭悅、郭珊:《王蒙:寫小說時,每一個細胞都在跳躍》,《南方日報》2023年4月2日。。《霞滿天》以蔡霞隱喻國族,以蔡霞的個人史隱喻國家史、民族史,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奮斗精神給予了崇高的贊美。
最后,《霞滿天》更是一部人類寓言,它是人類精神的贊歌。霞滿天的塔尖人瑞蔡霞顯然已經不僅僅是女性的代表,在極光中看到“堅強”、在南極反思人類該怎樣做人的蔡霞已經成為人、人性、人類的代表,“蔡霞是精神性的,王蒙標出了一種人格的高度”1吳俊:《好一部短篇紅樓夢》,《小說選刊》2022年第10期。,“王蒙先生的《霞滿天》所寫,何嘗不是關于人類的故事!”2何向陽:《女性知識分子形象及人格心理的文學探究——王蒙新作〈霞滿天〉讀后》,《北京文學》2022年第9期。王蒙的《霞滿天》立足當下、著眼全球,在宏闊的人類視野下,對以蔡霞為代表的堅毅良善、頑強勇敢、正直光明的人類精神給予了純粹的贊美與深情的歌頌。
綜合來看,《霞滿天》典型地體現了王蒙小說創作的新時代文學品格,也展現了新時代中國文學對“時代性、歷史性和文學性”3吳義勤:《現實書寫的新篇章——讀關仁山的長篇小說〈白洋淀上〉》,《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3年第3期。的有機融合。王蒙近年來的小說創作具有鮮明的“中華性的本位立場”與“人民性的價值指向”4白燁:《文藝新時代的行動新指南——習近平文藝論述的總體性特征探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5期。,在《生死戀》《笑的風》《猴兒與少年》《霞滿天》等作品中,王蒙根植于中國本土經驗,以自覺的文化自信與民族自信來建構新時代的“‘中國’的總體性”5李敬澤、李蔚超:《歷史之維中的文學,及現實的歷史內涵——對話李敬澤》,《小說評論》2018年第3期。,他從堅定的人民立場與強烈的家國情懷出發,在人類視野下,完成了對“中國故事”的文學講述。這既是《霞滿天》“回旋曲”中的王蒙“密碼”,也是王蒙新時代小說創作的共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