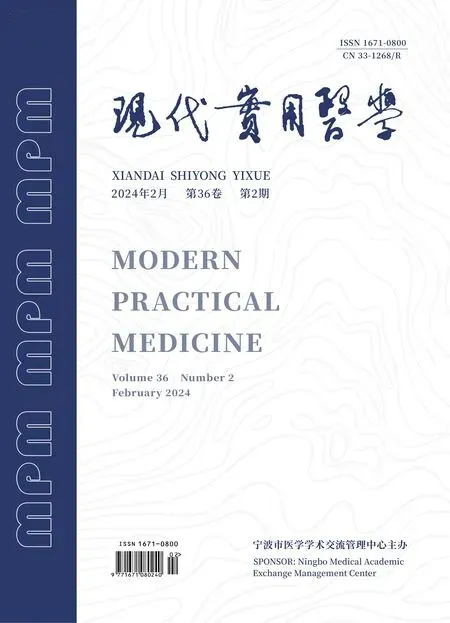成人支氣管哮喘氣道微生態及與細胞免疫關系的研究進展
鮑緒新,陳益靖,戴中
據報道,全球約有3.34 億人患有支氣管哮喘,其中約有4 570 萬成年患者[1-2]。在我國哮喘患者中,僅存在28.8%的患者被確診為哮喘,23.4%的患者接受過肺功能測試,而2017 年我國30 多個地區門診支氣管哮喘患者控制調查提示,我國城市地區支氣管哮喘總體控制率僅為28.5%[3]。這提示目前我國支氣管哮喘診療管理不規范的問題,為了改善這一現狀,對支氣管哮喘進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微生物組這一概念由MrCray 與Lederberg 首次提出,主要指與人類共享省空間的共棲、共生病原微生物的生態共同體[4]。隨后Ravel 與Marchesi 于2015 年將微生物組重新定義為整個棲息地,包括細菌、真菌、古細菌與病毒每種微生物及它們的基因組與生存環境[5]。近年來,有學者證實相較于健康人群,支氣管哮喘患者氣道微生態結構及各個菌群的相對豐度均產生了較大變化,尤其以嗜血桿菌、莫拉菌等變形菌門大量釋放為主[6]。目前有關支氣管哮喘病理機制未完全明確,但從免疫學角度分析,支氣管哮喘是由各種免疫細胞及細胞因子介導與相互作用而發生[7]。隨著對氣道微生態的探究,不斷有學者指出呼吸道中微生物的定植及細胞免疫變化之間的作用對疾病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1 支氣管哮喘的免疫學機制
自然界中充斥著較多的微生物,個體能在其中生存離不開自身的防御機制,即先天性與獲得性免疫系統。前者作為在個體內存在時間最長的防御機制,是個體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基礎[8]。而個體呼吸道的先天性免疫系統包括中性粒細胞、樹突狀細胞等細胞及非細胞成分,能對外部刺激產生非特異性反應,其中非細胞成分主要有乳鐵蛋白、防御素及干擾素等[9]。呼吸道免疫系統的第一道防線是氣道上皮細胞,可發揮清潔、屏障及免疫功能,當病原微生物進入機體后,部分伴隨呼吸運動呼出,部分聚集于呼吸道,伴隨纖毛運動將其運送至咽部被吞咽或咳出[10]。此外,氣道上皮細胞被活化后生成的白細胞介素(IL)-25 等上皮細胞因子及胸腺基質淋巴細胞生成素,有效連結先天性與適應性免疫[11]。獲得性免疫主要發生于患者被花粉、動物皮屑等過敏原接觸后,主要機制為機體Th1/Th2 免疫平衡被打破,過敏原特異性Th2 細胞被激活,生成一系列細胞因子調控過敏反應,即Th2 相關性哮喘表型。伴隨對支氣管哮喘表型研究深入,除Th2 型外還包括其他內在表型,但由于現階段尚未明確特異性生物標記物,人們對這些內在表型及其分子機制了解較少。
2 健康人群及成人支氣管哮喘患者氣道微生態特征
2.1 健康人群氣道微生態特征 人體呼吸道以甲狀軟骨為界線分成上呼吸道與下呼吸道,前者包括前鼻、鼻腔、鼻竇等結構,而前鼻內黏膜上存在較多漿液與皮質腺體,與外部環境距離最近,更易被棒狀桿菌屬、葡萄球菌屬等親脂性微生物定植[11]。下呼吸道包括聲帶下方喉部、氣管、小支氣管、細支氣管與肺泡,在以往認知中,該部分應是無菌環境,但隨著微生物檢查手段的發展,尤其是高通量16S rDNA技術的出現,已有學者于下呼吸道中檢測出微生物的存在。有學者認為,下呼吸道的微生物主要由上呼吸道微生物擴散而來,但也有研究發現下呼吸道富含上呼吸道中不存在的細菌種類,這提示上呼吸道并不是下呼吸道微生物的唯一來源[12-13]。氣道微生物對健康人群的適應性免疫反應的構建及協調微生物群、宿主與環境間的動態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同時氣道微生物還能夠誘導局部或全身上皮細胞、樹突狀細胞、中性粒細胞等因子生成,從而促進體內病原體的清除[14]。
2.2 支氣管哮喘氣道微生態改變 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微生物暴露、氣道細菌感染均可導致哮喘的發生,但其病理機制目前尚不明確。有研究指出,支氣管哮喘患者氣道內存在特定的微生物群,尤其是流感嗜血桿菌、鏈球菌等,影響疾病發生及發展[15]。白筱翠等[16]通過動物實驗,對小鼠進行高通量測序分析,將健康小鼠與支氣管哮喘小鼠支氣管組織切片進行病理學觀察,結果顯示支氣管哮喘小鼠呼吸道菌群較健康小鼠菌群豐度升高,放線及變形菌門增多,厚壁菌門下降,兩組小鼠菌群結構存在明顯差異,但該實驗統計分析的菌群與人體呼吸道微生態主要菌群存在一定差異。楊丹芬等[17]通過選取60 例支氣管哮喘患者為觀察組,35 例健康人群為對照組,對兩組呼吸道菌群進行觀察,結果顯示觀察組甲型鏈球菌占比明顯高于對照組,但該研究由于樣本量較少,病例代表有限,且從菌群豐富度、菌群特征、菌群類別等角度進行分析可能可以多角度反應氣道微生態改變具體狀況。此外,支氣管哮喘的發生與病毒關系同樣密切,當病毒入侵機體,其病原體相關模式分子能夠被先天性免疫中的受體識別,有效發揮抗病毒作用,同時樹突狀細胞被激活,介導特異性免疫清除作用;而哮喘患者存在部分免疫缺陷,抑制病毒活性降低,提高病毒感染風險。任天思等[18]研究通過對反復喘息患者依據支氣管哮喘預測指數進行分組,比較兩組病毒感染率及感染種類,結果顯示與陰性組比較,陽性組病毒感染率更高,感染種類更多,但該研究的對象主要為嬰幼兒,這與成人支氣管哮喘患者氣道病毒感染率及感染種類可能有一定差異。有研究顯示,氣道功能可被病毒經各種路徑影響,包括使氣道上皮屏障受損,在大量空氣變應原進入機體后,促進炎癥細胞等細胞因子大量釋放,引起氣道持續炎癥反應,是加重成人支氣管哮喘病情的重要原因之一[19]。
3 成人支氣管哮喘與先天性免疫的相關性
當細菌、病毒與氣道上皮細胞受體相結合時,能在細胞上內化或復制,生成先天免疫防御素。分泌性上皮細胞能夠生成IL-25、IL-33 等介導2 型黏膜免疫反應,還可以分泌防御素、溶菌酵素等抑菌肽,且上述細胞因子會刺激其他細胞類型,誘導下游Th2炎性反應[20]。
氣道黏液也具有重要的免疫功能,主要由水分與黏蛋白類、非黏蛋白質組成,黏蛋白含有豐富的糖蛋白,在成人氣道內主要表達為黏蛋白 5AC(MUC5AC)、黏蛋白5B(MUC5B)。有動物實驗指出,MUC5B 在氣道免疫防御機制中扮演重要角色,缺乏MUC5B 會打破免疫穩態,誘導肺部炎癥和慢性感染的出現[21]。此外,氣道黏液中還存在一切其他物質可與微生物相互作用,如噬菌體,噬菌體可暴露黏蛋白聚糖,阻攔細菌于氣道上皮細胞上定植,目前已有報道證實當噬菌體黏附于氣道黏液上能夠形成非宿主衍生的防御方式與細菌感染拮抗[22]。
作為一種特殊的抗原提呈細胞,呼吸道樹突狀細胞能夠連接先天性及適應性免疫系統,能夠攝取、加工并遞送過敏原。在過敏原進入機體后出現的免疫應答環節中樹突狀細胞的激活是較為重要的一環,過敏原能夠直接激活該細胞,且會被其他免疫細胞相互作用影響[23]。樹突狀細胞包括1 型、2 型樹突狀細胞,前者攝取過敏原后經過氧化物酶體、維甲酸等增殖物激活受體誘導Treg 細胞分化;后者則參與誘導Th17 與Th2 細胞分化[24]。
作為一類新發現的非B、T 細胞,固有淋巴細胞(ILCS)在全身多個組織中表達,可發揮適應性免疫功能。ILCS 包括ILC1、ILC2 與ILC3 三個亞群,ILC1即自然殺傷細胞,能發揮抗病毒效應;ILC2 可分泌IL-4 等Th2 型細胞因子,影響過敏性或非過敏性支氣管哮喘的發生及發展。有研究顯示,ILC3 在過敏性氣道炎癥中能單獨介導炎性反應的出現,而在非過敏性支氣管哮喘中,能經ST2-IL33 途徑生成2 型細胞因子介導肺部炎癥反應與氣道高反應性產生雙調蛋白,維持肺部修復功能與氣道上皮細胞完整性[25]。
4 氣道微生態改變與細胞免疫關系
4.1 氣道微生態與嗜酸性粒細胞的關系 成人支氣管哮喘依據細胞免疫途徑不同包括T2 炎癥型與非T2 炎癥型,其中T2 炎癥型支氣管哮喘以嗜酸性粒細胞分泌增多為主要特征,且T2 炎癥型是最為常見的一種類型,無論過敏或非過敏的狀況均可出現。參與T2 炎癥型免疫應答的細胞包括ILC2、TH2 細胞、B 細胞等,上述細胞均可分泌IL-13、IL-9、IL-5、IL-4等因子活化炎癥細胞,促進黏液分泌,引起氣道高反應與氣道重塑[26]。支氣管哮喘發病的過程中,流感嗜血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及普氏桿菌均發揮不同作用,3 種細菌能夠直接誘導嗜酸性粒細胞釋放各種趨化因子與細胞因子,如流感嗜血桿菌與普氏桿菌能誘導IL-10 的釋放,金黃色葡萄球菌能借助血小板活化因子受體直接活化嗜酸性粒細胞分泌IL-1 及腫瘤壞死因子-(TNF- )[27]。IL-10 作為一種抗炎細胞因子,主要由調節B細胞分泌,在免疫反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對單核細胞與巨噬細胞的作用主要為抑制炎性介質的產生與釋放及抗原呈遞,增強細胞吞噬作用;同時IL-10 能夠直接對CD4+T 細胞產生作用,下調Th1 細胞分泌的干擾素(IFN- )與IL-2細胞因子及Th2 細胞分泌的IL-4、IL-5。有研究表明IL-1 、TNF- 在支氣管哮喘患者體內高表達[28]。這些均可進一步證明流感嗜血桿菌與普氏桿菌具有抑制炎癥反應的作用,而金黃色葡萄球菌具有加重炎癥反應的作用。另有學者通過研究證實金黃色葡萄球菌能夠與Toll樣受體(TLR)2 相結合,誘導上皮細胞衍生細胞因子,如胸腺基質淋巴細胞生成素(TSLP)、IL-33 的釋放,進而導致T2 炎癥的出現[29]。
4.2 氣道微生態與嗜中性粒細胞的關系 非T2 炎癥型支氣管哮喘主要以嗜中性粒細胞浸潤及IL-8 高水平為主要特征,且Th17 與ILC3 細胞分泌的IL-17也可刺激嗜中性粒細胞分泌。支氣管哮喘患者上呼吸道檢測中發現的卡他莫拉菌與疾病的發生及發展有關,而該病原菌主要通過IL-17 與TNF- 依賴性炎癥反應加重HDM 觸發的過敏性氣道疾病。有學者通過動物實驗證明,流感嗜血桿菌能誘導巨噬細胞與Th17 細胞分泌Th-17 細胞介導嗜中性粒細胞炎癥反應的發生,這證實流感嗜血桿菌能通過調節氣道免疫反應促進非T2 炎癥型的發生及發展[30]。
利益沖突 所有作者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