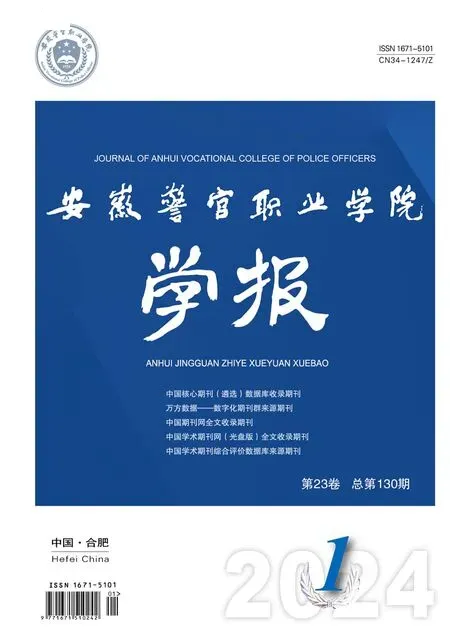法教義學視野下保理合同的規范要旨及裁判路徑
張文勝
(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1)
作為非典型擔保的一種形態,《民法典》首次對保理合同做出了專章規定,條文雖少(共9 個條文)但意義重大。它不僅在立法上首次確立了保理合同在我國合同體系中的獨立地位,其制度設計和法律構造,更是為我國建立統一的保理合同裁判規則提供了制度支持。但基于保理合同的復雜性和應收賬款形態的多樣性,在法教義學視野下對保理合同的規范要旨和裁判路徑進行深入探究,不僅有利于在理論上厘清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質和明晰保理合同的法律構造,規范保理業務的有序開展,更有利于在實務界推動保理合同統一裁判規則的建立,切實維護保理合同當事人的正當權益,以促進我國保理行業的健康發展。
一、保理合同規范要旨的厘定
(一)保理合同的法律構造
保理(Forting)是“保付代理”的簡稱,也稱托收保付,[1]最早是作為金融服務的一種模式出現在商業活動中。近現代意義上的保理肇始于16 世紀的歐洲,興起于19 世紀的美國。[2]我國自1987 年引入保理業務以來,歷經30 多年的成長和發展,目前保理業務量已躍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名副其實的保理大國。然而,《民法典》頒行之前,我國還沒有一部法律法規對保理或保理合同做出過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也未將保理糾紛作為獨立案由加以規定。雖然《中國銀行業保理業務規范》(2010 年發布)和《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2014 年發布)中對保理做出過相應規定,這些規范或辦法充其量也僅僅是部門規章,其效力階位較低,以至于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對保理合同規范要旨和裁判規則都存有較大的分歧,這不僅在理論上影響到我國保理合同體系的建構和法律適用的統一,同時在客觀上也妨礙了我國保理業務的規范開展和高質量發展。
對于保理合同的內涵如何界定?《國際保理公約》(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Factoring,1995 年5 月1 日生效)、《國際保理通則》(GRIF,2013 年修訂)、《中國銀行業保理業務規范》、《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以及我國《民法典》均做出了類似的規定。依據我國《民法典》第761 條,其內涵包括:(1)保理合同關系的主體是債權人(供應商)與保理人;(2)合同關系的內容是債權人(供應商)將其對債務人(客戶)現有的或將有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人(該應收賬款通常是基于債權人與債務人所訂立的貨物銷售合同而產生),保理人為債權人(供應商)提供資金融通、應收賬款催收、應收賬款債務人付款擔保等服務;[3](3)保理合同關系的客體是集應收賬款催收與管理、壞賬擔保及融資于一體的綜合性金融服務。[4]基于此,筆者認為保理合同的法律構造涉及到三方當事人和兩個法律關系。
首先,三方當事人即為債權人、保理人和債務人。第一,保理人并非一般民商事主體,而是須經國家金融機構批準可以從事保理業務的銀行和商業保理公司。因此,不具備保理資質的“保理人”訂立的“保理合同”無效,不能產生保理合同的法律后果。第二,盡管保理合同對債務人不產生拘束力,但由于債權人的融資本息需依靠債務人以其應償付的應收賬款來償還,若保理人不能獲得債務人應收賬款的償付,其可以要求債權人償還融資的本息或回購應收賬款,這將會直接影響到債權人訂立保理合同目的實現,并進而影響到保理業務的良性運行。從這個層面上看,債務人在保理合同中有類似于合同履行輔助人的角色,但其比一般合同履行輔助人的責任更重,尤其是在有追索權的保理合同中,它將面臨保理人直接追索的風險。
其次,在保理合同中存在兩個法律關系。一是應收賬款的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基礎法律關系,它是應收賬款產生的事實基礎,也是保理合同訂立的事實前提。也正是因為如此,法律不僅要求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應收賬款是真實、合法和有效的,而且還要求保理合同生效后,債權人與債務人不得隨意變更或終止基礎合同,即使有正當理由變更或終止基礎合同也不得對保理人產生不利影響。二是應收賬款的債權人與保理人之間的保理合同法律關系。在該法律關系中,債權人將其對債務人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人,保理人為其提供融資、應收賬款的催收和管理等綜合金融服務。應收賬款的轉讓是保理合同的核心,債權人將其對債務人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人并承擔該應收賬款瑕疵擔保是債權人的首要義務。此外,在有約定追索權的保理合同中,若保理人不能獲得應收賬款償付時,債權人還負有返還融資本息或回購應收賬款的義務。為債權人提供融資是保理人的主要義務,此外,對應收賬款進行催收與管理,即保理人催促債務人及時償還應收賬款,這既是保理人的義務,也是保理合同能否順利完成的關鍵。
基于此,保理合同的法律構造如圖所示:

(二)關于保理合同法律性質
對于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質,理論界一直存有分歧并形成了債權轉讓說、委托代理說、債權質押說、債權讓與擔保說、清償代為說、借款合同說、混合合同說[5]等多種學說,其中以債權轉讓說影響最廣。有觀點認為“保理其實無非是一種債權轉讓,受讓人通知、追索權及重復讓與的問題,其實依據債權讓與的規則均可解決”。[6]也有觀點認為“債權讓與是保理業的主導業務,是保理合同的主要內容,金融服務僅處于從屬或次要地位”。[7]但筆者卻認為此類觀點有失偏頗,盡管應收賬款的轉讓是保理合同得以訂立的基礎,也是保理合同最重要的內容,但其并不是保理合同的目的。雖然《民法典》第769條也規定“本章沒有規定的,適用債權轉讓的有關規定”。但保理畢竟是發端于商業貿易,債權轉讓說并不能完全涵蓋保理合同的內容并凸顯保理合同的本質。尤其在有追索權的保理合同中,若轉讓的應收賬款得不到清償,保理人則享有對應收賬款債權人的追償權,而在一般債權的轉讓中受讓人并不享有對債權人的追償權,此其一;債權人與保理人訂立保理合同的主要目的,是想從保理人處獲得融資,應收賬款的轉讓只是為其獲得融資而提供的擔保,具有權利質權的功能;保理人則是通過對債權人提供綜合性的金融服務而獲取利益。而在單純的應收賬款轉讓中,受讓人則是以獲取應收賬款為目的,此其二;盡管轉讓應收賬款是保理合同中債權人的主給付義務,但保理人為債權人提供資金融通、應收賬款的催收等綜合性金融服務卻并非是保理合同的從給付義務,而是與應收賬款轉讓相對應的主給付義務,并且該給付義務是保理合同典型、獨特的義務,缺少了該義務,保理合同則就不是保理合同。正如有學者指出,“保理不同于一般民事債權轉讓,還有些保理商不提供融資及壞賬擔保,僅為供應商提供銷售賬戶管理或代收應收賬款服務,不具有債權轉讓性質。”[8]此其三。
委托代理說則認為,鑒于保理脫胎于商業代理活動,保理人是債權人的特別委托代理人。保理業務與托收服務一樣,保理商與債權人之間為委托代理關系,保理商對債權人在賒購方式下產生的應收賬款進行催收。[9]但筆者認為委托代理說并不合乎保理合同的法律特征。盡管委托代理說發端于早期的保理業務,但卻無法解釋現代保理業務中資金融通這個核心功能;在無追索權保理合同中,保理人要自行承擔應收賬款得不到清償的風險,這與一般委托代理中代理的一切后果均由委托人承受的法律規定相矛盾;[10]同時,在保理合同中,債權人將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人后,意味著該應收賬款的所有權已移轉給保理人,這也不符合委托代理中一般不會發生權利移轉的法律構造。尤其是《民法典》第766 條規定,在有追索權的保理中,保理人既對應收賬款的債權人享有還本付息的請求權或回購應收賬款的請求權,又對債務人享有償還應收賬款的請求權,這說明我國《民法典》并不認可保理合同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因此,委托代理說不能成為詮釋保理合同性質的學說。
債權質押說認為,債權人之所以能從保理人處獲得融資,是因為保理人有債權人轉讓的應收賬款作為擔保,保理人可以通過債務人償付應收賬款來獲得融資款本息的清償,從這個層面上看,該應收賬款具有權利質權的性質。盡管債權質押說從權利質權視角為我們審視保理合同的法律屬性開拓了一條新的路徑,即債權人轉讓應收賬款于保理人具有為其獲得保理人的融資提供擔保的功能,但其與權利質權還是有著明顯的區別。首先,在保理合同中當債權人將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人后,其喪失的是應收賬款的所有權;而以應收賬款作為權利質權時,債權人并未喪失該應收賬款的所有權。其次,以應收賬款出質則是權利質權,具有從屬性和擔保物權的效力;而在保理合同中應收賬款的轉讓在本質上屬于債權轉讓,具有獨立性和債權的效力,保理合同一旦生效,保理人即取得債權人的地位,可以向債務人行使該應收賬款返還的請求權。再次,單純以應收賬款質押采登記生效主義,而在保理合同中債權人向保理人轉讓應收賬款則采登記對抗主義,登記與否不影響應收賬款轉讓的效力。
所謂債權讓與擔保說,是指擔保人(通常是債務人或第三人)將擔保標的物的所有權形式上轉讓于債權人,實質上則是以該標的物作為債務人債務的擔保,在債務人清償債務后,債權人將標的物所有權回轉于擔保人,債務未能得到清償時,債權人就該擔保物有優先受償的權利。盡管我國《民法典》對讓與擔保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但該法典第401條、第428 條關于流押和流質的規定,實際上是有條件地承認了讓與擔保的效力。從《民法典》第766條對有追索權的保理合同之規定來看,其比較合乎債權讓與擔保的法律構造。即債權人將應收賬款轉讓于保理人作為融資的擔保,當保理人的應收賬款得不到清償時,保理人既可以要求債權人主張返還保理融資本息或回購應收賬款,也可以向應收賬款的債務人主張應收賬款的債權。但以債權讓與擔保說來詮釋保理合同的法律屬性其最大的障礙在于:一是債權讓與擔保說無法契合無追索權保理合同的法律構造;二是債權讓與擔保說尚未得到我國現行法律的正式確認,以其來詮釋保理合同的法律屬性有名不正言不順之嫌。
借款合同說則認為保理實質上就是保理人提供融資,在本質上屬于借款合同。誠然,保理合同確實具有融資功能,融資也是保理人為債權人提供金融服務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但我們決不能將具有融資功能的服務合同都歸于借款合同的范疇。保理合同是以應收賬款轉讓為前提的金融業務,無應收賬款轉讓則不是保理。如果保理人與債權人僅約定應收賬款的催收則是委托合同;僅約定提供融資則是借款合同;僅約定以應收賬款為融資的擔保則為權利質權,但這均不是保理。在法教義學視野下,保理合同與借款合同的區別還是非常明顯的。首先,借款合同僅涉及債權人和債務人兩方當事人,而保理合同則涉及債權人、保理人和債務人三方當事人;其次,借款合同的內容就是資金的出借與返還,不牽涉到其他內容,而保理合同的內容除保理人為債權人提供融資外,還涉及應收賬款的轉讓、催收、擔保等內容;再次,借款合同的本息是由借款人償還,而保理合同的融資本息則是由債務人通過償還應收賬款來完成。
基于上述的分析,以單一的債權轉讓說、委托代理說、債權質押說、債權讓與擔保說、借款合同說來詮釋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質都是有缺陷的。筆者認為,保理合同在本質上是集應收賬款轉讓與催收、融資、擔保等于一體的合同,是一個獨立的混合合同。[5]也正是基于此,《民法典》第三編第十五章才得以專章的形式確立了其在我國合同法體系中的獨立地位。同時鑒于保理合同具有以應收賬款轉讓作為融資擔保的功能,《民法典》頒行后,有學者將其納于《民法典》第388 條“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范疇[11],作為一種非典型擔保的類型。對此,筆者予以贊同。
二、法教義學下保理合同裁判路徑的構建
(一)債權人虛構應收賬款的裁判路徑
基于應收賬款轉讓是保理合同中債權人的主給付義務,其對轉讓的應收賬款應承擔瑕疵擔保的義務。《民法典》第763 條就債權人與債務人通謀虛構應收賬款轉讓的情況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即債務人不得以該應收賬款不存在對抗保理人。換言之,即使轉讓的應收賬款是虛假的,保理人依然可以要求債務人承擔償還該應收賬款的責任。但需要說明的是,《民法典》第763 條在解釋路徑上并不是依據《民法典》第154 條之規定而是基于合同的相對性。因為依據《民法典》第154 條在債權人與債務人通謀虛構應收賬款(惡意串通)無效的情況下,債權人與債務人應對保理人承擔連帶責任,但《民法典》第763 條并沒有如此規定。而基于合同的相對性原則,債權人與債務人通謀虛構應收賬款的行為無效,這種無效僅在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產生效力,卻不能以之對抗保理人,是故保理人依然可以要求債務人承擔該虛構應收賬款的清償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763 條并未對債權人單方虛構應收賬款行為的效力做出規定,理論界和實務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存在真實、合法、有效的應收賬款是保理合同得以成立的基礎,如果債權人虛構應收賬款并將其轉讓,則保理合同就失去了事實基礎,保理合同應不產生效力。換言之,保理合同因其標的是虛假的而無效。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債權人單方虛構應收賬款的情況下,因其與債務人沒有通謀虛構的意思表示,不能單憑合同的標的是虛假的就簡單地判定保理合同無效。筆者認為,盡管保理關系的法律構造較為復雜,但對于保理合同效力的認定依然要遵循合同效力的一般規則。從我國《民法典》對無效合同的規定來看,一般包括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所訂立的合同無效、以虛假意思表示通謀的合同無效、雙方惡意串通損害他人權益的合同無效、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的合同無效,當然標的物自始不存在的合同也是無效合同。從保理人和債權人訂立保理合同的目的來看,保理人是希望通過保理合同獲得融資利息及保理費用,而債權人則是希望通過保理合同來獲得融資,在債權人單方虛構應收賬款轉讓的保理合同中,由于轉讓的應收賬款是虛構的,保理人訂立合同的目的不僅無法實現,而且還可能會造成損失,該保理合同因標的物自始不存在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實現而無效。因此,該應收賬款是否是債權人和債務人通謀虛構所為對保理合同效力不產生影響,只是對債務人是否具有對抗效力產生影響。在虛構通謀的情況下,該保理合同無效對債務人無對抗效力,保理人依然可以要求債務人承擔應收賬款的清償責任;反之,則對債務人有對抗效力,債務人可以拒絕保理人的履行請求。但需要強調的是,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基礎法律關系只是應收賬款產生的基礎,該應收賬款也只是保理合同中債權人融資款的擔保,債權人與保理人的保理合同關系并包括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基礎法律關系,基于該基礎法律關系產生的基礎合同也并非是保理合同的從合同。盡管在一般意義上該基礎合同的效力并不能對保理合同之效力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但保理合同的標的是否客觀存在則會直接影響保理合同的效力。
(二)以“將有的應收賬款”作為保理合同標的之裁判路徑
雖然我國《民法典》第761 條對“將有的應收賬款”能否作為保理合同法律關系的客體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并不能由此消弭學界和實務界對此而產生的爭議。所謂“將有的應收賬款”即未來債權,是指轉讓時尚不存在但將來可能會產生的債權。在民法理論上屬于“期待權”的范疇。對于未來債權的形態,我國臺灣學者史尚寬先生依據債權產生的法律關系是否存在將其分為三種,[12]一是存在基礎法律關系,待特定的條件成就或期限到來后就發生的債權。如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對將來一定時期某段高速公路的收費權、出租人對未來租金的收取權等;二是暫無基礎法律關系,但存在債權發生的部分要件。如債權人未來行使撤銷權或解除權所產生的返還請求權等;三是當前還沒有債權產生的依據,將來債權的發生僅存在蓋然性。房屋中介人員與看房者將來可能簽訂房屋買賣合同而產生的傭金等。后有學者在該學說的基礎上,根據未來債權發生是否存在基礎法律關系,將其分為有基礎法律關系的未來債權和無基礎法律關系的未來債權兩大類。[13]
對于具有基礎法律關系的未來債權,因其具有相對確定的取得來源和實現的可能性,在性質上是一種現實期待權,將其作為保理合同的轉讓的客體一般都沒有爭議。但對于無基礎法律關系的未來債權,因其發生具有或然性,學界爭議較大,實務界雖然肯定無基礎法律關系未來債權可以作為保理合同的標的,但堅持該債權須具有可讓與性。如山東省煙臺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魯06 民終3785號判決書認為,保理合同所涉債權可以是已經存在基礎法律關系的將有應收賬款,也可以是沒有基于法律關系純粹的將有應收賬款,但上述債權必須有特定的債務人,符合債權轉讓的法律特征,即所涉的將有債權必須能夠被轉讓,轉讓的債權應當可以被特定化。鑒于此,筆者認為,作為保理合同關系客體的應收賬款應具有可讓與性,這是判斷保理合同能否成立重要標準。對于“現有的應收賬款”因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基礎法律關系是確定的,應收賬款的數額是具體的,債權人對該應收賬款具有合理的期待,將其作為保理合同的客體學界和實務界均無異議;但若以“將有的應收賬款”作為保理合同的客體則需要法官對該應收賬款進行謹慎的審查核實,若該“將有的應收賬款”存在基礎法律關系,且該應收賬款具有可讓與性特征,則認定其作為保理合同的客體則是合適的;而對于無基礎法律關系“將有的應收賬款”,如果該應收賬款不能未來某一時期給保理人帶來確定性的合理期待并且不具有特定化,則不宜將其認定為保理合同的客體。否則,將會嚴重破壞保理合同糾紛的裁判規則,造成法律適用的不統一。
三、結束語
《民法典》對保理合同的確立,為市場經濟下我國保理合同體系的構建及裁判規則的確立提供了制度支持。但保理合同并不同于單純的債權轉讓,而是一個集應收賬款轉讓與催收、融資、擔保等于一體混合合同,涉及到保理人、債權人和債務人三方當事人,其權利義務關系復雜,尤其是作為保理合同客體的應收賬款,其構成形態多種多樣,更需要在司法實踐中審慎核實。在裁判路徑上,債權人和債務人虛構應收賬款對保理人不產生影響,但會影響保理合同的效力;在法教義學視野下《民法典》第761 條“將有的應收賬款”應排除無基礎法律關系的未來債權。囿于《民法典》保理合同章條文所限,從實用主義的視角當前亟需最高法院出臺相關司法解釋以及建立較為完善的指導性案例來確立統一司法裁判規則,以保障保理合同制度能夠順利運行,切實維護保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保理業務的健康可持續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