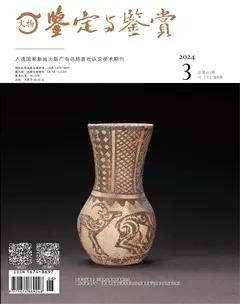何稠為綠瓷考
倪家 葛歸愚



摘 要:漢魏時期文獻所謂的“琉璃”主要指一類由西亞地區傳來的孔雀藍釉陶器。北魏時期,大月氏人在京師開始了國產琉璃器的燒制,但該技術并未于當時民間普及,未幾便失傳。因此,至隋代,何稠只得以中國本土技術生產的釉陶或瓷器,即“綠瓷”來模仿琉璃器。
關鍵詞:何稠;綠瓷;琉璃;孔雀藍釉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4.06.031
《隋書·何稠傳》載:“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①長期以來,學界對于“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一句的含義頗有爭議,其焦點在于何稠所為“綠瓷”究竟是何物,與“琉璃”的關系又如何。是故筆者不揣淺陋,擬對此展開探討,以求教于學界方家。
1 “綠瓷”與“琉璃”
曾有學者根據上文中“與真無異”一句提出何稠所為“綠瓷”即是“琉璃”。倘若如此,《隋書》大可直接將此事表述為“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復之”,而無須既將“琉璃”一詞以“綠瓷”相代,又云“與真不異”。《隋書》既云“真”,則必有與之相對的“假”,而此“假”只得是前文所謂的“綠瓷”。以較為通順的現代漢語對此句進行意譯,應作“何稠用‘綠瓷去模仿琉璃,看起來和真正的琉璃沒有區別”。所以,筆者認為何稠燒造的“綠瓷”是一種與“琉璃”在外觀甚至性質上都極為接近的產品,它們可能均屬于現代陶瓷科學所認定的釉陶或瓷器,但在古人看來二者仍有區別。
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何為“琉璃”?有學者將此譯作“帶彩的陶器”。筆者對此頗為贊同,但通讀文獻,則可進一步發現并非所有“帶彩的陶器”均是“琉璃”,“琉璃”通常情況下只是某一類釉陶的專稱。畢竟中國自戰國秦漢以來便生產綠釉、褐釉、青釉等類別陶器(圖1、圖2),且流布范圍較廣,數量頗多,卻未見有任何資料表明此類中國本土生產的釉陶器在古代曾被稱作“琉璃”。此時期文獻多將“琉璃”當作寶物,這顯然與數量龐大的國產釉陶器不相符合,且文獻多強調“琉璃”非本土產品,如《鹽鐵論》即將琉璃歸入“外國之物”②,或可據此認為此時期的“琉璃”是指外國來者。
檢索隋唐及此前文獻,關于琉璃顏色的描述以青色或綠色居多:如《漢武洞冥記》載“青琉璃為扇”③,《搜神記》載“車上有壺、磕、青白琉璃五具”④,《西京雜記》載“窗扉多是綠琉璃”⑤。此外,《漢書》亦載:“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逾于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⑥孟康對琉璃之注表明當時人們認為通常情況下琉璃即是青綠色,而《魏略》所謂的十色琉璃或并不都是常見品種,大量出口至中國的應只有青綠色一種。《一切經音譯》亦云:“琉璃……此寶青色。”⑦由于中國本就能生產綠釉陶器,故筆者推測《西京雜記》所謂的“綠琉璃”也應指偏青色,而非純粹的綠色。明確了此一時期文獻默認琉璃是青綠之色,便不難理解何稠為何獨以“綠瓷”去模仿“琉璃”。
回看《隋書·何稠傳》,除前文強調的后半句以外,此段文獻的前半句也值得推敲。琉璃屬佛教七寶,歷來為古人所珍視。作為極富商品價值的寶物,陶瓷匠人沒有理由不對此技術進行研究或仿燒,如此便與“匠人無敢厝意”一句相違背。“厝意”是“注意,關心”之義,以現代漢語解釋此句,即“沒有匠人敢于關心琉璃這門技術”,這說明了琉璃技術始終未能復燒并不是陶瓷匠人多番嘗試卻始終失敗的結果,而是根本沒有匠人敢于涉足這門技術。眾所周知,在古代封建社會中有能力做到如此程度限制的唯有政府,這也解釋了為何何稠有資格接觸琉璃技術。何稠于“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且“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逾所獻者,上甚悅”。此時的何稠已有官方身份,且據其仿“金綿錦袍”一事推測,何稠仿琉璃可能也是隋文帝授意。
此外,通讀《隋書》對何稠的描寫,在連續敘述何稠仿制波斯金綿錦袍及琉璃兩事之前,其先是交代了何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筆者認為,這種敘述順序及方式或暗示了何稠仿制波斯金綿錦袍及琉璃均是他“博覽古圖,多識舊物”的結果,即其以隋以前書籍中記載的古技術來進行仿制。故《隋書》刻意強調了“稠錦”在質量上優于波斯進貢者,此錦或許與“綠瓷”一般都只是在外觀上與原物近似,制作技術上或有所不同,畢竟僅憑外來成品是難以完全了解其制作技術的。或有學者將何稠習得琉璃燒造技術的途徑歸結于其來自西域的祖上,那么文獻有載的其祖何細胡、舅何妥及父何通亦應掌握這門技術。從文獻來看,稠祖何細胡已居郫縣,至何稠十余歲時則居江陵,后遷長安。由此可知,何稠久居漢地,身邊除祖、父、舅等直系親屬以外應無其余途徑可習得西域“奇技”。而前揭稠祖、父、舅三人從事的手工業門類是織造及斫玉兩項,并不包括燒造琉璃。并且后來何稠所參與的“參典山陵制度”“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連”及“制行殿及六合城”等事均非其祖上所能傳授⑧。故何稠習得“綠瓷”燒造技術的來源應屬“古圖與舊物”,同時“綠瓷”之“瓷”反映了何稠是以中國本土技術生產的釉陶或瓷器來仿燒琉璃器的。
2 “遂賤”與“久絕”
曾有學者據《魏書·西域傳》的記載認為魏世祖時大月氏匠人于京師鑄五色琉璃一事的直接結果是“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⑨,中國本土也開始了料珠類琉璃質飾件的生產。而前文已述,在隋代,由于政府的限制,民間工匠不得進行琉璃的燒造,而此種禁令或自北魏便有之。此外,即便琉璃于北魏以降實現了在民間相當程度的普及,造成了“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的結果,那便更難以想象這門技術會在短短百余年內失傳。并且與此前的五胡亂華時期相較,北魏時期人民生活水平確有所提高,但也遠未達到足以追求琉璃這類非生活必需品的水平,考古出土的此一時期釉陶器數量較兩漢時期大為減少亦可為證。既然琉璃于民間并非人人皆有,那便勢必不會造成“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的結果。從目前考古發現來看,我國境內出土的唐宋以前外來陶瓷器較少,且品種單一,均為西亞地區生產的孔雀藍釉陶器。此類器物多出土于唐宋時期遺存,時間可早至唐代以前者僅見廣西合浦寮尾東漢晚期墓M13b出土的一件執壺(圖3)⑩。
在開展進一步討論前,首先需解決的問題便是至遲于戰國已掌握鉛釉生產技術的中國為何需借助大月氏人來生產五色琉璃的建材?筆者以為西亞地區的琉璃磚的釉色以孔雀藍占絕對多數,綠釉及褐釉者鮮見,而綠釉及褐釉兩類釉陶是中國工匠本就有能力燒造的。所以魏世祖指派大月氏人燒造的“五色琉璃”應主要是中國匠人尚不能燒造的孔雀藍釉器。
《漢書·地理志》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赍黃金,雜繒而往。”k有學者提出所謂的“璧流離”即“碧琉璃”,“璧”字并非玉璧之義,而只為突出其珍稀性。此說是否正確尚待驗證,不過即便將“璧流離”依字面意思理解,即作“璧”這一器形的琉璃,那也不難想象此類僅作配飾之用的琉璃因尺寸較小,所以今天的考古發現中難以見到。而《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表明曾有自合浦出發的船隊于國外購得“璧流離”,那么如若琉璃確指孔雀藍釉陶器,則合浦出土的這例孔雀藍釉陶執壺便有了文獻上的佐證。當然,以目前可見的零星考古資料來推斷古代外來陶瓷對中國的影響顯然不甚科學,不過此類孔雀藍釉陶器在外來陶瓷器中所占比例之高,在釉色及性質上與文獻中的“琉璃”極為接近且出土地點和文獻記載相合應非純粹的巧合。此外,由于我國直至金元時期方可燒造孔雀藍釉瓷器(圖4),且孔雀藍釉屬堿釉與我國傳統的鉛釉工藝有根本上的區別,如此又可解釋何稠為何不得“琉璃”燒造之要領,而只得以“綠瓷”在釉色上盡可能模仿。
據《魏書·西域傳》記載,來華燒造五色琉璃的大月氏人來到首都平城最初的目的只是做買賣,然而他們在此過程中不知為何提到自己具備燒造五色琉璃的能力,自此之后他們來華的任務便改作燒造琉璃。這批大月氏人是在何種情況下提到自己能燒造琉璃已不得而知,不過此后的一系列活動均應與政府有關。此段文獻中共記載有兩次大月氏人燒琉璃的情況,其中后一次燒造的指派者顯然是北魏政府,甚至是魏世祖本人,而前一次的指派者則不甚清晰,或亦是北魏政府,畢竟對琉璃需求之大使大月氏人需專門建窯者除政府以外恐無第二人。據文獻記載,后漢、晉、宋、齊、北齊、隋及唐諸朝均設有管理陶瓷燒造事宜的甄官署,故推測北魏時亦應設之,限制民間工匠仿造琉璃或是其任務之一,而于京師設窯燒琉璃一事無疑也需經甄官署的批準。筆者認為大月氏第一次燒造琉璃或是試燒性質,此次燒造的成品是何物文獻并未明確交代。而當北魏政府見到其成品之光澤美于“西方來者”時便下令大月氏人繼續燒造行殿的建材。由此看來,由大月氏人建造的這處琉璃窯自始至終屬一處“官府窯場”,其服務對象或僅有北魏政府,并不為民間服務。如此帶來的問題便是既然大月氏人生產的琉璃專供朝廷,那么為何會造成“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的結果?筆者認為這當與魏世祖下令燒造的行殿有關。
《隋書·宇文愷傳》載:“時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后賞賜不可勝紀。”l又同書《何稠傳》載:“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m由此可見,“行殿”即“觀風行殿”的省稱,其內可容衛士百余人,而最關鍵的特點是可以移動。
復看“乃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一句。筆者認為此處“行殿”亦指“觀風行殿”的證據在于其強調了“容百余人”,若只是修建尋常宮殿,則無需強調可容納人數。再者,用于制造行殿的琉璃是在京師鑄造的,那么行殿完成后能夠見到的想必也唯有京師人民,畢竟“行殿”雖可移動,但仍難以想象其可用于長途運輸。所以宇文愷是直接在北方前線制造觀風行殿,而不是在京師制造再一路前進到北方。京師人口眾多,“行殿”想必經常在京城里開動,作耀武揚威之用,所以大量百姓見到行殿的同時也必定見到了覆蓋其上的琉璃建材。以往“西方來者”的琉璃對于普通百姓而言是但聞其名不見其實的寶物,而至北魏,通過行殿這一媒介,普通百姓雖然仍不能擁有但終究是得以見到了琉璃之實物,由此造成了“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的結果。
據此看來,文獻中未見有中國本土匠人參與琉璃燒造的記載,琉璃在民間的傳播也并不是以實物的形式,故已為普通百姓所熟知的琉璃技術竟會在短短百余年間失傳實屬正常。前文已述,大月氏人建造的這處琉璃窯屬一處“官府窯場”,故其生產狀態想必是“有命則燒無命則止”。一旦北魏或是后來的北朝皇帝對琉璃燒造失去了興趣,長期未下令燒造,甚至這批來華燒造琉璃的大月氏人一旦回國,均可能造成琉璃技術的失傳。若是琉璃技術在民間得到了普及,這一技術要徹底失傳則未必如此容易。
3 結論
漢魏時期文獻所謂的“琉璃”主要指一類由西亞地區傳來的孔雀藍釉陶器。北魏時期,大月氏人在京師開始了國產琉璃器的燒制,但該技術并未于當時民間普及,未幾便失傳。因此,至隋代,何稠只得以中國本土技術生產的釉陶或瓷器,即“綠瓷”來模仿琉璃器。
注釋
①魏征.隋書:卷六十八:何稠[M].北京:中華書局,2010:1596.
②桓寬.鹽鐵論:卷一:力耕第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5.
③郭憲,《漢武洞冥記》,陽山顧氏文房小說四十種本。
④干寶.搜神記:卷一[M].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10.
⑤葛洪.西京雜記:卷一:昭陽殿[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46.
⑥班固.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第六十六上[M].北京:中華書局,2007:3885.
⑦慧琳,《一切經音譯》卷二十三,清道光二十五年至咸豐元年番禺潘氏刻光緒十一年增刻匯印海山仙館叢書本。
⑧魏征.隋書:卷六十八:何稠[M].北京:中華書局,2010:1597-1598.
⑨魏征.魏書:卷一百二:列傳第九十西域[M].北京:中華書局,1999:2275.
⑩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縣博物館,廣西師范大學文旅學院.廣西合浦寮尾東漢三國墓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2012(4):489-545,551-566.
k班固.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下[M].北京:中華書局,2007:1671.
l魏征.隋書:卷六十八:宇文愷[M].北京:中華書局,2010:1588.
m魏征.隋書:卷六十八:何稠[M].北京:中華書局,2010:1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