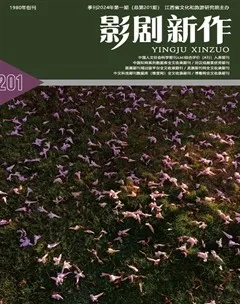贛劇《紅樓夢》的時空敘事
宋來源
摘要:贛劇《紅樓夢》分為“結社”“興社”“衰社”“散社”四折和“元春省親”“寶玉挨打”兩個楔子。全劇結構完整,符合戲曲結構的“起承轉合”,但導演張曼君在戲曲傳統敘事的基本遵循下,在時空敘事功能上做出多種嘗試,如劇目整體空間氛圍的營造,為表現經典場面在戲劇結構上的巧妙構思,通過心理空間、虛擬空間大大拓展戲劇表現維度,這些共同構成了贛劇《紅樓夢》獨特的時空敘事藝術。
關鍵詞:時空敘事 戲曲寫意 隱喻表達 經典場面
贛劇《紅樓夢》由羅周擔任編劇,張曼君執導。劇目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以詩社的發展為線索對《紅樓夢》進行敘事結構的重新組織,通過詩社的“結社”“興社”“衰社”“散社”來表現大觀園內個人和家族命運一從興盛走向衰敗。全劇結構完整,符合戲曲結構的“起承轉合”,但導演張曼君在戲曲傳統敘事的基本遵循下,在時空敘事上進行了諸多創新性探索。
一、充分遵循“戲曲寫意”的時空觀
戲曲是集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于一身的高度綜合的藝術。基于寫意的美學基礎,戲曲在時空的運用上是不固定的,對于流動時空的呈現有著屬于自身的特點。這些特點在贛劇《紅樓夢》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舞臺布景的寫意性。“中國戲曲的總體思想是寫意的藝術創造,盡管它的舞臺表演也有寫實的內容,但其總的精神是寫意的,排斥寫實布景的存在。”贛劇《紅樓夢》在舞臺的布景上整體色調以黑白灰等冷色調為主,將圓月、折枝、花瓣等意象融入舞臺背景,同時加入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書法、國畫等元素,簡約而不簡單,給人以空靈、悲切之感。
二是時空處理的靈活性。“中國戲曲藝術最獨特的舞臺原則之一,是時間與空間表現的靈活自由,是舞臺時空觀的十分超然而頗帶主觀的色彩。”贛劇《紅樓夢》在舞臺場景切換中,憑借可移動門框和椅子的變化以及燈光的移步換景,將一個個不同的時空場景呈現在觀眾面前,場景的切換或隨著主人公的一句唱詞、一句念白或者一個動作自由變化。如第一折結社中,從詩社比詩場景、到寶玉心理空間演繹,再到回憶“黛玉葬花”和“共讀西廂”場面,最后轉景回詩社,這一系列的空間切換靈活自由,既表現了詩社姑娘們的詩意才情,又有人物內心世界的呈現,同時還將紅樓經典場面穿插其中,這樣的處理大大豐富了劇目表現內容、拓寬了表現維度。
三是由演員來完成戲曲的景。面對極簡美學的舞臺設置,“要實現時間的虛擬、流動和空間的流動,最主要的是靠表演。演員的表演能夠和需要表現出社會及自然環境,表現人物的性格、感情和作品的意韻。”由此可見,演員在戲曲敘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面對簡約的舞臺布景,贛劇《紅樓夢》的場景轉換更多地是由演員實現的,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如“湘云醉臥”,劇目整體舞臺背景無法表現山石僻處,整個表演就是通過史湘云和一把椅子來表現,舞臺將史湘云置于前景,通過人物唱詞和使用團扇、酒杯等道具的動作,將一個直率純真、美麗動人、憨態可掬的少女形象塑造得非常到位,再現了“湘云醉臥”場面的詩意和美感。
二、物理空間的隱喻表達
贛劇《紅樓夢》的舞臺空間設置簡潔干凈,給人以空靈、悲切之感,可以說是“有”與“無”、“好”與“了”的隱喻表達,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主題契合。
異質空間帶來疏離感。全劇以“結社”“興社”“衰社”“散社”為基本敘事線,兩個楔子作為劇情交待,在時間上游離于“詩社”時間軸線外,在空間的處理上也存在特殊化。全劇在空間的設置上運用了可活動隔板來分隔空間,但唯獨在楔子處使用了白色框架,像是一個獨立空間的存在,與觀眾和劇中人物都存在距離感,容易讓人感到壓抑。這樣的特殊化處理隱喻意味很強。賈元春和賈政作為封建禮教的捍衛者,顯然與詩社眾人詩意化的青春氛圍有些格格不入,用白色框架隱喻他們自身處在封建牢籠之中,卻又或直接或間接釀成了“寶黛釵”愛情悲劇,與其他空間人物有很強的疏離感。
空間并置形成強烈對比張力。空間并置打破了故事情節的線性表達,將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發生的事情呈現在同一舞臺時空,拓寬了舞臺表現空間,增加了舞臺表現張力,有助于觀眾在多維空間中捕捉信息,與舞臺作品產生共鳴。贛劇《紅樓夢》在“釵黛掉包”情節上,將寶玉、黛玉、寶釵三人同時呈現在舞臺上,舞臺被分成了兩半,一半是瀟湘館里黛玉病重的畫面,清冷凄清;一半是怡紅院里寶玉和寶釵大喜之日,大紅喜慶。這兩個舞臺的并置,讓兩個氛圍完全不同的場景同時呈現,讓觀眾更為直觀地感受到三人的愛情悲劇,寶玉從之前站在黛玉邊旁白時的大喜,到揭開蓋頭那一瞬間的大悲,在這大喜與大悲的無縫對接中,悲劇意味愈發明顯。
舞臺空間劃分具有隱喻性。如贛劇《紅樓夢》在第三折衰社中,寶玉挨打后,黛玉和寶釵同時去看望寶玉,三人在同一舞臺演唱,舞臺被可移動隔板分割,以1:2的比例呈現,其中寶釵單獨占舞臺三分之一空間,寶玉和黛玉同時占舞臺另外三分之二空間,這種空間化的處理,也是人物關系的映射,寶玉和黛玉才是心心相惜的有情人。第四折散社中,劇目通過帷幕將舞臺的縱深分割為前景和后景,黛玉一人在前景中焚燒詩稿,詩社其他女性在帷幕之后焚燒詩稿,共同哀嘆著當下命運所帶來的心靈絕望。將“黛玉焚稿”改編為眾金釵同時焚稿,也正是對小說主旨“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最佳照應。
三、心理空間的敘事參與
贛劇《紅樓夢》在注重物理空間隱喻表達的同時,對人物心理空間的演繹也下了不少功夫,二者共同拓寬劇目的敘事維度,從而進一步深化主旨的表達。
以戲曲“打背供”的方式參與敘事。在楔子省親部分,面對元妃娘娘賞賜的差別對待,黛玉采用“背語”的方式念白:“新書一部、寶硯一方、金銀錁兩對……怎么到了她,便多出了這兩對錁子呢?”這一方面表現了黛玉的人物性格敏感,一方面也將黛玉的困惑拋給了觀眾思考。在第二折興社部分,元妃娘娘賞端午禮,寶玉和寶釵的相同,黛玉的不一樣,這時寶玉的心理活動同樣以念白的方式呈現:“怎么林妹妹的不和我一樣,寶姐姐的倒與我一樣?傳錯了,定是傳錯了!”這一方面表明寶玉的心意,他希望自己和黛玉一樣,而非寶釵,另一方面也揭開了之前黛玉的困惑,元妃娘娘支持“金玉良緣”,而非“木石前盟”。這在之后決定“沖喜”對象時賈母的話中得到了印證:“奈何鐘情太過,便生是非,想娘娘在時,賜下的禮份,也是這個意思。”劇目通過男女主人公寶玉和黛玉心理活動的外化,將兩人的內心感受向觀眾交待,但奈何現實不可能支持二人的“木石前盟”,這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作品的戲劇性,增強了人物內心感情外化的表現力,容易讓觀眾感受到人物因命運悲劇所造成的悲涼和無力感。
寶玉多處心理空間的演繹。劇目對寶玉心理空間的展示最為直接,在面對史湘云關于“蘅瀟之詩,你喜歡哪個?”問題時,寶玉進入心理空間,對寶釵和黛玉一一評價,同時表露個人心意:“這膀子若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她身上……”這一在當事人面前不好正面回答的問題,通過心理空間的演繹,讓觀眾一目了然。值得一提的是,劇目在處理心理空間和閃回有著明確的界限,在寶玉進入心理空間后,這一空間是與當下詩社品詩空間并行的,一個在舞臺前方,一個在舞臺后方;但后面回憶“黛玉葬花”,就只呈現葬花場面,并未處理并行空間,這可能也是劇目為做區分的有意為之。寶玉在“釵黛掉包”情節中,在揭蓋頭前的心理活動的外化表現十分精彩,從萬分期待,到想揭又不敢揭的心理演繹得十分到位,到最后驚心動魄的一揭,整個人魄亂魂丟,這段把寶玉性格里的“癡”表現得淋漓盡致,人物的心理狀態通過語言的外化,讓觀眾真切感受到寶玉冰火兩重天的心態,從而與主人公產生情感共鳴。
四、經典場面的時空重構
張曼君導演在訪談中曾經談到:“我完全忠實于原著的表達,只是在戲曲結構的方式上跟一貫的線性表達有所不同……正是為了尊重經典,包括文學經典和戲曲經典,我才會用到閃回。通過閃回,我可以把‘黛玉葬花‘寶玉瘋癲等這些經典橋段加進去。”
充分發揮楔子在時空敘事上的作用。將時間跨度大,卻又緊密關聯的情節用楔子交待。比如“寶玉挨打”。從時間線上講,寶玉挨打應當發生在“結社”之前,也正是有寶玉挨打后,賈政外出做官,才有寶玉和眾姐妹的這段美好閑暇時光。但劇目之所以安排在第二折后,以楔子的方式呈現,目的就是為了交待劇情,為后續寶玉與紫鵑二人的對話涉及挨打后,寶玉對寶釵和黛玉截然不同的態度,以及寶玉的心意做鋪墊。正是寶釵和黛玉二人在看待寶玉挨打后截然不同的態度,才能真正理解寶玉之前處處表明的心意:面對賞賜時,認為是元妃弄錯了;“這膀子若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她身上……”“好妹妹,這《西廂記》,我只愿共你一讀、只可共你一讀、只肯共你一讀呵!”“極是、極公,這都是瀟湘之作!”這些念白均是言語上的力證。
致敬經典,運用閃回呈現經典場面。“閃回在電影中主要是作為敘事方式而存在的”“其在電影中的功能主要有:揭示事件的原因和過程”。誠然戲劇在運用閃回手法時同樣也是一種敘述方式,在贛劇《紅樓夢》中出現的三次閃回場面就是主人公寶玉揭示內心的原因闡釋。這三次閃回手法的運用,都是通過寶玉的口頭敘述實現時間的跳躍:“想當日,一夕風雨……”句話帶出回憶“黛玉葬花”及“共讀西廂”情景;“紫鵑,我越來越明白啦,當日那頓板子,真把我打明白了。”帶出寶玉真切知道內心到底鐘情于誰。贛劇《紅樓夢》在這些特殊化處理中巧妙地將經典場面融入劇目結構中,是對經典的致敬,更是創作團隊對經典的藝術化表達的有益嘗試。
五、結語
張曼君導演說過,“贛劇《紅樓夢》一定要讓觀眾看到俗常的東西,但一定要把它完整化了,不能碎片化,它不能是一個像晚會拼盤一樣的東西。”為實現“完整化”追求,導演充分發揮了時空敘事功能講好紅樓故事。不論是對整部劇目空間氛圍的營造,還是為了表現經典場面在戲劇結構上的巧妙構思,亦或是通過心理空間、虛擬空間大大拓展戲劇表現維度,贛劇《紅樓夢》在實現時空敘事功能上做出多種嘗試,是對張曼君導演“實踐新的觀演關系的質變和突破”的有益探索。在現代化語境下,贛劇《紅樓夢》真正做到了用屬于現代人的視角來重新詮釋經典,實現經典的當代藝術表達。
責任編輯:伍文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