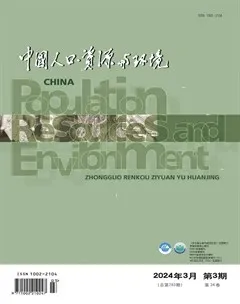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如何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
高長海 王鋒



摘要 地方政府生態保護的策略性行為選擇是影響其生態保護力度的關鍵因素。該研究在對各省份生態保護力度指數測度的基礎上,將生態保護與有為政府相結合,從策略性行為選擇的視角,考察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內在機理和市場化程度在兩者關系中的調節機制,并以2008—2021年中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為樣本,構建靜態面板模型和空間杜賓模型對上述機理機制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①各省份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均顯著提升;地理分區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表現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依次遞減,南方地區大于北方地區的格局;而增速則相反,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依次遞增,南方地區慢于北方地區;地理分區之間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梯度差表現為縮小的趨勢;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表現為“U”型特征,當前的影響表現為正向促進作用。②本地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鄰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具體溢出效果取決于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的策略性行為選擇;地理鄰近省份間的策略性行為選擇為“逐底競爭”,其空間溢出效應表現為反向;經濟鄰近省份間的策略性行為選擇為“競相向上”,其空間溢出效應表現為同向。③市場化程度是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調節機制;市場化程度對二者關系的影響表現為強化效應;且隨著市場化程度提升,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U”型曲線拐點值將向左移動。
關鍵詞 生態保護力度;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空間溢出效應
中圖分類號 F124. 6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4)03-0177-15 DOI:10. 12062/cpre. 20230912
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究竟如何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的“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為其指明了方向。作為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如何在對其改造和開發的過程中貫徹落實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既是以綠色發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實現的時代課題,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共同面對的重大問題。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性質,決定了市場資源配置機制難以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對環境要素的需求;只有政府適當的介入,才能實現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經濟高質量發展。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環境問題,不斷建立和完善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制度體系和法律法規,生態狀況得到顯著改善。但中國式分權及垂直式的治理體制,使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時具有較大的“因地制宜”裁量空間。一些地方和部門出于對資源流動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和標尺競爭效應的考慮,在執行生態保護相關政策時常表現出“謀利性”特征,具體表現為象征性執行、選擇性執行或消極執行等[1]。因此,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的大小,將會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加大生態保護力度”是決策層和學術界近年提及的熱點,但關于“生態保護力度”的研究,目前還處于理論甚至概念層面。本研究將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界定為地方政府執行生態保護相關政策的努力程度。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究竟如何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該問題的深入探討,可以為地方政府處理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提供依據。
1 文獻綜述
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生態保護問題。從“綠化祖國”到確立“環境保護”為基本國策,從“可持續發展戰略”到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從“生態城市”再到“美麗鄉村”,均是中國政府生態保護意志的彰顯。關于“生態保護”概念的界定,學術界雖然還存在爭論,但普遍認為生態保護就是人對自然界生態環境的保護和修復。保護主要體現在資源節約、污染治理和人居建設三個方面,即通過資源節約以減少人類活動對自然資源的不可持續性攫取,通過污染治理以減少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不可修復性破壞,通過人居建設以在滿足人們對宜居、健康、舒適生活環境需求的基礎上實現人工生態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共生。修復主要是指采取嚴格的監管和積極的保護措施,比如通過封山育林、育沙育草、補水保濕等措施封育自然生態系統,使其發揮自身生態的恢復力;或是針對區域流域范圍內嚴重受損、退化、崩潰的生態系統,采取恢復與重建的技術措施,解決已造成的生態破壞問題。人居建設作為緩解人工生態系統對自然生態系統造成不利影響的重要手段,不但是生態城市建設的必然要求,也是美麗鄉村建設的必經之路,更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體現。因此,沈國舫[2]認為,生態保護不僅要保護各種自然生態系統,人類賴以棲息的人工生態系統也要納入其中。鑒于此,本研究將“生態保護”的研究范圍界定為“資源節約、污染治理、生態修復和人居建設”四個層面。
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是指地方政府執行“資源節約、污染治理、生態修復和人居建設”相關政策的努力程度。關于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的研究,目前在檢索到的文獻中并沒有發現,與之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環境規制強度方面。現有研究中,度量環境規制強度的基礎指標可以被歸納為投入型、費用型和績效型三類。投入型指標主要包括資金投入、精力投入和保障型投入等。資金投入型指標主要包括污染治理投資[3]、環境友好型技術研發投資[4]和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精力投入型指標主要包括政府查處的環境違法企業數、環境規制機構對企業排污的檢查和監督次數和環境保護相關的行政處罰案件數[5]等。保障型指標主要包括制定的制度和投入的人員等指標,主要是指環境規制政策或文件的數量和環保機構人員數等。費用型指標主要包括與環境相關的稅收、行政費用和監管費用等,如排污費征收金額等。績效型指標主要是指污染物的利用率、去除率和污染物排放量或單位產值污染物排放強度等。現有研究既有選取單一指標作為環境規制強度的代理指標,也有將多個單一指標通過一定的方法進行加權求和或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測算環境規制強度的綜合指標。如傅京燕等[6]采用綜合指標法測算了中國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強度。相比而言,綜合指數法比單一指標法更能全面、客觀地反映環境規制強度。
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張軍擴等[7]認為,高質量發展是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的高效率、公平、綠色和可持續的發展;魏敏等[8]則認為高質量發展不僅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也有不少學者從新發展理念的視角探討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雖然不同學者從不同視角對高質量發展進行了詮釋,但普遍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就是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高質量、更可持續和更為安全穩定的發展。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現有研究主要采用的也是單一指標法和綜合指數法。單一指標法主要是將全要素生產率[9]、綠色全要素生產率[10]和勞動生產率[11]等作為代理變量。綜合指標法主要是以新發展理念為基礎,圍繞該理念或對該理念進行拓展選取基礎指標,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測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還有一些學者從不同視角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數進行度量。如聶長飛等[12]從質量和效益的視角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各省份的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數進行測度。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任保平等[13]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優路徑選擇應是符合價值邏輯要求的經濟系統、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三大系統之間的耦合與互動。
關于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當前主要集中在理論探討或兩者的耦合協調層面,而從策略性行為選擇的視角,考察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如何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相關研究在現有文獻中并沒有檢索到。與之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環境規制強度對企業行為、經濟發展的影響層面。這些研究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遵循成本說”,認為在環境規制加強時,企業會因為提升治污力度而擠占其生產費用或人力資本,進而造成生產成本增加,這既不利于企業提高生產率,也可能會因為環境成本過高而導致其選擇遷址,不利于當地的經濟發展。第二種觀點是“創新補償說”,認為當環境規制強度加強時,企業為了在競爭中長期保持優勢,將會選擇技術創新而不是遷址,創新產生的補償效應將部分甚至全部抵消環境規制帶來的“遵循成本”,這不僅有利于企業生產率的提高,也有利于企業盈利能力的提升,進而會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綜合來看,現有研究從不同視角探討了生態保護和環境規制強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并提出了豐富的見解,但仍存在著一些不足。具體表現在:一是當前關于生態保護力度的研究還處于理論甚至概念探討層面,與之相關的環境規制強度度量的僅是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或污染治理層面的努力程度,而在資源節約、生態修復和人居建設等方面的努力程度并沒有涉及。二是現有關于生態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兩者的耦合協調方面,而地方政府作為生態保護政策執行的主體,其努力程度究竟如何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其內在邏輯或理論機制有待進一步探討和揭示。三是現有研究很少關注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加大對企業或產業形成的“精選精洗效應”和“環境壁壘效應”。上述不足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空間。
2 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說
2. 1 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策略性行為選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生態環境的外部性決定了政府必須在生態保護中發揮主導作用。那么,影響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周業安等[14]將其歸結為地方政府間的競爭,即某個區域內部不同經濟體的政府利用包括稅收、環境政策、教育、醫療和福利等手段,吸引資本、勞動力和其他流動性要素進入,以增強經濟體自身競爭優勢的“謀利性”行為。在中國以經濟分權和行政分權為特征的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賦予了財政收入的“剩余索取權”,但保留了地方主要領導干部的人事任命權。在財政收入“剩余索取權”的激勵下,地方政府為獲得更大的財政收入往往偏向于實施契合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地方政府間的競爭。與此同時,地方官員為實現晉升,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員之間的晉升錦標賽。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地方政府非常關注競爭對手的行為,從而形成了地方政府競爭行為選擇的“策略性”。
就地方政府生態保護行為而言,地方政府競爭的策略性行為選擇大致可概括為“逐底競爭”和“競相向上”。“逐底競爭”是地方政府間為爭奪更多的流動性資源,爭相降低自身生態保護力度的策略性行為[15]。“競相向上”是地方政府間為爭奪更多的優質資源,爭相提升自身生態保護力度的策略性行為[16]。中央政府、社會公眾和企業的行為在地方政府生態保護“逐底競爭”和“競相向上”策略性行為選擇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在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剩余索取權”激勵和晉升錦標賽“相對排位的績效考核”激勵下,地方政府間通過資源流動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和標尺競爭效應三種渠道影響彼此的生態保護策略性行為選擇,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資源流動效應指的是資源在流動過程中具有方向性、靶向性、趨利性等特征,其流向某個地區的動力強度取決于該地區的區位條件、資源稟賦、基礎設施、政策法規、社會環境等方面的相對優劣程度。隨著區域間區位條件等因素的變化,資源流動的方向也會發生改變。因此,地方政府為吸引這些流動性資源,往往會通過改變財稅、土地、規制等政策手段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作為一種環境規制手段,不可避免地成為地方政府間爭奪流動性資源的工具。比如,地方政府為了競爭流動性資源,會爭相降低生態保護力度水平,形成相對于其他地區規制成本較低的區位優勢,進而形成地方政府間“逐底競爭”的策略選擇;也有文獻認為,地方政府的鄰避主義及對偏好優質環境的要素追逐,會競相提升生態保護力度水平,形成相對于其他地區優質資源的區位優勢,進而形成地方政府間“競相向上”的策略選擇。溢出效應是指一個組織的某項活動,不僅會產生活動的預期收益,而且會對該組織之外的人或社會產生外部收益,且這個外部收益是活動主體本身得不到的收益。就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的策略選擇而言,環境污染或生態改善具有跨界效應,在這種效應下鄰地政府往往存在“免費搭車”的心理,在這種心理作用下便形成了地方政府間“逐底競爭”的生態保護力度策略選擇。標尺競爭效應是指通過把代理人績效與在類似條件下的其他代理人績效進行比較,并以此為基礎衡量不同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標尺競爭效應相當于利用“相對績效”的比較來解決委托代理框架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就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而言,當競爭地區提高或降低生態保護力度時,本地區將秉承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根據競爭對手的生態保護力度選擇一個最優的生態保護力度水平。而這個最優的生態保護力度水平選擇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模仿”,即當競爭者加強生態保護力度或競爭者生態保護力度較高時,本地區將模仿競爭者跟隨加強生態保護力度,從而地方政府間形成“競相向上”的生態保護策略選擇;而當競爭者放松生態保護力度或競爭者生態保護力度較低時,本地區將跟隨放松生態保護力度,進而地方政府間形成“逐底競爭”的生態保護策略選擇,即在標尺競爭效應的作用下使自己在“相對績效考核”時不落后于競爭者。當然,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力度策略性行為選擇還會受到社會公眾和企業的影響。社會公眾作為生態公共物品的需求方,其生態環保訴求是地方政府生態保護策略互動的約束因素。中央政府的問責激勵和“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促使公眾環保訴求成為地方政府選擇“競相向上”行為選擇的壓力和動力[1]。企業的利益尋租容易使地方政府與企業合謀,衍生腐敗現象。利益尋租一方面扭曲了地方政府推動生態保護行為的動力,另一方面推動地方政府偏向于“逐底競爭”的生態保護策略行為選擇。
“逐底競爭”的策略性行為選擇,將導致生態保護力度整體較小,并通過以下3種途徑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消極影響:一是引致資源環境成本相對較低的“污染型”生產要素不斷流入,加大資源節約和污染治理的難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擠占生態修復和人居建設的投入,不利于綠色發展;二是引致對生態環境具有較高需求的“清潔型”生產要素(如人才)不斷流出,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三是固化產業結構的低端鎖定,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競相向上”的策略性行為選擇,將導致生態保護力度整體較大,并通過以下三種效應作用于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是“創新補償效應”,生態保護力度加大將倒逼企業進行生產技術革新和環保技術升級,由此產生的創新補償效應從長期看將抵消生態保護力度加大帶來的“遵循成本效應”,從而有利于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創新發展。二是“精選精洗效應”,包含“精選效應”和“精洗效應”。其中,“精選效應”是指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區的發展需要和生態環境空間對潛在進入者通過進入機制進行篩選的行為效應,該效應能夠阻止“污染型”生產要素流入、誘導“清潔型”生產要素流入,從而促進域內產業布局的合理化、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經濟發展的綠色化。“精洗效應”是指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區的生態環境目標通過退出機制強制與該目標相背離的在位企業退出或轉型的行為效應,該效應能夠引導低端產業和高碳排放產業的有序轉型和退出,有效改善由資源錯配導致的社會福利和經濟效率損失,促進域內的產業升級、技術創新和資源配置優化。三是“環境壁壘效應”,包括“環境標準壁壘效應”和“資金設備壁壘效應”。其中,環境標準壁壘效應,一方面指在位企業為達到新環境標準不得不采取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推進技術創新、轉型發展等,它們的這些行為將對其自身形成倒逼效應;另一方面指潛在進入者為達到在位企業所遵循的新環境標準,不得不采用更為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來跨越環境標準提升形成的進入屏障。資金設備壁壘效應,指在位企業為達到更高的治污標準,通常會使用更加先進的治污和用能設備,如此形成的在位企業規模經濟效應和對潛在進入者造成的機會成本、沉沒成本增加等壁壘效應。上述環境壁壘效應無形中增加了污染企業的進入成本和難度,從而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和資源配置優化產生促進作用。
綜上,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取決于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的策略性行為選擇。當地方政府間的策略性行為選擇以“逐底競爭”為主時,生態保護力度較弱,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當地方政府間的策略性行為選擇以“競相向上”為主時,生態保護力度較強,有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結合上述分析,提出假設1。
假設1: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表現為“U”型特征。
2. 2 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機制
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來自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策略性行為選擇造成的生態保護力度梯度差。具體而言,面對中央政府的生態保護政策,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在政策執行時根據被賦予的自由裁量空間常做出“謀利性”的策略性行為選擇。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驅使下產生的政企合謀現象,即對企業偷排行為等查處力度不足造成的生態保護政策實際執行力弱化,以及個別地方政府為實現經濟增長而放松生態環境管制、主動打造“生態環境政策洼地”的行為。當這種“謀利性”策略選擇表現為“逐底競爭”時,如果本地政府主動或被迫執行較強的生態保護力度,污染密集型產業則會瞄準周邊環境規制較低、區位條件優越、要素成本優勢明顯的地區。由于這些產業仍高于鄰地的平均生產率,鄰地政府有動機放松規制執行力以吸引其遷入,這將導致污染產業轉移,進而對鄰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負向溢出效應。相反,如果本地政府的生態保護力度低于鄰地,將造成鄰地的污染企業向本地轉移,進而會抑制本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可見,當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的策略性行為選擇表現為“逐底競爭”時,本地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將對鄰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反向的空間溢出效應。相反,當這種“謀利性”策略選擇表現為“競相向上”時,在長遠利益的作用下,本地較大的生態保護力度能夠通過學習和“示范效應”帶動鄰地政府增強生態保護力度,進而對鄰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促進作用。同理,鄰地較小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將不利于本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究其原因,地方政府間的模仿、學習、競爭使其政策執行力度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產生了“共振效應”,在該效應的作用下,這些地方政府間形成了經濟空間俱樂部趨同。可見,當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的策略性行為選擇表現為“競相向上”時,本地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將對鄰地產生同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2。
假設2:本地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鄰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具體溢出效果取決于地方政府間的生態保護策略性行為選擇。
2. 3 市場化程度、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市場化程度反映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程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經濟體的法治水平、行政水平和市場制度完善程度等。具體到生態保護領域,市場化程度能夠通過地方政府環境信息公開,以及產品和要素的資源配置效率等對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產生影響。具體而言:首先,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推動了地方政府信息公開等相關行政制度的完善,增強了法治的透明度,壓縮了地方政府在生態保護策略性行為選擇時自由裁量的空間,緩解了政府權力因得不到有效監督而產生的企業“尋租”行為,從而有利于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作用的發揮。反之,市場化程度越低,越有利于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抑制作用的發揮。其次,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驅使地方政府在長期利益的驅動下主動加大生態保護力度,在“精選精洗效應”和“環境壁壘效應”的作用下,企業不得不進行技術升級或生產結構轉型,從而有利于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作用的發揮。反之則反之。最后,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意味著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運行更具效率,有利于在生態保護相關政策的作用下將資源配置到綠色產業或效率更高的產業,減少資源配置的扭曲;另一方面意味著更有利于區域間的模仿、學習和人才等生產要素的流動,有利于技術擴散等,從而有利于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作用的發揮。反之,則會強化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抑制作用。結合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3。
假設3:市場化程度對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具有強化效應。
根據上述分析,地方政府生態保護策略性行為選擇的形成機理及其生態保護力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機制可用圖1表示。
3 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的測度
3. 1 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為更全面、客觀地反映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參考《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綠色發展指數體系》,基于前文分析,本研究從資源節約、污染治理、生態修復和人居建設四個層面構建評價指標體系,以刻畫地方政府生態保護的努力程度。具體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主要遵循以下原則:一是政府主導原則,即所選取的基礎指標能夠體現政府的努力程度,主要從反映政府投入、政府收費和政策執行成效三個層面選取指標。二是維度指標的全面性原則,即所選取的維度指標盡量全方位體現近年來黨和政府出臺的“生態文明、綠色發展、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等相關文件所關注的重點內容。三是堅持可比性、代表性和數據可得性原則。中國幅員遼闊,各省份的地理位置、資源稟賦、氣候環境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別,為使不同發達程度和規模的省份之間具有可比性,指標的選取以比例指標為主、兼顧規模指標,以避免因各地的發達程度或資源稟賦差異造成的評價結果偏失。
3. 2 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測度方法
參考《生態文明建設評價指標體系》和《綠色發展指數體系》的測度方法,將基礎指標按照重要程度分為三類,用★表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確定的資源環境約束性指標,用◆表示《綱要》和《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等提出的主要監測評價指標,用△表示其他重要監測評價指標;將上述三類指標的權數之比設定為3:2:1,所有指標的權重之和為1。由于基礎指標按評價作用分為正向和負向指標,按指標數據性質分為絕對數和相對數指標,在對這些基礎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的基礎上,通過模型(1)進行加權求和對各地方政府相應年份的生態保護力度指數進行測度。
指標體系會因具體指標和賦權法的選取帶來評價的不確定性[17],本研究的評價指標體系也不例外。但構建該評價指標體系的意義在于,首次從資源節約、污染治理、生態修復和人居建設四個層面對各地方政府的生態保護力度指數進行了測度,將當前仍處于理論甚至概念探討層面的生態保護力度用數據進行刻畫,為評估地方政府的生態保護力度提供了參考依據。
3. 3 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的測度結果
從各省份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看(由于數據可得性限制,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的測度不涉及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由圖2可知,2008年居于前五位的分別是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天津市和江蘇省,居于后五位的分別是青海省、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甘肅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2021年居于前五位的分別是北京市、山東省、浙江省、上海市和江蘇省,居于后五位的分別是寧夏回族自治區、黑龍江省、內蒙古自治區、青海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無論是2008年還是2021年,居于前五位的省份多為東部和南方地區,而居于后五位的省份多為西部和北方地區。從分區的角度看,如圖3所示,各地區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呈現依次遞減的格局,南方和北方地區之間表現為南強北弱的格局①。這說明,不同省份、不同地區均存在著明顯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梯度差。
從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的變動趨勢看,如圖2所示,2008—2021年各省份的指數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由圖3可知,各層面的指數均呈上升的變動趨勢。從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的增長速度看,居于前五位的省份分別是青海省、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甘肅省和江西省,居于后五位的省份分別是上海市、遼寧省、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全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以及南方、北方地區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 7%、1. 27%、1. 93%、2. 11%、1. 54%和1. 88%,西部、中部和東部地區的增速依次遞減,北方地區的增速大于南方。這說明不同省份、不同地區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梯度差距在縮小。
4 研究設計
4. 1 模型構建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可知,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可能表現為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因此,構建如下基準回歸模型對假設(1)進行檢驗:
考慮到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連續、緩慢變化的過程,本期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容易受上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因此將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納入模型,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并使用GMM估計法進行估計。該估計方法的優勢在于,既可以預防基本計量模型設定的偏誤,又可以通過計量方法解決內生性問題,進而得到參數的一致估計。因此,用該估計法來檢驗模型(2)的穩健性,具體公式如下:
由于地區間的地理空間鄰近性和經濟空間相似性,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可能存在空間溢出效應。鑒于此,在對被解釋變量和核心解釋變量進行莫蘭指數檢驗的基礎上,對回歸數據進行LM檢驗和穩健性LM檢驗,檢驗結果說明構建空間計量模型是合理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Wald和似然比檢驗,檢驗結果顯示空間杜賓模型(SDM)比空間滯后模型(SLM)和空間誤差模型(SEM)更適宜;經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均在1%的顯著水平上拒絕原假設,說明應選用固定效應面板回歸模型。因此,設定空間杜賓模型的具體形式為:
4. 2 指標說明
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參考上官緒明等[18]的方法選取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作為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度量指標。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不但同時考慮了生產過程中投入的資本和勞動,還將非期望產出納入其中,與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更加契合。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方法參考馮杰等[19]的研究,以2008年為基期,選取勞動、資本和能源作為投入變量,選取各省份的實際GDP為期望產出,選取工業廢水中COD排放量和工業SO2排放量為非期望產出,運用SBM模型和GML指數對各省份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度。
控制變量。參考以往研究,從經濟發展水平、科技創新投入水平、人力資本水平、經濟開放水平、城鎮化水平和政府干預六個方面選取指標作為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控制變量。其中,經濟發展水平(ln pgdp)采用以2008年為基期的人均實際GDP的對數衡量;科技創新投入強度(rd)采用R&D經費投入占GDP的比例表示;人力資本水平(hum)采用專科及以上學歷人數占6歲以上人口總數的比例表示;政府干預水平(gov)采用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GDP比例表示;經濟開放水平(open)采用實際利用外資占GDP的比例表示;城鎮化水平(city)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衡量。
4. 3 數據來源
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和Wind數據庫等。對于考察周期內的缺失值,采用均值插值法或趨勢外推法進行補缺。對涉及價格衡量的指標均按照2008年不變價進行平減。對于諸如實際利用外資等以美元為單位的指標,按照所在年度人民幣的平均匯率進行換算。考慮數據可得性,研究對象設定為西藏、香港、澳門、臺灣之外的30個省份。各變量統計性描述見表2。
5 實證結果分析
5. 1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基于模型(2),表3報告了基準回歸結果。由表3可知,無論是否添加控制變量,無論是否控制省份效應和時間效應,生態保護力度對高質量發展影響的一次項系數均為負、二次項系數均為正,且均通過了5%及以上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表現為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假說1得證。具體而言,在樣本區間初期,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的策略性行為選擇以“逐底競爭”為主,此時生態保護力度較弱,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隨著對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重點的轉變,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的策略性行為選擇轉變為以“競相向上”為主,此時生態保護力度也由弱變強,對經濟高質量發展表現為積極的促進作用。比較列(3)至列(6)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在采取不同固定效應的情形下回歸系數的絕對值并未發生明顯變化,這說明回歸結果是穩健的。根據列(6),可以計算出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臨界值(0. 391①)。比較臨界值與生態保護力度指數均值的大小可知,當前地方政府的生態保護力度指數已經跨過臨界值(0. 419>0. 391)。這說明,當前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已經跨過“U”型的最低點,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促進作用。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加大生態保護力度”成為決策層和學術界近年提及熱點的原因。
5. 2 內生性處理
工具變量法。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之間可能存在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本研究參考陳詩一等[11]的研究方法,選取省級政府工作報告中與生態環境相關的詞匯(生態、環境保護、環保、森林、草原、沙化、濕地、自然保護區、水資源、綠化、節約、節能、新能源、污染、能耗、減排、排污、綠色、低碳、空氣、COD、SO2、CO2、PM10和PM2. 5等)出現頻數的對數(ln ew)和各省份空氣流動系數的對數(ln vc)作為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的代理變量。選擇生態環境相關詞匯的頻數作為工具變量的理由在于:一是這些詞匯的頻數是地方政府生態環境治理主觀意志的反映,與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高度相關。二是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一般修訂在年初,而該年度的經濟活動無法反向影響年初已制定的政府工作報告,將政府工作報告中生態環境詞匯出現的頻數作為工具變量可以有效規避“反向因果”所引起的內生性問題,較好地滿足了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假定。選擇空氣流動系數作為工具變量的理由在于:一是空氣流動系數是由當地復雜的氣象系統和地理條件決定的,特別是與當地的海拔高度和風速緊密相關,當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相同時,空氣流動系數越大的省份越有利于污染物的消散,當地地方政府則越傾向于采取較弱的生態保護力度,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的假定。二是空氣流動系數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或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并不存在“反向因果”引致的內生性問題,滿足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假定。本研究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對工具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參考陳琪[20]的處理方法,將工具變量的一次項和二次項依次加入模型,觀察其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的變化。
表4報告了兩階段最小二乘法的回歸結果。從列(1)、列(2)和列(5)、列(6)中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工具變量生態環境詞頻和空氣流動系數的回歸系數在5%及以上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這兩個工具變量與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確實存在相關性。為考察工具變量選取是否合適,本研究對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當只考察工具變量的一次項時,由列(1)和列(5)所示,第一階段回歸的F統計量分別為12. 345和37. 576,均大于10。在加入工具變量的二次項后,模型相當于存在兩個內生解釋變量,引入兩個工具變量后第一階段回歸最小特征值統計量(MinimumEigenvalue Statistic)分別為16. 335和31. 517,也均大于10。這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問題,生態環境詞頻和空氣流動系數作為工具變量是恰當的。由表4列(3)和列(7)以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為因變量只引入一次項作為工具變量的第二階段回歸系數的正負性可知,生態環境詞匯頻數越大表示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越強則越有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空氣流動系數越大表示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越小則越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反之則反之。由表4列(4)可知,以生態環境詞頻為工具變量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一次項系數為負、二次項系數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只有跨過拐點值才能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促進作用,驗證了模型(2)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由表4列(8)可知,以空氣流動系數為工具變量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一次項系數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且均在5%及以上的水平顯著。這表明以空氣流動系數為工具變量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表現為倒“U”型關系,即較小的空氣流動系數引致較大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進而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促進作用,反之較大的空氣流動系數引致較小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進而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抑制作用,這也再次驗證了模型(2)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核心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為進一步檢驗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之間的內生性問題,本研究選擇將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回歸結果見表5列(1),回歸系數的符號與表3列(6)的符號一致,回歸系數相近,且均在5%及以上的水平顯著。這說明在考慮內生性問題后,模型(2)的回歸結果依然是穩健的。
5. 3 穩健性分析
改變回歸方法。為考察模型(2)的穩健性,構建了模型(3)的動態面板模型,采用系統GMM進行回歸,以緩解模型中的內生性問題,并根據Hansen檢驗和AR(1)、AR(2)檢驗來識別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和估計結果的可靠性。回歸結果見表5列(2),Hansen檢驗、AR(1)和AR(2)的結果表明模型(3)的估計結果是可靠的,且被解釋變量gtfp的一階滯后顯著為正,說明動態面板模型是合理的。核心解釋變量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符號與模型(2)一致,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同樣表現出“U”型特征。說明模型(2)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替換被解釋變量。參考陳詩一等[11]用勞動生產率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代理變量的方法,用勞動生產率(labp)替換被解釋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回歸結果見表5的列(3),核心解釋變量生態保護力度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符號與模型(2)基準回歸的系數符號一致,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模型(2)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5. 4 空間溢出效應
選取鄰接矩陣(w1)、空間地理距離矩陣(w2)和地理與經濟嵌套矩陣(w3)為空間權重矩陣,考察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地區之間的空間溢出效應。其中:鄰接矩陣(w1)是通過判斷兩個省份是否相接,分別取1 和0 并通過標準化后得到;空間距離矩陣(w2)是通過計算直轄市、省會城市間距離的倒數并標準化后得到;地理與經濟嵌套矩陣(w3)是通過計算直轄市、省會城市間距離的倒數,用該倒數乘以樣本區間內相應省份GDP平均值差值絕對值的倒數,并對上述乘積進行標準化后得到。根據前文構建的空間杜賓模型(模型(4)),空間溢出效應的回歸結果見表6。
由表6可知,在各種空間權重的回歸模型中,本地效應的生態保護力度一次項系數為負,二次項系數為正,這說明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本地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均表現為“U”型特征。這與模型(2)的基準回歸結論一致,再一次證明了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滯后項系數(ρ)在各空間權重矩陣的回歸模型中均顯著為正,這說明無論是地理鄰近還是經濟鄰近,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均會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空間溢出效應。對比表6列(1)和列(2)本地效應和鄰地效應中生態保護力度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發現系數的符號始終相反。這表明地理鄰近的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力度的策略性行為選擇表現為“逐底競爭”,即為競爭到更多的生產要素,各地方政府不惜以犧牲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代價競相降低生態保護力度。觀察表6列(1)和列(2)鄰地效應的回歸系數,發現生態保護力度的一次項回歸系數均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且均在10%及以上水平顯著。這表明,本地較小的生態保護力度,對鄰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影響;本地較大的生態保護力度,對鄰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負向影響。簡言之,本地的生態保護力度對鄰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了反向的空間溢出效應。究其原因,鄰近地區的生態保護力度越小,其轄區內的治污成本或資源環境生產要素的價格相對越低,這將造成本地污染企業向鄰地轉移,進而會促進本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相反,鄰近地區的生態保護力度高于本地,將造成鄰地的污染企業向本地轉移,進而會抑制本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沈坤榮等[21“] 鄰近地區的環境規制加強顯著加劇了本地的產業結構‘污染化,且污染基本就近轉移到周邊城市”,以及關海玲等[22“] 鄰地環境規制對本地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反向影響”的結論支持了上述結論。
對比表6列(3)本地效應和鄰地效應中生態保護力度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發現系數的符號一致。這表明經濟鄰近的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的策略性行為選擇表現為“競相向上”,即各地方政府為了長遠利益,爭相提升自身生態保護力度的行為。該結論得到了金剛等[23]“經濟相鄰城市間表現出競相向上的對稱性環境規制執行互動”研究結論的支持。進一步觀察表6列(3)鄰地效應的回歸系數,發現生態保護力度的一次項系數為負、二次項系數為正。這表明本地的生態保護力度越小,越不利于鄰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本地的生態保護力度越大,對鄰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越有利。簡言之,本地的生態保護力度對鄰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了同向的空間溢出效應。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一是經濟相近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和居民對生態環境的訴求等基本相似,地方政府間的模仿、學習和競爭使其政策執行和經濟發展產生了經濟空間俱樂部趨同或“極化效應”。二是經濟相近地區間的經濟往來更為密切,經濟鄰近地方政府的生態保護力度越強,對本地企業產品供給的“清潔度”要求也將更高,這將倒逼本地企業清潔化轉型進而促進本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
5. 5 調節機制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論分析,進一步驗證市場化程度對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調節機制。市場化程度選用市場化指數(參考樊綱等[24]的方法測算)、產品市場發育程度指數和要素市場發育程度指數作為代理變量。參考Dawson[25]的方法,將機制變量嵌入到基礎回歸模型(2),構建模型(5)進行路徑機制分析。
表7可知,epi × Moderator 和epiit 2 × Moderatorit 的回歸系數均在10%及以上水平顯著,這說明市場化程度是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機制。觀察表7 各列,epi×Moderator 的系數均為負,epiit 2 ×Moderatorit 的系數均為正。這表明市場化程度對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二者關系的影響表現為強化效應,即較低的市場化程度,強化了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抑制作用;較高的市場化程度,強化了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
為控制內生性問題,本研究采用工具變量法(Ⅳ)檢驗市場化程度在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同前文一致,此處仍選取省級政府工作報告中與生態環境相關的詞匯出現頻數的對數(ln ew)為工具變量。在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回歸之前,首先對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主要包含不可識別檢驗和弱工具變量檢驗。其中,不可識別檢驗結果顯示,Kleibergen?Paap rkLM統計量的P 值為0. 000,強烈拒絕不可識別的原假設,說明工具變量與內生變量具有相關性;弱工具變量檢驗結果顯示,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統計量和Cragg?DonaldWald F 統計量均大于Stock?Yogo weak ID test 10%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本研究所選取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在工具變量有效性檢驗的基礎上,進一步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檢驗市場化程度在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具體結果見表8。
表8展示了將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替換工具變量后,市場化程度與工具變量的交互項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顯示,市場化程度與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工具變量交互項的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表明市場化程度對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具有明顯的調節作用,這一結果與表7的研究結論相一致。因此,在控制內生性問題的前提下,市場化程度的調節機制依然成立。
為考察市場化程度對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U”型曲線拐點值的影響,模型(5)可以轉化為:
將表7 中的回歸系數代入式(7),可得α11 -α12α13 /α14 小于零,-α12 和-α14 也均小于零。因此,假定在其他條件均不變的情況下,隨著Moderator 變大,拐點值epi0 將變小。參考Dawson[25]的研究,市場化程度對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和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效應如圖4所示。市場化程度越高,拐點值將越小,即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U”型曲線拐點值將左移,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越容易跨過拐點值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促進作用;反之,市場化程度越低,拐點值將越大,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越不容易跨過拐點值,進而對經濟高質量發展越容易產生抑制作用。
6 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研究在對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機制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基于2008—2021年中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通過構建靜態面板模型和空間杜賓模型,考察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和市場化程度在兩者關系中的調節機制,得到主要結論如下。
(1)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表現為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就全國整體而言,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的均值大于其臨界值(0. 419>0. 391),表明當前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各地區的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呈依次遞減格局,南方和北方地區之間呈南強北弱格局;而各地區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指數的增速,與上述格局相反。省份之間、地區之間均存在著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梯度差,但梯度差呈現出縮小的趨勢。
(2)本地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鄰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具體溢出效果取決于地方政府間的生態保護策略性行為選擇。具體而言,地理鄰近省份間生態保護的策略性行為選擇表現為“逐底競爭”,本地的生態保護力度對鄰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反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即本地的生態保護力度較小時,對鄰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影響;本地的生態保護力度較大時,對鄰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負向影響。經濟鄰近省份間生態保護的策略性行為選擇表現為“競相向上”,本地的生態保護力度對鄰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同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即本地的生態保護力度越小,越不利于鄰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本地的生態保護力度越大,對鄰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越有利。
(3)市場化程度是調節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路徑機制。市場化程度對兩者關系的影響表現為強化效應,即較低的市場化程度會增強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抑制作用;較高的市場化程度則會增強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升,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U”型曲線拐點值將向左移動。這意味著在相同的生態保護力度水平下,較高的市場化程度更容易使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跨過拐點值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促進作用。
基于以上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積極引導地方政府加大生態保護力度。一是要引導地方政府正確認識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使其在思想上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的觀念,提高生態保護工作在地方政府績效考核中的占比,提升其加大生態保護力度的內驅力。二是鼓勵地方政府根據當地實際有效加大生態保護力度。比如針對生態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應引導地方政府將加大生態保護的重點集中在生態修復等方面;對不宜居生態區的居民推行易地搬遷,真正做到退耕還林、退耕還草、退耕還荒,推進生態區的“擬自然化”和“再野化”,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頻共振”。三是加大對地方政府生態保護政策落實的監督力度和對相關主體違規處罰的執法力度,引導群眾參與到生態保護的行動中來并形成違規行為的監督力量。
(2)切實推進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聯防聯控”。一是引導地方政府正確看待地方政府間競爭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推動地方政府間的經濟圈、城市群建設,使地方政府間結成利益共同體,消除或縮小彼此間的生態保護力度梯度差,破除“逐底競爭”策略性行為選擇的土壤,共享經濟鄰近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二是構建地方政府間生態保護的共建共享機制。生態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如果僅著眼于自我轄區的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間很容易顧此失彼,相互掣肘。搭建綜合數字化平臺,推進數據資源跨地區跨部門互通共享,是實現地方政府間聯防聯控的重要保障。三是建立生態保護的跨區補償機制,提高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彌補生態資源豐富區因生態保護導致的經濟增長損失,提升地方政府間聯防聯控的能力。
(3)有效推動各地區的市場化建設。一是加強各地區的市場化制度建設、法制環境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提升地方政府依法整頓、規范市場秩序的意識和營造公平、有序、競爭市場環境的能力;通過市場化程度提升推動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力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U”型曲線拐點值向左移動。二是清除地方政府轄區之間的市場壁壘,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打通轄區之間產品和要素流動的堵點,利用市場規律提升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三是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優勢,在政府職能和市場功能良性互動中推動生態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華. 地區間環境規制的策略互動研究:對環境規制非完全執
行普遍性的解釋[J]. 中國工業經濟,2016(7):74-90.
[2] 沈國舫. 關于“生態保護和建設”名稱和內涵的探討[J]. 生態學
報,2014,34(7):1891-1895.
[3] 盧維學,吳和成,王勵文. 環境規制政策協同對經濟高質量發展
影響的異質性[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2,32(3):62-71.
[4] DI W H.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 savings and FDI inflows to polluting
sectors in China[J].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12(6):775-798.
[5] ACEMOGLU D. Equilibrium bias of technology[J]. Econometrica,
2007,75(5):1371-1409.
[6] 傅京燕,李麗莎. 環境規制、要素稟賦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實證
研究:基于中國制造業的面板數據[J]. 管理世界,2010(10):
87-98.
[7] 張軍擴,侯永志,劉培林,等. 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要求和戰略路
徑[J]. 管理世界,2019,35(7):1-7.
[8] 魏敏,李書昊. 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研究
[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8,35(11):3-20.
[9] JAHANGER A. Influence of FDI characteristics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021,28(15):18977-18988.
[10] 余泳澤,楊曉章,張少輝.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
的時空轉換特征研究[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36
(6):3-21.
[11] 陳詩一,陳登科. 霧霾污染、政府治理與經濟高質量發展[J].
經濟研究,2018,53(2):20-34.
[12] 聶長飛,簡新華. 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測度及省際現狀的分析比
較[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37(2):26-47.
[13] 任保平,李培偉.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
系統邏輯[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22,42(12):4-19.
[14] 周業安,馮興元,趙堅毅. 地方政府競爭與市場秩序的重構
[J]. 中國社會科學,2004(1):56-65.
[15] WOODS N D. Interstate competi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 test of the race?to?the?bottom thesi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6,87(1):174-189.
[16] FREDRIKSSON P G,MILLIMET D L.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cross U. S. stat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2,51(1):101-122.
[17] 張友國,竇若愚,白羽潔. 中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建
設水平測度[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37(8):83-102.
[18] 上官緒明,葛斌華. 科技創新、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來
自中國27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經驗證據[J]. 中國人口·資源
與環境,2020,30(6):95-104.
[19] 馮杰,張世秋. 基于DEA方法的我國省際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評
估:不同模型選擇的差異性探析[J]. 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
版),2017,53(1):151-159.
[20] 陳琪. 環保投入能提高企業生產率嗎:基于企業創新中介效應
的實證分析[J]. 南開經濟研究,2020(6):80-100.
[21] 沈坤榮,金剛,方嫻. 環境規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轉移嗎[J]. 經
濟研究,2017,52(5):44-59.
[22] 關海玲,武禎妮. 地方環境規制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是
技術進步還是技術效率變動[J]. 經濟問題,2020(2):118-129.
[23] 金剛,沈坤榮. 以鄰為壑還是以鄰為伴:環境規制執行互動與
城市生產率增長[J]. 管理世界,2018,34(12):43-55.
[24] 樊綱,王小魯,張立文,等. 中國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
[J]. 經濟研究,2003,38(3):9-18.
[25] DAWSON J F. Moderation in management research:what,why,
when,and how[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2014,29
(1):1-19.
[26] BRAMBOR T,CLARK W R,GOLDER M. Understanding interaction
models:improving empirical analyses[J]. Political analysis,
2006,14(1):63-82.
(責任編輯:王愛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