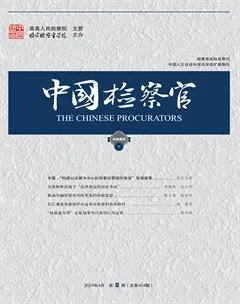網(wǎng)絡(luò)黑灰產(chǎn)中游技術(shù)幫助行為的刑法規(guī)制
陳冰慧 黃俊杰
一、基本案情
2021年至2022年,犯罪嫌疑人A以牟利為目的,將自己編寫的“小XX”下單工具等配套軟件通過網(wǎng)絡(luò)平臺予以售賣,該軟件的功能在于通過輸入從上家處購買的cookie值[1],便可繞過購物平臺的識別驗證機制,從而免密登陸他人的新人賬號。為提高成功率,犯罪嫌疑人A還編寫了自動增加字符以修改收貨地址、更換IP地址等繞過購物平臺的封號機制的程序。下游的用戶通過他人的新人賬號下單,便可使用平臺專門發(fā)放給新用戶的大額購物優(yōu)惠券,在購物時獲得減免優(yōu)惠。
期間,下家B通過該軟件下單累計獲利8萬余元;犯罪嫌疑人A造成相關(guān)平臺損失達78萬余元,獲利40余萬元。第三方公司出具意見,認為“軟件在未經(jīng)授權(quán)的情況下,突破了網(wǎng)站賬號登陸和交易的風控、反爬等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安全保護措施,破壞和干擾了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的功能和正常運行”。
二、分歧意見
案發(fā)后,公安機關(guān)以犯罪嫌疑人A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程序、工具罪將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但經(jīng)審查發(fā)現(xiàn),犯罪嫌疑人A制作涉案軟件的行為,既不同于惡意注冊賬號的上游行為,也不同于直接實施薅羊毛的下游行為,應(yīng)當屬于網(wǎng)絡(luò)黑灰產(chǎn)業(yè)的中游幫助行為。因此,針對本案的處理,形成了以下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涉案軟件未經(jīng)授權(quán),突破網(wǎng)站賬號登陸和交易的風控、反爬的計算機系統(tǒng)安全保護措施,侵入了計算機系統(tǒng),并獲取平臺的后臺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服務(wù)數(shù)據(jù),本案應(yīng)定性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程序、工具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犯罪嫌疑人明知他人會利用軟件實施侵財類犯罪,仍然售賣軟件為他人的犯罪活動提供技術(shù)支持,應(yīng)當在下游構(gòu)成犯罪的前提下,將本案定性為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犯罪嫌疑人未與下游犯罪達成共同犯罪的合意,單純售賣軟件的行為不應(yīng)認定為犯罪。
三、評析意見
學理層面針對黑灰產(chǎn)業(yè)鏈的刑法規(guī)制問題也以討論上游與下游犯罪為主,對中游犯罪的表現(xiàn)形式一般僅提及“養(yǎng)號”行為,或以上中游共同認定為最終目的的準備行為或手段行為。而實務(wù)界也因最高檢指導(dǎo)案例檢例第34號“李駿杰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案”[2]于2024年2月27日宣告失效而再度產(chǎn)生爭議。因此,有必要對避開封號實現(xiàn)網(wǎng)絡(luò)黑灰產(chǎn)中游幫助行為的刑法規(guī)制進行探討。經(jīng)審查,筆者贊成第二種意見,即本案應(yīng)當在下游構(gòu)成犯罪的情況下認定為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罪。理由如下:
(一)當前刑法對計算機保護“重系統(tǒng)輕數(shù)據(jù)”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犯罪嫌疑人是否侵入了計算機系統(tǒng),即需明確使用從上游獲取的cookie值免密登陸的行為是否突破了相關(guān)平臺的安全防控措施。而通過對相關(guān)法條的拆解,可得知當前刑法計算機類的罪名完全依附于舊有的“計算機系統(tǒng)”的概念,強調(diào)侵入計算機系統(tǒng)是構(gòu)罪的應(yīng)有之義,導(dǎo)致本案中的cookie值這一未進入計算機系統(tǒng)內(nèi)部的數(shù)據(jù)無法被認定屬于計算機系統(tǒng)數(shù)據(jù),而被排除在計算機系統(tǒng)犯罪保護范疇之外。
1.立法的遲滯性難以應(yīng)對現(xiàn)實發(fā)展。根據(jù)我國計算機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刑法關(guān)于計算機犯罪的規(guī)制路徑是經(jīng)歷了由計算機犯罪到網(wǎng)絡(luò)犯罪再到網(wǎng)絡(luò)空間犯罪的三次樣態(tài)轉(zhuǎn)變。[3]第一次計算機系統(tǒng)犯罪入罪是由于我國的計算機發(fā)展剛剛起步,當時尚無互聯(lián)網(wǎng)的概念;第二次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增設(shè)計算機系統(tǒng)的相關(guān)罪名是因為彼時黑客猖獗,計算機的系統(tǒng)安全被提升到一個較高的層面;第三次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的出臺則是在于解決互聯(lián)網(wǎng)跨地域性帶來的共犯處理證明難的問題,將預(yù)備犯、幫助犯的行為獨立入罪評價。同時,相關(guān)的司法解釋于2011年施行此后尚無其他規(guī)定。
在互聯(lián)網(wǎng)迅猛發(fā)展的當下,我國的數(shù)據(jù)發(fā)展已經(jīng)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有關(guān)的信息也不只局限于計算機數(shù)據(jù),移動終端、服務(wù)器、云盤,都有可能承載著公民的個人信息,而AI時代的到來也意味著數(shù)據(jù)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但立法固有的遲滯性使得法律保護總是落后于現(xiàn)實問題的出現(xiàn),現(xiàn)有的法規(guī)仍停留在10年前。因此,從上述立法調(diào)整過程可以看出,我國現(xiàn)有刑法對計算機犯罪的規(guī)定重在保護系統(tǒng),而鮮有規(guī)定對計算機數(shù)據(jù)的保護,本案的cookie值被排除保護范疇之外。
2.現(xiàn)有刑法數(shù)據(jù)保護的范圍局限于身份認證信息。刑法第285條第2款為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數(shù)據(jù)、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罪。由于司法實踐對于數(shù)據(jù)的解讀呈現(xiàn)一定的恣意性,包括游戲服務(wù)器內(nèi)的數(shù)據(jù)[4]、教務(wù)管理系統(tǒng)內(nèi)的數(shù)據(jù)[5]都有被界定為“系統(tǒng)數(shù)據(jù)”,缺乏一致性,因此需要準確界定何為“系統(tǒng)數(shù)據(jù)”。
根據(jù)2011年“兩高”《關(guān)于辦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安全刑事案件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1年《解釋》”)第1條前兩款規(guī)定了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數(shù)據(jù)的行為,包括“獲取支付結(jié)算、證券交易、期貨交易等網(wǎng)絡(luò)金融服務(wù)的身份認證信息10組以上”“獲取前述以外的身份認證信息500組以上的”,應(yīng)當認定為刑法第285條第2款規(guī)定的情節(jié)嚴重。而本解釋所稱“身份認證信息”,是指用于確認用戶在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上操作權(quán)限的數(shù)據(jù),包括賬號、口令、密碼、數(shù)字證書等。
據(jù)此,計算機系統(tǒng)罪名的系統(tǒng)數(shù)據(jù),應(yīng)當局限于“身份認證信息”。從現(xiàn)有的刑法框架之下,適用計算機犯罪系統(tǒng)數(shù)據(jù)必須局限于用戶在網(wǎng)絡(luò)上操作的權(quán)限,對于金融服務(wù)信息則在信息數(shù)量這一入罪條件有所放寬;同時,由于前述立法背景,本罪對于數(shù)據(jù)的保護仍是針對計算機系統(tǒng)的,沒有規(guī)定對于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安全的保護,保護的范圍實際較窄。由于相關(guān)立法的缺失,導(dǎo)致司法實踐將系統(tǒng)安全與數(shù)據(jù)安全雜糅,錯誤地適用相關(guān)罪名。
3.刑法第285條第3款系規(guī)制前兩款規(guī)定行為的幫助犯。刑法第285條第3款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程序、工具罪”,屬于幫助行為正犯化,也即為正犯提供幫助行為。該規(guī)定重在規(guī)制提供相關(guān)程序、工具的行為,與前兩款系關(guān)聯(lián)性罪名,屬于前兩款行為的幫助犯。而本案的正犯即下游行為人,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獲取滿減優(yōu)惠,從而給平臺造成損失,理應(yīng)以包括詐騙罪在內(nèi)的侵財類犯罪進行規(guī)制。因此,從刑法邏輯進行推導(dǎo),若犯罪嫌疑人觸犯刑法第285條第3款,那么正犯的行為必然要構(gòu)成刑法第285條第1款或第2款規(guī)定的罪名,這顯然與本案將正犯定為侵財類犯罪的邏輯沖突。
(二)偵查實驗印證涉案軟件未侵入平臺計算機系統(tǒng)
1.刑法第285條第3款的“侵入行為”應(yīng)滿足三要件,可總結(jié)為“突破安全保障+無授權(quán)或超授權(quán)+獲取控制”。根據(jù)2011年《解釋》第2條的規(guī)定,構(gòu)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程序、工具罪,必須同時滿足三個要件:一是避開和突破安全保護措施;二是未經(jīng)授權(quán)取得授權(quán)或超越權(quán)限;三是具備對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獲取數(shù)據(jù)和控制功能。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的的安全是一套嚴密的體系,只有同時具備三個要素,方能損害危害計算機信息安全。該要件的設(shè)計參考了黑客軟件實施侵入和非法控制的三個步驟,黑客侵入系統(tǒng)首先要避開和突破安全防護措施,進入后再針對系統(tǒng)漏洞植入木馬或者獲取弱密碼等超級用戶權(quán)限,最后利用超級用戶權(quán)限非法獲取數(shù)據(jù)或非法控制計算機系統(tǒng)。
認定“侵入”計算機系統(tǒng)的行為應(yīng)同時滿足三要件,目的是防止犯罪圈層的不當擴張。根據(jù)漢語詞典的釋義,侵入意味著強行或非法進入,也強調(diào)外來或有害的事務(wù)進入內(nèi)部。而刑法特有的謙抑性立場則意味著刑法意義上的侵入明顯有別于進入。刑事法律層面上更應(yīng)當對侵入行為作狹義解釋,否則會造成打擊面過大的情況。
2.通過偵查實驗?zāi)軌蛴∽C涉案軟件調(diào)用的cookie值是本地文件,不涉及平臺系統(tǒng)及數(shù)據(jù)。為了復(fù)現(xiàn)“小XX”軟件的犯罪過程,特開展以下偵查實驗,步驟如下:第一步,操作者關(guān)閉網(wǎng)絡(luò),登陸在本地電腦上的谷歌瀏覽器。第二步,通過啟用F12鍵調(diào)用“開發(fā)者工具”,進入“網(wǎng)絡(luò)”板塊,可調(diào)取存儲在本地計算機內(nèi)谷歌瀏覽器訪問時儲存的cookie值。第三步,在其他設(shè)備輸入保存好的cookie值,成功實現(xiàn)免密登陸。通過偵查實驗,印證了cookie值的作用是避免登陸賬號需要頻繁驗證,cookie值是本地數(shù)據(jù)。
3.使用cookie值登陸,未涉及計算機信息安全問題。首先,windows防火墻、黑白名單規(guī)則、端口和IP地址段限制等,屬于平臺為了計算機安全設(shè)置的操作。其次,使用cookie值避開封號,不屬于“突破”安全防護網(wǎng)。舉例而言,平臺通過黑白名單等安全保護規(guī)則,禁止相關(guān)賬號登陸,如犯罪嫌疑人修改規(guī)則或突破規(guī)則限制,強行登陸相關(guān)賬號,此時便涉及安全問題。而本案則是客戶自主選擇登陸方式的問題,并非安全問題。行為人雖然進入了平臺,但僅是一種登陸方式,顯然沒有影響平臺安全,行為人也不能實施任何危害平臺的行為。行為人使用涉案軟件下單功能屬交易問題,也與計算機安全無涉。
4.同一IP登陸多賬號導(dǎo)致凍結(jié)是賬號管理問題,而非計算機信息安全問題。為提高成功率,A編寫更換IP等繞過購物平臺的封號機制的程序,也被鑒定為影響平臺安全。但是平臺設(shè)立凍結(jié)規(guī)則是為防止同一用戶掌握規(guī)則漏洞后使用大量賬號惡意“薅羊毛”,因此凍結(jié)賬號規(guī)則是平臺對于賬號和用戶的管理問題,而非計算機信息安全問題問題。涉案軟件設(shè)計更換IP,也是防止行為觸發(fā)凍結(jié)機制。舉例說明,某些論壇的賬號超過6個月未登陸,便會被凍結(jié)且限制發(fā)言,但長期未登陸并不涉及系統(tǒng)安全問題,而僅是網(wǎng)站為了管理不活躍用戶而設(shè)置的管理機制。
還需注意,普通客戶通過通信公司上網(wǎng)的IP地址屬于動態(tài)IP,隨機性意味著無法被平臺事先封禁。路由器重啟后,完全可能獲取與之前不同的IP地址。IP地址由電信公司分配到客戶終端上,在沒有登陸前,任何平臺的服務(wù)器都無法事先得知客戶IP地址。因此,平臺基本不大可能事先封禁IP段,否則可能會影響客戶的正常登陸。
因此,涉案軟件預(yù)先導(dǎo)入cookie值免密登陸與更換IP功能不是規(guī)避平臺登陸上的安全防護措施,而是規(guī)避平臺用戶和交易管理的風控機制。通過上述的技術(shù)分析可知,涉案軟件未侵入平臺計算機系統(tǒng),更無法獲取計算機系統(tǒng)數(shù)據(jù)。
(三)全鏈條網(wǎng)絡(luò)犯罪應(yīng)當適用正犯行為共犯化的應(yīng)然立場
傳統(tǒng)的共犯從屬性理論在規(guī)制網(wǎng)絡(luò)犯罪出現(xiàn)弊端。按照傳統(tǒng)的犯罪理論,共同犯罪的參與人必須圍繞某一核心主體形成犯罪的意思聯(lián)絡(luò)和共同行為。[6]網(wǎng)絡(luò)空間內(nèi)的幫助行為的特點呈現(xiàn)一對多的模式,幫助者與受助者之間的意思聯(lián)絡(luò)趨弱,幫助行為獨立性變強,但社會危害性隨著網(wǎng)絡(luò)鏈條的延長而擴大。這種情況下,傳統(tǒng)的共犯理論在規(guī)制此類問題時就會出現(xiàn)失靈問題,黑灰產(chǎn)業(yè)中該特征更為明顯。以本案下游犯罪“薅羊毛”為例,上游惡意注冊大量賬號、中游提供技術(shù)支持,下游實施“薅羊毛”行為,每一環(huán)節(jié)行為人對其他人的行為都知之甚少,基本上通過網(wǎng)絡(luò)溝通,彼此沒有實際接觸,對于受助者的行為無法產(chǎn)生清晰認知。[7]由于傳統(tǒng)犯罪的共犯從屬性理論出現(xiàn)失靈,難以囊括業(yè)已存在甚至可能異化的違法行為,對于打擊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之類的犯罪產(chǎn)生了極大的困難,有必要基于網(wǎng)絡(luò)犯罪的特點進行回應(yīng),遵循正犯行為共犯化的立場規(guī)制網(wǎng)絡(luò)犯罪。
司法實踐層面已經(jīng)先于立法對于網(wǎng)絡(luò)犯罪參與行為予以回應(yīng),正犯行為共犯化是解讀行為性質(zhì)的應(yīng)然立場。根據(jù)2023年最高檢《關(guān)于辦理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及其關(guān)聯(lián)犯罪案件有關(guān)問題的解答》、2022年“兩高一部”《關(guān)于“斷卡”行動中有關(guān)法律適用問題的會議紀要》等規(guī)定精神,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罪的明知內(nèi)容不限定被幫助行為的類型。行為人僅需有概括性的故意,即認識到他人利用信息網(wǎng)絡(luò)實施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就能推定其主觀明知,即使對行為類型認識有誤的,也不影響明知的認定。一般而言,司法解釋、會議紀要、問題解答等都會先于立法出現(xiàn)對實踐進行探索,待理論成熟后通過立法的形式予以最終確認。司法解釋先于立法對網(wǎng)絡(luò)犯罪參與行為予以回應(yīng),對于網(wǎng)絡(luò)犯罪共犯的主觀明知可以適當放寬。[8]
因此在正犯行為共犯化的立場之下,A明知自己設(shè)計的“小XX”軟件作用就是幫助他人違法獲取平臺提供給新人的優(yōu)惠,從而給平臺造成經(jīng)濟損失,A主觀上持概括性故意。因此,理應(yīng)對其認定為下游犯罪的共犯。
(四)虛擬財產(chǎn)應(yīng)認定為財物
正因網(wǎng)絡(luò)犯罪的共犯論證存在爭議,為防止過于擴大打擊面,導(dǎo)致犯罪圈層的不當擴大,按照限制從屬性說、最小從屬性說等多種學說,結(jié)合司法實踐的觀點,都要求下游的實行行為必須構(gòu)成犯罪,方能對上中游的行為進行刑事處罰。
而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復(fù)雜性與特殊性,對于案件的處理也產(chǎn)生了影響。由于下游犯罪系通過網(wǎng)絡(luò)實施,被害人或單位遭受損失的往往是虛擬財產(chǎn),包括游戲幣、裝備、優(yōu)惠券等。雖然受損失的虛擬財產(chǎn)屬于無體物,也無法否認被害人或單位通過該無體物獲利的期待可能性。因此,通過“小XX”軟件在平臺獲取的優(yōu)惠券,能否被認定為財物,直接影響下游犯罪的認定,也成為本案能否定罪的關(guān)鍵。
對于虛擬財產(chǎn)的爭論,主要有肯定說與否定說兩種理論。肯定說主張,具備財物特征的虛擬財產(chǎn)應(yīng)當被刑法所保護,其中財物特征是指管理可能性、轉(zhuǎn)移可能性與價值性。[9]這種觀點認為,司法解釋沒有否認難以準確計價財物的盜竊性質(zhì),且財物的多重屬性并不足以否認其財產(chǎn)性的特點。將針對虛擬財產(chǎn)的違法行為排除在財產(chǎn)犯罪之外無法做到罪責刑相適應(yīng)。而否定說主張?zhí)摂M財產(chǎn)應(yīng)當認定為計算機數(shù)據(jù),回避討論其法律屬性。否定說認為,除非有特殊規(guī)定,無體物和“財產(chǎn)性利益不是我國刑法中盜竊罪的對象”。即使將虛擬財產(chǎn)的本質(zhì)界定為無體物和財產(chǎn)性權(quán)利,也不能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10]
結(jié)合最高檢的觀點,更傾向于肯定說。例如2017年10月12日最高檢發(fā)布的第九批指導(dǎo)性案例之“張四毛盜竊案”中,將網(wǎng)絡(luò)域名認定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11]。包括各種數(shù)據(jù)在內(nèi)的虛擬財產(chǎn)的重要程度現(xiàn)已不亞于普通財物,例如某些手機公司推出“數(shù)字遺產(chǎn)”廣受好評等,都說明虛擬財產(chǎn)的重要性。如張明楷教授談及,刑法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但也必須同時適應(yīng)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否則便沒有生命力。[12]所以,對刑法必須采取同時代的解釋,虛擬財產(chǎn)可以被認定為財物。舉例而言,電雖然無法用實體形式體現(xiàn),但電屬于財物。優(yōu)惠券雖然看似可以無限生成,但用戶一般只能獲得有限數(shù)量的優(yōu)惠券,不可能無限制地獲取實惠。行為人將優(yōu)惠券的抵扣數(shù)額用于購買商品后,優(yōu)惠券就會產(chǎn)生稀缺性,產(chǎn)生了相應(yīng)的使用價值,產(chǎn)生了節(jié)省金錢的實際效果與期待可能性,符合民眾的一般認知。采用肯定說的觀點,能夠更好地適應(yīng)時代的發(fā)展,也更有利于保護實現(xiàn)法益保護的功能。
(五)黑灰產(chǎn)下游構(gòu)罪的前提下應(yīng)當適用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罪
由于網(wǎng)絡(luò)犯罪鏈條的松散性,行為人之間的犯意聯(lián)絡(luò)并不緊密,難以適用傳統(tǒng)的共犯理論認定為詐騙罪,而是在正犯行為共犯化的立場之下,適用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罪。
第一,根據(jù)體系解釋,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犯罪屬于第六章擾亂公共秩序罪下屬章節(jié)內(nèi)的犯罪,屬于對公法益的犯罪。本案下游“薅羊毛”造成了被害單位的財產(chǎn)損失,但沒有造成網(wǎng)絡(luò)大規(guī)模的癱瘓、用戶無法使用權(quán)益等公共利益受損情況,因此應(yīng)當認為屬于對私犯罪,屬于侵犯財產(chǎn)犯罪。當下游犯罪構(gòu)成了侵財類犯罪,而幫助犯只能以侵財類的幫助行為追究責任,而不適宜定性為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的犯罪類別。
第二,虛擬財產(chǎn)應(yīng)當被認定為財物,下游犯罪構(gòu)成詐騙罪。如上所述,優(yōu)惠券這種虛擬財產(chǎn)應(yīng)當被認定為財物,下游犯罪的行為人使用其他用戶賬戶內(nèi)的優(yōu)惠券自行下單,給被害單位造成了一定的損失,下游犯罪有處罰的必要性,構(gòu)成詐騙罪。隨著ChatGPT的爆火、Soar模型的出現(xiàn),當前及未來的機器已經(jīng)區(qū)別于弱人工智能,機器逐漸成為自然人意志的延伸。平臺已經(jīng)設(shè)置了對IP識別的程序防范“薅羊毛”行為,但是機器根據(jù)程序的設(shè)定難以識別犯罪嫌疑人對該程序的規(guī)避,基于認識錯誤而自愿產(chǎn)生了的交易行為。可以設(shè)想,如果下游行為人喬裝、更換身份拿著一個賬戶僅能獲取一張的新人優(yōu)惠券多次去線下找工作人員兌換優(yōu)惠時,工作人員也未必能發(fā)現(xiàn)其行為,而此時可以認定為詐騙罪。類比可知,程序只能識別cookie值的身份,機器作為工作人員的意志延伸,可能存在被騙。此時,下游犯罪構(gòu)成詐騙罪。
第三,本案行為人構(gòu)成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罪。從邏輯分析,當下游行為構(gòu)成詐騙罪,而幫助犯只能以詐騙的幫助行為追究責任,而不適宜定性為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的犯罪類別。否則,就會出現(xiàn)正犯實施詐騙罪,而幫助犯構(gòu)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程序、工具罪的結(jié)果,這不符合共犯與幫助犯之間的罪名邏輯。
綜上,本案犯罪對象是數(shù)據(jù)從而排除了計算機系統(tǒng)犯罪的適用,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應(yīng)當在準確下游犯罪構(gòu)成詐騙罪的前提下,構(gòu)成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罪。
另需注意,本案認定幫信罪情節(jié)嚴重的標準也應(yīng)當適用兜底條款。2019年“兩高”《關(guān)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wǎng)絡(luò)、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9年《解釋》”)第12條規(guī)定了“情節(jié)嚴重”的標準,由于客觀原因限制只能查證一名下家B構(gòu)成詐騙罪,而公安機關(guān)認定A的違法所得雖然遠超第4款規(guī)定的“違法所得1萬元以上”,但經(jīng)審查,其售賣給下家B的軟件金額僅為200元,其他違法所得沒有完整的證據(jù)鏈能夠證實售賣的軟件均被下家用于詐騙活動。由于行為人對下游犯罪持概括性故意,因此,本案應(yīng)當適用2019年《解釋》第7款,即因客觀條件無法查證被幫助對象是否達到犯罪,相關(guān)數(shù)額達到第1款第(二)項至第(四)項適用標準5倍以上,可以構(gòu)成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罪。
* 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qū)人民檢察院梧田檢察室四級檢察官助理[325000]
**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qū)人民檢察院梧田檢察室書記員[325000]
[1] 指某些網(wǎng)站為了辨別用戶身份進行Session跟蹤而儲存在用戶本地終端上的數(shù)據(jù),由用戶客戶端計算機暫時或永久保存的信息。簡言之,即用戶為免輸密碼,主動一鍵保存在本地的用戶名、密碼等公民個人信息。
[2] 犯罪嫌疑人冒用買家身份,騙取客服審核通過后登陸購物網(wǎng)站內(nèi)部評價系統(tǒng)刪除差評。
[3] 參見皮勇:《網(wǎng)絡(luò)黑灰產(chǎn)刑法規(guī)制實證研究》,《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
[4] 參見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qū)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4)龍泉刑初第390號判決書。
[5] 參見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6)川0184刑初第611號判決書。
[6] 參見王肅之:《論為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提供支持行為的正犯性——兼論幫助行為正犯化的邊界》,《刑事法評論》2020年第1期。
[7] 參見江溯:《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罪的解釋方向》,《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年第5期。
[8] 參見王肅之:《論網(wǎng)絡(luò)犯罪參與行為的正犯性——基于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罪的反思》,《比較法研究》2020年第1期。
[9] 參見張明楷:《非法獲取虛擬財產(chǎn)的行為性質(zhì)》,《法學》2015年第3期。
[10] 參見陳云良、周新:《虛擬財產(chǎn)刑法保護路徑之選擇》,《法學評論》2009年第2期。
[11] 參見《張四毛盜竊案》,最高人民檢察院網(wǎng)https://www.spp.gov.cn/spp/jczdal/201710/t20171017_202593.shtml,最后訪問日期:4月5日。
[12] 同前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