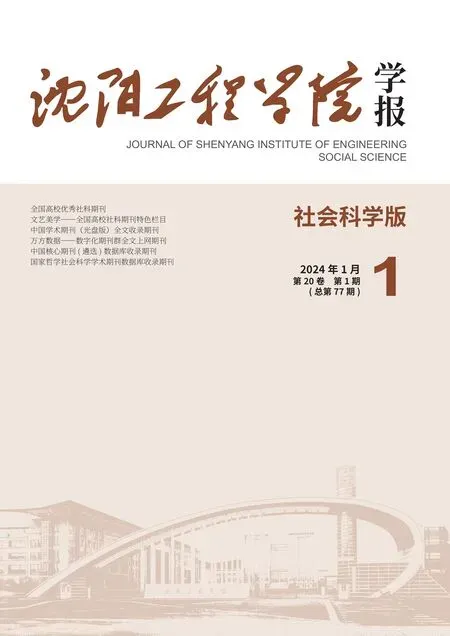亂世中的忠君之心
——杜甫《哀江頭》“去住彼此無消息”句考釋
萬圣雅
(安徽大學 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1)
一、諸家匯評
自北宋討論杜詩的風氣興起,及南宋形成蔚為大觀的“千家注杜”繁盛現象以來,歷代學者對杜甫詩歌的探討與研讀層出不窮。隨著杜甫研究的不斷充實與深入,時至今日,幾乎每一首杜詩及其字句都存在多種解釋。而《哀江頭》作為杜詩中膾炙人口的名篇,情感充沛,字字泣血,又涉及后人所津津樂道的貴妃題材,更是深得注家偏愛,其詩句及旨意釋讀,實是眾說紛紜。其中“去住彼此無消息”一句,千百年來,亦引發廣泛探討,歷代注解者的關注點相對集中在“彼此”二字,所持觀點大抵可分為以下三種。
1.父子:玄宗與肅宗
即認為安史之亂中,玄宗與其子肅宗之間兩無消息。此觀點見于唐注,謂“托諷玄、肅二宗”[1],又稱“舊謂”,言“諷玄、肅父子”[2]。此說法多被后世所否,大致可定為出現于宋前,為早期所注。
2.君臣:玄宗與杜甫
即認為亂世之中,玄宗與作者杜甫之間兩無消息。此觀點一般見于早中期所注,言“渭水即京城之水,劍閣在蜀。甫睹渭水東流,翻思玄宗入劍閣,彼此消息斷絕。深咎肅宗不能迎父歸大內以盡孝道故也。”[3]9結合上句“清渭東流劍閣深”,以“清渭”作渭水解,指代長安,即杜甫所在之處;而劍閣作為玄宗所幸之地,取君臣二人彼此消息斷絕之意。即趙次公所云:“此言明皇既幸蜀矣,長安與蜀相望于數千里之間,去蜀與住長安者,皆不知消息也。”[4]60仇注載“朱又云:‘渭水,杜公陷賊所見。劍閣,玄宗適蜀所經。去往彼此,言身在長安,不知蜀道消息也’。”[1]明代的王嗣奭亦持此觀點,認為“彼此”確指玄宗與杜甫君臣,有“‘清渭東流’二句,謂帝西幸未嘗不懸念京師,而臣子留住京師,又主上今何下落,故就目前境地言之,以寫其憂君之極思耳”[5]。然而值得注意,持此種觀點者多以宋人為主,至清代已逐漸不為主流之說。
3.帝妃:玄宗與楊妃
即認為馬嵬賜死后,玄宗與死去的楊妃之間兩無消息。此說法多見于清代及以后,且為近代研究者所普遍接受。清代仇兆鰲注:“考馬嵬驛,在京兆府興平縣,渭水自隴西而來,經過興平,蓋楊妃稿藏渭濱,上皇巡經劍閣,是去往西東,兩無消息也。唯單復注,合與此旨。”[1]清代浦起龍《讀杜心解》記有“清渭,貴妃縊處。劍閣,明皇幸蜀所由”[2],暗示“無消息”者實為玄宗與楊妃。清代錢謙益注杜詩亦持此觀點。箋曰:“此詩興哀于馬嵬之事,專為貴妃而作也。清渭劍閣寓意于上皇貴妃也。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門過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則清渭以西,劍閣以東,豈非蛾眉宛轉,血污游魂之處乎?故曰去住彼此無消息。”[6]35從地理角度做出了人物判斷。此外,清代楊倫言:“清渭,貴妃縊處,劍閣,明皇入蜀所經。彼此無消息,即《長恨歌》所謂‘一別音容兩渺茫’也。”[7]同樣將“清渭”與“劍閣”作為兩個地點名詞加以理解。蕭滌非《杜甫詩選注》亦采用此說[8],莫礪鋒關于該問題的探討也以錢、仇二人之說為是[9]。
二、君臣說合度
通過上文對各家觀點的歸納梳理,“去住彼此無消息”的對象主要存在父子、君臣與帝妃三種可能。筆者認為,杜甫《哀江頭》中“去住彼此無消息”一句的主語應落在君臣上,即玄宗與杜甫之間。以下將聯系詩句上下文,從具體詩句解讀、詩歌的主旨辨析與內容探討及宋代的杜詩接受三個方面出發,對此進行論證。
1.“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句的解讀
“清渭東流劍閣深”作為“去住彼此無消息”的上句,是各代注杜者在解釋“彼此”對象問題時難以忽視的部分。學者多從句中的地理要素切入,認為“劍閣”指代玄宗所在,故另一對象必與“清渭”相關,并以此為基本邏輯,對相應觀點加以探析。不可否認,上下文對詩句的正確理解作用匪淺。然筆者認為,《哀江頭》一詩,過度強調“清渭東流劍閣深”中的地理因素更易導致詩句的誤讀。
就父子說而言,仇氏一句“肅宗由彭縣至靈武,與渭水無涉”[1],便篤定此解為曲說。就帝妃說而言,莫礪鋒在對《哀江頭》的岐解論述中,也只是說:“馬嵬坡在渭水以北三十馀里,謂之‘渭濱’自無不可。且玄宗攜楊妃奔蜀,出長安后一路沿渭水西行,至馬嵬驛而突遇兵變,從此天人永隔。”[9]從而表示贊同。然結合文本加以仔細推敲,便很容易發現,若以此為判斷標準,則過于依賴地理因素,所得結論總歸稍顯牽強。
回到作品本身,“去住彼此無消息”偏向一時感慨之言,應有時間限定。聯系詩歌的創作背景與具體內容,已然“血污游魂”,其范圍大致在貴妃被誅后至作此詩時。在這一時間段內,誅貴妃后,玄宗入蜀途中,肅宗“至渭北便橋”“次永壽縣”[10],單從地理上實在算不得與渭水無涉。而杜公作此詩時(至德二載春),至德二載二月,肅宗次于鳳翔,其后及至春盡,史書未復提肅宗蹤跡。然渭水東流,又經鳳翔所在。且玄宗、肅宗父子間,戰火紛擾,亦難通消息。這樣一來,相同的邏輯下,帝妃說如果正確,那么父子說自然也無甚不妥了。且杜甫時居長安,同樣符合“清渭”的地理條件。如是三種觀點皆可說得通,顯然無法據此定論。再者,“清渭東流劍閣深”一句單指玄宗入蜀過程,與另一對象無關,亦并非不可。
是故必先跳出地理解讀的慣常思維,方才能夠得到詩句的真正含義。暫且拋開“清渭東流劍閣深”句的地理要素,簡單將其視作兩處遙遠不相聞的指稱,重新將關注點落在“去住彼此無消息”本身。不免發現,其中“去住”二字卻自來不多被關注。從字義出發,“住”本義為“停留、停住”,又有“暫居、居住”之意。如果默認“去”是玄宗西幸,那么要探討的便是“住”的對象,彼時肅宗致力收復河山,東征西討,自是難“住”。而楊妃已是玉殞香消,作停留于馬嵬之地,與玄宗兩無消息解,雖可通,不免別扭。畢竟其長眠馬嵬,一生已然終結,陰陽兩隔,不需要亦不產生所謂消息了。而以“居住”來理解,更顯荒謬。又若依上文楊氏所言:“彼此無消息,即《長恨歌》所謂‘一別音容兩渺茫’也。”[7]倘以《長恨歌》為前提,則楊妃未死,反是往之海外仙山,而此時明皇幸蜀,二人孰去孰住,又是一樁懸案,更是跳出“清渭”的地理限定了。
其實明代王嗣奭注杜詩時已注意到這一點,故其取“去”為“帝西幸”意,“住”為臣“留住京師”。縱然不作此說,取“暫居、居住”意亦無不可。由此可見,“去住彼此無消息”的對象定為君臣更為合適。當然,此等亂世,玄宗自是不會在意杜甫的消息,這里引申作玄宗所在的蜀地與杜甫所停留居住的長安兩地間消息不通之意為佳。且詩句如此解釋,更顯老杜一派憂國忠君之心,昭明可見,誠若冰雪,亦合乎其人物形象及創作旨意。
2.《哀江頭》的主旨辨析與內容探討
君臣說與帝妃說二者之間的主要爭議點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其一是《哀江頭》的主旨所在。其根本矛盾點在于《哀江頭》全詩是否為楊妃而作。就此,前人已多有論駁:“自蘇黃門云,‘《哀江頭》即《長恨歌》也。’后潘耒駁之曰:‘《長恨歌》本因《長恨傳》而作,公則安得預知此事。’浦起龍按:‘潘氏之說亦非也。黃門之意,謂與《長恨》同旨,非謂預知其傳而賦之。’”[2]錢謙益箋曰:“此詩興哀于馬嵬之事,專為貴妃而作也。”[6]35仇兆鰲注云:“此慨馬嵬西狩事,深致亂后之悲。妃子游魂,明皇幸劍,死別生離極矣。”[1]以上觀點大抵皆贊同《哀江頭》確為哀楊妃之作。
然潘氏《杜詩博議》提出異議,言明:“《北征》詩既有‘不聞殷夏衰,中自誅褒妲’句,杜公才以貴妃之死,卜家國中興,不應專意另做他詩以哀帝妃天長地久之恨。”[6]35對此,浦起龍又做出反駁,明言:“至以《北征》例此詩,則又迂甚。語有之:‘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告中興之主,《北征》自應莊語;過傷心之地,《江頭》定激哀衷。發情止義,彼是兩行。一派頭巾氣,未可與言詩已矣。”[2]但觀其反駁之語,稍加斟酌,則明顯有強詞奪理之嫌。詩作既成,非敝帚自珍,自會為時人乃至后人所覽。無論告中興之主的莊語,或是過傷心之地的抒情,皆同在杜集中,流傳后世,風格或有差異,觀念又何必自相矛盾,為他人攻訐留有把柄?且《江頭》與《北征》同年所作,不過春秋之別,短短幾月,豈會對一件事的認識大相徑庭?退一步說,戰亂流離中,以詩人之情懷,創作《北征》時,未嘗不是處處傷心地;《江頭》所成日,未必不念天下之主。浦氏將其全然視為“兩行”,實在有失偏頗。再者,試想老杜作品盡以此來推論,大凡詩歌旨意矛盾之處,皆以一時一地之差異,或作者心態之變遷來解讀,則不同杜詩的參照價值,恐怕是蕩然無存。
由是,筆者認為《哀江頭》所哀,更多昔盛今衰,物是人非之哀,是作者對君主的擔憂,戰亂的悲嘆及個人命運的迷惘,并不以帝妃之情為主。將它的主旨等同于《長恨歌》,認為其只關注男女之情,不免有些狹隘,亦是對杜甫的小覷。誠然,通過對杜詩的整體把握,杜甫素來具有“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的高尚人格。但需要注意到,他對“草木”的哀憐背后,是以一顆忠君憂國之心作為支撐的。換而言之,相較于“草木”,“乾坤”才是第一位的。這一時期作品中,杜甫對百姓、戰士乃至貴妃的哀憫,實質上都是對將傾之社稷的悲慟的外化。由此,“去住彼此無消息”應作君臣解,方與作者原意更為貼合。
其二是《哀江頭》的內容安排。在詩歌內容的解讀上,主要是帝妃說對君臣說的反駁。如清代仇兆鰲按,朱注君臣說為非,稱:“上文言馬嵬賜死事,不應下句突接長安。”[1]同時代的楊倫亦反駁朱注云:“作公自言,恐與上下文不相連屬。”[7]總結起來,即認為采用君臣說,則在詩歌內容上有轉折突兀,文意不連之嫌,故皆以帝妃說為是。
筆者認為,這其實是將《哀江頭》主旨默認等同于《長恨歌》后,一種先入為主的體現,在論證的邏輯順序上仍有待商榷。即如果不完全將帝妃愛情視為詩歌主題,而將之作為詩人哀嘆盛世不再的相關表現,這一觀點便難以自圓其說。
就詩歌具體內容安排來看,該看法亦如其所反對的那樣,對上下文進行割裂。現試以對詩歌內容結構加以總結:前四句由自身起頭,引出長安曲江景色,后轉入對變亂未起時的曲江盛事的書寫,隨即又回到當下,以詩人之口,發出“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的嘆息。再想到清渭劍閣,君臣兩地消息阻絕,感嘆人生無常,不若江水江花永無終極之日。最后再回歸自身,以己之茫然,興傷情之致。以上,從內容出發,筆者認為,詩中帝妃的部分至“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句便已經結束,下文由帝妃之事過渡到君臣間,并不能算得上是突接長安。言其突接長安,則過于拘泥于帝妃內容,未從整體處入手,沒有充分理解詩歌中的時空轉換。即假設仇楊之說成立,清渭二句仍是關于帝妃的內容,以此推導,其后“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亦可說是突接長安。且“清渭東流劍閣深”句同樣可作為過渡來理解。賈島有“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句,可見唐時渭水和長安,本就緊密相關,由是上下文仍屬流暢,并無明顯突兀感。故仇、楊二人的相應觀點,無法于根本上使君臣說動搖。
3.兩宋:真正理解杜甫的時代
聯系各注家解釋的歸納梳理,不難發現,父子說源于唐注,君臣說多見于宋時,而帝妃說的興起則多是清代及以后。這一現象顯然并不是巧合。就作品接受而言,不同時期的讀者對經典作品的接受必然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而兩宋時期,正是真正理解杜甫的時代,對杜甫的詮釋更為接近其內心深處所感所思。
概觀杜甫坎坷曲折的一生,他的時代與他的靈魂是齟齬的。他與他的作品,含蓄、沉重、內斂,飽含忠君之熱忱、士大夫之責任感,充斥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縱使時而詼諧,也展現自己的小幽默與單純的樂趣,然終究難以徹底融入這一派盛唐的天真。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在杜甫的時代里,他始終是孤獨的,不被理解的。縱然是他聲名日顯的中晚唐時期,時人或學其詩藝,致力于模仿其創作手段與風格;或注重其道德解讀,試圖借詩歌干預現實政治,都流于表面,不過是對他的努力與學識的肯定,對他的才華與作品的贊賞。而杜甫忠君愛國的光輝人格,亂世顛沛中一片老臣之心,隱藏在錦繡詩篇背后,依舊是人跡罕至。
及至宋代,前期統治者總結前人之教訓,以崇文抑武作為基本國策,重視對倫理綱常(尤君臣間)的恢復,儒學呈復振之勢。適時又改進科舉,廣開普通士人為官之路,激發其參政議政的熱情,使其葆有忠君愛國的情懷,憂慮社稷之苦心及高度的文人自信。在這一時期,個人位置明顯提高,仁義忠信的教育背景下,士大夫多以“長城”自許,日益關注自身價值的實現。
回到杜甫其人的解讀,同樣的以天子近臣自詡,同樣的具有高度自信與社會責任感的澹蕩文人,同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選擇,此時的文人可謂是深以為是。南宋時期,時局動蕩,正是風雨飄搖之際,便愈增黍離之悲,詩人多有“塞上長城空自許”的悲嘆,就國家與個人的前路未卜自怨自憐。而這份破碎感,又與經歷安史之亂的杜甫產生了強烈的共情。凡是時人對此亂世的可傷可感,皆有杜甫先為之代言。不可否認,不論是其人格追求或是政治理想,這都是一個與杜甫其人高度適配的時代,這一時期的社會風尚與文人價值觀與杜甫的思想可以說是不謀而合。而理解始終是雙向的,杜甫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感染宋代文人之時,構成他偉大人格的仁義之心、忠愛之魂,以及山河破碎身世浮沉的痛楚,同樣無不在宋人的解讀下,展現得淋漓盡致。如此詩人,正值國破家亡的亂世背景下,如果拋卻大局觀,僅僅著眼于帝妃的兒女私情,或徒是哀嘆楊妃的悲劇命運是不應當的,這與其所接受的儒家教育及源自內心深厚的忠君責任感自然是相違背的。
總之,宋代是杜甫形象的蘇醒期,是杜甫接受面的再塑造。正如學者區別唐宋文化時所指出的,“和唐人相比,宋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靜、現實和腳踏實地,它超越了青春的躁動,而臻于成熟之境。”[11]這種時代的成熟恰好是與杜甫的成熟所契合的。據此,《哀江頭》中“去住彼此無消息”句的對象亦應以君臣為是。
三、歷代解讀變遷之原因
優秀的文本往往是多義的,接受者的多重解讀也正體現了它的經典性。《哀江頭》便是這樣的作品,就“去住彼此無消息”句中“彼此”對象問題而言,歷代的不同解讀與當時接受層面的需求是分不開的。且通過上文的辨析,“彼此”對象在歷代解讀中主流觀點的變化情況,本質上是隨時代的發展而改變的,且這一轉變并非偶然,而是人性在文學史及文學作品的解讀中不斷演進的表現。
正如章培恒先生所言,“文學的發展根本上取決于人性的發展,并反映著人性的狀況。在社會生產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個人越來越多地獲得其作為個體存在的價值,人性中原來被抑制的東西會日漸活躍,因而文學中所反映出的生活面貌、人物性格和感情等也就越來越豐富復雜,它的成就不斷提高了。”[12]對經典作品的解讀也是如此。自早期的父子說發展到君臣說,再逐步向帝妃說的過渡,恰是人們對自我關注與自我審視不斷深入在文學作品解讀中的明確體現。
首先,就父子說而言,對象所指的玄宗與肅宗皆為君主,是不作為普世意義上的“人”的概念來理解的,此處的“父子”并非是親情的體現,更多是傾向于政治的象征。各家所注釋的皆是“諷玄、肅父子”[2]之類,是對帝王治國不力,以致亂世流離的委婉批評。二位君主根本上還是作為國家政治符號出現的,而非世俗的“人”,社稷國運是遠遠凌駕于人情之上的,由是此解讀并未體現出明晰的人性因素。
再是兩宋盛行的君臣說,結合此前的時代分析,文學亦逐漸關注個人。“彼此”一詞不再指向兩位君主,而是出現新的“忠臣”形象。即解讀開始代入士人群體的心態,意在發掘士大夫在戰亂中哀世憂君的使命感與責任感。這里雖仍然是政治主題,但已涉及個人在國家層面上的價值認同,凝練出相對的自我意識,詩歌中的情感濃度得到顯著提升,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人性在文學作品理解方面的成長。
此后,“隨著后陽明學時代的到來,經明清思想轉型而逐漸形成了一股學術新思潮。這股思潮由理學、心學乃至氣學等多重思想合力推動,主要表現為對廣義宋明理學的反思與批判,更有一批嚴肅的儒者試圖通過‘回歸原典’的方法重新審視儒家經典的知識系統。特別是儒家人性論乃至孟子性善說也遭遇了來自理學陣營內部的反駁,以及基于文字訓詁學的猶如‘眼中挑刺’一般的嚴格檢視。及至乾嘉時期,考據學家竟不約而同地就人性問題表達了重要關注。”[13]在此基礎上,學者作為文本解讀的主體,其對杜甫詩歌選擇的再接受,必然更加重視“人”和“自我”,對人的平凡的本性、世俗的欲望予以更多的關注與承認,從而在文本闡釋方面,亦逐漸由宏觀政治向個體之間的情感過渡。此時,統治者開始作為人而非政治符號被理解,被賦予“人”的種種或悲哀或無奈之情緒,《哀江頭》已然完成從政治主題向愛情主題的轉變。就此,“去住彼此無消息”句中“彼此”對象所指,本時期的注家自是多贊同帝妃之說。
綜上,《哀江頭》中“去住彼此無消息”句中的“彼此”對象的歷代解讀之變遷,正是人性在文學作品中不斷演進的縮影。
四、結語
“歷史是總體的人的生成過程,人是歷史的劇中人和劇作者。”[14]葛兆光在撰述思想史的寫法時,曾就“六經皆史”與“史皆文也”兩種不同的觀點,引出關于后現代歷史學的討論。在后現代歷史學派看來,先是存在“過去”,即真實發生過的事件。而“歷史”不過是對“過去”的敘述,屬于文本,帶有敘述者的主觀色彩。葛兆光同樣認為,文本是無法全然反映既定真實的,“每一個歷史敘述都在無意識地追求‘趨近真實’”,即“指向真實”[15]146。且古人所表達的思想情感作為“生活在‘過去’的人的無法重復的想法”[15]147,便愈發真偽難辨,難以通過具體文本來被今人理解。
而《哀江頭》作為杜甫在安史之亂時期寫下的名篇,迄今已歷經一千二百余年,“作者在創作作品時,往往會同時受意識和無意識兩個心理層面的控制”[16],彼時作者之所思所想,恐怕早已是舊時流水,不可復追。其成詩之時,杜甫之心意顯然是確定的,即此處存在既定真實,但時過境遷,后世眾人都無法得知。因而千百年后,讀者只能通過傳世文本對其進行再次解讀。而對文本的分析,必然會涉及個體經驗,個體經驗又與時代需求息息相關。所以作品問世之后的解讀,相較于對既定真實的挖掘,更多的還是通過一種邏輯層面的自洽,從而盡可能地去還原當時詩人的真實想法。
綜上所述,筆者通過對杜詩解讀及接受的時代特點的分析,進一步確定君臣之說為詩句對象指涉之正解,認為其背后蘊含的是暫居長安的詩人對遠在蜀地的君王的惦念與擔憂。并由此得以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更好地去理解“去住彼此無消息”句,理解《哀江頭》篇,理解杜詩,繼而深深地體味出這位偉大的詩人在亂世之中的一顆忠君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