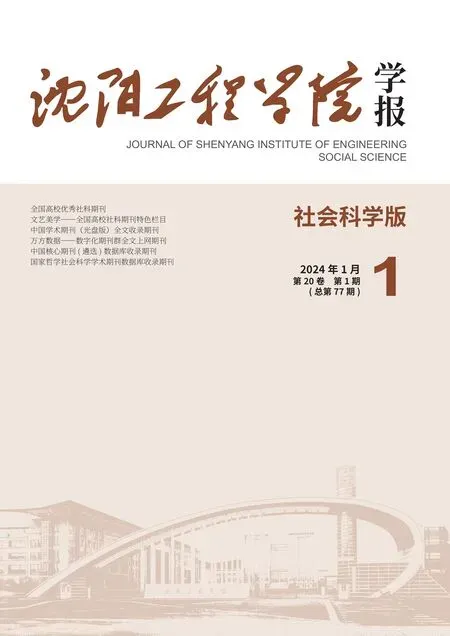眾生相的深層結構
——論徐坤的長篇小說《神圣婚姻》
南彎彎
(遼寧大學 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136)
《神圣婚姻》以一對年輕情侶的突然分手作為開篇,引出他們身邊親友形形色色的婚姻異變,小說以婚姻為線索編織出故事的網。毫無疑問,婚姻是小說的核心要素,不過小說并沒有走向商業化誘導的一般言情路線,相反它更像是一部問題小說。婚姻只是其外殼,人性才是內核。“文學始終是歷史的載體,是歷史記憶的當下呈現”[1],文學與歷史現實有著密切的關系。《神圣婚姻》生動地展現出了當代社會的眾生相,通過一個個人物鏡像折射出市場經濟背景下人性的異化,記錄著當代社會的熱點與痛點,完成了與時代的“近身肉搏”。
一、情感失敗者形象與性別文化思考
從20 世紀80 年代到當下,徐坤的女性主體意識逐漸加強,更加注重女性群像的塑造,這在《神圣婚姻》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單純的90 后海歸女孩程田田、原二人轉臺柱子于鳳仙、事業有成的研究所副所長毛榛、人生贏家的大律師顧薇薇、尋仇母夜叉梁桂芳……她們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性格也千差萬別,但她們卻有一個共同點——都在愛情中受了傷。《神圣婚姻》中的女性大多都遭遇了情感上的挫折,她們都是情感關系中的失敗者,但這些失敗者又有所不同。
1.成長型女性
開篇就被莫名分手的程田田無疑是情感中的失敗者。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不難發現二人的戀情從一開始就注定是失敗。兩人擁有不同的價值觀,孫子洋認為“買了房子,才能成為真正的北京人”[2]29。而田田則認為“能不能成為北京人,也不是有沒有房就能決定的”。孫子洋為了能在北京買房子,不惜讓父母假離婚。同樣的問題讓程田田做出抉擇,田田卻語氣決絕地喊出“不樂意!”[2]81。愛情或者婚姻,并不是一時的沖動,而是一種契約關系的締結,締結雙方應該有精神上的契合,價值觀不一致的二人顯然難以達成這種契合,二人的愛情自然以失敗告終。該情節的設計不僅揭示出這段感情失敗的根本原因,同時還批判了物質的力量和資本的邏輯對中國人的裹挾,更是將一個單純、三觀端正的女孩形象立于讀者面前。程田田是一個成長型女性,她經歷了從“子君”向“林道靜”的蛻變。
小說借毛榛、毛丹之口披露了田田在這段情感關系中的位置,田田是依賴者,孫子洋是被依賴者,二人在情感關系中有著不平等的兩性地位。魯迅早已在《傷逝》中借助子君的遭遇警示過女性,在不平等的兩性關系下,愛情會走向悲劇。子君作為那個時代的新女性,集眾多美好品質于一身,有才情、有膽識。但長期的依賴致使她逐漸失去了獨立的人格,出門在外她會小心翼翼扯著涓生的衣角,在家中沒有經濟能力的她只能卑微地向涓生討要生活費,逐漸迷失了自我,她最終只能面對被拋棄的悲慘命運。早期的程田田,作為學成歸來的“海歸”她有學識,敢于和孫子洋同居,她也有膽識,而且她與子君一樣是情感關系中的依賴者,兩個女性有著驚人的一致性。不過在見識過涓生的真面目后,子君可以毅然離開。但程田田在被無情拋棄后依舊迷戀著孫子洋,甚至為了能再見孫子洋一面,不惜住在“不足十平方米平房偏廈里”[2]86,忍受每天十小時的工作時長,甚至每個月“倒貼進去1000元”[2]86。田田缺少了子君的清醒,她對愛情仍然抱著天真的幻想。子君在與涓生的情感失敗后,在他人的流言蜚語與家人的指責冷眼中凄然離世。但田田在情感失敗后,卻在家人的陪伴與開導中走出了陰影,擁有了嶄新的人生。更加清醒的子君,卻最終走向了凄慘的結局,這是時代背景所造就的。與生活在舊時代的子君相比,生活在新時代的田田無疑是幸運的。
后期的程田田實現了從“子君”到“林道靜”的飛躍。前期的田田與林道靜有著截然相反的追求,一個沉溺于對男友和家人的依賴,一個一心渴望著自由與獨立。但后來經過愛情的失敗與支教的鍛煉,田田的形象發生了轉變。情感上,從對孫子洋的依賴,到與潘高峰的并肩而立,完成了“依賴型戀愛”向“革命加戀愛”的轉變,找回了曾經在戀愛中迷失的自我。事業上,從工作不順的“海歸”,成長為了鄉村振興的建設者,在鄉村的土地上她實現了迷茫者向鄉村振興者的轉變。她與林道靜一樣接受連續洗禮,一樣努力追求人生價值,一樣最后也都成功實現了人生的價值。從北京到沈陽再到“壩田村”最后再回到北京,這是小說場域的轉移,同樣也是田田的成長之路。
故事的尾聲,田田不僅擁有了“革命伴侶”潘高峰,還獲得了中科院大學的博士錄取通知書,情感與事業雙豐收。徐坤給予了田田一個美好的歸宿,這充滿希望的結局與程田田身份設定有關。小說中多次表明田田90后的身份,田田的形象超出了小說角色的本身,她實際上象征著年輕一代。田田實現了從“子君”向“林道靜”的成長,擁有了美好的結局,這象征徐坤對年輕一代的美好期許,也是徐坤對年輕人在今天如何尋找真正的愛情所做出的回答。
2.傳統型家庭婦女
如果程田田是新一代女性,那么于鳳仙則象征著中國傳統家庭婦女,她的形象滿足了對家庭婦女的所有要求。對于長輩而言,正如孫爺爺的內心獨白那般“還真就是于鳳仙這個兒媳婦最拿他當回事。不管有錢沒錢,不管跟著走到哪兒,兒媳婦都伺候得他舒舒服服的”[2]104,她是一個孝順的兒媳婦。對于兒子而言,她對兒子的衣食住行事無巨細,將兒子照顧得妥妥帖帖,她是一個稱職的媽媽。對于丈夫的兄弟姐妹而言,她力所能及地提供幫助,連丈夫弟弟妹妹的婚禮也是她幫著張羅的,她是一個合格的大嫂。對于丈夫而言,她盡心地照顧一家老小,并且對婚姻忠誠,即使已經早早地假離婚,也是在得知丈夫早已出軌的事實后,才以為兒子與自己找出路為目的選擇與炮三在一起,毫無疑問她也是一個好妻子。她任勞任怨、體貼細致、美麗大方,作家不遺余力地將這些優點堆砌在于鳳仙的身上,塑造出了一個賢妻良母的形象。當然為了人物的立體飽滿,徐坤還設計了當她得知田田的副所長大姨無法為兒子提供幫助后教唆兒子分手的情節,體現出了她勢利、自私的一面。不過單純從母親這個角度而談,她的出發點也是為了兒子可以擁有更好的未來,而且最后她還向田田道了歉,滿懷歉意地說出了那句“孩兒呀,對不住啊”[2]119。
就是這樣一個集眾多美好品質于一身的好妻子,還是遭到了丈夫的欺騙與背叛,更加體現出了婚姻的脆弱與人性的異化。當她為給兒子買房做出假離婚的犧牲時,她的丈夫卻滿心想著如何弄假成真,想著與情人雙宿雙飛,頗具諷刺的意味。于鳳仙是家庭的無私奉獻者,也是遵循傳統觀念的最大受害者。也許是出于女性的身份認同,徐坤想借助這一形象告誡女性同胞,要勇敢打破傳統觀念對女性的束縛。徐坤選取“溫情敘事”的模式,為并沒有太多過錯的于鳳仙安排了圓滿的結局,讓曾經被傷害的于鳳仙,不僅擁有了工作實現了經濟上的獨立,還收獲了與炮三幸福的婚姻。這次她選擇為自己而活,她收獲了生命的輕盈感,也成為了擁有無限精神疆域的享受者。
3.婚姻中的“強勢派”
徐坤是一位極具女性意識的作家,但同時她也“意識到一味與男性保持二元對立的模式,是無法找到女性健康成長之路的”[3]。《神圣婚姻》中顧薇薇和梁桂芳形象的塑造,就充分體現出了徐坤對兩性關系的思考。
無論是小商販梁桂芳,還是大律師顧薇薇,她們都是婚姻關系中強勢的一方,當然她們的婚姻也都以失敗告終。梁桂芳是個愚昧粗魯的女人,妄想憑借給丈夫穿丑陋內褲來預防丈夫的出軌。她還喜歡大聲地用言語侮辱丈夫,甚至最后不惜打到丈夫單位,又吵又鬧,毫無顧忌地踐踏著丈夫的尊嚴。顧薇薇與愚蠢的梁桂芳不同,她聰明睿智,聽完毛榛對孫子洋一家的敘述后,可以一語道破“他爸是不是外邊有人了”[2]59的真相。雖然她可以一眼看穿別人的婚姻,卻從來不了解自己的丈夫。自以為是地認為丈夫不在意研究所的事業,以為丈夫熱衷于圍著家庭轉,甚至用“絕對的大內總管”[2]58來形容丈夫,惡狠狠地抹殺了丈夫的尊嚴。當丈夫提出掛職時,不僅不支持丈夫的事業,反而借離婚來威脅拿捏丈夫。程田田與于鳳仙的情感失敗是方方面面原因共同造成的,但是梁桂芳與顧薇薇卻是咎由自取。
這兩位女性,處于不同的社會階層,擁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卻都因為強勢親手葬送了自己的婚姻。程田田與孫子洋兩性關系的不平等,是二人愛情悲劇的根源之一,徐坤借二人的情感關系說明女性不能在愛情中成為依賴者。梁桂芳與顧薇薇失敗的婚姻,也是由不平等的兩性關系造成的,作者借助她們說明女性不能成為依賴者同樣也不能成為“強勢派”。在《神圣婚姻》中徐坤并沒有進行男女性別的對立,用夸大女性的悲慘境遇的方式來對男性進行控訴,相反她花費大量筆墨將男性的不易展現出來,散發著人文的關懷,這也正是其女性意識成熟的表征之一。徐坤清醒地認識到并在小說中反復體現出:平等的兩性關系,才是幸福婚姻的重要條件。
徐坤塑造了一系列的愛情失敗者,在她們的形象構建中將婚姻的本質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她先將婚姻進行解構,而后又進行了重塑。將愛情的真諦藏匿于小說的文字之中,健康的愛情是情侶雙方并肩而立,女性應該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幸福的婚姻需要平等的兩性關系等。作家最難做到的就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寫作,但徐坤卻從不諱言與時代同行,她總是會在認真地思考后給出自己的回答。
二、“奉獻型長輩”形象與社會熱點透視
小說中有著豐富的情感關系描寫,不僅展現出了不同代際之間的愛情糾葛,還充滿著大量的親情關系的敘述,更是有意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設定成“奉獻—索取”的二元模式,塑造出了一系列的“奉獻型父母”和“奉獻型長輩”。
徐坤借著小說人物樊梨花之口道出了當今時代為人父母的心理,“不替你們解決,你們自己能行啊?再說啥叫解決呀?那不就是出錢出力,犧牲自己有所奉獻嗎?”[2]202獨生子女政策、優生優育的觀念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共同造就了“獨生子女”的誕生,同時也催生了“奉獻型父母”。小說中程田田的母親對女兒的付出有目共睹,因為她不舍得女兒做家務,所以田田讀高中時還會將臟衣服帶回家給她洗;女兒情感受挫時,她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放下一切陪同女兒去北京找男朋友;女兒找不到工作,她就不辭辛苦地托關系給女兒找工作等。同樣女強人樊梨花為了守護女兒也是費盡心思,女兒結婚時“為防止老孔前妻來鬧,樊梨花還特意地雇用了保安公司”[2]179;女兒家里的一切家務都由她料理;她還替女兒“出馬”與女婿的前妻進行談判等。在《神圣婚姻》中不乏“奉獻型父母”的身影。
宣揚父母對子女的無私奉獻并非新的寫作模式,但徐坤寫作的新在于她沒有將奉獻的對象局限于父母雙方,而是將筆觸延伸到了孩子身邊的各位長輩。田田的大姨為幫田田找到工作,“開動腦筋,搜索所有能幫得上忙的人際關系”[2]7。為了讓孫子洋在北京買房,整個家族為他湊錢,從叔叔到姑姑再到爺爺,每個長輩都貢獻了一份力。是什么原因使人情冷漠的社會產生了眾多甘愿奉獻的長輩,徐坤在小說中給出了她的答案。她借毛榛之口說出:“我們家姐妹倆,下一代就這一個孩子”[2]7,反映出了這樣一個社會現實:雖然現在已經沒有了獨生子女的政策,但是新生兒的出生率卻一直呈現下降趨勢。相比之前政策,一個小家一個孩子,現在沒有了獨生子女政策,反而產生了一個大家族一個孩子的情況。當孩子成為“稀缺資源”,那孩子自然會獲得家族中各位長輩的關愛。
徐坤的《神圣婚姻》是小說,但更加像是這個社會的記錄手冊,記錄了這個社會的熱點與痛點,在小說中留下時代的烙印。而且她不僅僅記錄,她還會在小說中給出她自己思考后的答案。徐坤通過“奉獻型長輩”的塑造記錄了“人口紅線”的問題,同時她還通過塑造“媽寶男”孫子洋和早期的“戀愛腦”程田田,提出了她的觀點,即“奉獻型長輩”的出現對于孩子的成長也許并非好事。她一直都在仔細地記錄,也在認真地思考。
三、新時代知識分子與理想主義堅守
“作為經濟學思想的經濟理性主義逐漸侵蝕人文理性主義的疆域,人文知識分子風光不再,人文知識分子由社會的導師降格為普通市民。”[4]緊握時代脈搏的徐坤早已對此有所察覺,在其之前的作品中,知識分子就早已經走下了神壇,他們不再是人們崇拜的精英,也不再是大眾思想的啟蒙者,環繞在知識分子身上的光環逐漸失去了它往日的光輝,他們被還原成了平常人,《神圣婚姻》則延續了這一寫作傳統。徐坤在小說中借助了一個笑話表明知識分子的現實處境“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撿破爛的,仔細一看是社科院的”[2]135,戲謔中也透露著心酸。新時代的知識分子面對如此處境,應選擇現實主義妥協還是理想主義堅守,徐坤通過三種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做出了她的回答。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知識分子的地位受到沖擊的同時,他們的心理也受到了干擾。在眾多誘惑之下,一部分知識分子被金錢、物欲所裹挾,他們放棄了理想,迷失了自我,漸漸成為了妥協者。《神圣婚姻》中的老黃和菲利普便被金錢和權利所誘惑,成為了妥協者。老黃為了省錢,竟虛報發票,不惜用科研經費報銷外孫的買書款。菲利普則不想著如何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反而一心鉆營應該如何巴結領導。二人甚至合作利用女留學生的照片來栽贓陷害老孔。在二人身上知識分子的品德良知早已不復存在,他們是《神圣婚姻》中為數不多的反面形象。作者巧妙地設計情節,最后讓二位學者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作者對這些妥協者的態度顯而易見了。
有向金錢與權利妥協的人,那自然也有堅持知識分子初心的人。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堅守者形象充滿了理想色彩。與以往“賦予女性人物以主體地位,且有意淡化男性的社會價值”[5]不同,在塑造《神圣婚姻》中研究所帶頭人老孔的形象時,作者毫不吝嗇地使用了“吃苦耐勞”“學識淵博”“義薄云天”等眾多褒義詞,還把他比作“關云長”“林沖”一般的人物。小說中的老孔是具備科研能力、管理能力、決策能力等于一身的“能人”。小說中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使命的堅守者,與淪為金錢與權利的奴隸的妥協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不僅是堅守者與妥協者的抗爭,也是作者的理想主義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抗爭。老孔的出現,象征著徐坤對知識分子的美好期冀。
小說中徐坤毫不避諱地披露出學術界的問題,“在論資排輩的老牌科研機構里,各種掣肘制約的因素太多”[2]57,小說中的薩志山就深受其害,“論資歷和能力,他也是有資格提副所長的,但被空降的菲利普頂了”[2]57,但他既沒有像妥協者那般被俗物所羈絆,為了獲得名利而鉆營,也沒有像堅守者那樣只是沉浸于學術的天地。薩志山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他決定帶著自己的才能與滿腔熱血走出去,不在研究所也可以為人民做貢獻。薩志山的出現,是徐坤對知識分子形象塑造的創新。在安嶺市,在脫貧攻堅的路上,他實現了人生的價值。不僅撕下了“軟飯男”的標簽,還從郁郁不得志的研究員變成了人民愛戴的薩市長。薩志山的出現為廣大知識分子指明了一條新出路。徐坤將筆觸伸向社會巨變的前沿與激流,對知識分子處境問題進行了新思考,給出了新答案,成功為小說融入了“真理”,體現出了作家的預見性。
“作家對自我的身份認知始終是關乎自身從何而來、將往何處而去的重要問題,它既是生命經歷的結果,也是文學創作的基點。”[6]出于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徐坤孜孜不倦地反復思考著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走出所面臨的困境,應該如何去充實萎靡的靈魂的問題。這三類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就蘊含著徐坤對知識分子現狀的深刻批判與無限反思。
《神圣婚姻》從社會的最小單位——婚姻出發,觀察著社會眾生與時代震蕩,試圖追尋人生價值的實現路徑。這是一本小說更是一幅當代中國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現實圖卷,淋漓盡致地展示著社會的眾生相,散發出現實主義的光輝。通過對這些眾生相深層結構的研究探討,直面社會的熱點與痛點問題。將對兩性關系的思考、親情關系的反思、知識分子出路的找尋等一系列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通過小說形式展現出來,及時地對時代做出了回應,《神圣婚姻》是一部極具現實主義色彩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