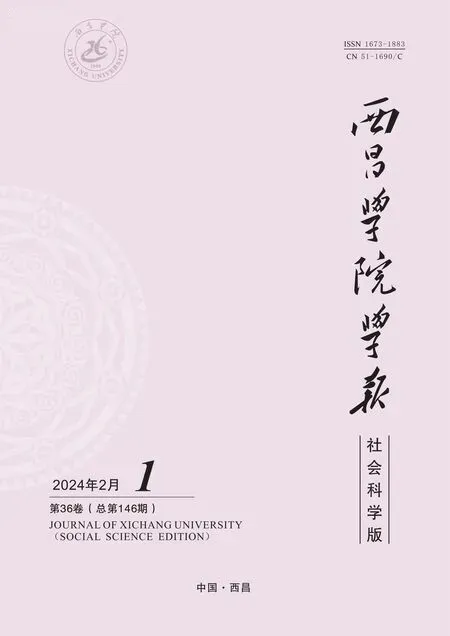彝族“都火舞”的身體表述與文化內涵
李曉鷗
舞蹈作為藝術中最古老的一種形式,是人與生俱來的。我國漢代《毛詩序》中所說:“情動于衷,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這足以說明,舞蹈這門藝術是人最本質、最直接、最真實的體現。少數民族舞蹈作為一種民族藝術的形式,其特點是源自民間,真實地反映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與情感,以及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宗教思想等。我國有著眾多少數民族,各民族都有不同風格特色的舞蹈。彝族是我國西南地區中歷史悠久且具有其獨特文化的少數民族。存在于大山之中的彝族在世世代代的遷徙中找到了各自的歸宿,根據文獻資料記載,彝族或其先民遷入四川涼山地區的歷史也相當久遠,據民間傳說及追溯家譜,有古候和曲涅兩系,遷徙涼山已有幾十代,所以,有的人推測彝族遷入涼山已有幾百年,或上千年,更有人認為有兩千多年之久。涼山彝族人在長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各種舞蹈,按照我國著名學者樸永光先生的劃分,將此地區的舞蹈分為六種類型,在節日、慶典里跳的舞蹈《都火舞》等;在喪事中跳的舞蹈《跳維茲》等;在祭祀中的舞蹈《蘇尼且》等;游戲時跳的舞蹈《蕎子舞》等;婚禮時跳的舞蹈《喜希蘇且》等和自娛時跳的舞蹈《達體舞》等。在這些舞蹈中,彝族人用身體去表達本民族的情感、精神和愿望,而在他們舞動的身體背后體現的是彝族人民深厚久遠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內涵。
一、“都火舞”的歷史溯源
“都火舞”是涼山彝族在火把節期間表演的女子集體歌舞。彝語“都”即火,引申為火把、火把節;“火”為唱。“都火”即唱火把節。在涼山不同地區對此舞也有不同的名稱,有“都格”“朵洛荷”“者火”等說法。“都火舞”也是涼山彝族傳統舞蹈中歷史最悠久的一種舞蹈。其蹤跡可以追溯至彝族原始社會,是遠古先民的文化遺存。因為年代久遠,對于這一歌舞的形態已無從考證,但在當前我國很多專家學者的研究中表明,這一舞蹈形式是自古傳下來的。原始時代的“都火”男女圍火歡舞,狂放無羈。因此可以看出,“都火”源自原始狩獵時代的群婚時期,是遠古時代族人圍火共享獵物,崇火、祀火的行為[2]。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修的《布拖縣志》中,記錄了當時人們對“都火舞”來源的兩個傳說:“據傳,在若干年前,火把節期間婦女手拿約5尺長的樹皮剝一節留一節的花棍,在男人組成的夾道中穿行,并不時抽打摸扯她們的男人們的手”。“又傳男人們狩獵歸來,婦女們在火堆邊燒烤獵物,向圍在周圍的男人斟添酒肉,以示慶祝,圍圈而舞”[3]。而直到今天,我們看到的“都火舞”已大為改變,舞者在一人領唱、領舞的帶動下,一手持黃油布傘,一手牽著前面的人的荷包帶或牽著頭巾的兩端或手拉手,低頭、矜持地行走于一個個逆時針運動的圓圈。這樣的畫風,在保留原始意味的同時,又加入了藝術的審美性,色彩、情感、表演的融合使得“都火舞”更具觀賞性。由此,從“都火舞”的歷史流變來看,這一古老的傳統民族舞蹈形式,經過時代的演變已有所變化,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窺探到這一古老的舞蹈形式中體現出的最主要的歷史文化遺留信息——“群體性”。這也是舞蹈這門藝術,最初呈現的形式,標志著我國舞蹈最早形態的,與青海大通出土的舞蹈彩陶盆“頓地為節、連臂而舞”的環形群舞形態不謀而合。
對“都火舞”的歷史溯源,需將其放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域中進行研究。每年農歷6月24日是彝族火把節,火把節以“點火把”“玩火把”“唱歌跳舞”為中心,流行于整個彝族地區。這一天彝族地區的女子們(沙拉洛后,即換童裙)將集結于當地村寨的廣場或山間進行“都火舞”。彝族除了“彝族新年”,“火把節”是彝族人最看重的節日。說到“火把節”當然是跟火脫離不了關系的,彝族人與火的關系十分密切,火對他們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從滿足單純的飲食起居的需要,發展為一種精神的象征[4]。彝族諺語所云:“一個人一生需要三把火。出生一把火;活著一把火;老時一把火。”火貫穿于彝族人的生老病死的全過程,滲透著他們曾有過的宗教信仰,寄托著其內在的精神企求。火把節也正是源于彝族先民對火的崇拜。有關火把節的來歷,傳說甚多,但較為普遍的說法是:相傳天上的恩梯古茲(彝族神話中的天神)派了他的奴差耿丁洛惹下凡間催租逼債。耿丁洛惹來到人間后,與人間英雄惹地毫星比賽摔跤,被毫星摔死,天神大怒,放出大群蝗蟲到人間糟蹋莊稼,危害百姓,惹地毫星知道后,在農歷6月24日這天領著人們砍來許多的松枝、蒿草,扎成火把,舉火燒蟲,保護了莊稼,戰勝了天神,于是彝族人民把這天定為火把節,代代相傳[5]。
人們對“火”既敬奉又畏懼。在人們對火還沒有科學認識之前,把這一切都看作是“火神”的作用,所以會不斷地進行祭火的活動,以祈求火神降福于人類。在祭火的活動中,就逐漸萌生了火崇拜的觀念意識和文化形態,而這些文化形態就與舞蹈密切相關,表現在各種習俗活動之中。從彝族火把節的傳說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們不畏天命,敢于反抗天神,利用火消滅蟲害,頑強地與自然災害斗爭。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彝族已從狩獵、游牧進入了農耕社會,為保證豐收而進行各種努力,通過儀式和祈禱進行,從而促進舞蹈的發展。“場域”作為“都火舞”的另一個因素,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彝族舞蹈大多是在公共場合中進行,也有在私人空間里完成,例如“喪事舞”或“婚禮舞”。公共場合包括了山間、田野或街道、廣場,這些地方使得“都火舞”除了具有自娛性,更增加了社交性。當一年一度火把節到來之際,彝族女性以家支為單位,結伴來到公共場合進行集體舞蹈,他們從長期居家的婦女形象中解脫出來進入到公共視野中,對于她們來說是難得的展示自己、與人交往的好機會。因此,無論從歷史還是今天來看,“都火舞”都是一種兼具自娛性和社交性的群體舞蹈。都火舞”的歷史起源與彝族先民的“火崇拜”有著密切的關系,彝族女性在特殊的時間和地點中一改平時為人母、為人妻的形象,展示出自己既本真又風姿綽約的一面。而“都火舞”中的動作和姿態是彝族女性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這些都存在于她們有意識的身體表達中。
二、“都火舞”中“逆時行走”的身體表述
對一個民族而言,歷史文化習俗的留存形態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一是文字或文物記載的形態,一是口述形態(包括詩詞和音樂),還有一種便是身體形態。身體作為舞蹈這一藝術形式的媒介,通過動作表達民族特有的思想與情感,而思想和情感的背后是這一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西南少數民族彝族舞蹈具有古樸、渾厚、典雅、含蓄、沉穩的特點與風格。“都火舞”又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種舞蹈,整個舞蹈的動作以“走”的步伐貫穿,且步法古樸、簡單,主要包括“平步”“交叉步”兩種。然而,就是這樣一種看似最簡單的動作,卻讓彝族女子走出了“意味”。英國形式主義美學家克萊夫·貝爾在其著作《藝術》中認為意味指不同于日常情感體驗的一種特殊的、高尚的、排斥有關現實生活的種種考慮的“審美感情”。“有意味的形式”指能引起人們審美情感的、以獨特方式組合起來的線條、色彩等形式關系,包括“審美的感人的、激發審美感情的意味”和“形式或形式間的關系”兩個不同的方面。因此,我們能從“都火舞”的“行走”中看到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我國的少數民族舞蹈不論是舞姿形態還是律動都豐富多彩、風格各異,很多民族的舞蹈動作繁雜且具有高超的技術。彝族舞蹈在眾多少數民族舞蹈中動作較為單一,這與民族生活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有關。被圍繞在大山之中的彝族,在20世紀50年代前,可以說是與世隔絕的,封閉的環境使得他們生性非常樸實,也造就了彝族人民內斂卻堅忍不拔的性格,因此,他們的舞蹈相對比較單一,但是卻很純粹。彝族舞蹈動作多以下半身腿部的動作為主,上身軀干的動作較少,這與他們生活在大山之間,寒冷的氣候與較高的海拔相關,他們通過“行走”燃燒身體的脂肪,進行暖身,用腳丈量每一寸土地。“行走”是人最根本的方式,從生物學角度講,人從爬到坐到直立行走標志著生物進化的完成,是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之所在。我國人類學家彭兆榮提出:行走的歷史是一部沒有書寫過的歷史。人們在大部分時間里,行走只是一種現實生活的需要,完成從一地到另一地的空間轉移過程[5]。從文化的意義上看,我們更愿意將人類的行走看作是一種探索、一個儀式、一種求知的途徑,甚至是人類思索的方式。而舞蹈者的身體中隱喻著特定文化的一種敘事。在“都火舞”的表演中,彝族女性通過單一的、重復的“行走”寓意了彝人從古至今的歷史演變,就如人類發展的歷史一般,她們每一步都走得堅定、踏實。西方“身體理論”代表人物福科,對身體的理解圍繞著社會性方面展開,他對人的身體社會化持尖銳的批判態度,他認為“古典時代的人發現人體是權力的對象和目標,這種人體是被操縱的、被塑造、被規訓的”[6]。所以,人的身體至少有兩種性質:一是生理性的身體物質存在。二是文化體系內部的規約和義務。這兩種身體同時存在于一個有限的歷史語境中,并打上那個時代語境的強烈烙印。在“都火舞”中的身體“行走”動作中印刻著彝族女人的歷史記憶[6]。資料顯示:在1956年民主改革之前,男權在涼山彝族社會中居于支配地位,而彝族婦女長期受壓迫、受屈辱、受摧殘。她們處于社會最底層,政治上沒有發言權,完全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經濟上沒有支配權,沒有財產繼承權,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社會上無地位,被要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沒有獨立的人格和身份,被剝奪了接受文化教育和參加社會活動的權利;婚姻上沒有自主權,必須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彝族女性在“都火舞”中的“行走”是對當時女性社會地位不滿的一種表達,這種表達雖沒有強烈的情感,但是卻用腳步發聲,走出了力量。
當在“行走”中窺探到彝族女性的心聲時,“都火舞”還有一個值得分析的形式,她們手持黃傘、足踩綠蔭、微微低頭、低聲吟唱、并以逆時針的形式,“繞行不絕”地“行走”成一個個圓圈。在田野調查中,“都火舞”以繞行不絕的逆時針行走為主要形式,其間伴隨誦詞的節奏變成順逆方向旋轉的多層同心圓。值得注意的是,當地民間認為“行走”的方向“反著轉能交好運,把身上的污穢轉跑”[7]。在西南地區的許多少數民族民間舞蹈中都存在著相同的形式,向左或向右的繞行方式不僅是一種路徑,更是一種身體的象征,這與族群文化密切關聯。在彝族文化體系中左與右的分類很明顯,并且與價值觀聯系在一起。左與右不僅是神圣與世俗的界定也是好與壞的區分,這與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生活經歷和歷史記憶有關聯。在涼山彝族傳統觀念中,順時針方向寓意為解或松,逆時針方向象征著緊或纏,以逆時針為“轉進來”,他們認為在推磨、盛飯時按順時針方向繞動,就會對主人家吉利,以順時針為“轉出去”,則好運和吉祥都會離開自己,對主人家不利,在圈舞中沿逆時針方向轉動就會成“好、幸運”等含義,因此,“都火舞”以逆時針方向繞行不絕地行走,是彝族女性將美好的愿望寄予現實生活的體現。“都火舞”除了逆時行走,還有一個特征便是繞行不絕。在涼山大褲腳地區的“都火舞”,不論是在民間自娛性的活動還是具有表演性的演出,都能看到她們行走于大山或公共場合之中,呈現出不間斷的行走場面。
三、“都火舞”中的女性文化內涵
有著悠久歷史的“都火舞”是從歷史中走出來的民俗藝術,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淀,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在現代社會的今天,對傳統民族藝術的沖擊使得古老的民族藝術煥發新生的同時也改變了許多歷史遺留的信息,但是民族文化的本體仍然能在其中看到。因此,我們需要將民族藝術放在特定的人文傳統和文化語境中進行研究。在藝術人類學看來,對藝術活動的研究不僅要考察其本身,還要考察該活動的對象(實踐者)和與其相關的其他活動,以及該地區的社會文化整體。那么,對于“都火舞”的研究,除了時間、場域,對象也就十分重要。以彝族女人為對象的實踐者是“都火舞”的主體,對于女性這一研究對象,也是彝族歷史中具有鮮明意義的內容。在眾多彝族舞蹈的類型中,“都火舞”為什么只有女性跳?女性在彝族社會中的身份、地位以及心理是什么?這都需要我們從彝族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歷史中去探索。目前學界對彝族舞蹈或“都火舞”的研究,更多的都是集中在對舞蹈本體的研究,對于彝族女性這一實踐者的關注是不夠的,彝族文化中對于女性的重視與她們在生活中的存在和地位是值得關注的。因此,我們需要以彝族女性作為對象考究其背后的文化內涵。從文獻資料和國內彝族學者的研究中可以判斷,對“都火舞”的實踐對象——彝族女性的研究,主要體現了從原始狩獵的群婚時期到母系氏族社會文化遺留,再到家支文化制度中女性地位、角色的復現。據《中國彝族通史綱要》《中國原始社會史》等有關資料記錄,“都火舞”在原始社會時期便出現,最早的形式是男女一起共舞,體現出彝族先民們群婚制的習俗。這一時期彝族女性的地位與男性沒有明顯的區別,舞蹈也沒有所謂“藝術”的成分,完全是一種與生活相關的活動。因此,這一時期的“都火舞”具有更強的游戲性。隨著歷史的演變,彝族經歷了漫長的母系氏族社會,大約于公元前6世紀前后,這一時期以女性為主導地位是社會制度的重要特征。因此,“都火舞”已從男女混合而舞演變為女子群體舞蹈。在舞蹈中她們手持“花棍”不時地抽打著男人的手,從這一行為動作,可以看出,此時,彝族女性的地位較之原始社會時期有所提升,體現出了以女性為主導的社會地位。這一時期的“都火舞”除了具有原始遺留的畫風,還帶有某種表現性的特征,這也是藝術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從母系氏族社會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后,涼山彝族經歷了長達幾百年的奴隸制社會,同時,彝族最具特點的家支制度也出現了。彝族社會建立起的女性從屬地位的家支文化,使女性在彝族家支文化建構中被邊緣化,女性在這一時期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壓抑,在生活和社會中缺少話語權和主導地位。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彝族女性逐漸形成了逆來順受的身份和地位,也形成了沉重、內斂的性格。因此,在“都火舞”的表演中,她們總是低頭吟唱、目不斜視,帶著沉重而內斂的步伐行走。而到了今天,尤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穩步推進和文化旅游業蓬勃發展下,“都火舞”已成為外界了解彝族人民社會生活的一扇窗和對外宣傳中的一張響亮“文化名片”,此時,彝家姑娘通過“都火舞”展現出了新時期彝族女性的風采。我們可以從彝族女性的歷史演變中看出“都火舞”由表現自我的功利性到社會需要的程式性與儀式性的過程。
如果說女性在彝族歷史中的地位是“都火舞”文化內涵的一個方面,那么,彝族女性在生命中自身角色的轉變也是“都火舞”中的另一個女性文化特征。從“都火舞”的敘事文本中能看出彝族女性的角色構建,對深入了解彝族女性的人生經歷、思想情感等,更全面地認識“都火”對于她們的意義[8]。在著名的敘事長詩《媽媽的女兒》中有序歌、成長、議婚、訂婚、接親、出嫁、哀怨、懷親、明志9個部分。以女性生命史為主線,講述了彝族女性在生命歷程中的各個階段。我們可以從中認識當地的社會結構、文化習俗對彝族女性的角色建構,進一步理解“都火舞”背后的社會根源。少數民族對于生活中的禮節、禮俗是十分看重的,在彝族女性的一生中會經歷很多階段,而每一個階段都會以極其重要的儀式來進行。一出生便會舉行“出生禮”,出生三天后會舉行“出戶禮”,接著是“滿月禮”,當彝族女子生長到15-17歲時就會迎來非常重要的“成人禮”,接著便是人生重要時刻“婚禮”,最后是“葬禮”。由此可見,彝族人是非常重視人生中每一個重要階段的,對于“生與死”也是很看重的,而跟“都火舞”相關的一個禮節便是“成人禮”,彝語俗稱“沙拉洛”,即“換童裙”。能夠參與到“都火舞”中的每一個彝族女性都需要在“成人禮”以后。根據彝族民間習俗,女孩滿17歲時就會舉行“成人禮”的儀式,這時會由家族中的母親或姐姐為女孩舉行儀式。首先,將平時穿的兩節短裙換為三節長裙;然后,把以往的一根辮子梳成兩根,盤在頭上;最后,將準備好的耳環和銀飾為女子戴上,這樣的儀式也稱為“假婚”,標志著彝族女孩從孩童時期進入到青春期,那么,經過“成人禮”后的彝族女子便可以談婚論嫁了,彝族女子經過這一階段后便完成了人生中的轉折,成年后的女性擁有了自己進入社會場合交往的權利,同時也需要承擔起養兒育女的社會責任。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成人禮”也寓意著彝族女性從“舊我”到“新我”的一個自身轉變,這對于彝族女子來說是一種“新生”,而“都火舞”便是“新生”過后的一個重要活動,在這里她們實現了人生角色的轉換,也實現了自我的一個全新表達。
四、結 語
格爾茨[9]認為“舞蹈可看作是通過人們的身體動作與行為方式的具體化實踐和群體文化特征與精神的投射”。彝族在中國眾多少數民族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造就了他們獨特的舞蹈形態。涼山彝族節日性舞蹈“都火舞”作為一種傳統舞蹈形式,它是彝族女性集體情感和族群記憶的表達。通過對“都火舞”的田野調查與研究,筆者從今天“都火舞”的形態溯源過去的歷史,將“都火舞”的神秘面紗層層揭開,希望從這一古老的舞蹈形式中去探究其中的文化內涵,這對我們深入了解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舞蹈文化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