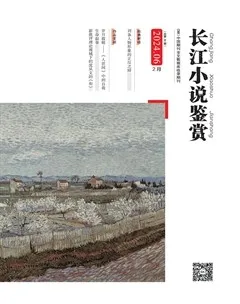殘雪小說英語譯介和傳播的行動者網絡研究
何玲
[摘? 要] 殘雪小說因其實驗性質本身具有很強的抗譯性,卻能得到英語世界的青睞和贊譽,其成功之道值得深入探究。本文運用行動者網絡理論,分析殘雪小說英譯生產過程的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經分析得知,其三個子網絡——殘雪小說英譯項目發起行動者網絡、殘雪小說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殘雪小說譯作傳播行動者網絡分別由譯者和出版社為關鍵行動者,招募其他行動者協同配合,促成了整個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的高效運作,使殘雪小說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和傳播獲得成功。
[關鍵詞] 殘雪小說? 譯介與傳播? 行動者網絡
[中圖分類號] I207.4[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6-0075-05
一、引言
“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當代中國文學中,只有殘雪一人得到了歐美社會的廣泛認可。”[1]三十多年來殘雪的英譯作品持續得到出版,根據殘雪在麻省理工大學個人網站的列表,至今她的小說英譯出版包括37篇短篇小說和13部單行本。殘雪的英譯作品不僅數量多,而且得到西方文學界高度認可,其中三部在近年來分別入圍或者斬獲英美重要文學獎項。《最后的情人》曾獲2015年美國“最好翻譯文學獎”和“英國獨立報”“外國小說獎”的提名,并于第二年被提名為“美國諾貝爾獎”的紐斯塔特文學獎;《新世紀愛情故事》(2019)和《貧民窟是我的家》(2021)都獲得了國際布克獎提名,這兩部影片被稱為“現代英語小說的最高獎項”。前者在2019年也同時獲得美國最佳翻譯文學獎提名。一些學者分析了殘雪小說在英語世界成功譯介和傳播的原因:王文強[2]指出殘雪在海外受到青睞的三個要素是贊助人的積極影響、作品中的西方文學傳統和高質量的翻譯;吳赟、蔣夢瑩[3]分析殘雪小說的成功譯介經驗為譯者、作者與贊助人合力的譯介主體,譯者對譯介內容的把關與抉擇,海外出版的譯介途徑,殘雪小說符合譯介受眾的閱讀興趣、閱讀需求和文學訴求;劉堃[4]認為,殘雪的小說得到了西方文壇的肯定,這主要是因為她的作品符合西方視野、西方對中國的社會現實關懷、對中、英兩種語言的了解以及對跨文化的注重。這些研究分析了殘雪小說在西方成功傳播的內因和外因,也都提到了譯者、作者、贊助人等譯介主體的關鍵作用。但是這些譯介主體是如何合力促進殘雪作品譯介傳播的?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主體參與其中?這些問題均需要深入研究。鑒于此,本文從社會翻譯學視角切入,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為基礎,通過解析翻譯生產過程的行動者及其作用,聚焦殘雪小說英譯生產過程,嘗試分析其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及成功之道,以期給中國文學走出去提供一些啟示。
二、理論分析工具:行動者網絡理論
行動者網絡(ANT)是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卡龍以及英國社會學家約翰·勞于上個世紀80年代創立的一種社會學理論。這三個基本概念是:演員,網絡,翻譯。行動者指能引起其他行動者產生行動的任何事物,包括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5]。把非人類行動者如技術、機器、文本等也納入行動者網絡中,是該理論的創新之處。網絡指的是各類行動者的聯結(ibid),由于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在生產過程中不斷變化,網絡也是動態的。轉譯指的是異質行動者之間的利益共謀[6],即行動者根據自身目的聯結其他行動者,征召他們參與活動(必要時還會解散)[7],構建起網絡。簡單地說,ANT可以理解為參與社會實踐的行動者,通過轉譯發生相互聯系和角色改變,形成網絡并運行,最終完成社會生產過程。從20世紀90年代起,社會學領域的理論被翻譯學者引入翻譯研究,ANT關照下的翻譯研究成為其中一個新的參照系。加拿大學者比澤蘭(Hélène Buzelin)是ANT翻譯研究的先鋒和代表學者。比澤蘭[8]指出,ANT可以提供概念工具和方法論,研究翻譯生產過程中的行動者以及相互關系。迄今為止,研究者們挖掘出了翻譯生產過程的多個行動者,例如:人類的行為體,如作者、翻譯者、出版社、編輯、設計師、書評人、讀者,以及非人類的行為,如翻譯、手稿、電影、技術、觀念[9][10]。各類翻譯行動者作為個體參與翻譯生產過程,同時也在轉譯中不斷協調形成合力,聯結成翻譯行動者網絡,保障翻譯生產過程成功完成。根據汪寶榮[11]的定義,翻譯主體所形成的“翻譯傳播行動者網絡”是指將翻譯生產劃分為“項目啟動—翻譯生產—翻譯傳播”三個環節,而每一環節的實現都離不開行動者網絡的搭建與運行,因此“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可以分為“項目發起行動者網絡”“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譯作傳播行動者網絡”三個環環相扣的子網絡。
1.殘雪小說英語譯介和傳播行動者網絡的構建與運作
鑒于行動者網絡理論對翻譯生產過程研究的指導作用,本研究將考察殘雪小說英語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的動態構建與運作,分析在三個子網絡中核心行動者征召和聯結其他行動者的過程以及相互關系,以期總結殘雪小說英譯的成功之道。
2.項目發起行動者網絡的構建與運作
項目發起行動者網絡的構建,即某個翻譯行動者發起翻譯項目,聯系并征召相關翻譯行動者參與到翻譯項目中,明確各自的責任和利益的過程,其構建和運作順利的標志為翻譯合同的順利簽訂和翻譯項目的成功確立。英語國家中國文學翻譯與傳播計劃的主要參與者包括:英語國家的譯者、中國作家和他們的海外代理人、西方的商業出版社以及我們的外國出版公司。[11]這個階段主要涉及翻譯項目發起的問題,主要包括:文本的選擇,即翻譯哪位作家的作品,在這位作家的諸多作品中選擇哪個文本進行翻譯;譯者的確定,即譯者能否達到作者和出版商的要求;出版商的確定,即出版商是否有意愿并有能力出版和傳播譯文。
殘雪小說版權輸出并非她本人聯系,多半是翻譯去找出版社[12]。殘雪作品英譯主要有五位譯者,分別是:RonaldJanssen(羅納德·詹森)、張健、Karen Gernant(葛凱倫)、陳澤平和Annelise Finegan(安妮莉絲·瓦斯曼)。詹森在采訪中透露[13],1985—1986年,他曾任上海華東師大的訪問學者,當時他上課時,英語系的一位學生曾向他推薦過殘雪的一首詩,他一看便一見鐘情。1986年,詹森回到美國,向以翻譯非英語國家作品的《形態》雜志的編輯喬納森·布倫特推薦了《山上的小屋》與《公牛》,并迅速出版。此后,詹森又和華東師大英語系的老師張健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殘雪,并將譯文送到殘雪的手中,在征得她的同意后,才著手進行翻譯工作。兩人共同完成了殘雪的處女作——《天窗》,并于1988年發表于《形態》第一期。布倫特還兼任美國西北大學出版社主任,經過他的精心策劃,出版了詹森與張健合著的長篇小說《天堂里的對話》與《蒼老的浮云》兩部小說。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因為詹森病重,殘雪作品翻譯出版一度中斷。殘雪作品英譯出版的重啟始于美國南俄勒岡大學中國歷史榮休教授、漢學家葛凱倫,他在讀了殘雪作品之后,主動聯系了殘雪。在獲得殘雪同意之后,2003年起葛凱倫與福建師范大學教授陳澤平開始翻譯,并一直保持到現在。至今,他們合作翻譯出版了殘雪的5部單行本——《天堂里的藍光及其它小說》《五香街》《垂直運動》《邊疆》《紫蘇》和《赤腳醫生》。另一位譯者安妮莉絲在中國文學課上發現殘雪便對其印象甚佳,2007—2008年在耶魯大學出版社擔任助理編輯期間,她通過時任耶魯大學出版社總編輯的布倫特認識了殘雪,先翻譯一章樣稿,經殘雪看過同意之后,獲得翻譯《最后的情人》的機會,與耶魯出版社簽訂了翻譯合同[14]。《最后的情人》在2014年出版之后便大獲成功,她翻譯的《新世紀愛情故事》于2018年繼續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從以上可看出,殘雪小說英譯項目發起行動者網絡主要是由譯者發起,譯者主動聯系殘雪,獲得翻譯授權,再與海外出版社聯系,簽訂翻譯合同,確立翻譯項目。
3.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的構建與運作
翻譯生產過程主要包括“翻譯、編輯和出版”[11]。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的構建,即譯者征召其他行動者參與翻譯、編輯和出版的過程。毫無疑問,譯者是其中的關鍵行動者,而其他行動者也影響譯本的生產過程和最終形態[11]。翻譯生產網絡的順利運行需要協調各行動者的利益和作用,促使他們通力合作,實現譯本的出版。
由于殘雪實驗性的、超現實主義的寫作方式,其小說不僅在結構上缺乏邏輯、情節松散,而且語言晦澀難懂,充斥著扭曲的人物形象、恐怖的夢魘、奇怪的對白等等。殘雪指出她的小說猶如一個迷宮,如讀者“能拼命闖入迷宮,會發現那里面的故事比傳統的故事更為有趣,結構更為奇巧,甚至會有天衣無縫的感覺”[16]。因此,讀者要在這些看起來古怪、不合常理和缺乏邏輯中找到其內在邏輯和精神內核,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譯者不但要翻譯成英文,還要讓英語讀者看懂喜歡,更是難上加難。但是,殘雪英譯本得到了英語文學界的高度肯定,甚至提名或者獲得英語世界中很有分量的文學獎,可見其翻譯生產過程十分成功。首先,譯者作為翻譯生產網絡中的關鍵行動者,具有決定性作用。除了安妮莉絲,殘雪小說一直以來都保持中外合作的譯者結構,即美國漢學家和中國譯者的組合。中外譯者組合可以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并且優勢互補。美國漢學家可以根據其對西方讀者閱讀喜好的把握,選擇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用母語進行創作,譯文的語言表達也更適合西方讀者閱讀。中文譯者深諳漢語和中國文化,在理解原文上可以充分發揮母語語言文化的優勢。中外合作翻譯的方式為殘雪作品邁進西方文學殿堂并得到認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另一位譯者安妮莉絲雖為獨立譯者,但是她豐富的翻譯、學習和工作經歷也促成了她翻譯殘雪作品的成功。她曾通過清華大學的校級交流項目到北京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也曾翻譯過蔣韻、魯敏、王蒙等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和散文,翻譯殘雪小說的同時她也在華盛頓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專業博士學位。并且,她長期在出版界供職,擔任過雙語編輯、項目經理,在翻譯出版方面經驗豐富。其次,譯者也積極征召各類行動者進入翻譯生產網絡,共同為翻譯、編輯和出版作貢獻。比如,詹森提到了他的博士生導師蓋伊·達文波特,他對殘雪作品中實驗性的、探索式的題材與風格的贊賞[11]。作者殘雪也被征召進入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中。例如:詹森翻譯過程中曾專門找到殘雪,一起走訪長沙的街道,以便對作品里描寫的街道有直觀了解。并且,殘雪精通英語,和幾位譯者、主編都成為好朋友,經常交流。她一直堅持閱讀譯文,給葛凱倫、陳澤平和安妮莉絲提供參考意見。安妮莉絲在訪談中提到她一直和殘雪通信,分享翻譯草稿,討論出版的所有細節,殘雪的積極幫助貫穿《最后的情人》整個翻譯過程。
4.譯作傳播行動者網絡的構建和運作
翻譯交流的內容主要有“對書籍的評價,市場的流通,學術的、社會的認同等等”。[11],譯作行動者網絡的關鍵行動者是出版機構,出版機構利用自身資本征召聯結媒體、作者、譯者、讀者、文學評論人等行動者,推進譯作的傳播和接受。在殘雪英譯項目發起階段,西方知名出版社被成功征召進入行動者網絡,為譯后傳播打下了良好基礎。其性質及受歡迎程度,不但體現了翻譯作品的品質與文學水準,還在財政支援、行銷方式及行銷途徑上,都擁有無可置疑的優勢。[3]迄今為止,美國已出版殘雪13部小說單行本,出版機構既有大學出版社,也有商業出版社。大學出版社有西北大學出版社、耶魯出版社,以及羅徹斯特大學所屬的《開放圖書》;商業網絡由亨利·霍爾特出版社,新方向出版社,以及公共時間出版社組成。這6個出版社不僅歷史悠久且在出版界享有盛名。西北大學和羅徹斯特大學均為美國知名大學,耶魯大學世界排名前列,其出版社成立于1908年,已有百年歷史,旗下近年來創立的“馬格洛斯世界文學共和國”書系頗有影響力,旨在將非英語世界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譯成英文,而該社出版的4部殘雪小說均為該系列作品。亨利·霍爾特出版社是全球出版社三大巨頭之一的麥克米倫出版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成立于1886年,也是美國最老牌的出版社之一,致力于發行高質量的文學或人文學術類圖書。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屠格涅夫,英國作家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都是它的代表作。還有美國的一家綜合性出版社,以出版先鋒性和實驗性的作品見長,其作品屢獲大獎,在英、美兩國的主流出版界都有很大的影響。這些出版社因為以往高質量的出版物已獲得大量讀者的擁護,殘雪作品一經出版,就能引起廣泛關注。他們也擁有專業的營銷資源,可以招募主流媒體、著名書評家來撰寫書評,組織讀書會、作者譯者訪談等活動,這些因素也極大影響譯作推廣和讀者接受。例如:在《黃泥街》出版之后,美國著名作家鮑爾(Daniel J. Bauer)和麗莎·米歇爾斯(Lisa Michaels)都在《紐約時報》發表過書評,美國女性漢學家弗朗西斯·拉弗勒,也曾為《今日世界文學》撰文;另外,英國資深專欄作家博伊德·唐金(Boyd Tonkin)在《獨立報》撰文、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內爾·帕克教授還在《音樂與文學》雜志上為《最后的情人》寫過一篇書評。同時,殘雪也主動走出國門,參加由出版社、國外知名大學、國際文學期刊等舉辦的文學訪談、讀書會等,與文學界、讀者積極交流,促進作品的傳播和接受。
三、結語
殘雪小說雖然具有很強的抗譯性,在英語世界卻能得到廣泛好評。根據行動者網絡理論,殘雪小說英語譯介與傳播的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其翻譯行動者網絡的成功構建和順利運作。具體而言,殘雪小說英語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的三個子網絡——殘雪小說英譯項目發起行動者網絡、殘雪小說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殘雪小說譯作傳播行動者網絡分別由譯者和出版社作為關鍵行動者,積極征召聯結了眾多行動者,例如編輯、文學評論家、讀者等人類行動者,以及原作、書評、訪談等非人類行動者。在行動者網絡中,各種行動者分工明確,分工合作,保證了行動者網絡的高效運轉,為殘雪小說的翻譯與傳播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特別是在美國。殘雪小說譯介傳播個案對中國文學走出去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參考文獻
[1] 戴錦華.殘雪:夢魘縈繞的小屋[J].南方文壇,2000(05).
[2] 王文強,郭恩華.殘雪作品的海外傳播[J].外文研究,2016,4(03).
[3] 吳赟,蔣夢瑩.中國當代文學對外傳播模式研究——以殘雪小說譯介為個案[J].外語教學,2015,36(06).
[4] 劉堃.西方讀者視野中的殘雪[J].社會科學,2017(05).
[5] Latour,B.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6] 王岫廬.行動者網絡翻譯研究[J].上海翻譯,2019(02).
[7] Buzelin,H.Unexpected allies: How Latours network theory could complement Bourdieusian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J].The Translator,2005,11(2).
[8] Buzelin,H.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A].In C. Millan & F. Bartrina.The Routledge Handbookof Translation Studies[C].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13.
[9] 汪寶榮.中國文學譯作在西方傳播的社會學分析模式[J].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17,24(4).
[10] 駱雯雁.行動者網絡理論在翻譯生產描述研究中的應用——以亞瑟·韋利英譯《西游記》為例[J].外語研究,2020,37(02).
[11] 汪寶榮.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模式——以西方商業出版社為中心[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20,43(02).
[12] 舒晉瑜.十問殘雪[N].中華讀書報,2007.
[13] 楊柳.殘雪作品在美國的譯介與接受[J].當代文壇,2022(03).
[14] 岑群霞.殘雪介入《最后的情人》英譯與接受的社會學探析[J].山東外語教學,2018,39(03).
[15] 駱雯雁.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名與實及其對社會翻譯學研究的意義[J].外語學刊,2022(03).
[16] 殘雪.為了報仇寫小說——殘雪訪談錄[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