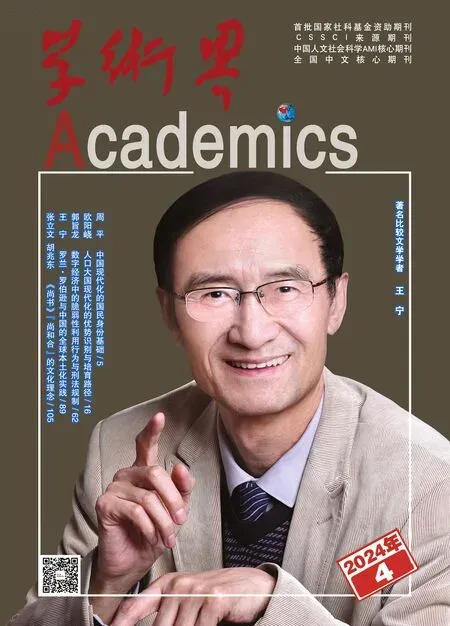羅蘭·羅伯遜與中國的全球本土化實踐〔*〕
王 寧
(上海交通大學 人文藝術研究院, 上海 200240)
全球化作為一個最先出現在西方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現象,或者作為一種批評和理論話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些著名的歐美思想家和學者的幫助下從西方舶來中國的。在與中國有著直接接觸、對中國的全球化研究產生重要影響并在中文語境中廣為引證和討論的西方全球化思想家和學者中,羅蘭·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1938—2022)無疑起到了十分獨特的作用。他與其他西方全球化學者和思想家,如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阿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等,經常在中國的語境中被引用和討論。他的專著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全球化:社會理論與全球文化》)(1992)早在21世紀初就被譯成中文在上海出版,并在翌年中國加入WTO之前成為一部具有拓荒意義和參考價值的重要學術專著。〔1〕在當時的中國學界,人們只承認經濟全球化,而文化上的全球化則沒有得到中國大多數人文知識分子的認可,或者即使承認這一現象也認為只是西方文化影響中國,中國文化只能被動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筆者和少數學者則從一開始就堅持認為,中國文化也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平臺走向世界,并產生世界性的影響。應該承認,羅伯遜建構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理論概念直接地影響了筆者和其他一些中國學者在中國語境下對全球化的研究和實踐,這種自覺實踐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凸顯,我們的研究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今天我們紀念羅伯遜這位對全球化問題有著精深研究并且著述甚豐的理論家和學者就有著尤為重要的意義。
一、羅伯遜的中國之旅:一些個人的回憶
羅蘭·羅伯遜與中國學者的關系是雙重的:他不僅依靠中國學者在中國傳播他的理論學說,同時他也幫助這些學者在國際論壇上發揮強有力的作用,并在國際著名出版社出版他們的著述,這在他于2006年領銜主編的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全球化百科全書》)中得到了特別的體現。〔2〕這部百科全書被譯成中文出版后,為中國政府官員、企業家和學者在全球化研究和實踐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3〕此外,作為參與編輯這部百科全書的副主編之一,本人也從這個浩大的項目中受益匪淺。今天,在紀念羅伯遜、評估他對國際全球化研究的批評理論遺產時,筆者不禁回憶起與他相識并在他的指導下寫下關于全球化問題的一系列著述和論文的那些難忘的插曲和時刻。
本人主要是一名人文學者,或者更具體地說是一名專事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的學者,主要從世界主義和世界文學的角度切入研究全球化問題。在筆者看來,全球化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上的現象,更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現象,它涵蓋了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和科學技術的各個方面。因而筆者率先將全球化的概念引入中國的人文學術研究,并主持了首次在中國舉行的“全球化與人文科學的未來”國際研討會,取得了廣泛的國內和國際影響。〔4〕后來又在羅伯遜的支持下,繼續從文化和人文學術的角度切入研究全球化問題,并率先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相關論文。今天,當我們翻開中國著名的學術期刊《外國文學》2002年第1期,很容易就能看到這樣一則新聞報道:
2001年11月26日,由清華大學外語系和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全球化和文化論壇在京召開。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國家行政學院等4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論壇。主辦方邀請了在國際全球化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性作用的著名社會學家和文化理論家羅蘭·羅伯遜,就全球化概念及其與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關系作主題演講。
本人作為論壇的組織者,向中國同事,特別是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同事介紹了羅伯遜,并就全球化之于中國的人文學術意義作了主題演講。盡管與羅伯遜來自不同的學科(他主要是一位社會學家,而筆者則主要是一位人文學者),但我們的兩場演講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跨學科和跨文化意義的對話。
中國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并成為其第143個成員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羅伯遜于2001年11月訪問中國正是恰逢其時。也就是說,從那時起,中國正式開始參與了全球化的機制和發展進程。那是羅伯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訪問中國,雖不主要是應筆者的邀請,但事實上筆者卻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與羅伯遜相遇純屬偶然,但在這偶然的相遇中卻有著某種必然的因素:我們都具有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野;都關注自己文化傳統以外的學術進展。事情的緣由是2001年11月下旬,武漢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發起主辦了一次全球化國際研討會,羅伯遜和筆者分別作為西方和中國研究全球化問題的學者應邀出席,并發表主旨演講。由于與會的中國學者大多剛剛開始接觸全球化這一新的課題,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通過閱讀中譯本才對這一新出現的理論問題略有所知,而本人則已經成為為數不多的能夠直接與羅伯遜進行深入討論和對話的中國學者之一,自然對羅伯遜的來訪感到由衷的高興,并認為這是一個與他進行直接對話的難得機會。甚至在武漢會議期間,筆者就想充分利用羅伯遜的來訪在北京也舉辦一個為期半天的高峰論壇,以便我們得以與這方面的國際權威學者直接交流,并與他進行深入的討論和對話。這就是筆者與羅伯遜相識的機緣,同時也是我們得以一見如故的原因所在。
盡管羅伯遜是一位典型的西方學者,他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知之甚少,但他通過翻譯閱讀了一些關于中國的著作,并對全球化在中國的登陸及其對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巨大影響非常感興趣。可在當時,全球化現象雖然吸引了許多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但在國際英文期刊上發表全球化問題論文的中國學者卻鳳毛麟角。在文化全球化研究方面,本人當時在國際英文期刊上發表了三篇關于文化全球化的文章,便忐忑地把這三篇并不算成熟的文章復印件送給羅伯遜,希望能得到國際全球化研究權威學者的批評和指導。羅伯遜利用在北京的短暫逗留時間讀完了這三篇文章,并對其中的兩篇非常感興趣,其時,他應英國勞特里奇出版社邀請,正在編輯一部六卷本的全球化研究論文集。他希望筆者能授權將這兩篇文章收錄在編輯的文集中。筆者當然十分高興,并立即授權他選錄這兩篇文章。〔5〕
雖然羅伯遜的中國之行很快就結束了,但正如他在回國后寫給筆者的信中所說,他此行最大的收獲就是和筆者相識相交。他和華威大學的楊·阿特·肖爾特(Jan Aart Scholte)教授計劃于2002年下半年在英國舉辦一次全球化問題的研討會,并邀請本人以中國人文學者的身份出席。第二年,我們在英國再次會面,當時我們在會上討論了是否有必要編輯一部《全球化百科全書》以及擬定其編寫原則,出席者一致贊成這一建議,于是這一浩大的項目就在那次活動之后啟動了。由于本人是唯一一位參加研討會的人文學者,便被指派擔任副主編,并加入了編委會,負責50個關于人文學科的條目。本人寫了三個條目:“比較文學”“翻譯”和“東方主義”,此外還負責評審所有其他關于人文學科的條目。
如前所述,筆者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便開始對全球化產生了興趣,甚至于1998年在北京組織了第一屆“全球化與人文科學的未來”國際研討會,但正是在與羅伯遜的會面和討論之后,本人才很快地進入了國際全球化研究的前沿。故由衷感謝這位以著述影響和啟迪我的域外老師,他影響和激勵了包括筆者在內的其他中國學者,將全球化理論及其“全球本土化”的理論建構與考察中國的具體實踐聯系起來。在羅伯遜的“全球本土化”理念的啟發和鼓勵下,筆者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在國際論壇上發表了許多關于全球化與中國文化和文學關系的著作和論文,〔6〕并應邀在多個國際場合就全球化與中國文化作主旨發言。在下一節中,本人嘗試著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作為一種“全球本土化”的模式進行考察,并從這一視角出發來分析中國式現代化的全球本土特點,因為筆者認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全球化在中國的實踐以及建設中國式現代化模式的確立所印證。
二、“全球本土化”語境下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眾所周知,羅伯遜對全球化與文化最有影響的思想是所謂的“全球本土化”,這一點尤其適用于描述文化上的全球化。按照他的這一思想,全球化只有在特定的本土文化語境下才能得以實現,這一點在中國的成功實踐中得到了印證,盡管中國的實踐與羅伯遜的理論建構只是一種平行的關系,并非受到他概念的影響,但這二者的印證也說明了他的理論建構是能夠被實踐檢驗的,并且也可以為未來另一民族/國別的全球化實踐所效法。在闡述“全球化”的概念時,羅伯遜這樣寫道:
事實上,全球化的概念傳達了我近年來所寫的關于全球化的大部分內容。從我的角度來看,全球化的概念涉及傳統上所稱之的全球和地方,或者更普遍地說,普遍和特定的同時性和相互滲透。嚴格地說,在當前關于全球化的辯論和討論中,我自己的立場,我(和其他人)甚至認為有必要偶爾用“全球本土化”一詞來代替頗有爭議的“全球化”。〔7〕
筆者不僅受到他關于“全球本土化”理論建構的啟發,寫了一篇關于中國的“全球本土化實踐”的文章,而且他的理論也證明了全球化在中國的成功實踐。〔8〕在這一部分,筆者將嘗試著運用羅伯遜的全球化/全球本土化理論來探討和分析馬克思主義是如何通過翻譯和建構性解釋駐足中國的,以及中國的文化和人文學術是如何走向世界的。在筆者看來,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全球化理論已經與中國的特定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實踐相結合,并取得了預期的成果。同樣,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在1949年取得勝利,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種“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擯棄了那種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強調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特殊性。當前我們所從事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實踐的自然發展和延伸。因此,羅伯遜的理論遺產應該得到正確評價和發揚光大,尤其是當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出現時,這種全球化在中國實踐的方向已經發生了變化:從中國走向世界,也即以中國的實踐和中國道路的成功來為那些仍在建設現代化大業的民族和國家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此外,也以中國的實踐經驗為具有總體化特征的全球化理論作出貢獻。
在大致描述了羅伯遜與筆者個人的學術交流關系及其對中國的全球化研究的影響之后,筆者將集中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全球性實踐的普遍意義。本人曾在其他場合對西方學術界關于現代性的主要理論及理論家的觀點進行比較研究和討論,此處不再贅言。〔9〕
作為一名人文學者,筆者主要聚焦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內涵及理論建構。在我看來,中國式現代化是全球現代性的一種“全球本土化”或“中國化”的版本。正如全球化的概念一樣,現代性的概念確實也來自西方。但是,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中,始終存在一些現代性的成分。如果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我們甚至可以很容易地分別在中國的儒家和道家哲學中看到近似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元素:前者以積極參與社會現實為特征,后者以“以不變應萬變”的超然態度處理現實;前者強調一種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后者則強調一種雙贏的策略。應該說,中國文化傳統中包含著這兩個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影響的思想片斷。因此,中國從古代發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積累了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現代性元素,其中一部分就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的。在西方思想的激勵下,中國現代性的進程便自然而然地開始了,其標志就是1915年至1923年間發生的新文化運動。受到西方現代性精神的啟發,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文化翻譯運動。西方的各種理論和文化思潮通過翻譯的中介蜂擁進入中國,加速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特別是為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新傳統的形成鋪平了道路。現在,我們可以結合中國發展的現狀來反思和重構現代性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
如果說中國的現代性大計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的,那么它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模式,即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的雙向發展模式,或者說中國化的現代性特征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模式。這種獨特的發展模式,在文學和文化中具體體現在這樣一條道路上:西方理論激活了中國的思想,推動了中國的創作和理論批評實踐。在中國的實踐中,它又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理論,并經過理論家的抽象和建構,進入了國際理論界和思想界,對仍在建設現代化的那些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啟發和影響。同時,它也解構了曾經的大一統“總體化”的西方中心主義現代性。因此,現代性又是一種催化劑,它不斷地鼓勵理論家在中國的背景下,特別是在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時代探索新事物。在回顧西方現代性理論出現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如何界定中國的現代性?既然我們承認中國也有自己的現代化計劃和道路,那么我們就進一步追問:中國的現代性與全球的現代性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對當前的中國式現代化意味著什么?筆者想重申,中國的現代性是全球現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其獨特性,它又不同于西方主導的全球現代性。因此,它也像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一樣,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另類現代性。它的特點是包含了被激活的中國傳統文化,并融入了一些西方的現代和后現代的因素。這些都已經開始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得到呈現。
現在,筆者將從文化的角度來探討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內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的不同。具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新模式。它同時強調生產和經濟的發展,以及技術、生態文明和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因此,這種現代化便是一種可持續的、并可以被其他國家所效仿的。
我們都知道,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戰略和發展模式是以自然資源的耗竭作為代價的。當它們的現代化大計初步完成時,自然和生態環境已經遭到破壞,因此,它自然會受到各種以解構為己任的后現代思想觀念的抵制和挑戰。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國家興起的文學生態批評和環境研究,就是對由來已久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強有力挑戰和解構,與西方國家現代性的成熟密切相關。世紀之交,中國的現代化大計在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問題,特別是生態環境問題。因此,生態批評一經被引入中國,就迅速地得到中國學者和文學評論家的回應。在這方面,中國作家和文學評論家起到了帶頭作用,他們的作品和批評著述在為政府作出一系列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決策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參考作用。事實上,中國古代哲學家對生態問題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因為儒家和道家都非常重視自然生態的平衡,尤其是儒家的中庸思想在解決發展過程中的極端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然而,面對西方國家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趕超和領先,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明顯地感到落后和被邊緣化。他們非常渴望通過大規模翻譯西方學術和理論,從發達國家引進現代化建設的理論和經驗。
盡管在中國古代人與自然的關系大多是和諧的,但由于人類在過去幾百年中不斷地利用各種自然資源為自己服務,甚至達到了使自然資源枯竭的地步,其原因是他們沒有善待自然,沒有著力去保護有限的自然資源,這樣大自然便對人類發起了無情的報復。因此,我們需要反思人與自然的對立和不平衡關系,并從自然生態的角度,扭轉人類中心主義的專制和排他意識,使人們重新樹立尊重自然、關愛我們所賴以生存的環境的觀念。
致力于探索人與自然關系的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對我們所賴以生活的環境的變化尤其敏感。今天的自然寫作研究者和生態批評家在討論自然與生態的話題時,總是會提到美國作家梭羅的散文作品《瓦爾登湖》。事實上,作為一位著名的浪漫主義作家和現代環保主義的先驅,梭羅相信人類可以在大自然中快樂地生活,除了儲備一些必需品外。他的烏托邦理想主義思想可能讓今天的人們難以接受,但梭羅尊重甚至崇拜自然的精神至少對我們有一定的啟迪。近年來,中國一些人文知識分子也效仿梭羅,遠離城市的喧囂,隱居荒野,平靜地思考和寫作。有些人甚至出于保護生命的動機而成為素食主義者。在筆者看來,這些都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初步嘗試。然而,無論他們的動機如何,在一個具有各種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消費社會提倡梭羅的樸素和節儉,至少是對奢華喧囂的城市生活的一種抵制。生態作家和批評家,雖然不像生態學家那樣走極端,但他們致力于文學中的生態研究,至少可以在當代眾多不同流派的文學批評中發出不同的聲音。
此外,中國式現代化的許多基礎理論學說都是從西方傳入的,但西方的理論進入中國以后就和中國的本土實踐相交融進而形成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觀念。在這些理論指導下所取得的成功經驗也可以為全世界人民,特別是那些正在抵抗帝國主義霸權的發展中國家所分享。因為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就仿佛生活在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彼此分享福祉、共擔責任。共同體的概念早就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里得到闡述,它也應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當代的豐富和發展。不可否認,“共同體”一詞的內涵不僅在中國,而且在西方也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但就其基本含義而言,只有如下幾點:首先,人們在共同條件下形成的集體或群體,如共同的經濟或利益關系。其次,由幾個國家根據各自的需要和共同利益組成的集體組織,如早期的歐洲共同體或當前的歐盟,這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再次,使用相同語言或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們往往發現他們同處一個共同體中,彼此交流也很方便,這樣的共同體往往被稱為文化共同體,比如英聯邦的松散組合和維系就是一例。最后,就愛情而言,它指的是最有凝聚力彼此相愛的人們所形成的群體。如此等等。我們今天所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主要指涉前三個含義。這是中國領導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根據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以及中國當下的具體實踐,提出的一個具有普適意義的理論概念。
關于共同體概念的起源,人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來說,它指的是具有共同或大致相似目標和利益的人自愿組成的群體。簡而言之,這個詞在英語中最早的含義是“公共群體”,直到中世紀才衍生出“公民”等詞匯。后來演變而來的“公社”一詞也有這個含義。當然,作為一個理論概念,最早的共同體概念是由法國啟蒙哲學家盧梭提出的。后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共產黨宣言》中將這些零散的思想發展起來,提升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境界。因此,我們可以說,共同體的概念在現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其歷史淵源和發展脈絡。從共同體一詞的角度來看,它與公社和共產主義有著相同的根源。在這方面,巴黎公社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一次實踐。盡管巴黎公社失敗后,革命處于暫時的低潮,但公社詩人歐仁·鮑狄埃(1816—1887)悲憤地寫下了《國際歌》的歌詞,而且很快便由比爾·狄蓋特(1848—1932)譜成曲子。雖然公社的社員在世界各地流亡,但一曲熟悉的《國際歌》便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為一個共同的理想奮斗到明天,甚至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奮斗終身。這應該是當前中國人民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中具有的歷史和理論基礎。因此,建立一個既代表全人類共同利益,又具有自身“全球化”特征的命運共同體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所要達到的一個目標。
三、走向全球人文的理論建構
盡管中國在20多年前就已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從而進入了全球化的機制,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中國的“全球本土化”實踐的成功,中國已經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在海外的傳播仍然相對滯后,并且不斷地面臨新的困難和障礙。事實上,中國的人文學者早就認識到全球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且積極地介入全球化進程,使得全球化成為近20年來中國語境中使用頻率最高的理論術語之一。如果說全球化對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那么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還體現于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增強。但我們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全球化的另一個方面。也就是說,全球化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給人類生活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貧富等級差距的加大、自然資源的枯竭、國家/民族界限的模糊以及文化上的趨同等。
今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就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全球化也有不同的起源,它并不只是西方的專利。事實上,許多西方學者已經意識到,如果經濟全球化始于西方發達國家,或者更準確地說,始于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那么文化全球化則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從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開始,這至少是它的起源之一。因此“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具有很高的戰略意圖和站位,這實際上是一種中國版的全球化新理念。盡管全球化概念的引入標志著西方發達國家試圖將其發展模式和價值觀推向全世界,因此它一開始確實包含了一些帝國霸權的成分。就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是最早出現在西方世界的一個現象。然而,全球化一旦得到推廣,便給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帶來了非常寶貴的機遇,并通過中國的“全球本土化”實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美國前兩屆政府都高舉“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大旗,企圖對中國實施全面制裁。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該怎么辦?既然美國威脅要退出一些國際組織,中國就應該堅持自己的立場,發揮應有的主導作用。因為無論是幾千年的文明史,還是目前的政治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中國都完全有資格,而且有信心在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發揮領軍作用。
正如筆者在前面所指出的,全球化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實現必然會與當地的民族文化發生碰撞和融合,最終形成一種“全球本土化”的態勢。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文化的全球化上,也即意味著文化全球化現象不僅僅是單一的“趨同”,還在于其多樣性。此外,文化全球化并不是單向的,而是一個雙向的過程:西方文化早已進入中國,中國文化也應該在海外傳播,盡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會出現一些變異。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西方各種理論和文化觀念進入中國后的變化中見出端倪。因此,我們可以說,全球化在中國的成功登陸,不僅使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為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的國際化鋪平了道路。
面對這樣一種態勢,我們作為人文學者,應該怎么辦?毫無疑問,在整個20世紀,我們都致力于引入各種外國文化觀念和理論思潮,尤其是來自西方的文化觀念和理論思潮。因此,我們中國的人文學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的理論概念和話語來解讀中國現實。而隨著全球化發展到今天,我們長期關注的一個焦點已發生了轉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如何成功地實現海外傳播。有人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文化和人文學術自然會得到世界的認可。但事實又是怎樣呢?中國的崛起反而更加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警惕,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制裁。
我們都知道,經濟上和科技上的硬實力是任何國家都必須關注并效仿的,而文化軟實力則不一定如此,它包含著一個民族文化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特征。因此,單靠國外漢學家們來承擔推廣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的任務,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都知道漢學在國外,尤其在西方國家也是很邊緣的,經常伴隨著該國與中國的關系而進行不斷的調整。此外,除了漢學本身的邊緣地位外,漢語也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之一。再加上中國文學和人文學科的深厚積淀,一位才華橫溢的漢學家往往需要五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掌握中文的閱讀和交流,而達到中文出版的水平則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這段時間里,他必須全心全意地從事專業學科的教學和學術研究,因而很可能遠離該國和國際學術主流。
當然,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國內人文學者提出了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發出中國聲音的想法,甚至提出了構建中國自己的學術理論話語的設想。這自然是合法和必須的。事實上,中國被公認為全球化進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這主要體現在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上。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它逐漸開始體現在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在世界各地的傳播中。在過去的十年里,一些國內知名學者的著作在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資助下逐漸進入國際學術界,可以說,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確實已經“走出去”了,但是否真正走進國際學術界或國外的大學圖書館和圖書市場,則有待時間的檢驗。在這方面,新一代人文學者將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為一名人文學者,筆者相信互聯網的普及甚至使我們與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們“實現了聯通”。可以說,今天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地球村”里。雖然它曾經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但經過各國人民的努力,現在這個“想象的共同體”已經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了:在這里我們不僅分享利益,而且共擔責任。
盡管我們仍不時地聽到反全球化的噪音,但筆者仍堅信,全球化是當今世界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任何人都無法阻擋。為了有效利用全球化這個平臺,大力推動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的國際傳播,筆者提出了一個“全球人文”的概念,并在一些場合作了表述。〔10〕在這里再次深入闡述筆者的全球人文觀。我們經常說科學無國界,實際上人文也沒有國界,特別是文學藝術更是如此。一部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經過翻譯或改編的中介,完全可以為全世界的文藝愛好者所共享。中外人文學術交流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種“人文外交”,這完全可以在某個方面取得突破。因此再次重申筆者的“全球人文”觀點并且作如下闡釋。
首先,在全球化進程加速發展的今天,人文學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在文學研究界,世界文學這一話題重獲新生,并成為21世紀比較文學學者的一個前沿理論課題。在語言學領域,筆者還提出了復數的“全球漢語”之概念,以應對全球化對全球英語形成的影響,并相信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語言體系將得到重建。在哲學領域,一些渴望探索普世問題并試圖建立新的研究范式的哲學家也效仿文學研究者,提出了“世界哲學”的主張,并認為中國哲學應在這一領域建立中發揮奠基性的作用。在一直被認為是最傳統的歷史學領域,學者們在分析世界體系和編纂全球通史方面作出了杰出貢獻。而藝術就更是可以為全世界不同國家的人民所欣賞。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今天提出“全球人文”的概念是非常及時的,而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的學者也確實就這個話題有發言權,并可以在這個層面上與國際同行進行有效的對話。
其次,既然“全球人文”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人們不禁要問,它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它是世界各國文學、歷史和哲學等學科的簡單相加嗎?筆者認為事情沒那么簡單。就像世界文學不是各種民族文學的簡單總和一樣,它必須有一個評價和選擇的標準。全球人文學科也是如此。它主要探討全球文化、全球現代性、跨國主義、世界主義、全球生態文明、世界圖景、世界語言體系、世界哲學、世界宗教、世界藝術等具有普遍意義的主題。盡管全球化總是可以在“全球本土化”的背景下實現,但對全球化人文的探索必須著眼于全球視角,以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視角。
最后,全球人文概念的提出并非意味著各民族的人文學術朝著一個模式去發展,而更是一種“全球本土化”的發展模式和方向。具體說來,中國的人文學術既產生自中國的本土,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同時又具有普適的意義和價值,因而其著述也可以為其他國家的人文學者所閱讀和研究,并參與國際性的評價。〔11〕
綜上所述,我們今天在中國的語境下紀念羅伯遜這位全球化研究和理論探索的先驅,就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