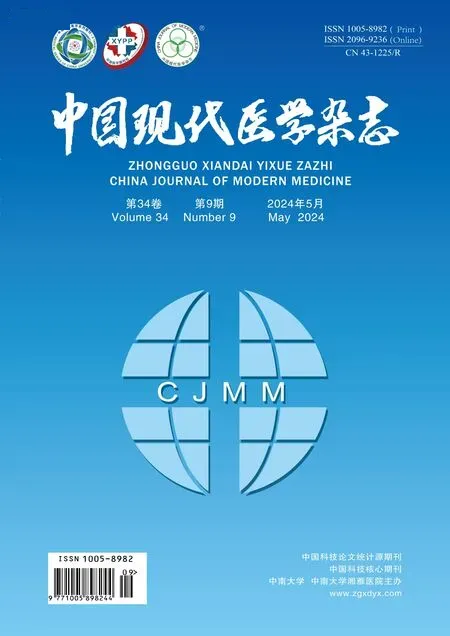肺動脈高壓生物標志物研究進展*
何祖益, 李昇鈴, 劉偉, 戴海龍
[昆明醫科大學附屬延安醫院 心血管內科(云南省心臟疾病臨床醫學中心),云南 昆明 650051]
肺動脈高壓是指由多種異源性疾病(病因)和不同發病機制所致肺血管結構或功能改變,引起肺血管阻力和肺動脈壓力升高的臨床和病理生理綜合征,繼而發展成右心衰竭甚至死亡。肺動脈高壓血流動力學診斷標準為:在海平面、靜息狀態下,右心導管檢查肺動脈平均壓≥25 mmHg(1 mmHg =0.133 kPa)[1]。2022 年ESC/ERS 肺動脈高壓指南[2]將肺動脈高壓定義為靜息時平均肺動脈平均壓>20 mmHg。也有專家建議我國施行此標準,但從經濟衛生角度來看,降低我國肺動脈高壓的診斷標準可能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另外我國目前尚缺乏針對肺動脈平均壓為21~24 mmHg 患者的相關研究,因此是否降低我國肺動脈高壓的診斷標準尚存在很大爭議[3]。肺動脈高壓全球患病率為1%[4],其中,女性更容易發生肺動脈高壓,但生存率較男性更高[5]。
肺動脈高壓的病理生理機制較復雜,并且尚未完全闡明。研究表明,肺動脈高壓病理生理學與缺氧、高剪切應力、低氧張力、肺血管內皮功能障礙、免疫系統失調、遺傳、女性、表觀遺傳、環境因素及DNA 損傷有關[6]。肺動脈高壓的發病率和病死率均較高,且多數患者發現時已出現右心功能不全,進展至疾病終末期,因此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及預后評估分層對肺動脈高壓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尤為重要。目前,右心導管檢查仍然是評估和診斷已知或疑似肺動脈高壓患者血流動力學的金標準,通過獲得的血流動力學數據有助于確定肺動脈高壓的病因,并提供診斷和預后信息,以幫助患者進行危險分層[7]。但右心導管檢查為有創性檢查,費用較高,不利于疾病的早期篩查。而用于篩查肺動脈高壓的敏感生物標志物的需求尚未得到滿足,目前只有腦鈉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或氨基末端B 型鈉尿肽原(N-terminal pro-B-type natriureticpeptide, NT-proBNP)被指南推薦作為常規臨床檢驗的標志物[2]。因此,更好的血清生物標志物有待開發。血清生物標志物能夠反映肺動脈高壓的病理過程,具有無創、操作簡單、成本低等優點,其作為非侵入性標志物,為肺動脈高壓的診斷和療效評價提供了良好的幫助。
1 炎癥標志物
炎癥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肺動脈高壓形成的重要機制之一。肺動脈高壓組織中可見炎癥細胞的浸潤,提示炎癥在肺動脈高壓發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1.1 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單核細胞-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比值
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NLR)是一種新的全身炎癥標志物,對多種心血管疾病具有預測和預后價值。有研究指出,NLR 與冠狀動脈疾病嚴重程度,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非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發展有關[8-9]。近年一項回顧性分析發現,在特發性肺動脈高壓(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IPAH)和結締組織相關性肺動脈高壓(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s-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CTD-PAH)患者中,與低NLR 組(以4.8 為界值)相比,高NLR 組患者的1、3 和5 年生存率較低(P< 0.05);且與男性相比,女性NLR 與肺動脈高壓生存率之間的關聯更大,提示NLR 可作為肺動脈高壓生存率的獨立預測因子[10]。同時,BILIK 等[11]研究發現肺動脈高壓組患者單核細胞-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比值(monocytetohigh to densitylipoprotein ratio, MHR)、NLR顯著升高,提示MHR 可作為肺動脈高壓的預測因子。NLR、MHR 作為一種易得且易于評估的炎癥指標,其聯合評估與肺動脈高壓的相關性比單一炎癥指標評估更具特異性,為臨床研究提供了更多思路。但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數據并不多,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確定這些生物標志物在肺動脈高壓中的預測價值。
1.2 紅細胞分布寬度
紅細胞分布寬度(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是反應紅細胞體積大小和均一性的參數,已有研究發現RDW 升高與心血管事件(心力衰竭、心房顫動、冠狀動脈疾病)發生率增加之間有關,其參與心血管疾病的機制可能與炎癥狀態和異形紅細胞增多有關[12-13]。近年來,相關研究發現RDW 升高與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動脈高壓(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 CTE-PAH)、CTD-PAH 的嚴重程度和病死率相關,被認為是肺動脈高壓預后不良的生物標志物[14-15]。YANG 等[16]的研究發現RDW 可預測繼發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肺動脈高壓。一項納入119 例混合性結締組織病患者的研究顯示RDW 與肺動脈收縮壓呈正相關(r=0.716,P<0.05),提示了RDW 在肺動脈高壓中的預測價值[17]。RDW 作為一種臨床常規的實驗室指標,其水平降低反映了肺動脈高壓患者良好的療效和更好的預后,但仍然需進一步研究探索其與肺動脈高壓確切的病理機制。
2 免疫系統相關標志物
免疫系統是另一已確定與肺動脈高壓病理、病理生理、發病機制有關的因素。臨床研究表明,免疫系統疾病在肺動脈高壓的發展和維持中起著重要作用[18],且免疫細胞、其釋放的細胞因子和免疫調節因子對肺動脈高壓功能調控具有相當的復雜性。
2.1 細胞毒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
細胞毒T 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 CTLA-4)( 又名CD152)屬于免疫球蛋白家族成員,是T 淋巴細胞膜上的一種跨膜受體,其與CD28 具有同源結構,兩者通過競爭結合其相同受體B7 介導對T 淋巴細胞的抑制;CTLA-4 對T 淋巴細胞TCR/CD3 激活的作用與CD28 相反,是T 淋巴細胞功能的負調控因子,通過細胞內和細胞外兩種機制參與免疫反應的負調節[19]。IPAH 患者的CD4+T CTLA-4+淋巴細胞表型百分比顯著高于CTE-PAH、CTD-PAH 及先天性心臟病相關肺動脈高壓患者,且在IPAH 患者中,CD4+CTLA-4+T 細胞百分比與紐約心功能分級(NYHA)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r= 0.708,P<0.05)[20]。上述結果提示CTLA-4 是一種很有潛在價值的IPAH 無創診斷生物標志物,但該研究樣本量較小,其在肺動脈高壓中的作用機制也尚不清楚,需進一步研究來確定其與肺動脈高壓之間的關系。
2.2 聚谷氨酰胺蛋白
FAM171B 是一種新型多聚谷氨酰胺(polyglutamine, polyQ)蛋白,在哺乳動物大腦中廣泛表達。FAM171B 被證明小鼠腦中廣泛表達,在海馬體、小腦和大腦皮層中具有明顯的定位,主要定位于神經元細胞質中的囊泡樣結構。FAM171B 也在人腦中強烈表達,被視為尚未表征的分子神經退行性疾病的候選基因[21]。QU 等[22]研究發現FAM171B在肺動脈高壓組織中大量表達,其高表達與肥大細胞和CD8 T 細胞浸潤程度密切相關,提示FAM171B可能通過刺激免疫浸潤和免疫應答促進肺動脈高壓的發展,FAM171B 可作為肺動脈高壓新型生物標志物(曲線下面積= 0.873)。
3 MicroRNA
MicroRNA(miRNA)是在真核生物中發現的具有參與基因表達調控的功能的一類非編碼小RNA,miRNA 與靶基因mRNA 組裝形成沉默復合體,通過兩種途徑下調靶基因的表達:miRNA 和靶基因mRNA 完全互補或不完全互補結合形成雙鏈修飾蛋白質表達,通過改變靶基因mRNA 的穩定性介導沉默基因轉錄后的表達或特異性抑制基因表達,miRNA 參與了細胞的生長、分化、衰老、遷移、侵襲等多種過程[23]。此外,miRNA 表達水平的改變可導致各種心血管疾病,包括動脈粥樣硬化、外周血管疾病和肺動脈高壓。目前,大量研究分析了肺動脈平滑肌細胞或肺動脈內皮細胞、肺動脈高壓動物模型和肺動脈高壓患者中miRNAs 表達譜,顯示miR-204、miR-322、miR-451、miR-22、miR-30、miR-223、miR-328、miR-339、miR-4632、miR-1181、miR-1281、miR-20a、miR-125a、miR-145、miR-21、miR-210、miR-138、miR-17/92、miR-124、miR-328、miR-424/503、miR-204、miR-98、miR-193、miR-29、miR-140、miR-204 等miRNAs 與肺動脈高壓密切相關,都有相似表達模式,有成為肺動脈高壓診斷、治療、疾病嚴重程度、預后評估的生物標志物的潛力[24-25]。
有研究發現,IPAH 患者的miR-596 表達水平升高,并且與IPAH 存活患者相比,非存活患者的miR-596 水平更高,該研究也顯示miR-596 水平與生存時間、平均右心房壓、肺血管阻力和心臟指數顯著相關;高水平的miR-596 和肺血管阻力與較差的生存率顯著相關[26]。這表明miR-596 可能是一個獨立的生存預測因子,可為IPAH 患者的臨床預后和疾病嚴重程度評估提供參考。DüZGüN 等[27]的研究發現,hsa-miR-21-3p 在多種類型肺動脈高壓的平均表達量均下降,hsa-miR-143-3p 在除CTE-PAH 患者外的其他肺動脈高壓類型中表達量均下降,且與hsa-miR-21-3p 相似,在中度、重度肺動脈高壓組達到最低水平。因此,miR-596、hsa-miR-143-3p、hsamiR-21-3p 有望作為評估肺動脈高壓嚴重程度的指標。
4 氧化應激相關生物標志物
可溶性糖基化終末產物受體(soluble 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sRAGE)是細胞表面蛋白超免疫球蛋白家族的成員,由裂解酶和金屬蛋白酶10(ADAM10)對膜結合分子蛋白進行蛋白裂解而產生的,充當糖基化終末產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的誘騙受體[28]。AGEs和其受體相互作用引起氧化應激,并隨后在各種細胞中引起炎癥反應和血栓形成,在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壓、慢性腎病、神經退行性疾病等疾病的發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29]。一項包含120 例患者(83 例IPAH 和37 例CTD-PAH)的隊列研究顯示[30],IPAH 患者血漿sRAGE 濃度為(3 044.0±215.2)pg/mL,CTD-PAH患者為(3 332.0±321.6)pg/mL,均高于對照組的(1 766.0±121.9)pg/mL;研究還通過對sRAGE 與NT-proBNP 進行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分析,發現其診斷準確性與NT-proBNP 相當,在輕度肺動脈高壓和對照組之間的鑒別表現甚至更好。綜上所述,sRAGE 可作為肺動脈高壓診斷的敏感生物標志物,可用于臨床診斷和監測成人肺動脈高壓患者對治療的反應和疾病進展,進行早期干預。
5 代謝類相關標志物
5.1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肺動脈高壓復雜的病理生理學機制是開發肺動脈高壓潛在干預措施的限制因素,2000 年的一項研究中就描述了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參與肺動脈高壓的發病機制[31]。KOPE? 等[32]的研究中發現LDL-C 水平與肺動脈高壓患者死亡風險呈負相關。最近研究也發現肺動脈高壓患者的LDL-C 水平較低,肺動脈收縮壓與LDL-C 呈負相關,同時發現,低水平LDL 對系統性紅斑狼瘡相關性肺動脈高壓的影響可能由D-二聚體介導,D-二聚體介導了25.61%的這種效應[33];LDL 水平的降低也與IPAH 患者的右心功能下降有關[34]。有研究表明LDL-C 對肺動脈高壓的影響可能與氧化的LDL-C 水平升高有關,其參與肺動脈高壓的病理生理過程,包括平滑肌細胞增殖、內皮細胞凋亡和炎癥[35]。然而,LDL-C 與肺動脈高壓關系的確切機制尚未得到闡明,對其潛在的分子機制進行更多的基礎研究,將有利于確定肺動脈高壓的治療靶點,增加對肺動脈高壓患者的干預措施。
5.2 銅代謝相關生物標志物
銅是許多細胞酶的一個重要輔助因子,參與酶的氧化還原反應、線粒體呼吸、鐵代謝、自由基清除和彈性蛋白交聯等生理學過程,其穩態在生物系統中非常重要[36]。早在1985 年,研究人員就發現血清銅升高可能是肺動脈高壓的病因或標志物,靜脈輸注硫酸銅可顯著增加肺血管阻力[37]。一項無銅飲食對暴露于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SU5416 并缺氧4 周小鼠模型(SuHx 模型)右心室功能影響的研究發現,在SuHx 小鼠模型中加入無銅飲食不會加劇右心室重塑[38]。后續對SuHx 大鼠模型的研究表明,無銅飲食逆轉SU5416/低氧所致嚴重肺動脈高壓的發展,表明肺動脈高壓血管增殖性改變具有銅依賴性[39]。研究發現,銅代謝相關基因DDIT3、NFKBIA、OSM 和PTGER4 在肺動脈高壓中表達下調,這項研究揭示了銅代謝相關基因與肺動脈高壓之間有關聯,可作為生物標志物對肺動脈高壓患者進行診斷和評估[40]。綜上所述,銅代謝有可能成為肺動脈高壓的一種新的生物標志物和治療新靶點,但其潛在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
5.3 三甲胺-N氧化物
三甲胺-N 氧化物(Trimethylamine N-oxide,TMAO)是腸道菌群代謝產物,富含膽堿和l-肉堿的食物被腸道菌群代謝生成三甲胺(trimethylamine,TMA),然后TMA 被一種肝臟酶——黃素單加氧酶-3(FMO3)迅速氧化為TMAO[41]。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表明,TMAO 與高血壓、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心力衰竭等多種心血管疾病有相關性[42]。有研究表明,TMAO 通過多種機制對內皮細胞產生直接毒性,也可誘導活性氧產生,促進內皮細胞衰老進而導致內皮功能損害[43]。內皮功能障礙是目前已確定和肺動脈高壓發病有關的因素之一,因此不難推測出TMAO 通過干擾正常的內皮功能來加重肺動脈高壓。YANG 等[44]的研究也提示TMAO 和肺動脈高壓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且經治療后病情穩定或好轉的肺動脈高壓患者血漿TMAO 水平出現動態下降[ΔTMAO =-0.2(-1.6,0.7)μmol/L,P=0.006],相反,在病情惡化的患者中觀察到TMAO 水平的潛在增加趨勢[ΔTMAO =0.7(-0.9,2.5)μmol/L,P=0.234];此外,高水平的TMAO 預示肺動脈高壓預后不良,在調整混雜因素后,相關性仍然顯著。TMAO 可能有著類似于BNP 的作用,TMAO 增高的程度與肺動脈高壓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可作為評估肺動脈高壓病情和預后判斷的指標。
6 血栓相關標志物
部分肺動脈高壓在發生、發展過程中存在血栓性的病變,由血小板、凝血因子和內皮活化引起,轉化為血小板聚集、血管收縮和內側增生[45]。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是在血管內皮損傷時釋放的一種大分子糖蛋白,參與血小板的聚集和黏附過程。有研究發現肺動脈高壓患者血漿vWF 及其抗原(vWF:Ag)水平升高與預后不良相關[46]。XUE 等[47]的研究也顯示了vWF 水平在CTEPH患者的血漿和肺內皮中上調。血小板活化在肺動脈高壓病理生理過程中起重要作用,血小板活化在內的止血異常可能直接影響肺動脈高壓的發病機制[48]。而MAHA 等[49]的研究顯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伴肺動脈高壓患者的平均血小板體積,這一被認為是血小板活化的客觀指標,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且隨著肺動脈高壓嚴重程度的增加,平均血小板體積的統計學顯著升高。此外,肺動脈高壓患者具有高水平的血小板源微粒,給予更高劑量依前列醇有降低血小板源微粒水平的趨勢[50]。D-二聚體是指示微血管血栓形成的交聯纖維蛋白的標志物,有研究發現,經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檢測,原發性肺動脈高壓患者的D-二聚體水平顯著升高[51]。一項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表明,D-二聚體是肺動脈高壓的獨立預測因子,與對照組相比,肺動脈高壓組患者的D-二聚體和纖維蛋白降解產物水平更高[33]。綜上所述,在參與肺微小動脈原位血栓形成,加重肺動脈高壓過程中的纖維蛋白降解產物、血小板及其衍生物可能是預測肺動脈高壓嚴重程度的生物標志物。然而,這些結果及相關機制需要大量臨床試驗進一步驗證。
7 右心室重塑標志物——軟骨中間層蛋白
軟骨中間層蛋白(cartilage intermediate layer protein, CILP1)是轉化生長因子-β 的拮抗劑,是一種參與心肌纖維化信號轉導的細胞外基質蛋白,主要來源于心臟成纖維細胞。肺動脈高壓導致右心室的壓力過載,在疾病早期階段,右心室出現代償性變化,如室壁增厚和心室肌肥大,以此通過增加心肌收縮力維持耦合,然而,持續增加后負荷會導致失代償性的病理重構,如心室動脈解耦和右心衰竭[52]。一項觀察性單中心研究表明,右心室重塑導致CILP1 水平顯著升高,相反,CILP1 水平與左心室參數之間沒有關聯[53]。KERANOV 等[54]通過小鼠實驗發現,行肺動脈環束術后的小鼠CILP1 含量明顯高于假手術的小鼠,血漿前體CILP1 蛋白和N-末端片段能結合轉化生長因子-β1,從而抑制轉化生長因子-β 信號轉導,進而導致肺動脈高壓的發生和發展,并發現對照組患者的血清CILP1 水平低于肺動脈高壓組,右心室功能不全的肺動脈高壓患者的CILP1 濃度高于右心室功能正常的患者,同時研究也表明CILP1 和NT-proBNP 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證明CILP1 和NT-proBNP 都是右心室適應不良的良好預測因子。NT-proBNP 雖是肺動脈高壓診療指南推薦在診斷和隨訪期間常規測量的項目,但NT-proBNP 不具有特異性,幾乎可在任何心臟疾病中升高[2]。CILP1 可以作為右心室病理性重塑的新型生物標志物,不僅能評估肺動脈高壓的預后,還能夠區分左心室和右心室疾病,其較NT-proBNP 特異性更高,但仍需大樣本臨床研究進一步驗證。
8 總結
目前發現了一些新的、具有應用前景的肺動脈高壓的生物標志物,但仍缺乏反映肺動脈高壓疾病特征的特異性標志物。這些標志物多處于臨床前研究階段,或研究樣本量較小需大樣本研究進行驗證。同時,鑒于肺動脈高壓復雜的病理生理機制,大部分生物標志物僅僅與肺動脈高壓相關或只反映肺動脈高壓發生、發展的某個階段或病理過程,單一的生物標志物很難充分反映肺動脈高壓患者的病因、疾病分期、臨床預后和死亡風險,多種生物標志物的聯合應用將會有更廣闊應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