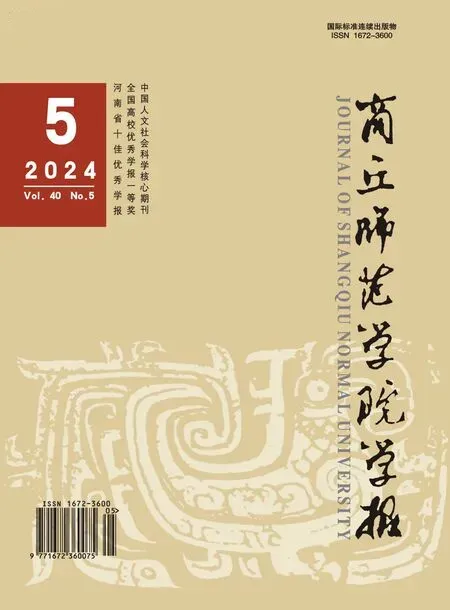目的論擴(kuò)張的再思考
鄭 易 通
(澳門科技大學(xué) 法學(xué)院,澳門 氹仔 999078)
一、引言
雖然法學(xué)界通說認(rèn)為“目的論擴(kuò)張”是漏洞填補(bǔ)工具,但是不少學(xué)者對其概念的成立仍有質(zhì)疑。這些質(zhì)疑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目的論擴(kuò)張是否存在適用前提;第二,目的論擴(kuò)張的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總之,以拉倫茨的觀點為代表的傳統(tǒng)概念面臨著多重進(jìn)路的挑戰(zhàn);既有從邏輯的角度對概念的否定[1]125,也有從效果意義和推理方式進(jìn)行批判[2]。無論是對目的論擴(kuò)張的適用前提還是概念合理性的否定,這些研究雖然在形式上都證明了類推可以取代目的論擴(kuò)張,但是實質(zhì)上都是在工具個體層面將類推和目的論擴(kuò)張對比,未能全面系統(tǒng)地分析法律漏洞對填補(bǔ)方法的影響,人為地割裂或者忽視了二者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因此,目的論擴(kuò)張存在與否并非可以孤立地看待或?qū)Ρ?而是應(yīng)將其置于法律漏洞的背景之中進(jìn)行分析。
卡納里斯的法律漏洞理論不僅對法律漏洞展開了細(xì)致的分析,還揭示了法律漏洞與填補(bǔ)手段之間的關(guān)系。雖然其他學(xué)者也對二者間的關(guān)系提出過看法,但多數(shù)看法僅停留在初步的描述階段,而且多側(cè)重于揭示填補(bǔ)手段自身的特征,對法律漏洞的分析相對不足。因此,本文將在卡納里斯漏洞填補(bǔ)理論的基礎(chǔ)上推進(jìn)關(guān)于目的論擴(kuò)張的研究,具體的論證將遵循以下路線:首先,梳理反對立場存在的問題和合理性,并分析目的論擴(kuò)張既有的辯護(hù)手段;其次,從卡納里斯漏洞填補(bǔ)理論出發(fā)分析類推適用的局限性,明確目的論擴(kuò)張的前提;最后,在肯定既有辯護(hù)觀點合理性的基礎(chǔ)上,對其進(jìn)一步地完善并與類推區(qū)分,澄清目的論擴(kuò)張的概念。
二、“目的論擴(kuò)張”受到的批判與可能辯護(hù)
傳統(tǒng)通說認(rèn)為目的論擴(kuò)張不能夠被視為類推主要有三種理由:第一,填補(bǔ)漏洞的依據(jù)不同。類推是借助法律相似性標(biāo)準(zhǔn),而目的論擴(kuò)張是訴諸立法宗旨[3]74。第二,推理過程不同。類推是從“特殊”到“特殊”的推理,而目的論擴(kuò)張則是從“一般”到“特殊”的推理[4]149—156。第三,方法的正當(dāng)性依據(jù)不同。類推依據(jù)的是“積極平等原理”[3]55,目的論擴(kuò)張則是依據(jù)法律目的。這三種理由顯示了傳統(tǒng)目的論擴(kuò)張概念的特征,亦即目的論擴(kuò)張就是指法律規(guī)定的文義相對于其意義可能過于狹隘,此時法律目的要求該規(guī)范擴(kuò)張適用[5]499—500。該觀點還跟新興典范默勒斯的《法學(xué)方法論》在內(nèi)容上有傳承關(guān)系[6],但是默勒斯對目的論擴(kuò)張的看法與拉倫茨有明顯差別,一個理論上可能的原因在于,它是對目的論擴(kuò)張的批判進(jìn)行回應(yīng)的結(jié)果。
(一)批判方式及其分析
在反對立場看來,目的論擴(kuò)張本質(zhì)上就是類推的特殊形式。首先,目的論擴(kuò)張在邏輯上就是類推或者是類推的一部分。一方面,對二者概念的邏輯分析表明,目的論擴(kuò)張的概念“實系一并無實質(zhì)意義之‘空集合’”[2];另一方面,類推的推理過程“應(yīng)是先從特殊到一般,再從一般到特殊的過程”[7],目的論擴(kuò)張只是該過程“一般”到“特殊”部分的體現(xiàn)。其次,看似目的論擴(kuò)張雖然可以填補(bǔ)開放漏洞[5]500,但是目的論擴(kuò)張發(fā)揮的功能效果不僅與類推一致,而且二者的正當(dāng)性不存在差異,因為法律目的同一是平等原理重要的表現(xiàn)形式,即是從“規(guī)范中抽取一個可適用到相似案件上的基本思想”[8]184。最后,當(dāng)然也就不存在類推的“相似性”與目的論擴(kuò)張“訴諸目的”的區(qū)分,因為“類推所依據(jù)的‘相似性’,也是遵循‘規(guī)范的意旨’而得來的”[2],二者本就同出一源。
種種質(zhì)疑明確指出區(qū)分目的論擴(kuò)張與類推之間存在的硬傷,而且將類推視為填補(bǔ)法律漏洞,特別是開放漏洞的核心甚至是唯一手段都是有道理的。雖然批判進(jìn)路不同,但是他們都是從目的論擴(kuò)張的傳統(tǒng)概念入手作為批判的起點,這就指明目的論擴(kuò)張的傳統(tǒng)概念確實存在問題。或者說這種概念無法清晰且準(zhǔn)確地表達(dá)出目的論擴(kuò)張的獨特屬性,因為反對立場的理由概括起來都是認(rèn)為目的論擴(kuò)張的存在有疊床架屋之嫌,而且這種質(zhì)疑目前來看是成功的。這至少可以認(rèn)為目的論擴(kuò)張受到批判的直接原因在于其概念的模糊性,它無法像其他漏洞填補(bǔ)方法一樣表現(xiàn)出獨特性。
目前來看,這種模糊性體現(xiàn)在目的論擴(kuò)張概念內(nèi)涵的兼容性:目的論擴(kuò)張的概念也完全可以包括類推。首先,目的論擴(kuò)張是指法律規(guī)定的文義相對于其意義可能過于狹隘,此時法律目的要求該規(guī)范擴(kuò)張適用。其次,類推適用的情形就是“……沒有設(shè)定適用規(guī)則的場合,雖然根據(jù)制定法自身的目的,這種規(guī)則本應(yīng)被包含”[5]500。實際上就是因為構(gòu)成要件的文義相對于法律目的過窄,才讓類推的適用超越了文義[9]101—102。因此,目的論擴(kuò)張概念的特征完全可以包含類推,同理甚至也可以將創(chuàng)造性補(bǔ)充等方法納入其中。總之,只有對目的論擴(kuò)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更為清晰和準(zhǔn)確地理解,才能夠消解概念的模糊性。
(二)可能的辯護(hù)途徑
雖然說目的論擴(kuò)張的傳統(tǒng)概念存在模糊性的問題,但是這并不等于目的論擴(kuò)張不存在。因為反對立場雖然指出了二者區(qū)分的硬傷,但是他們也沒有注意到“類比之困難在于兩案之間些許的相似以及某些特征的相干,不代表所有重要的特征全都相干”[10]。也就是說,類推的適用是有局限性的。此外,他們對目的論擴(kuò)張的否定都是孤立地從工具視角展開,沒有考慮作為填補(bǔ)工具的它們與法律漏洞之間的關(guān)系。更為重要的是反對立場僅是對概念做出反駁,并沒有對概念的基礎(chǔ)進(jìn)行否定。這就意味著通過對目的論擴(kuò)張基礎(chǔ)的再認(rèn)識,重新思考法律漏洞對填補(bǔ)方法的影響,仍有為目的論擴(kuò)張辯護(hù)成功的可能。
針對目的論擴(kuò)張概念的模糊性問題,有兩種側(cè)重不同的辯護(hù)方式:外部辯護(hù)和內(nèi)部辯護(hù)。外部辯護(hù)主張類推與目的論擴(kuò)張“并無嚴(yán)格區(qū)分,二者只具有程度的差別”[11]188。之所以是外部辯護(hù),一方面是因為它并未突破目的論擴(kuò)張的傳統(tǒng)概念,只是在細(xì)化;另一方面,基于外部效果來看無論是目的論擴(kuò)張還是類推,它們都表現(xiàn)為擴(kuò)大了法律規(guī)則的適用范圍和重視法律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外部辯護(hù)仍嘗試在外部視角下尋求突破的可能,它們強(qiáng)調(diào)類推適用的局限性,主張二者具體適用情況不同[12]421。所謂內(nèi)部辯護(hù)就是重新發(fā)現(xiàn)目的論擴(kuò)張自身獨特的屬性,特別是與法律漏洞之間的聯(lián)系。例如默勒斯主張目的論擴(kuò)張“是在構(gòu)成要件之上補(bǔ)充了某個構(gòu)成要件要素”[13]390,內(nèi)部辯護(hù)在效果上雖然看似與外部辯護(hù)一致,但是其不僅清晰地指出目的論擴(kuò)張的獨特屬性,還提到了當(dāng)只有缺乏與法律漏洞“相應(yīng)的‘聯(lián)結(jié)點’時”[13]391,才能適用目的論擴(kuò)張。亦即闡明了法律漏洞對目的論擴(kuò)張的影響。
無論何種辯護(hù)方式都注意到了原有概念的模糊性,只是都未能全面解決該問題。不可否認(rèn),外部辯護(hù)指明了在具體情境中區(qū)分目的論擴(kuò)張和類推適用的必要性,強(qiáng)調(diào)類推的適用是有局限性,但是外部辯護(hù)忽視了法律漏洞的影響,無法說明區(qū)分二者的可行性,即缺乏具體區(qū)分的實現(xiàn)方式。內(nèi)部辯護(hù)無疑更為成功,因為它注意到了目的論擴(kuò)張與法律漏洞的關(guān)聯(lián)性,也因此能夠提供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只是當(dāng)下默勒斯的辯護(hù)仍有部分不足:一方面,他未能全面澄清目的論擴(kuò)張的概念。因為他只注意到了構(gòu)成要件,忽略了對“法律后果”的討論。另一方面,他缺乏對法律漏洞影響的細(xì)致討論。默勒斯雖然提到法律漏洞對目的論擴(kuò)張的影響,但只是一筆帶過并未具體分析。然而瑕不掩瑜,相較而言,內(nèi)部辯護(hù)不僅實現(xiàn)了和外部辯護(hù)一樣的效果,還更加清晰地說明了目的論擴(kuò)張的獨特屬性和類推的不同。
總之,兩種辯護(hù)方式對澄清目的論擴(kuò)張的努力值得肯定,但無疑內(nèi)部辯護(hù)更具可靠性。因此將在內(nèi)部辯護(hù)的基礎(chǔ)上,借助卡納里斯的漏洞理論完善對目的論擴(kuò)張必要性的討論。具體而言,從禁止拒絕裁判漏洞理論出發(fā),分析類推適用的局限性和明確目的論擴(kuò)張適用的前提。因為漏洞的發(fā)現(xiàn)方法和填補(bǔ)方式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3]180,這一點恰好能夠說明類推的局限和目的論擴(kuò)張的必要性。
三、禁止拒絕裁判漏洞
禁止拒絕裁判漏洞的特征,在于法官裁判某個具體案件時最終的選擇只有兩種:要么拒絕裁判,要么補(bǔ)充法律。但是基于法治國或者說分權(quán)原則,法官不得拒絕裁判,因此法官此時只能在這種情形下強(qiáng)制續(xù)造法律。這種漏洞通常情形例如:法律只規(guī)定了訴訟時效的要求,卻沒有規(guī)定具體的訴訟時效期間,導(dǎo)致難以時效抗辯的情形出現(xiàn);法律只規(guī)定了利息,但是卻沒有對利率進(jìn)行規(guī)定,以致法官無法對具體利息數(shù)額的訴求裁決等等。
(一)禁止拒絕裁判漏洞的認(rèn)定
如何認(rèn)定或者說發(fā)現(xiàn)禁止拒絕裁判漏洞,有學(xué)者言簡意賅指明“通過法律解釋去發(fā)現(xiàn),是否法律真的沒有就某個具體問題提供任何的答案”[7]。也就是說該漏洞的認(rèn)定方式其實是看法律解釋的效果是否充分,即法條是否能完整解釋或者涵攝案件事實。只有當(dāng)法條不進(jìn)行實質(zhì)上的補(bǔ)充便無法適用時,該情形才能被認(rèn)定為禁止拒絕裁判漏洞。
尤為注意的是,禁止拒絕裁判漏洞并非體系解釋適用的對象。舉例來說,《德國民法典》第904條關(guān)于緊急避險的規(guī)定。雖然根據(jù)文義可以直接得出受侵害的所有權(quán)人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quán),但是現(xiàn)有的法律解釋方法無法指明誰是請求權(quán)的相對人。因此該規(guī)定存在不經(jīng)補(bǔ)充便無法適用的問題,而且若拒絕適用該法條便會造成拒絕裁判的結(jié)果,此時針對該情形可以認(rèn)為存在禁止拒絕裁判漏洞。體系解釋的適用例如我國民法典第272條對業(yè)主們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規(guī)定,看似沒有規(guī)定業(yè)主違反義務(wù)損害其他業(yè)主合法權(quán)益的法律后果,但是可以結(jié)合民法典第236條至第238條的規(guī)定,來排除物權(quán)侵害。因此,對拒絕裁判漏洞的認(rèn)定,必須注意到與體系解釋的區(qū)別,特別是有關(guān)規(guī)定是否能夠在體系上呈現(xiàn)出不經(jīng)補(bǔ)充便無法適用的情形,這樣才能避免混淆二者。
(二)禁止拒絕裁判漏洞的類型
依據(jù)法條自身狀況,導(dǎo)致“法律不經(jīng)補(bǔ)充便無法適用”的情形可以劃分為兩種:第一種從體系視角來看,法律規(guī)范存在缺陷,具體表現(xiàn)為“缺少整個法條即‘規(guī)整漏洞’”[3]44。第二種從規(guī)范自身來看,法律規(guī)范存在瑕疵,具體表現(xiàn)為“法條的一部分缺失了,實際是缺失法效果”[3]44,即規(guī)范漏洞。當(dāng)然這種分類不能夠窮盡卡納里斯提出的類型,但是卻可以很好地概括出類推和目的論擴(kuò)張這兩種方法的特點,因此對于其他類型暫不提及。
1.規(guī)整漏洞
規(guī)整漏洞不同于目的性漏洞,卡納里斯認(rèn)為目的性漏洞與禁止拒絕裁判漏洞之間是并列而非包含關(guān)系。從形式上來看,導(dǎo)致規(guī)整漏洞和目的性漏洞出現(xiàn)的直接原因是法律規(guī)范存在問題,而且填補(bǔ)二者工具都是類推,因此會將規(guī)整漏洞視為目的性漏洞并非無稽之談。但是該觀點會面臨三個方面的質(zhì)疑,從而消解該觀點的合理性。首先,兩種漏洞類型的認(rèn)定方式不同。規(guī)整漏洞本質(zhì)上仍是以法律規(guī)定是否在體系上不經(jīng)補(bǔ)充便無法適用作為標(biāo)準(zhǔn)。在該認(rèn)定方式出現(xiàn)的場合,實證法通常是“欠妥當(dāng)?shù)匚醋骰卮稹盵3]124;而目的性漏洞則是基于法律目的續(xù)造法律,特別是與平等原理相聯(lián)系。其次,拒絕漏洞填補(bǔ)的后果性質(zhì)不同。如果不對規(guī)整漏洞作出一個法律上妥當(dāng)?shù)幕卮?就意味著法官違背了禁止拒絕裁判這一司法原則,其駁回起訴的裁判結(jié)果不具有任何形式的合理性。但是拒絕填補(bǔ)目的性漏洞至少在形式上是具有正當(dāng)理由的,因為法官可以基于規(guī)范的缺乏不違反法律目的為理由,做出消極的裁判——駁回起訴,即使這是錯誤的判決[3]41。很明顯,目的性漏洞涉及規(guī)范的價值評價,而規(guī)整漏洞則表現(xiàn)為規(guī)范的事實論述。最后,僅憑填補(bǔ)手段相同不足以作為漏洞相同的理由。因為禁止拒絕裁判漏洞的認(rèn)定和填補(bǔ)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這與目的性漏洞不同。在前者的規(guī)整漏洞情境中,類推只是作為恰當(dāng)而非必然的填補(bǔ)手段,不具有決定意義。
強(qiáng)調(diào)規(guī)整漏洞不同于目的性漏洞的目的在于,對類推適用的變化提供合理性的說明。卡納里斯注意到類推適用的不同特點,例如其在填補(bǔ)拒絕裁判漏洞時是“可能”,而在目的性漏洞中是“必然”[3]129。值得檢討的地方在于,已經(jīng)強(qiáng)調(diào)類推作為目的性漏洞填補(bǔ)的必然,乃至唯一手段,而且目的性漏洞的確定和填補(bǔ)是同一思維,那么如何解釋目的性擴(kuò)張在目的性漏洞中存在的意義?當(dāng)然,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類推和目的性限縮是分別在積極平等原理、消極平等原理下作為唯一漏洞確定工具,而目的論擴(kuò)張則是屬于“由立法宗旨直接要求補(bǔ)充規(guī)范的情形”[3]180。但是,該解釋的依據(jù)仍然面臨模糊性問題,因為平等原理往往也是依據(jù)立法宗旨作為判斷標(biāo)準(zhǔn)。其實,該問題的出現(xiàn)源于對目的論擴(kuò)張適用的誤解,它不適合填補(bǔ)目的性漏洞。以卡納里斯所舉的遺孀養(yǎng)老金請求權(quán)為例,他與拉倫茨都認(rèn)為該案件不適用類推,因為“這里涉及的是與已規(guī)定的事項完全不同的事實構(gòu)成,但為了使制定法的調(diào)整目的能夠?qū)崿F(xiàn),必須將其包含于制定法的這一規(guī)則中”[5]501。問題在于兩種事實構(gòu)成并非絕對不同,理由有兩點:第一,從邏輯角度看,無論是撫養(yǎng)費請求權(quán)還是法律未規(guī)定的養(yǎng)老金請求權(quán),都可以被視為“對現(xiàn)金流的損害”[13]391。這就使得類推有了基礎(chǔ)。第二,該情形完全可以適用積極平等原理。毫無疑問遺孀養(yǎng)老金請求權(quán)的缺失是法律漏洞,但是拒絕填補(bǔ)該漏洞不會使法官犯下拒絕裁判的錯誤,因為它只涉及規(guī)范的價值評價問題,所以該漏洞為目的性漏洞。同時,因為被適用的法條的關(guān)鍵點在于維系喪失撫養(yǎng)的請求權(quán)人的生計,而撫養(yǎng)費的請求事實與未規(guī)定的養(yǎng)老金請求事實在此并無二致,即構(gòu)成同類案件。因此,目的論擴(kuò)張并不能夠適用于目的性漏洞,類推則擁有填補(bǔ)的必然性。
至此,可以明確類推適用的必然性僅局限于目的性漏洞中,它在禁止拒絕裁判中的適用不具有必然性。因為規(guī)整漏洞與目的性漏洞的差別已經(jīng)說明,不能默認(rèn)類推的適用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必然性;而目的論擴(kuò)張的模糊性造成了其可以適用目的性漏洞的錯誤認(rèn)識,這被反對立場正確指出。因此,雖然類推確實可以填補(bǔ)規(guī)整漏洞,但類推不具備必然性,這就意味類推只是填補(bǔ)拒絕裁判漏洞的手段之一。同時對于目的論擴(kuò)張而言,正因為其不具有填補(bǔ)目的性漏洞的合理性和類推在禁止拒絕裁判漏洞中不具有必然性,所以目的論擴(kuò)張?zhí)钛a(bǔ)的漏洞只可能是禁止拒絕裁判漏洞。
2.規(guī)范漏洞
規(guī)范漏洞與規(guī)整漏洞雖然同為禁止拒絕裁判漏洞,但是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第一,法條的缺失形式不同。規(guī)整漏洞是整個法條或者說法律規(guī)范,本應(yīng)規(guī)定但是并未規(guī)定的情況。例如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qū)終審法院針對司法援助的上訴期間確定的問題,進(jìn)行的類推填補(bǔ)就是典型的規(guī)整漏洞情形。因為它不是基于相似性而確定漏洞填補(bǔ)手段,而是由存在體系上不經(jīng)填補(bǔ)便無法適用的情形確定。規(guī)范漏洞是法條或者說法律規(guī)范部分缺失,不是以完整的形式呈現(xiàn)的情況。例如我國法律規(guī)定了自然人之間可以約定逾期利息,但是并沒有指明利息數(shù)額的計算。第二,填補(bǔ)效果不同。規(guī)整漏洞的填補(bǔ)是擴(kuò)大了既有規(guī)范的法律效果適用范圍,例如董事會的召集存在瑕疵,法律雖然作出規(guī)定但遺漏違反該規(guī)定的制裁的情況,就需要類推填補(bǔ)法律效果;規(guī)范漏洞的填補(bǔ)則使得法律效果的實現(xiàn)具有可操作性,例如,針對設(shè)置了訴訟期間卻沒有規(guī)定其具體長度的情形,可以在既有期間范圍內(nèi)明確一個合理性的時間。因此二者不可等同,而且效果是對立的。
規(guī)范漏洞與規(guī)整漏洞的不同,就意味著類推不能填補(bǔ)規(guī)范漏洞。首先,類推填補(bǔ)的效果不符合規(guī)范漏洞的要求。因為類推的重點在于擴(kuò)大或者說填補(bǔ)法律效果,不涉及規(guī)范自身的結(jié)構(gòu)問題。相反,造成規(guī)范漏洞出現(xiàn)的原因是構(gòu)成要件或者是法律后果,要么是前者的規(guī)定有缺漏,要么就是后者規(guī)定得不夠清晰準(zhǔn)確。因此規(guī)范漏洞涉及的不是法律問題已經(jīng)存在,卻沒有任何規(guī)定的情況。其次,類推的適用是有條件限制的。第一,此時類推只能作為填補(bǔ)方法。因為禁止拒絕裁判漏洞的認(rèn)定和填補(bǔ)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所以作為填補(bǔ)手段的類推在這里不是發(fā)現(xiàn)漏洞的方式,也就不能成為判斷規(guī)范漏洞的標(biāo)準(zhǔn)。第二,類推在邏輯上不具有必然的效力,它只是一種概率上的可能。可能性實現(xiàn)的程度取決于“類似事件的相同特征與比擬的標(biāo)的有相干性”[14]108,特別要說明特征與標(biāo)的之間是否具有某種聯(lián)系,亦即所謂的“相關(guān)性條件”[15],僅強(qiáng)調(diào)相似性不足以證明類推成立。然而規(guī)范漏洞不是缺少規(guī)定而是規(guī)定得不夠細(xì)致,它不需要通過相關(guān)性尋求適用其他法律規(guī)范效果的正當(dāng)性。最后,規(guī)范漏洞所要求填補(bǔ)的特征更加貼合目的論擴(kuò)張。就該漏洞類型而言,它只要求完善法條的構(gòu)成要件或者是法律后果,而非是補(bǔ)足缺少的制裁或者整個法條的缺失,因為法條是由普遍化的“構(gòu)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組合而成[5]321。故而規(guī)范漏洞的填補(bǔ)是有限制的,它不會像類推在符合相關(guān)性的條件下就可以移植有關(guān)法律后果,而是只作用到法條出現(xiàn)瑕疵的地方。這也是默勒斯主張目的論擴(kuò)張是填補(bǔ)缺少法條構(gòu)成要件的原因,同時亦是對他缺少法律漏洞對目的論擴(kuò)張影響的具體分析的補(bǔ)足。
總之,類推確實對法律漏洞的填補(bǔ)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但是類推的適用也是有局限性的,而這恰是目的論擴(kuò)張必要性的體現(xiàn)。對于目的性漏洞而言,類推不僅是確定漏洞的方法,還是填補(bǔ)該漏洞的必然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默認(rèn)類推“必然”適用于禁止拒絕裁判漏洞,因為規(guī)整漏洞不同于目的性漏洞。此外,類推的局限性就體現(xiàn)在它只是填補(bǔ)禁止拒絕裁判漏洞的手段之一,特別是對于規(guī)范漏洞而言,無論是基于填補(bǔ)效果、類推自身條件的限制、還是規(guī)范漏洞的要求,規(guī)范漏洞更適合由目的論擴(kuò)張而非類推填補(bǔ)。
四、“目的論擴(kuò)張”的概念澄清
目的論擴(kuò)張的內(nèi)部辯護(hù)更具可靠性和說服力,但是當(dāng)前的內(nèi)部辯護(hù)只表明了目的論擴(kuò)張的構(gòu)成要件,對法律后果的說明則不夠充分。默勒斯雖然已經(jīng)充分地說明了部分構(gòu)成要件缺失對法律效果的影響,但是忽略了對法律后果瑕疵的說明。之所以強(qiáng)調(diào)對法律后果的說明,是因為規(guī)范漏洞是以法條結(jié)構(gòu)的瑕疵作為表現(xiàn)形式,而一個完整的法條通常被視為“兼?zhèn)錁?gòu)成要件與法律效力這兩個要素”[16]159。因此對目的論擴(kuò)張概念的澄清,必然是要依靠對規(guī)范漏洞的說明,也就是要對“構(gòu)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展開具體論述。
(一)“目的論擴(kuò)張”的內(nèi)涵界定
關(guān)于目的論擴(kuò)張概念內(nèi)涵的討論,默勒斯對“構(gòu)成要件”已經(jīng)有了較為充分的論證,因此只對其進(jìn)行簡要的說明,接下來將主要分析“法律效果”的影響。默勒斯注意到了目的論擴(kuò)張傳統(tǒng)概念的缺陷,因為它很容易與類推混淆,使得對目的論擴(kuò)張的適用略顯牽強(qiáng)[13]390。為此他從待填補(bǔ)的規(guī)范漏洞出發(fā),發(fā)現(xiàn)了當(dāng)規(guī)范缺乏相應(yīng)具體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時,才能夠適用目的論擴(kuò)張。他以《德國民法典》第904條關(guān)于緊急避險為例,通過“注水案”來說明適用該規(guī)定時出現(xiàn)的因缺乏相應(yīng)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造成實踐中引發(fā)的缺乏請求權(quán)相對人規(guī)定的問題。對于該問題的解決,他利用目的論擴(kuò)張的方法擴(kuò)張該法條第2款的規(guī)定,填補(bǔ)缺乏請求權(quán)相對人的漏洞,最終使得該案件得以恰當(dāng)解決[13]391—393。通過結(jié)合前一章對目的論擴(kuò)張前提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確定填補(bǔ)方法最重要的并非功能效果的考量,而是填補(bǔ)方法要與漏洞的特征具有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或者說要能滿足漏洞自身的要求。
就規(guī)范漏洞而言,它與填補(bǔ)方法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或者說要求,就體現(xiàn)為“構(gòu)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前者經(jīng)由默勒斯論證,明確目的論擴(kuò)張的概念內(nèi)涵包括對構(gòu)成要件要素缺乏的補(bǔ)充,接下來將說明法律后果亦應(yīng)包括進(jìn)目的論擴(kuò)張的內(nèi)涵。具體而言,當(dāng)對案件事實的法律評價缺乏與法律規(guī)范相應(yīng)的具體評價內(nèi)容時,也可以適用目的論擴(kuò)張。例如,我國《民法典》第676條“逾期利息”的問題即如此。在該情形中,就無法通過添加構(gòu)成要件要素而填補(bǔ)漏洞,所以應(yīng)通過明晰法律后果適用目的性擴(kuò)張。逾期利息的問題之所以是規(guī)范漏洞,原因在于它無法通過法律解釋來解決,特別是自然人之間只約定了逾期利息,卻并未約定具體數(shù)額時,該情形不僅在法體系上呈現(xiàn)出不經(jīng)補(bǔ)充便無法適用的特點,而且是由法律后果缺乏具體化形式造成的,并非沒有法律效果,因此也就不考慮類推為填補(bǔ)手段。為了明確法律后果具體化的形式,法官可以通過目的論擴(kuò)張將逾期利息的數(shù)額明確為“借款人自逾期還款之日起參照當(dāng)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標(biāo)準(zhǔn)計算的利息承擔(dān)逾期還款違約責(zé)任”(1)具體內(nèi)容詳見《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法釋〔2015〕18號),第28條。。由此,法官借由目的論擴(kuò)張明確了逾期利息的數(shù)額,使原有的法律后果的一般性規(guī)定變得清晰并具有了實現(xiàn)的可能性,解決了拒絕裁判的難題。
可以說通過對規(guī)范漏洞的分析,發(fā)現(xiàn)它與默勒斯對目的論擴(kuò)張的定義相關(guān)聯(lián),即符合該漏洞對于填補(bǔ)方法的要求。這說明了“缺少構(gòu)成要件要素”不僅是規(guī)范漏洞的體現(xiàn),也表明是目的論擴(kuò)張內(nèi)涵的獨特屬性,但同時也呈現(xiàn)出默勒斯觀點的問題所在——疏于對“法律后果”的討論。繼而在對法律后果評價的具體化進(jìn)行說明后,可以發(fā)現(xiàn)目的論擴(kuò)張實際上就是補(bǔ)充了某個構(gòu)成要件要素或具體化了法律后果,清晰且準(zhǔn)確地呈現(xiàn)出了內(nèi)涵的獨特屬性。
(二)不同于“類推”的外延特征
通過對目的論擴(kuò)張概念內(nèi)涵的澄清可以發(fā)現(xiàn),它與類推不是同一事物。雖然反對立場對傳統(tǒng)目的論擴(kuò)張的批判有正確的一面,但是若從法律漏洞的視角對兩種方法的特征進(jìn)行比對,則很清晰地呈現(xiàn)出二者的核心區(qū)別。具體而言,無論是二者的邏輯推理過程、適用前提及其正當(dāng)性,還是它們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都不能說明目的論擴(kuò)張就是類推的特殊形式。
首先,就邏輯推理過程而言,該區(qū)分不具有實際價值。第一,就二者概念自身的邏輯分析而言,澄清后的目的論擴(kuò)張概念不僅與類推的適用前提不同,其適用的領(lǐng)域亦是類推局限性所在,至少類推沒有涉及對構(gòu)成要件要素的填補(bǔ)。最為關(guān)鍵在于此時目的論擴(kuò)張的概念不同于傳統(tǒng)定義,而基于傳統(tǒng)定義展開的邏輯分析,面臨著稻草人謬誤的風(fēng)險。第二,就二者的推理過程而言,無論是從一般到特殊,還是特殊到特殊等等,該視角解釋二者相似與否的意義有限。因為依法律原則補(bǔ)充也是從一般到特殊,也可以被包含于“從特殊到一般,再從一般到特殊的過程”[7],但是這不等于依法律原則補(bǔ)充就是類推。因此,就推理過程對探析兩種事物的屬性而言,意義有限。
其次,就適用前提及其正當(dāng)性而言,二者有所差異。雖然說類推也被用于填補(bǔ)禁止拒絕裁判漏洞,但不同于它在目的性漏洞中適用的必然性。因為基于類推自身的局限性和規(guī)范漏洞對填補(bǔ)方法的要求,類推不宜用來填補(bǔ)規(guī)范漏洞,因而它只是可能的填補(bǔ)手段之一。而目的論擴(kuò)張則能滿足規(guī)范漏洞的要求,并且它還不用受類推的相關(guān)性條件限制。因此就兩種方法所填補(bǔ)漏洞的性質(zhì)來看,二者雖然有可能會有交集,即都適用于禁止拒絕裁判漏洞,但是二者都是可能的手段,并且適用的具體情況各不相同,故而目的論擴(kuò)張是有成立的必要性。當(dāng)然,區(qū)分二者適用的前提其實也就意味著兩種方法的正當(dāng)性其實是有所不同的,因為所謂方法的正當(dāng)性本質(zhì)上就是為解決法律漏洞服務(wù)的。但是正如反對立場所提到的類推實質(zhì)上依然是用法律目的作為相似性判斷標(biāo)準(zhǔn),無論是目的論擴(kuò)張還是類推都是圍繞法律目的開展活動,它們正當(dāng)性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因此就該正當(dāng)性而言反對立場所言非虛。只不過問題在于類推僅是比目的論擴(kuò)張多了一個相關(guān)性條件的約束,這就意味著如果想要適用類推,就必須考慮兩個或者兩個以上規(guī)范之間的相似性。但是目的論擴(kuò)張卻只需要考慮單個規(guī)范自身的瑕疵,無須借助其他規(guī)范的效果來解決問題。
最后,就外在形式而言,二者表現(xiàn)各不相同。目的論擴(kuò)張著重于對規(guī)范自身瑕疵的完善,因此它的應(yīng)用就是通過補(bǔ)充構(gòu)成要件要素和具體化法律后果。從法律規(guī)范的視角來看,它是從規(guī)范內(nèi)部對其瑕疵部分進(jìn)行完善,因為它的適用沒有突破規(guī)范原有的構(gòu)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的范圍。類推則是著重于擴(kuò)張法律規(guī)范的效果,因此它的應(yīng)用是擴(kuò)大既有規(guī)范的適用范圍,通過法律目的判斷規(guī)范與待決案件事實之間是否滿足相關(guān)性條件。簡單來講,就是將本應(yīng)規(guī)定卻沒有規(guī)定的法律規(guī)范與欲適用于待決事實的其他規(guī)范之間,是否滿足相似性和相關(guān)性的要求,如果滿足就可以適用后者。這種適用直觀地表現(xiàn)為擴(kuò)大了原有規(guī)范的適用范圍,因為將原本基于演繹推理不會納入該規(guī)范的結(jié)果,卻因類推的相似性而納入,所以類推從規(guī)范外部擴(kuò)大了規(guī)范法律效果的適用范圍。
五、結(jié)語
本文的主要觀點總結(jié)如下。
第一,對傳統(tǒng)目的論擴(kuò)張概念的批判和辯護(hù)而言:批判的合理之處在于指出了目的論擴(kuò)張概念的模糊性,不足之處在于忽視了類推適用的局限性,而且沒有能夠從法律漏洞的視角對二者展開全面的分析。既有辯護(hù)方式的合理之處在于都在努力消解概念的模糊性,不足之處在于從法律漏洞視角展開的討論不夠清晰和細(xì)致。
第二,禁止拒絕裁判漏洞可以分為規(guī)范漏洞和規(guī)整漏洞。目的論擴(kuò)張的適用對象是規(guī)范漏洞,同時它不能填補(bǔ)與禁止拒絕裁判漏洞并列的目的性漏洞。類推在目的性漏洞中具有適用的必然性,但在禁止拒絕裁判漏洞中不具有必然性。
第三,目的論擴(kuò)張概念的準(zhǔn)確表達(dá)應(yīng)該是:補(bǔ)充了規(guī)范的某個構(gòu)成要件要素或?qū)⒎珊蠊唧w化的漏洞填補(bǔ)方法。目的論擴(kuò)張在適用前提、正當(dāng)性和外在表現(xiàn)形式上不同于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