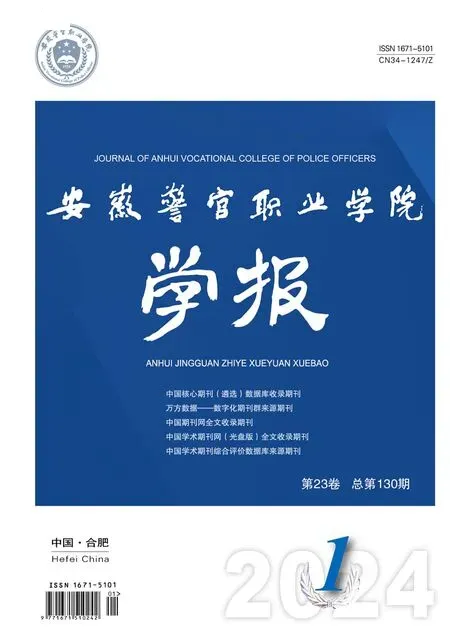論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的計算規則及其構建
周曉莉
(安徽大學,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問題之提出
根據2010 年修訂的《工傷保險條例》第三十九條,職工因工死亡,其近親屬可以從工傷保險基金領取的有喪葬補助金、供養親屬撫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其中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的標準為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 倍。該條規定似乎是為了回應因法釋[2003]20 號《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以戶籍確定死亡賠償金數目導致賠償金額懸殊而引發的爭議,條文中取消了死亡賠償中的城鄉二元標準,全部按照全國城鎮居民的標準計算,在形式上不再“同命不同價”。相較于修訂前規定的“48 個月至60 個月的統籌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現有的規定大幅地提升了職工遺屬可以獲得的補償數額,但是這種一刀切式的規定忽略了我國長期存在的發展不平衡的事實。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22 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9283 元。根據上海市和甘肅省統計局數據,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4032 元,甘肅省為37572 元。甘肅省和上海市之間足足有46460 元的差值,這樣巨大的生活成本的差距如果被忽略,將會使得有因工死亡職工的家庭無法獲得公平的救濟機會。那為何我國的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標準會如此設置呢?歸根到底還是因為立法者在“同命不同價”的輿論壓力下做出了妥協,對工亡補助金性質的界定出現了偏差,所以如果要對工亡補助金的計算標準進行糾偏。因此,就需要明確工亡補助金的性質,其次確定其補償范圍,最后再結合合理的計算方法才是正確的邏輯進路。
二、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的性質
(一)學說分歧
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是指在職工因工死亡后,向職工近親屬一次性支付的一筆補償金,其在性質上高度類似于人身損害賠償中的死亡賠償金,在不少學者的文章中也是將其納入死亡損害賠償的范疇下一并進行討論[1-4],除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的支付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死亡賠償金的賠付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外,二者相對本文來說幾乎是同一個概念。目前專門討論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性質的文章較少,但是學界對死亡賠償金的性質與標準存有廣泛而激烈的爭論,現根據死亡賠償金權利主體的不同可以分為以下代表性觀點:
第一,命價補償說。有人認為死亡賠償金是對死者生命價值的賠償,對生命試圖精確地進行金錢評價并不可取,宜采用定額化的計算規則[5];也有學者認為死亡賠償金是對死者的余命補償,應按照死者可能喪失的生命期間乘以一個平均值計算損失額[6]。還有學者主張死亡賠償金是不同權利主體生命權財產內容的物質體現,在死亡賠償金的標準的制定上雖可以通過法律確定幅度但是需要頒布司法解釋確定具體的數量標準[2],死亡賠償金是對死者遭受的財產損害的補償,相同事故下對個體造成的可得利益的喪失是各異的,基于個體差異制定出的賠償方案才真正符合矯正正義的精髓[3]。
第二,逸失利益說。采此學說的學者主張死亡賠償金并非對生命利益本身的賠償,而是對近親屬逸失利益的賠償,因為生命無價且不能繼承,在賠償標準上整齊劃一并不可取,應按照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制定賠償標準[7]。也有學者認為死亡賠償金是用來維持死者近親屬未來的生活水平,死亡賠償金的數額應考慮死者的收入水平,對死者近親屬的生活環境等情況進行有限的個別化計算[8]。還有學者認為死亡賠償金對應的是死者剩余生命的收入損失,應以死者生前收入作為死亡賠償金計算的基準[9-11],定額化的賠償模式忽略了對生命價值的多重性評價[12]。
第三,雙重損害說。針對逸失利益說,又有學者提出侵害生命權實際上給死者以及其他人共同造成了財產損害和精神損害,否認對生命權喪失本身的賠償在價值判斷上并不妥當[13]。不對受害人的死亡進行救濟,會使得加害人逃避法律制裁,對近親屬因死亡引發的反射損害進行救濟不代表對死者遭受的直接損害也進行了救濟[14]。不能只關注死亡賠償金的填補功能,還需要關注其預防和懲戒功能,死亡賠償金賠償的是生命的矯正價值[15]。
(二)學說評析
1.對命價補償說的評析
本文并不贊同命價補償說,其原因有三點:第一,民事權利主體既然已經死亡,其權利能力資格便已經消滅,再也沒有行使自己權利之可能,如何向侵權主體主張其權利?第二,縱觀歷史,只有在生產力落后,物資匱乏的時期,才有以金錢衡量人命的做法,比如西方中世紀的贖金制度(Wergeld)就是自由人在被殺害后根據其身份、等級、國籍、性別等確定不同數額的贖金。而在當今社會,正因為社會的進步,人命才更不能用經濟價值衡量[9]。第三,生命權屬于人格權的一種,與財產權不同,人命并非如物那般可以用金錢計算其價值,如果連人命也可以明碼標價,那將會是對人的尊嚴最殘忍的踐踏。
2.對雙重損害說的評析
與命價補償說相同,該學說同樣認為應該對死者本人進行救濟。雖然一些學者通過一些法律技術對死者的權利能力問題進行了解釋,并且提出了“民事權利能力轉化說”“間隙取得請求權說”、“同一人格代為說”等學說,但是正如日本學者末弘嚴太郎博士所指出的那樣,“大體上試圖承認不使用難度很高的技巧就無法說明結果的做法恰恰說明其本身存在的錯誤”[14]。
3.對逸失利益說的評析
本文較為贊同逸失利益說,尤其是張新寶教授提出的“維持一定物質生活水平說”。從賠償對象來看,逸失利益說不同于雙重損害說和命價補償說,其主張死亡賠償金的對象是近親屬,并不包括死者。死者的生命既然已經逝去,在民法上便很難保護,只有從生者的角度考慮才是正確的方向[16]。從賠償內容來看,逸失利益說主張死者死亡的事實會使得與其有密切關系的人的生活水平遭受重大影響,較為可取,至于遺屬逸失的利益究竟是否屬于純財產利益留待后文作進一步探討。逸失利益說也并非沒有缺點,它無法解釋沒有收入的家庭主婦、未成年兒童、退休老人的逝去給一個家庭帶來的影響。不過在工傷保險的適用領域中,因為職工都是具有收入的群體,所以這個缺點并沒有造成解釋上的困難。總體來說,逸失利益說更值得采納。
三、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的補償范圍
(一)補償范圍是物質損害
關于像一次性工亡補助金這一類生命權賠償金的賠償范圍,學界和實務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多數人認為死亡賠償金賠償的是財產性損失,主要是依據法釋[2003]20 號《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三十一條[17]、《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和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條以及《國家賠償法》第三十四條第三款、第三十五條中都把死亡賠償金和精神撫慰金并列[18]。而且目前在我國的附帶刑事訴訟中一般并不支持賠償死亡賠償金,因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將死亡賠償金認定為間接損失和精神性損害的賠償,這也使得一些學者從保護死者近親屬權益的角度出發認為應該將死亡賠償金認定為是物質損害的賠償。也有人認為死亡賠償金賠償的是精神損失[6][19],還有人認為死亡賠償金既賠償精神損害又賠償物質損害[20]。本文較為支持的是工亡補助金補償的是物質性損害的觀點,不能因為工亡補助金對死者近親屬具有精神上的撫慰功能就認定其為精神損害賠償,死亡賠償金是死者近親屬因死者的死亡所遭受的收入損失以及生活水平因此所遭受的負面影響的財產性損害賠償,它與精神損害賠償在功能和適用上迥異,而且從重視精神損害賠償的角度來看也不宜將精神損害賠償與死亡賠償金合并,而是應該將其單列[8]。
(二)與遺屬撫恤金應并存
既然將工亡賠償金的賠償范圍認定為死者近親屬的收入損失,那么此時不無疑問的是:工亡待遇中遺屬撫恤金也是以死亡職工生前的收入為標準設置的補償金,它與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又是什么樣的關系呢?二者是否可以并存?有學者提出工亡補助金和遺屬撫恤金的并存是借鑒了民法上的人身損害賠償制度,現既然《民法典侵權編》已經將死亡賠償金和被撫養人生活費二選一,更說明工亡補助金和遺屬撫恤金并存的不合理[21]。筆者并不贊成此觀點,工亡補助金面向的是死者所有的近親屬,而遺屬撫恤金針對的是由工亡職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并且無勞動能力的親屬,二者雖然可能存在重疊,但是這并不說明遺屬撫恤金和死亡賠償金可以互相取代。更何況,如果直接將遺屬撫恤金并入死亡賠償金的給付中,在現有的法律規定下實際上會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有學者提出除非對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七條做擴大解釋,不然將被扶養人生活費賠償計入死亡賠償金會排除被扶養人生活費賠償適用定期金的可能性[22]。所以,筆者認為工亡補助金不僅可以和遺屬撫恤金并存而且應是各自獨立的項目。
四、一次性工亡補助金計算規則的構建
(一)國外立法例
國外有關工人因工死亡的待遇中,并沒有專門的類似于我國的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的項目,但是大多數設置了遺屬撫恤金一項,因為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和遺屬撫恤金的設置都是為了彌補因職工死亡而造成職工遺屬的財產性損失,所以外國有關遺屬撫恤金的立法例也十分具有借鑒意義。目前,德國、美國、法國、日本采取的是個別化的計算方式。其中,德、美、法三國是以死者過去12 個月的年度總收入為計算基數,乘以一定的百分比支付給死亡職工的配偶、孤兒和其他符合條件的親屬。日本則是以死者生前三個月的工資計算出基本每日津貼,根據遺屬的人數每年按基本每日津貼乘以153 至245 天發放遺屬撫恤金。而英國與以上國家不同,英國采取的是一種定額化的計算方式,每月或者每周支付給死者家屬固定數額的英鎊,該金額會受遺屬年齡影響,并會根據前年的消費者價格指數的變化進行調整。英國的規定與我國類似,但是英國的遺屬撫恤金是每月一次性支付2500 英鎊加100 英鎊,最長18 個月;如果寡婦領取或有權領取家庭津貼,則為最高可達18 個月3500 英鎊外加每月350英鎊,折合成人民幣最高約635369 元。[23][24][25]
(二)我國現有法律規定
我國與以上國家和地區都不同,現有的一次性工亡補助金采取的是一種類型化的計算方式。受“同命不同價”輿論的影響,我國的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的計算基數由統籌地區職工月平均工資更改為統一的全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這樣的選擇在我國的立法例中并不是孤例。法釋[2022]14 號《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中將死亡賠償金的標準統一為受訴法院所在地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再按照戶籍做區分處理。不難看出,現有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標準的設立,一是為了與其他法律法規銜接;二是這樣統一化的規定計算簡易,可以大幅提升行政效率;三是可以回應以往“城鄉不同命價”的爭議。但是這樣的規定有著無法忽視的弊端:一是忽視了我國不同地域發展懸殊的經濟水平;二是以完全抹平人與人差異性的做法去行填補個別遇害職工家庭損失之舉實在是前后矛盾,可能導致不公平的結果。任何一個理性人都應該明白,拋去年齡、階層教育水平等因素不談,我們身處不同的地理位置維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生活成本一定是不一樣的。只是因為可以節省管理成本提升效率就選擇一刀切的規定是完全沒有說服力的。那究竟我國工亡補助金究竟應選取何種計算方式和標準,需要進行進一步探討。
(三)采取類型化計算和有限個別化的計算方式
首先,我國工亡補助金不宜采取定額化的計算方式。均一主義雖然看似公平,但是會使得有的家庭從損害中得利,有的家庭卻還未得到較好的補償。所以立法者不能只顧生命權議題的倫理性而采納了平均主義,反而忽視了一個喪失勞動力的家庭需要生存的現實性。工亡補助金計算規則的制定需要體現出個體的差異性。
其次,我國現有的類型化的計算方式也有其可取之處:一是就高不就低的選擇大幅提升了死亡職工近親屬可以領取的補助,沒有選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者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是選擇了數額更高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作為計算基數;二是20 倍的選擇既與其他有關人身損害的法律法規相銜接,又可以幫助喪失勞動力的家庭渡過難關。不過工亡補助金來源于工傷保險基金,工傷保險基金是由企業根據其職工工資水平繳納,依據2022 年的標準,一次性工亡補助金需要一次性支付985660 元,過高的一次性支付會影響到工傷保險基金的平衡,制約到工傷預防和工傷康復的發展[21],所以現有的類型化計算也需要進行改良。
再次,個別化的計算方式可以說是理想的計算方式,但是工傷立法發展程度高如德國、法國,也只是主要考慮了死亡職工的生前收入,并沒有按照死亡職工的年齡、教育程度、所處地理位置等再做區分。本文認為這樣做的原因還是個別化計算的成本較為高昂而且因為死者近親屬的逸失利益并非固有利益,而是一種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期待利益,對這種利益只能做到盡可能的估算,所以說絕對的個別化計算無法實現也沒有必要實現,但是可以采取有限的個別化計算。
最后,通過對國內外立法的分析和比較,本文認為,第一,我國工亡補助金的計算方式可以采取一種將類型化與個別化計算結合的計算方式。具體而言,雖然現有的收入分配機制并不是十分公平卻也是比較客觀的物質損失參考標準,可以說工亡補助金的適用對象中以職工生前12 個月的年平均工資收入(以下簡稱:職工年平均工資)作為標準仍然是較為合理的選擇。第二,為了防止加劇貧富差異,需要設置最低限額和最高限額。具言之,可以以工傷基金統籌地區上一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水平(以下簡稱:統籌地區職工年平均工資)作為衡量死亡職工個人年工資水平的標準,如果死亡職工的個人年平均工資低于統籌地區職工的平均工資,則按照統籌地區職工的平均工資作為計算基數,換言之,統籌地區的職工年平均工資水平是工亡補助金發放的最低限額。另外,根據統籌地區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的一定百分比制定最高限額(可以是150%~200%),即當死亡職工的個人工資高于統籌地區職工平均工資時,按照職工的個人年平均工資進行計算,但是不得超過最高限額。第三,需要扣除一定比例。原因一是工亡補助金與遺屬撫恤金存在重疊部分,防止雙重受償,二是死者的工資收入中有一定比例是用于其個人的生活和消費。結合域外的立法例和我國遺屬撫恤金的規定,需要扣除的比例在30%—70%之間,具體的幅度可以由司法解釋作出進一步的規定,由法官依照具體案情進行自由裁量。第四,可以保留20 倍的立法習慣。基于法律銜接的考慮,和既有法律法規的實施效果來看,20 倍是較為合適的選擇。最后,不需要將死亡職工的年齡納入考慮,職工壽命并非穩定因素,過多的不穩定因素會增加計算難度和管理難度,最終的計算結果也未必精準。而且《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中死者年齡超過60 歲對賠償金額才會進行扣減,我國職工的退休年齡最高是60 歲,沒有進行扣減的必要。
以上內容轉化為公式即為,若職工年平均工資≥統籌地區職工年平均工資,一次性工亡補助金=職工年平均工資X(1-30%~70%)X20,該結果不超過統籌地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的150%~200%。若職工年平均工資<統籌地區職工年平均工資,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統籌地區職工年平均工資X(1-30%~70%)X20。
五、結語
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在工傷死亡待遇中占據著較高的比重,理應安排合理的標準以填補死者近親屬因職工死亡的遭受財產損失。合理的工亡補助金不應采取一刀切的類型化計算方式,結合我國國情和域外立法,我國工亡補助金應采取類型化結合有限的個別化的計算方式,具體而言可以職工為類型,統籌地區職工的年均工資與死者個人生前年均工資為計算基數。另外設置最低限額和最高限額以防加大貧富差距,如此,才能兼顧社會公平與填補死者近親屬損失,并且有利于工傷基金的可持續發展,不阻礙工傷預防和工傷康復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