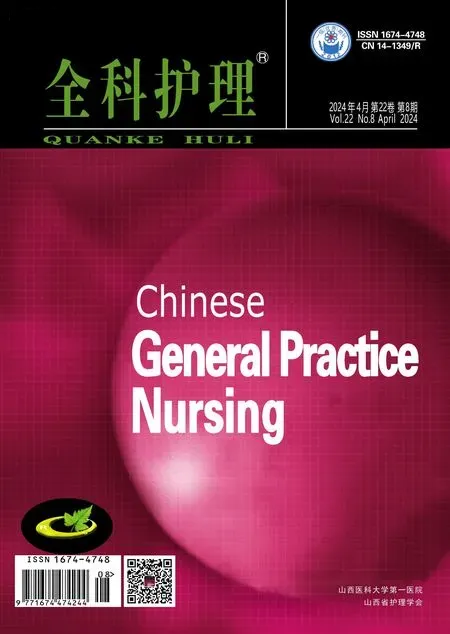1例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皮疹伴大面積皮膚損傷合并消化道出血病人的護理
王 瑩,丁 瑋,馬穎麗
近年來以細胞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抑制劑為代表的免疫治療藥物在惡性腫瘤病人中應用越來越廣泛,它在疾病進展和生存期方面均有顯著療效,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進步[1-2];但其獨特的作用機制易致機體免疫耐受失衡,誘發免疫相關不良反應(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可波及皮膚、胃腸道、肝臟、肺臟、內分泌等多臟器,其中皮膚irAEs是出現最早、最普遍的副作用[3],以皮疹、瘙癢多見,嚴重者可出現中毒性表皮壞死松解癥,不同程度影響病人生活質量及皮膚完整性,增加死亡風險。文獻報道其平均病死率高達25%~35%[4]。我科2022年3月30日收治1例輸尿管膀胱惡性腫瘤術后應用替雷麗珠單抗治療繼發嚴重藥疹伴大面積皮膚損傷合并消化道出血的病人,經多學科團隊協作診療護理模式為病人實施個體化的綜合護理方案,入院28 d后好轉出院。現將護理體會報道如下。
1 病例介紹
病人,男,75歲,2022年9月行輸尿管下段切除+膀胱部分切除+輸尿管膀胱再植術,經2022年11月信迪利單抗2個周期免疫治療、2023年2月替雷麗珠單抗1個周期治療后,自覺左肩部間斷疼痛,自服鎮痛藥后出現食欲缺乏、乏力,后間斷排鮮血便5次,每次量約200 mL,當時伴周身散在紅疹,瘙癢感明顯,搔抓可出現皮下滲血,在聯勤保障部隊第983醫院對癥治療,行胃腸鏡檢查顯示慢性胃炎急性活動、十二指腸球部多發潰瘍。入院前15 d病人出現言語含糊伴情緒煩躁,入本院急診科治療,行顱腦磁共振成像顯示點狀急性腦梗死,對癥治療后轉往重癥醫學科,給予抑酸、止血、抗感染、改善凝血功能等治療,期間完善皮膚(黏膜)檢查,排除其他致病因素,且病人無過敏性皮膚疾病史,病情相對穩定后于2023年3月30日轉入我科。
病人意識清楚,反應稍遲鈍,言語不利,生命體征:體溫(T)為36.7 ℃,心率(P)為60 /min,呼吸(R)為18 /min,血壓(BP)為132/75 mmHg。經皮血氧飽和度(SpO2)為97%,體質指數(BMI)為22.5 kg/m2,周身皮膚晦暗,軀干以及四肢可見散在紅疹,部分皮疹存在表皮脫落及血性滲出,以雙側臀部及軀干肩部為重,累積體表面積約50%(9分法計算);根據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的毒性管理指南[5]中斑丘疹/皮炎分級定為3級。兩肺呼吸音低,可聞及少量濕啰音。給予心電監護、抑酸、替加環素抗感染、營養支持治療。實驗室檢查顯示全細胞減少,白細胞計數(WBC)為3×109/L,血紅蛋白(Hb)為63 g/L,血小板計數(PLT)為18×109/L,初步診斷:消化道出血、心功能不全、皮疹伴皮膚破損、惡性腫瘤免疫治療相關副作用。
病人轉入我科后消化道出血已停止,可經口進食流質飲食。入科第2天由神經內科、皮膚科、腫瘤科、血液內科、泌尿外科醫護人員共同進行多學科團隊診療,考慮出血及皮疹與免疫治療相關,給予注射用甲潑尼龍琥珀酸鈉(甲強龍)聯合丙種球蛋白沖擊治療,皮膚破損處采用重組牛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凝膠(貝復新)+紫草油濕敷,間斷輸注懸浮紅細胞、血小板等血液制品。入科第4天病人有痰,黏稠不易咳出,痰細菌培養結果為肺炎克雷伯菌(++++)、銅綠假單胞菌感染,白細胞介素-6(IL-6)、白細胞介素-10(IL-10)升高提示革蘭陰性菌感染;予氨溴索化痰、乙酰半胱氨酸霧化,抗感染藥物調整為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入科第7天病人進食生梨后排7~10次墨綠色稀糊便,增加益生菌,皮膚損傷情況好轉,調整為甲潑尼龍30 mg/d口服。入科第9天病人突發胸悶、呼吸困難,BP為149/91 mmHg,SpO2波動在82%~95%,P為105~135 /min,心電圖示室性期前收縮、初發性心房顫動,血鉀為5.3 mmol/L,心內科會診后予胺碘酮轉復心律及利尿治療。入科第10天病人T為37.8 ℃,WBC為2.23×109,降鈣素原(PCT)為0.50 ng/mL,C反應蛋白(CRP)為2.48 mg/dL,調整抗生素為哌拉西林鈉他唑巴坦鈉。入科第11天病人再次發生消化道出血,間斷排暗血便10次,量約850 mL,立即給予禁食水、抑酸、止血、輸血等治療,后病情逐漸穩定。入科第20天啟動序貫營養支持治療,病人未再發生活動性出血,Hb升至93 g/L,每天排1次或2次成型墨綠色軟便,大部分皮膚破損處結痂脫落,新皮膚組織生成,無新發皮疹出現,住院28 d后好轉出院。
2 以多學科團隊為基礎的綜合護理方案
2.1 出血與再出血的風險管理
本例病人發生消化道出血,與免疫治療相關胃腸道毒性、胃腸道黏膜受損有關,轉入我科后處于穩定期,但大量激素沖擊治療、全血細胞嚴重減少是再次出血或隱匿性出血的高危因素。成立由護士長為責任組長的專科小組[6],由1名主管醫生、1名消化專科護士、4名主管護師組成,小組成員每天應用格拉斯哥-布拉奇福德出血評分(Glasgow-Blatchford Score,GBS)系統評估病人再出血風險等級,并制訂以危險評估為指導的分層護理方案[7-8]。病人轉入我科后前期GBS評分波動在8~11分,等級為中危。入科第9天病人因發生心房顫動,GBS評分≥12分,轉為高危,期間Hb最低降至45 g/L,評估病人存在隱性失血可能性大,立即啟動高危病人分層護理方案:1)采用專人負責、一對一護理模式,指導病人嚴格臥床休息,持續心電監護,每小時監測生命體征,緊急合血備血,做好應急搶救準備,早期識別意識、頭暈、腸鳴音亢進等出血征象。2)在發生出血時持續采用注射用艾司奧美拉唑鈉(耐信)8 mg/h及奧曲肽0.05 mg/h泵入,給予矛頭蝮蛇血凝酶4 IU與磷酸鋁凝膠20 g口服每隔2 h 1次交替止血,促進黏膜修復;間斷輸注懸浮紅細胞,病人皮膚損傷情況改善后及時調整激素劑量。3)精準化液體管理,實施以目標為導向的液體管理,通過血流動力學、尿量、滲出液等指標動態調整輸入液量。病人轉入后初期血鉀波動在4.0~5.0 mmol/L,出量大于入量約1 000 mL,初發心房顫動考慮與容量超負荷有關,制定目標值心率為60~100 /min,尿量≥30 mL/(kg·h);正確使用刻度尿壺及稱重儀,準確記錄尿量、滲出液及血便的量,每隔2 h統計1次出入量;使用微量泵精確控制液體入量,輸液量控制在100 mL/h;在保證組織灌注的情況下,以每天出量多于入量300~500 mL以達到負平衡。病人Hb由45 g/L升至93 g/L,心房顫動轉復后未再復發。
2.2 積極處理皮膚損傷,加速剝脫皮膚修復,預防新皮膚損傷發生
本例病人皮膚損傷主要集中在臀、后背、肩及四肢,剝脫累及的黏膜占體表面積的約50%,伴血性滲出。Braden壓力性損傷評分波動在10分(高度危險)~13分(中度危險),在預防性氣墊床基礎上使用科室自制的翻身監督卡,以大角度左側和右側臥位為主,縮短翻身間隔時間為1 h。皮膚損傷部位的護理遵循暴露療法[9]和TIME原則[10]:應用支被架減少皮膚損傷部位與被服摩擦,避免加重皮疹剝脫;按照TIME原則中的保持創面濕潤平衡原則,做好滲液有效管理,專人負責皮膚護理。采納皮膚科會診意見,應用重組牛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凝膠[11]聯合紫草油濕敷破潰處,抑菌的同時促進創面修復,每天涂抹3次,厚涂1 mm后用2層紫草油紗布覆蓋保持濕性微環境,每隔4 h更換1次,并在濕潤狀態下揭開紗布,干燥部位使用生理鹽水充分噴灑后再行揭除。病人入科15 d后皮膚損傷面積縮小至約10%,出院時皮膚損傷部位已基本愈合,無新皮膚損傷發生,住院期間未發生壓力性損傷。
2.3 感染的綜合預警護理
本例病人住院期間肺部感染明確,各種置管、高齡、骨髓功能抑制、疾病消耗、激素應用等增加了感染加重的風險,積極進行全面抗感染治療,降低感染加重是改善病人不良結局的關鍵,特制定以下護理措施。1)呼吸道管理:每小時監測病人呼吸頻率、血氧飽和度,觀察咳嗽、咳痰情況并記錄;根據痰培養藥物敏感性試驗調整抗生素,嚴格按時間間隔給藥;每隔4 h監測1次體溫,除夜間休息外,抬高床頭15°~30°;指導病人有效咳痰,霧化后翻身叩背,促進排痰,霧化器每日消毒,專人管理[12]。2)皮膚黏膜的護理:清除口腔內血痂(忌暴力),每日低溫(20 ℃)碳酸氫鈉溶液與康復新液每隔6 h 1次交替含漱,減輕黏膜炎癥反應[13];肛周作為機體隱私部位極易被忽視,此部位的感染存在隱匿性,每次排便后用非刺激性濕巾擦凈,蒙脫石散作為皮膚保護劑在肛周噴灑[14];每日評估病人肛周皮膚是否有皮膚溫度升高、干裂等感染征象。3)管路管理:病人轉入時攜帶有右頸內靜脈置管(CVC)、胃腸減壓裝置及尿管,專人負責每日評估拔管指征并提醒醫生。針對CVC周圍有少量滲血和皮屑問題,采納靜脈治療小組專家建議應用水膠體敷料代替透明敷料[15],使用碘伏消毒以降低皮膚觸痛感,增加換藥頻次為每周2次;換藥時嚴格無菌操作,揭除貼膜采取180°反折法避免皮膚二次損傷。經評估轉入科室第4天拔除胃管及尿管。4)實施保護性隔離:由于大面積表皮脫落,皮膚保護屏障缺失,因此給予病人單間安置,嚴格限制探視,陪護人員經科室感控護士指導示范,培訓合格后方可陪伴;保持病室溫濕度適宜,每日通風換氣2次,每次30 min。病人入科第13天咳嗽、咳痰情況較前緩解,SpO2波動在95%~97%,復查PCT為0.27 ng/mL,CRP為2.11 mg/dL,IL-10為5.37 pg/mL,IL-6為10.22 pg/mL,較前下降,提示感染得到一定控制。
2.4 序貫式營養支持,降低胃腸道刺激
病人轉入我科后,營養風險篩查量表(NRS-2002)評分為5分,提示有營養不良風險。成立以護士長為責任組長、中華營養專科護士為骨干的營養專科小組,負責討論并制定營養支持方案,營養目標量不低于2 450 kcal/d。入科前7 d,病人以口服腸內營養制劑聯合流質飲食為主,每天腸內營養混懸液(TPF)1 000 mL和腸內營養乳劑(瑞能)200 mL,等分為5次攝入,每天評估病人腹瀉、腹脹等胃腸不耐受情況,并由責任護士按周期反饋。病人入科第7天開始出現腹瀉,每天7~10次墨綠色稀糊便,再次經多學科會診后考慮為PD-1抑制劑相關性腸炎[16],給予布拉氏酵母菌調節腸道菌群、蒙脫石散止瀉。入科第11天,病人再次發生消化道出血,立即禁食水,給予滿足病人每日所需營養量的腸外營養液2 440 mL,包括20%脂肪乳、復方氨基酸、葡萄糖注射液,輔以谷氨酰胺保護腸道黏膜。在上述出血得到有效控制3 d后重啟序貫腸內營養支持聯合腸外營養方案[17-18],首日給予病人5%葡萄糖注射液250 mL口服,未訴不適后第2天給予短肽類營養制劑,以低劑量起始喂養(50 mL/h),每隔2 h 1次,每天增加20%目標喂養量,經過5 d完全過渡到腸內營養;營養液溫度接近體溫(36~37 ℃)[19]。入科20 d開始逐漸過渡到整蛋白型營養制劑瑞能400 mL/d聯合流質飲食,每天4~6次,少食多餐。病人出院時可半流質飲食,未再發生胃腸不耐受情況。
2.5 及時評估并促進心理康復
本例病人病程長,病情復雜,身體出現較嚴重的藥物不良反應,輾轉多家醫院和科室治療,心理負擔較重,焦慮自評量表得分為55分,提示輕度焦慮。病人入科后寡言、脾氣暴躁,缺乏信心,與家屬頻發口角,治療配合度差。采取以敘事護理為主導的全程心理護理方案[20-21],由經過專業培訓的敘事小組專科護士與病人進行多次心理訪談,每次15~30 min并做好記錄,每次訪談為病人提供隱私、安靜的環境,選擇陪護人員不在病房的時間進行心理訪談,分3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建立信任為主。第二階段進入病人故事,從困擾的問題切入。該階段發現病人有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其兒子在外地工作無法長期陪伴,嚴重缺乏安全感。基于此,護士充分調動家庭支持系統,動員其兒子每天通過電話或微信視頻方式與病人進行交流,并及時了解病人心理需求。第三階段訪談以認識現在、重建未來為主題。該階段了解到病人因皮膚潰爛嚴重影響形象而煩惱,對未來失去信心,對此醫護人員給予的護理干預是通過見證階段性進步讓其重新找到戰勝疾病的信念,責任護士每天向病人耐心解釋治療的有效性及下一步診療方案的可行性,每次換藥時拍照留存讓病人查看,增強治療信心,緩解病人的不安和焦慮。在病人住院后期焦慮評分由55分降至43分,治療依從性有所提高。
3 小結
PD-1抑制劑在惡性腫瘤的免疫治療中應用越來越廣泛,皮膚irAEs通常在治療初期出現,也可是嚴重皮膚毒性的早期表現,而繼發的消化道出血是一種危及生命的并發癥。當兩種并發癥同時出現時會使病人病情更加復雜,明顯增加護理難度。采用多學科團隊協作診療護理模式,為病人制訂個體化、精準的綜合護理方案對此類病人的疾病轉歸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有效減輕病人痛苦、預防并發癥、提高病人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