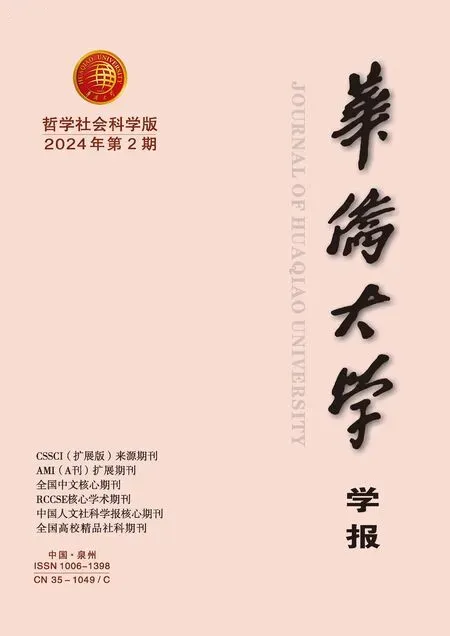重現·跨越·融合:讓共情照進歷史
——對文化類綜藝節目《典籍里的中國》的情境分析
○劉文輝 季唯可
歷史與當下總是存在著無法割舍的邏輯關聯。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克羅齊認為,“惟有當前活生生的興趣才能推動我們去尋求對于過去事實的知識;因此那種過去的事實,就其是被當前的興趣所引發出來的而言,就是在響應著一種對當前的興趣,而非對過去的興趣。”對于當下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時刻的中國人而言,克羅齊的話只說對了一半,新時代強起來的中國人其所升華的民族自豪感,不僅“推動”人們自覺地回溯悠悠五千載的風華歷史,而且還引發人們對歷史進行再認識的熱烈“興趣”。問題的關鍵是,懷揣著對歷史的“興趣”就能真正理解歷史嗎?歷史是曾經在過去的時間中出現的人、物與事,它們在博物館里,在考古遺址中,在古代文獻里,在歷史教科書中,向人們敘說著過去。然而,上述任何一種敘說難以讓今人沉浸式感受古人的情懷。不過,科林伍德認為,“歷史的知識是關于心靈在過去曾經做過什么事的知識,同時它也是在重做這件事,過去的永存性就活動在現在之中。(1)[英]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譯,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247頁。”葛兆光認為科林伍德所指稱的“關于心靈在過去曾經做過什么事”,而且“活動在現在之中”,就是幾千年來古人前赴后繼對宇宙、社會、人生問題的苦苦思索,最終形成的關于宇宙、社會、人生的觀念與方法等思想的知識,就是“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2)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頁。。借助這些思想的知識,今人可以一定程度重溫古人的思索,以及感受這些思索背后靈動的情感。遺憾的是,不得不說這種“重溫”與“感受”,卻是難以充分實現共情以及消弭歷史的隔膜感的。那么,對于歷史有“興趣”的今人來說,在歷史與當下時空的雙重錯位中,歷史如何才能打破時空界域,從古代穿梭到當下,達到與今人的共情,從而塑構古今共通的意義空間的呢?
值得關注的是,《典籍里的中國》作為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綜合頻道推出的大型文化節目,利用新興媒介技術,以場景化的時空呈現形塑了新的傳播結構,形成以人為中心、以情感為聯結的新型時空場域,使得人與傳播媒介、傳播場景得到有機融合,達到人景合一,實現古今時空的融合與統一,重構出新的時空格局。在節目中,媒介作為一種場景建構的中介物,通過多舞臺的演繹、時空對話與典讀會解說等創新形式,以“戲劇+影視化”的表現方法,在歷史空間呈現上使時空解構,讓人們能夠體會到歷史的時空環境,實現時空的交叉與跨越。在場景塑造中,人與典籍內容所共生的時空達到了同頻在場,通過媒介創造的歷史場景,給人們沉浸式的體驗,讓觀眾形成穿梭古今的觀感,以古今交融的場景變換滿足人們的時空想象,強化人們的情感共振,最終使優秀傳統文化重新浸潤人心,實現了跨圈層的傳播,引發受眾共情。由是,以“共情”透視《典籍里的中國》中媒介跨越時空的情境塑構,不僅具有學術價值,也具有現實意義。
一 共情的時空性
“共情”是指人們覺察和感知到他人的情緒與感受,并能夠基于此種感受做出類似的情緒及反應。共情這一概念的提出最初可追溯到德國哲學家勞伯特·費肖爾,后來由心理學家羅杰斯引入心理學領域。巴特森指出,共情在于能夠站在他人的立場上,感受他人的情緒。這一觀點從共情本身的特質出發,認為共情是基于個人生理機能的情緒體驗,能夠和被共情對象形成相似的情緒通路。因此,在歷史時空的重現中,共情能夠通過歷史時空的跨度呈現形成對于過去的感知,從而為情緒流動做鋪墊。
共情的運作系統十分復雜,包括心理活動、信息處理、情感表征及認知神經的作用,對內涉及人們的內在情緒與生理感知,對外則引申至社會、倫理與文化等多重維度。黃翯青和蘇彥捷認為共情貫穿于人的一生,情緒共情與生俱來,認知共情則在社會生活中得到不斷深化(3)黃翯青、蘇彥捷:《共情的畢生發展.一個雙過程的視角》,《心理發展與教育》2012年第4期,第434—441頁。。在共情理論的文化共性中,人與社會存在著本質上共通屬性,社會奠定了人類文化的審美共同性。陳蔚指出各個民族在地域、文化、習俗上各有特點,但是在藝術呈現上人們存在著相似的審美理念(4)陳蔚:《試論民族藝術審美價值的共同性》,《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第132—135頁。。曹磊、白貴指出了人類的共情基礎是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共有價值,在中國古代文化中這種共情意識依舊得到傳承(5)曹磊、白貴:《培養全球化的文明觀與“共情”的溝通能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背景下對新聞傳播教育未來的思考》,《新聞記者》2018年第2期,第31—39頁。。哈佛心理學教授斯蒂芬·平克認為,共情是人們在閱讀小說、自傳、回憶錄等時產生的角色的轉移(6)[加]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么會減少》,安雯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679頁。。如在閱讀書籍或是觀看影視作品時,受眾能夠通過其所塑造人物的經歷與情感,將穿越時空的歷史內容呈現到受眾眼前,使受眾對于歷史文化產生自我內傾反應,出現和歷史角色相似的情感變化,從而將自我情感轉移至共情對象。
在共情的跨時空融合中,共情能夠通過時空情境的塑造凝聚人們的情感,在時間流轉與空間場域中形成一致的情緒感染。于共情過程而言,巴雷特·倫納德提出了共情循環理論,將共情的產生和作用過程分為五個階段,包括共情的條件、共鳴、表達、獲得和反饋。這一共情循環模式揭示了共情機制的完整鏈路,從而在一定的時空中,情緒能夠通過傳遞與擴散,在人們生理層面與社會化層面形成一致的覺知與情感。同時,共情有利于實現人們的社會化,能夠在深層次上激發人們的社會身份和自然身份,從而使“我”變成“我們”,讓人類成為一個整體(7)郭蓓:《融合傳播時代網絡輿論引導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之踐行——基于共情理論的思考》,《現代傳播》2019年第8期,第56—59頁。。由個人變成整體的過程是人們對于自身文化身份一致性認同的過程,在歷史情境的塑構中交織情感,實現跨時空的文化認同與感知交融,進而形成歷史流動中古人與今人的跨時空情感融合。
當談論共情時,時空性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時代變遷與歷史迭代,媒介成為了重塑時空的途徑,不斷書寫著時空的經緯。“每一種新的傳播媒介都以獨特的方式操縱著時空。(8)[美]詹姆斯·羅爾:《媒介、傳播、文化——個全球性的途徑》,董洪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44頁。”時空通過媒介的塑造得以在不同的歷史進程中呈現,時空的重現可追溯至哲學時空觀和物理時空觀,哲學時空觀注重對于宇宙的探尋,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提出空間是“相對的”“有限的”,而柏拉圖則認為空間是“絕對的”“無限的”;我國古代哲學家則強調時空的同一性,認為“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變遷密不可分,兩者統一于物質的運動之中。”(9)何鎮飚、王潤:《新媒體時空觀與社會變化:時空思想史的視角》,《國際新聞界》2014年第5期,第33—47頁。時空的重現在同一性中得到了印證,跨越歷史的時空能夠通過一脈相承的同一性達成重現。
時空的跨越首先可以溯源至傳播學時空觀的源頭,其中,馬克思提出了“用時間消滅空間”觀點,認為“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10)[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頁。,表明其認識到傳播媒介對時空的影響,時空能夠通過媒介實現界限的跨越。其后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的學者哈羅德·英尼斯則正式提出了“媒介時空偏向論”,認為傳播媒介可以分為倚重時間和倚重空間兩類,導致媒介所承載的文明(文化、知識)產生時間或空間的偏向(11)[美]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1頁。。時空的跨越在麥克盧漢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的延伸,“媒介即訊息”“媒介即人的延伸”(12)[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50頁。等觀點,認為媒介影響了人們對于時空的感知,不僅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方式,還使人們的感官在時空范圍內得到了延展(13)[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第33頁。。
對于媒介時空情境的塑造,媒介環境學派代表人物梅羅維茨在吸收了英尼斯、麥克盧漢以及戈夫曼等人的觀點后提出了“媒介情境論”,他認為前人的理論對媒介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對人們日常社會生活中的情境分析缺位,無法解釋電子媒介對人們社會行為帶來的影響。而“媒介情境論”則針對現代大眾傳媒尤其是電子傳媒進行研究,其重點關注的媒介為電視,認為電子媒介跨時空情境的塑造能夠達到時空的融合。在其中,“場景”是一種信息系統,地點和媒介同為人們構筑了交往模式和社會信息傳播模式(14)[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的影響》,肖志軍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4頁。。電子媒介的出現對于人們的社會生活與行為產生了強大的影響,不再僅僅局限于媒介訊息的傳達,而是體現在電子媒介對于社會時空的重組,使得人們的心理活動與社會行為改變以適應新的社會場景。媒介技術不僅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消除了物質場景的壁壘,甚至時間和空間也一同被“簡化”,“一切地域和一切時代都成了此時此刻”(15)陳長松、蔡月亮:《技術“遮蔽”的空間:媒介環境學派“空間觀”初探》,《國際新聞界》2021年第7期,第25—42頁。。因此,具有“物質性”的地點通過媒介的情景塑造,創造了異時空同場的社會交往方式,透過媒介的情境表達帶給人們擬態場景交流。
而隨著“數字化浪潮”的掀起,數字媒介的出現更加融合了時空,使得媒介的時空偏向性朝著時空一體性方向發展(16)朱海松:《網絡的碎片化傳播:傳播的不確定性與復雜適應性》,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10年,第24頁。。在梅羅維茨看來,“電子媒介跨越了以物質場所為基礎的場景界限和定義”(17)[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的影響》,肖志軍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3頁。,電子媒介的出現打破了由“地域”構成的時空隔閡,以情境來重組、重現新的信息環境,形成了新時空的情境。其中,物理實體空間和社會場景之間的固有關系發生了變動,新的社會場景模式融合了不同的社會文化情境,使原本處于不同場景中的人們形成情感交融。情境的變化將會改變人們原先的身份和行為界限,影響其行為和社會角色(18)何夢祎:《媒介情境論:梅羅維茨傳播思想再研究》,《現代傳播》2015年第10期,第14—18頁。。因此,人們在時空情境的重現、跨越與融合中能夠感受到身份認知與情感體認的變化,進而影響其社會文化的覺知與行為。因此,媒介發展的新方式打破了以往的媒介時間偏向或空間偏向的二元維度,拓展了對媒介時空研究的新視角。
綜上可見,在媒介情境論提出之前,在對媒介的研究中,場景只是一個固定的物理概念。而梅羅維茨則在界定場景中引入了電子媒介的情境塑造,他認為:“對人們交往的性質起決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質場地本身,而是信息流動的模式。”(19)[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的影響》,第42頁。人身處的現實場景本身是固定的,相互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物質與文化區隔,但媒介情境的塑造重現改變了這一切,跨越了時空的隔閡,使社會場景得到融合重組。通過對時空的表達與轉換,媒介以特定的方式“操控”著時空,在情境中形成時空在不同向度的重現,在歷史的跨越中實現時空的融合。那么《典籍里的中國》是如何“操控”時空,以媒介構建情境,通過場景的打造實現“觸境”生“情”,從而讓典籍中的歷史與現實場域實現有機交融、古今共情呢?本文嘗試從時空重現、時空跨越以及時空融合等三個維度對其進行“共情的時空性”分析。
二 時空重現:敘事元素中的情境塑構
文化代表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其習得的行為模式、態度和物質材料的總和(20)[美]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連樹生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4頁。。《典籍里的中國》運用媒介塑構情境,通過多元的敘事元素營構場景,于多層次敘事中實現情境營構與時空重現,在舞臺場景中塑造意蘊豐富的精彩故事,呈現中華傳統典籍中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價值,使歷史文化穿梭千年實現當代的創造性轉化,在情境的表達與敘事的多維中增加了人們對于中國傳統經典的認識,達到歷史時空的重現與歷史人物的還原。
(一)復調式敘事呈塑歷史在場感
“復調”源于音樂術語,在電影作品中,它指的是在結構方法上與一種以上的敘事聲音建立一種“對話”關系的交流結構(21)李顯杰:《電影敘事學:理論和實例》,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第392頁。。《典籍中的中國》采用橫向敘事與縱向敘事雙重復調式敘事結構,橫向敘事詮釋現實與歷史雙時空的并行,打造雙重時空情境的交織,將歷史時空嵌入現實,實現時空的重現,演繹古代典籍故事,闡釋古典文學意義。縱向敘事貫穿古今,以連接橫向敘事時間節點聯通古代時空與現代時空,實現古今的交叉敘事,重演歷史時空。梅羅維茨認為“當兩個場景融合后,不再是兩個場景的簡單組合,而是常常會演化成具有統一新規則和角色的新場景”(22)[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的影響》,第41頁。,因此,復調式敘事融合了媒介的新場景,在混合場景中實現歷史與當代的重組。
在橫向敘事上,《典籍里的中國》在歷史和現實兩個時空進行平行同步敘事,在舞臺展演中以歷史場景塑構為主,由演員演繹的歷史人物詮釋中國經典創作過程,還原經典古籍原文中的人物形象,重現典籍故事;在現實呈現上,由主持人作為當代讀書人引入當代視角解讀,在場專家在典讀會與訪談間中對經典的深入分析和詮釋,在現實情境中融入古今思想的碰撞,實現當代文化意義的傳達。節目通過現場的多舞臺展演,向觀眾展示典籍的核心內涵,通過藝術化的風格演繹呈現歷史故事,實現古代時空的歷史重演,在電視媒介中構建歷史情境,再由現實時空中主持人的詮釋與專家訪談的解說相互連綴與貫穿,構成了一場復調式敘事情境展演。
在縱向敘事上,縱向的時間聯動古今,節目以古今交叉敘事實現歷史場景的重現,在重現歷史情境中搭建時空對話場,由主持人對歷史人物的介紹和典籍故事的引入,讓人們走進歷史,在節目塑造的歷史場域中,逐步進入歷史情境,理解歷史文化。節目的敘事結構是其影像呈現的獨特之處,通過跨媒介的敘事表達,運用多機位的實時拍攝剪輯,使人們沉浸于不同時空場景,塑造出多重歷史情境,將古今人物置于同頻時空中,使歷史時空在當代得以重現,從而形成古今交錯的敘事框架。這種自由變化的多視角媒介空間,讓屏幕前的觀眾產生一種沉浸式的歷史體驗感,能夠同時在不同的歷史敘事場景中切換游走,在現實中感受歷史重演的時空往復。
《典籍里的中國》中復調式敘事結構為節目影像呈現帶來了獨特展演風格,節目巧妙運用蒙太奇手法進行拼接,將多舞臺進行貫穿與融合,實現多條線索與多重時空的交織,打造別具匠心的歷史舞臺設計。如《史記》篇中,節目挖掘司馬遷的人生故事,以其為敘事核心與線索,從老年司馬遷的視角出發,回憶追溯其青年時期,在多舞臺的場域配合中,將司馬遷的精神世界徐徐鋪展。一號主舞臺呈現了青年司馬遷遍歷祖國的游歷過往,二號舞臺圍繞當代讀書人與老年司馬遷的對話展開,塑造了歷史并置場域,而三號舞臺則追溯司馬遷幼年的讀書經歷,三個舞臺分別貫穿司馬遷的一生,通過媒介情境打造出歷史場景的畫面還原,提升了影視畫面的歷史真實感。
(二)感染力敘事話語營構歷史文化情感
梅羅維茨在埃爾文·戈夫曼“擬劇論”觀點基礎之上,認為對于媒介的研究,不單單局限于媒介的傳播形式,而是要能夠使媒介情境與現實社會交往相聯系。電子媒介的發展塑造出新的社會情境,使社會文化與人們的文化角色發生了一定的改變。《典籍里的中國》將中華傳統典籍以極具感染力的大眾化方式呈現,在媒介場景的生動塑構中,使廟堂式文化逐漸走進平民文化,以通俗易懂的演繹與表達構筑感染力話語,在歷史時空的重現中聯結人們的情感。節目將典籍中的古文文本從文言文轉化為旁白解說詞、主持臺本、展演臺詞以及訪談闡釋,以現代化敘事方式實現了原始文本的精華提煉,同時融入了當代意義的流暢建構,在媒介構建的現實情境中順利轉化歷史文本,于典籍歷史時空的重構中勾連情感。
節目的敘事話語打破了歷史的文化屏障,不再拘泥于生澀死板的歷史情境,而是重構歷史時空,構建易于當代理解的現實情境,使歷史文字在當代實現“活化”。古籍中晦澀難懂的表述轉換為平民化的口吻,在舞臺展演中演員運用通俗易懂的白話,以實現故事演繹與文本的創新闡述,在歷史承接上盡力還原古時人物形象,從而在現代場景中構筑歷史。節目注重觀眾的接納性,以感染力的敘事口吻使古籍的文化壁壘得以消解,為沉浸式共情提供了話語鋪墊。例如,吳樾飾演的周武王在舞臺演繹中將書面語言轉換為白話,以人們易于理解的方式演繹了“牧野之戰”,使這一氣勢恢宏的歷史過程通過通俗化與極具感染力的表達,在舞臺空間中構建了生動的情境以承接歷史,提升了觀眾的代入感與體驗感。
敘事話語的平民化轉換也促使中國古典文學更接近公眾,通俗易懂的話語表達能夠使悠遠的文化沖破歷史隔閡,在現實情境中得到當代的創新性轉化。在強感染力的歷史場景塑造中典籍得以深入人心,形成人們對于歷史文化的情感連接。節目在訪談間的內容詮釋更進一步揭露典籍的核心思想,如點評解讀《天工開物》一書時,專家闡述天工開物的含義,指出“天工”的意義為自然的能量與職責,而“開物”則是開創萬物與成就萬物,將古文以淺顯的方式表述,在文化轉換上配合現代語境,引導觀眾有序地理解話語的意義和核心內涵,體會到由古至今傳承而來的文化精神,感受格物致知、開拓創新的科學態度。
(三)視聽敘事結合重演歷史
電子媒介使時空重組,打破了傳統固有的時間與空間觀念,媒介塑造的場景聚合了不同的群體,使人們能夠在媒介情境的打造中進入同一場域,實現媒介信息在不同群體間的傳播。影像的敘事表達是電視節目的主要輸出方式,《典籍里的中國》通過視聽敘事塑造新型歷史情境,將典籍內容進行文本的藝術化再創造,以視覺化與聽覺化呈現作為聲音和圖像表達載體,構建電視敘事的聽覺和視覺藝術,彌補文本語言的可視化表達缺位,填補文本敘事的意象空白。通過節目塑造的視聽空間,在節目舞臺上構筑了全新的歷史時空場景,對歷史故事的重演與歷史人物的還原,極大增強了觀眾的當場體驗感,強化情感共振。
節目將現代化媒介信息技術巧妙地運用于節目敘事表達,配合虛擬現實技術輔助舞臺演繹,使燈光、人物與舞臺融為一體,在視覺傳達上形成一致的風格呈現,塑構穿越千年的歷史場景。同時,臺詞、旁白、解說、背景配樂、鼓點等聽覺符號構建了舞臺展演的三維空間,形塑歷史情感氛圍。因此,畫面直觀真實的生動呈現,配合恰到好處、點到為止的背景音樂,在視聽的雙重強化感染中,時空由此流轉,歷史在舞臺上徐徐鋪展。節目深耕典籍文本,依據文本風格與意蘊搭建截然不同的敘事場景,在視覺呈現上,巧妙融合精巧的道具、變換的光影與專業的服飾等元素,實現了歷史場景的高度還原。節目運用巨型LED環幕,并且配合多舞臺布景切換時空,給人身臨其境之感,多空間的流轉使觀眾進入歷史時空情境,實現歷史的在場體驗。極具感染力與體驗感的舞臺氛圍,為典籍構建了生動的敘事畫面,實現了中華傳統文化中偉大歷史畫面的重現。
美國學者L.伯德惠斯特爾認為傳播活動中有75%的意義是通過非語言符號傳遞的(23)趙蕊、何艷、林剛:《從符號運用看文化綜藝節目的創新——以《國家寶藏》為例》,《青年記者》2018年第32期,第82—83頁。,電視節目作為視聽藝術,視覺演繹的生動亦需與舞臺演繹風格相契合的配樂襯托,才能夠真正形成視聽一體的歷史情境,營造文化意蘊濃厚的視聽氛圍。《典籍里的中國》致力于為人們打造身臨其境的歷史場景,背景音樂以古典樂為主,尤其是中國傳統古樂器,演繹風格趨于肅穆莊重,以長笛、古箏、揚琴、蕭、塤等中華傳統民樂器塑造核心背景旋律,營造古典素雅的氛圍,重現千百年前的時光,從而在素雅莊嚴的歷史情境中娓娓道來中國典籍故事。如《尚書》篇背景以黃鐘大呂為主,音律沉重而低沉,引出歷史的緩慢步伐,在牧野誓師時,背景伴隨著鐘鼓與歌聲,配合人物的莊重宣誓,營造出雄偉肅靜的氛圍。節目通過音樂設計烘托情感氛圍,在歷史場景的營構中突出古籍核心主題,呈現了大氣磅礴、大開大合的中華傳統文化意蘊,在視聽情境的搭建中實現歷史的當代重演,使觀眾得以體會中華歷史濃重的文化況味。
三 時空跨越:情境織構下的感情融通
麥克盧漢認為,媒介能夠使人們的感知得到延伸或擴展,而“沒有一種媒介具有孤立的意義和存在,任何一種媒介只有在和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實現自己的意義和存在”(24)[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第44頁。。節目通過媒介場域的構造形成古今穿梭的新型場景,通過“場景式”的歷史畫面壓縮時空距離,構建具體的歷史情境,通過古今對話與場域交融實現時空的穿梭,交錯古今,讓人們能夠在直面歷史中感受情緒的迸發與情感的碰撞。《典籍里的中國》通過古今對話實現文化重構,在時空場域的交叉下觸發情感,最后通過理性層面的跨時空讀解,在古今傳承中實現情感的融通。
(一)古今對話場域中的思想重構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認為,對話能夠在符號互動之間形成深層意義,一切受到意識觀照的人的生活都具有對話性(25)[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白春仁、顧亞鈴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16頁。。“對話場”象征著自由的交流空間,電子媒介通過改變信息獲取模式塑造新型的媒介情境,從而在情境塑造中打造古今同在的對話場域,主動消解時空隔閡,通過分離現實地點與社會場景來影響人們的文化認知,改變人們的社會行為。因此,《典籍里的中國》通過塑造跨越時空的對話場使古今思想的交流有了媒介承接,在媒介的情境交織中跨越時間長河,形成古今時空的交錯。
由于文化是基于特定的時代背景產生和發展的,古今時代的演變造成社會文化與價值觀的流變,從而古今價值觀念存在不可避免的碰撞。因此,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更需要去糟取精,通過適時的重構,在古今交錯對話中實現理解,使文化意義能夠跨越時空在當代情境中釋放價值。在《天工開物》篇中,典籍文本強調自古以來根深蒂固的重農抑商思想,但這一源來自古代社會體制的思想,已不再適應現代的社會情境。因此,在對文本內容的當代轉換中,節目在歷史情境的當代打造中注重文化創新與轉化,將典籍中“貴五谷而賤金玉”引申為重農固本思想,實現文化的跨時空重構,使傳統得以跨越時空在當代實現文化認同與理解。
節目的展演過程亦突破了時空的單線程與封閉性,讓千百年的時光交匯重疊,一改共時性的局限。節目在此的編排也別具匠心,現代造型的主持人以當代讀書人的角色融入舞臺展演,進入舞臺塑造的歷史場景中,與古時先賢對話交流,于古今思想的流通中實現時空的連接,在一來一回的溝通中聯結古今思想。雙向互動的過程,增強了人們對于古籍的理解,亦在精神層面回應了先賢的期盼,實現了古人與今人跨越時空的情感交融。《尚書》篇中,節目構建了王維名畫《伏生授經圖》這一著名場景,在舞臺上運用環幕技術構筑畫作內容,于畫作中展現歷史,再由主持人走進畫作,打破古今時空壁壘,實現不同時代的人們在同一歷史情境下的同場。主持人親身體驗伏生說書傳經,并請教伏生《書》好在哪兒,展開了一場名畫中的古今對話,給畫作外的觀眾帶來了沉浸式的歷史重現,透過媒介場景的塑造,使人們在時光流轉中感受到緩緩而至的中華傳統文化,激發了人們一脈相承的文化歸屬感,從而引導觀眾在臺上臺下、熒屏內外中感受到跨越時空的歷史場景,體會到古今交錯對話中的思想凝聚。
(二)歷史場景透視中的情感迸發
電子媒介對不同歷史時空距離的消弭往往只是被動存在的,若非仔細主動探尋,則難以找到時空的跨越據點。但《典籍里的中國》使用媒介打破了現實空間和社會場景之間的傳統關系,在電子媒介在塑構歷史場景的過程中“消解”了時空差異,運用先進技術與巧妙編排實現時空場域的跨越,實現一場主動的時空距離消弭。
在時空場域的跨越中,節目在主舞臺中央設計了一條甬道,作為兩個舞臺的連接,也寓意著古今連通的時空隧道。甬道穿梭歷史長河,連接著古今時空,使身處不同歷史時空的人物能夠在數千年的時光中自由行走,實現古今交織中的場域跨越。甬道不僅能使主持人走進歷史人物的故事,懷揣著現代問題與古人溝通求索,也能使古人能夠穿越歷史長河,走進現代,看到后人對中華文明的發揚與傳承,感受當代的文化繁榮。聯通時空的甬道,使古今交流渾然一體,在場域的連接中使人們感受到古今交融的震撼。同時,節目透過主持人視角實現時空的跨越,帶領觀眾進入節目塑造的歷史情境現場,親眼見證典籍的歷史重現。觀眾得以跟隨著主持人進入歷史進程中,和先賢一起回顧其人生歷程與命運故事,與歷史人物一同置身于歷史時空中,沉浸領略古籍意義。
在節目的鏡頭語言中,媒介的調度亦極大程度配合舞臺時空呈現,拍攝角度、景別、運鏡、畫面等都巧妙與舞臺展演的情感氛圍適配,在鏡頭下拉近時空距離,實現情感的時空跨越。鏡頭敘事上關注點的聚焦,使觀眾最大程度實現“身在其中”的在場感,拉近了觀眾與典籍之間的距離。在歷史場景的透視中,節目通過鏡頭語言的調度突出人物內心世界,調動觀眾情緒,如《楚辭》篇中,當主持人以當代讀書人的角色為屈原帶來2000年后的柑橘時,節目拉近鏡頭,聚焦于屈原的臉部表情,挖掘其內心情感,在演員演繹與鏡頭轉換中,凸顯了屈原對家鄉的思念之情,使屏幕外的觀眾能夠切身體會屈原對家鄉的懷念,鏡頭語言為觀眾提供了沉浸的情感代入。因此,節目鏡頭語言的運用使敘事畫面有了聚焦點,從而觀眾視線與情感能夠跟隨畫面講述而起伏,實現觀者的沉浸式共情。
在畫面上,節目還巧妙地運用時空對望來實現歷史時空的跨越,將舞臺表演與歷史背景縫合,通過鏡子透視古今,以完備的視聽技術和剪輯拼接呈現美輪美奐的畫面效果,將古今的直觀流動呈現在人們眼前,極大提升了人們代入感與體驗感,促進情感的瞬時迸發。節目舞臺展演前,以后臺中角色古今對望作為導入,演員本人與其飾演的古代先賢站在同一面鏡子前,千百年的目光得以穿越古今實現交織。在鏡頭的無縫拼接下,運用媒介打造轉場的自然流暢,演員透過鏡子窺見古代先賢,看到其從青年到老年的轉變,在同一位置下塑造了古今穿梭的驚奇感,使觀眾感受到超越客觀戲劇舞臺的超時空體驗。如《傳習錄》篇中,演員辛柏青站在鏡子前,與鏡中自己飾演的王陽明對望,實現演員即角色的融合,相隔百年的對拜更使演員與古人有了情感的同頻,亦使觀眾在沉浸式的古今情境交匯中體會到今人對先賢的崇敬與尊重。
(三)文本解讀中的歷史情境詮釋
舞臺展演作為第一現場,為典籍的可視化呈現和藝術化表達提供載體,而典讀會與訪談間作為第二現場,以學者與參演者的對話實現古籍內容的理性釋義,在穿越時空的歷史表達中使典籍的深層意涵得到更加豐富的詮釋。演員的導入與專家學者的點評,為歷史情境做了完備的詮釋,豐富了古籍的文本意義,為典籍內容的跨時空理解做了深度的探索。通過對歷史典籍的解讀,在文本內涵和文化價值的闡述中,融入當代思想與社會時代主題,能夠有力實現傳統價值的現代轉換與當代詮釋,在歷史場景構建的時空中跨越古今、融合思想,為古籍的當代理解提供新的視角,促使典籍內容在時空的跨越中得到完備的詮釋。
梅羅維茨將情境比喻成“信息系統”,以媒介塑造出擬態交流場景。節目將典讀會作為客觀引入,形成理性的擬態交流與文本分析場域,在專家解析與主創團隊配合中,“抽絲剝繭”對歷史情境進行解讀,明確古籍主線與角色特性,使演員在進入角色之前,能夠對古籍的文本意義和精神蘊含有深入體會,達到與角色身份認同和情感融合上的同頻,在思想連通中對先賢形成跨越時空的情感共鳴,為展演做出情感鋪墊。訪談間作為舞臺展演后的詮釋,以“專家訪談”的形式對古籍內容與歷史先賢進行文本和人物剖析,以更加客觀、理性的角度剖析故事內核,解讀歷史背景,建構全面且豐富的歷史情境,填補場景構建帶來的意義空缺,幫助受眾在感受舞臺演繹基礎之上充分了解人物的思想內核,使典籍的文化價值能夠在跨時空的傳達中得到精確的解讀。如專家們闡述《孫子兵法》的當代價值與歷史意義,表明中華民族珍愛和平、以和為貴的傳統思想,也表達中華人民不懼怕戰爭的勇敢精神,進一步激發觀眾的愛國熱情,調動觀眾感情,強化國家與民族認同。
訪談間的解讀彌補了舞臺展演場景中深層意義空缺,使舞臺上立體鮮活的視覺形態回歸理性的文本解讀,致力于挖掘典籍中傳達出崇高的民族精神,通過觀眾個體的情感波動,喚醒深厚的文化認同,使人們的靈魂受到文化洗禮,體會到文化精神的傳承。如司馬遷著《史記》,遭受腐刑法,忍辱負重,節目訪談突出其憑借著毅力完成著書的經歷,使人們感受道其剛健自強、永不放棄的精神光輝;《齊民要術》篇中訪談以“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點明典籍主旨,聚焦于賈思勰對于后代都能夠“吃得起吃得飽”的天下富足追求,詮釋著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在跨越時空的文化價值傳達中,觀眾得以深入體會中華歷史的情感認同,感受中華典籍經世致用的文化精神,在時空的跨越中實現文化的回歸。
因此,節目第二現場對于古籍的闡述與解讀,強化了古籍的文學魅力,幫助以理性對話深層次地分析古籍的價值內涵,使典籍能夠在跨越時空在當代得到意義的精確還原,在跨時空詮釋中實現價值的升華。
四 時空融合:共通情境下的情感升華
文化空間超越了具象的地域空間,包括了文化參與生成的價值判斷(26)李鵬飛:《文化空間再造——新媒體非物質文化遺產紀錄片的媒介傳播與文化傳承》,《文化藝術研究》2018年第4期,第1—6頁。。電子媒介能夠融合了不同的情境,在異質的時空中創造出同一的文化場域,形成共通的歷史情境,打破了印刷時代的文化地域化,融合了不同社會背景的觀眾。《典籍里的中國》創造了一個極具感染力的文化表達場域,為故事中的古人和現代敘述者打造了思想交匯的共通情境空間。以典籍為核心主軸,將中華傳統文化和中國當代思想進行融合,使典籍從具象的文本信息由藝術化表達轉變為形象的舞臺展演,在媒體技術的加持下,使舞臺場景成為古代和現代交匯的文化意義空間。節目通過文化空間的塑造,在真實的舞臺場域與節目場景中塑造了源于歷史的文化空間,于真實中融入抽象與虛擬,使文化意蘊與文學精髓得以煥發生機,在文化的共通意義下打造古今交融的擬真情境,凝聚共同的文化價值與人文情感。
(一)歷史時空交融的意義呈構
媒介對社會環境中的社會行為與文化都產生了影響,電子媒介為社會塑造了新型的信息系統。人們也對媒介環境有了新的理解,當人們試圖理解一個社會場景時,需要以特定的情景與信息為依據。歷史是時代的產物,雖然存在于一定的歷史空間中,歷史記憶卻能夠通過歷史場景的再現被喚醒,在媒介的觸發下,歷史場景依憑媒介對于信息系統與技術的整合,使情境在不同時空下得以交融。《典籍里的中國》運用環幕技術、虛擬現實、道具布景與舞臺展演等將歷史故事在藝術拍攝技術中形象地呈現出來,在鏡頭拼貼與巧妙的剪切技術加持下,極大程度還原了歷史場景,呈現歷史時空情境,為古今時空交融做媒介鋪墊。雖然歷史早已過去,歷史故事淹沒于時間長河,但在節目的媒介化呈現下,舞臺空間作為歷史空間的承載,歷史情境的呈現能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情感與歷史記憶,喚醒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在時空的交融中實現歷史文化意義的解讀,使人們能夠對歷史產生一致情感共鳴。
戲劇敘事情境的即時性使典籍實現了歷史文化的當代“活化”,古今時空的交融中,典籍內的文字得到栩栩如生地展現,一脈相承的歷史文化記憶使人們形成了對同一歷史情境的共通感知。在視聽作品敘事中,通過特定歷史空間的建構可以完成特定歷史場域中不同人物角色權利關系的建構(27)范玉明、楊曉茹:《文化類電視綜藝節目敘事空間的多重建構》,《電影評介》2020年第21期,第97—100頁,。節目以主人公的時代作為歷史淵源,錨定到過去和未來的兩個歷史尺度,帶著觀眾走進歷史長河中,從過去向當代流淌,在古今的流動中實現時空交融。在其中,節目創造了異質的圖像空間,不同于現實空間的呈現,通過構造虛擬場景重塑人們對于歷史空間的想象與認知,在虛擬歷史場域的交融中觸發歷史文化記憶與情結。
《典籍里的中國》以多時空作為場景塑造的亮點,通過虛擬異質空間的構造形成時空交融的歷史呈現,滿足了觀眾的時空想象力,同時在多時空場域的共存中,最大限度地激發了觀眾的歷史記憶。如《本草綱目》篇中同時展現了李時珍幼年、少年與青年的三個時期,不同時空的交融為觀眾展示了李時珍的一生,將同一時間線上的三個歷史時空場景統一展演,以李時珍的成為醫者的偉大志向和堅毅意愿為核心貫穿,在多舞臺的同時呈現中,展示其終其一生的人生追求,使人們對于歷史人物的文化意義有了深入感受。節目通過舞臺構造歷史空間,在古今交錯的場景建構中實現歷史時空的融合,于虛構的歷史情境和真實的演繹空間中呈現古今流淌之美感。
同時,節目的融合時空的意義塑造有利于提升觀眾的文化自信,在歷史與當代的交融中呈現中華文明的恢弘氣勢,使人們感受到中華民族文化中家國一體的認同價值。節目將個人敘事作為節目實現宏觀敘事與線性敘事的切入點,聚焦于典籍人物自我身份的建構,使個人敘事被投射到國家敘事的高度,幫助觀眾從個體視角尋求人物共性。在古今交融中模糊了時代背景,突出個人的身份認同,實現觀眾文化身份的喚醒。如《史記》篇中,對于“華夏為何一體?華夏自古就是一體”的古今問答,塑造了家國一體的文化情感與歷史認知,通過對于《禹貢》“茫茫禹跡,劃為九州”的大一統盛景的塑造,《五帝本紀》中炎黃合體、諸侯賓從的大同天下夢描繪,建構炎黃子孫的情感認知和民族身份認同。
(二)古今情境交融的共通文化
波茲曼認為“媒介對于文化的精神重心和物質重心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媒介能夠決定了文化信息的內容與表現形式,從而影響受眾的價值觀(28)高金萍:《西方電視傳播理論評析》,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2頁。。節目在文化空間的塑造上,聚焦于中華傳統經典文化,塑造出古今共通的歷史情境,以典籍為文本核心進行創作,致力于挖掘典籍的文化意義,探究其時代精神。節目基于觀眾共通的文化意義空間進行考量,尊重不同觀眾的認知水平和認知層次,將典籍的晦澀文本通過影像畫面進行傳達,運用當代理解邏輯來詮釋傳統的語言規則。通過歷史故事的戲劇化情節呈現,消解歷史傳統的壁壘,構建古今交融的現實場景,以淡化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理解壁壘與障礙。節目最終通過情境演繹賦予了人物血肉,使人們于角色中窺見古代先哲,在古今交匯的思想碰撞中探尋共通的文化價值,對典籍的文化內涵有深入的理解與情感滿足。
文化空間的塑造不僅在于突出傳統文化價值,更能夠結合當代核心思想,在古今交融的情景塑造中體會共通的文化意義,由今憶古,牽引當代觀眾的共通情感與文化記憶,于當今的價值思想體系中找尋傳統價值,增強文化認同。在《永樂大典》篇中,陳濟需對被燒毀的“師”字冊進行補撰,其圍繞著“師”發散思維,引發人們對于“師”的思考,在立志與悟道的啟發中,探索出“以苦為師”“道德為師”“萬物為師”的思想境界,將“師”的概念進行多維度擴展,從不同維度表明中華民族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使人們深切感受到中華傳統“以師為范”的美德,作為經久不衰的價值導向,在古今交融的文化背景下,加深觀眾對于立德樹人、教書育人的師德情懷的感觸。
《典籍里的中國》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當代呈現與創造轉換的過程中,始終秉持與時代同步,將當代疑惑與現世價值融入節目的文化傳播中,在現實空間的互動中以古喻今,于古籍中挖掘當代意義與文化價值。中華傳統文化價值在如今依舊熠熠生輝,能夠在時代的傳承中不斷浸潤人心,歷史傳統文化價值在古今情境交融中,更能探尋到同根同源的文化意義。如老子“上善若水,澤被萬物”的人生處世哲理,是中華民族的性格根基,是中華子孫代代相傳的處世智慧;李時珍作為醫者的“身如逆流船,心比鐵石堅,至死不怕難”的醫者仁心大愛,是當今醫者的精神榜樣;屈原“矢志不移,不斷求索”的堅定信仰與精神,是國人不斷探索真理的精神指標;更有王陽明“知行合一,心向光明”的生活原則,讓人們悟出現世生活的人生意義。
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的傳承,在節目的媒介塑造與歷史場景呈現中勾連了共通的文化價值,在古今順承的歷史情境中喚醒了人們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記憶,激發人們作為華夏兒女的民族自豪。節目通過歷史時空的交融構筑了共通的文化情境,實現對歷史文化的詢喚,使人們窺見輝煌的歷史文明與恒久的文化意義,使典籍在當代綻放別樣的文化光彩。
(三)歷史情境的同頻心理情感
心理空間以具象的物質空間為基礎,通過客觀實在的物質背景作為鋪墊,形成自身的心理感受與情感通路。電子媒介能夠聚合多種視聽形象塑造虛擬場景,面向不同的受眾群體實現信息的同頻共享。在由媒介所介入與建構的新型情境中,歷史能夠實現與當代的交融,重塑人們對場景的感知,使人們能夠在交融情境中產生一致的情感震動。
《典籍里的中國》借助電子媒介對演播廳的場景進行捕捉與記錄,以現實客觀場景架構出虛擬歷史時空,在熒屏上實現歷史與當代時空的交融,典籍內容得以抽象化展示,引發人們的內心活動變化與情感觸發,通過鏡頭敘事語言的表達塑造身臨其境的歷史情境,在時空的交融中形成與歷史人物異地同場的感受體會與心理共鳴。從而節目借助情感在觀眾的心理空間內重組歷史時空,促使心理空間與歷史空間交融,使人們能夠產生感同身受的情緒感知。一定的情感意義被觀眾接受并且內化為自身情緒與認知后,在媒介構筑的沉浸式的歷史情境中,更能深切體會到交融時空下同頻的情感認同,將傳統文化內容轉變為自身的內在文化記憶,為文化認同的加深做了心理鋪墊。
歷史情境要能夠真正深入內心情感,也需要在心理空間賦能。節目首先聚焦于喚醒文化歸屬感,激發典籍文化內容與觀眾同根同源的歷史情感,于歷史時空交融中傳承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積淀。通過打造沉浸式的舞臺場景區域,交織歷史與現實時空情境,引發觀眾情感共振。現場的舞臺演繹是對文本的藝術化影像轉換,對文本的內容進行意義建構與文化傳達,構筑了虛實相生的歷史與現代雙重時空,融合情境。多空間的轉換給人身臨其境之感,進入現實中的歷史文化情境,實現歷史的在場體驗。
同時節目通過典籍故事的核心主題打造與概念呈現,調動觀眾情緒,營造由今憶古的場景氛圍,在時空呈現上貫通古今,滿足觀眾共通的情感體驗,在極具感染力的情境演繹中與舞臺角色實現同頻感知。節目從先賢自身的領悟與精神力量的指引中進行切入,在情感敘事中呈現四兩撥千斤的提點之恩,舞臺的場景呈現中構建先賢頓悟的點睛之筆,塑造大道至簡、融會貫通的思想幻境。其中,屈原對于彭杰大夫的崇敬、老子與先賢商湯的思想交談、王陽明龍場悟道時腦海中的智者的問答等,都塑造了對于自身精神世界與理性境界探尋的求道者形象。節目將這一幕幕停留在腦海中的想象幻境借由媒介展示,向觀眾展示了先賢的思想境界,揭露了他們的精神支撐與情感來源,在歷史情境的交融中加強古今思想的連通,使觀眾在探尋先哲的內心世界的同時亦能夠學會向內求,深入理解歷史文化的意蘊與精髓,實現與先賢思想的交織,探索自身豐富的心理世界,達到自身的情感滿足。
文化典籍是歷史文明的結晶,對于文化的領略不應只停留在典籍中隨手翻過的一頁,對于文明的感知也不應只駐足于過去的時空,典籍中的一頁可能蘊藏著歷史人物波瀾壯闊的一生,過去的時空中亦流淌著中華上下五千年經久不衰的歷史文明,記錄著中華民族跌宕起伏的偉大來路。因此,讓歷史時空得以在當代生動重現,使中華文化穿越時空煥發光彩,是《典籍里的中國》對典籍文本的視覺化與藝術化的探索。其通過媒介技術筑構了聯通古今的橋梁,塑構了虛實相生的歷史情境,將典籍轉化為生動的戲劇故事,使歷史流轉呈現于展演舞臺,使“情”與“境”在媒介加持下實現互構,最終寓情于境,境中生情。節目展現了史詩迭代,跨越時空塑造貫通一體的歷史情境,使觀眾沉浸其中、感同身受,催生中華血脈里的文化覺醒,激發出共通價值下的情感體驗。在歷史場景下的當代敘事傳達中,透過時空場域交叉與情境打造,讓人們體會到穿梭時空的情緒流動,最終在同一歷史情境的意義空間中領略古今文化交融,喚醒人們共通的文化感知,形成同一血脈傳承下的情感凝聚。
不過,《典籍里的中國》在“共情”建構上存在問題也是顯在的,諸如部分戲劇化的表達過度煽情、過于形式化、套路化以及說教意味濃重等,過猶不及,這是節目在以后的制作中需要努力修正的方向。同時由于節目播放仍在不斷更新,“共情”如何在后繼的節目里繼續跨越時空、浸入人心,還需要跟進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