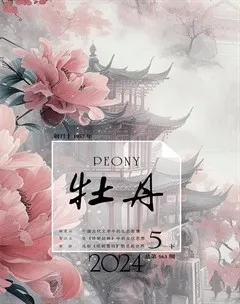王躍文小說《漫水》的結構主義二元對立解讀
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的鄉土文學一直都在直面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實際問題,許多作家紛紛在他們的作品中呈現鄉村世界被現代化力量所沖擊的圖景,包括村民的背井離鄉、土地田園的荒廢、農村老人的老無所依、村民的窮困孤獨,以及道德人性的扭曲。作家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展示了中國鄉村在現代轉型和全球化進程中所承受的代價,揭示了那些過去理想化、宛如田園牧歌般的鄉土世界正岌岌可危。
《漫水》曾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小說以淳樸生動的鄉土語言延續了自沈從文以來的湖南鄉土小說的傳統,并表達了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真善美品質的贊美,描繪鄉村美好的人情人性,通過獨特的敘事手法,展現了鄉村世界的變遷,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對歷史的深刻洞察與反思。在鄉村世界日漸消逝的背景下,作家的鄉土敘事呈現出一種峻急和嚴酷的歷史感受,這種感受不僅揭示了鄉村世界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挑戰和困境,也反映了作者對傳統文化的懷念和對未來發展的擔憂。二元對立是結構主義的核心要素,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結構主義文論家們繼承和發展了二元對立的原則,借助索緒爾的二元對立語言理論原則,闡釋了二元對立應用于分析文學的可行性,并試圖探索組成文學文本的成分結構以及支配文學文本的深層的普遍規律,列維-斯特勞斯、羅蘭·巴特、格雷馬斯等結構主義文論家從不同角度對二元對立原則進行了具體的闡釋,將二元對立原則應用在文本批評中,豐富了文學批評的方式和方法,為作家的創作實踐提供了豐厚的理論基礎,為讀者分析文本提供了新的視野。國內也有學者論證了結構主義二元對立原則應用于文學批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通過閱讀《漫水》,可以發現小說中存在許多對立的元素和結構,這些對立結構成為學者解讀文本的關鍵。
一、《漫水》主題的二元對立
在《漫水》中,生死議題構成了漫水人日常生活的核心主題,頻繁出現在諸如預備壽衣、建造棺木、接生、尸體化妝、喪葬儀式以及吹奏笛子等生活場景中。這些循環出現的儀式和事件,絕大多數與生命的起點和終點緊密相連,反映出漫水人對生死的獨特看法——一種既向死而生又坦然敬重的生命哲學。通過對生與死的不斷重述,作品展現了漫水人對生命循環的深刻理解和對死亡的超然態度,從而構成《漫水》作品中的重要主題。余公公便經常用一種哲理深刻的話語來表達這種看法,“蟲老一日,人老一年。人一世,蟲一生,都是一回事”。余公公把人的一生和蟲的一生相比,透露出一種“天上一日,人間千年”的從容與智慧。漫水人常說:“你爭贏了又算老幾?都要到太平垴去的!”漫水人對逝者的最后儀式同樣表現出極高的尊重,慧娘娘在為秋阿婆化妝時,每一個細節都做到精益求精,水溫的調節都恰到好處,她堅信“死者為大”,對待逝者的態度應與生者無異。余公公在制作秋阿婆的壽屋(棺材)時,同樣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從木材的挑選到最后的涂漆,每一步都親力親為,這些復雜的儀式不僅代表了生者對逝者的告別,更是對逝者生前給予的幫助和關愛的感恩表達。在漫水人的世界觀中,無論生死,生命都在不斷地前行,邁向新的階段。
漫水人對生死保持著敬畏與平和的態度。余公公對漫水的自然景觀和生物了如指掌,在余公公眼中,不論是山川、江河,還是動物,都展現著蓬勃的生命力,他熟知每塊石頭下藏著的蛐蛐,后山荊棘叢中的菌類和蕨菜。他常與養的小狗進行家常對話,就像和一個人正常對話般,仿佛它就是人類,顯示了人與自然間的深刻聯系。余公公通過與動植物的感知和交流,建立起一種超越語言的默契,體現了他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親密關系。而慧娘娘更是被視為觀世音菩薩般的存在,她年輕時憑借所學的文化知識成為赤腳醫生,為村民看病接生,漫水村里凡是四十歲以上村民的生辰八字,慧娘娘每個都記在心里。當漫水的尸妝老人去世后,慧娘娘主動擔起尸妝的任務。面對丈夫的不解,她反問:“做事都要有好處嗎?日頭照在地上,日頭有什么好處呢?雨落在地上,雨有什么好處呢?”慧娘娘的行動體現了她對生死的深刻理解:生與死同等重要,應平等對待。
漫水村的空間布局也巧妙地融入了生死循環的主題,太陽的東升西落象征著生命的循環,宛如生命的輪回,昭示著生與死的交替,而西邊的山脈,則與死亡的陰影相連,暗示著生命的終結,漫水的“太平垴”是深山中的靜謐之地,成為漫水人祖先的安息之所,他們長眠于深山的墳墓中,為這片土地增添了一份莊重與肅穆。慧娘娘的去世,更是將這一生死主題推向了高潮,在她離世的那一刻,山頂上飄起了七彩祥云,火紅的飛龍駕起她的靈魂。“七彩祥云”和“火紅飛龍”的傳說以及神話景象,不僅增添了神秘的美感,也緩和了死亡的氣氛,作者以豁達和坦然的方式,消解了死亡的沉重,傳達了深刻的哲學理念:生命與死亡是相輔相成的,我們應該以開放的心態接受它們。
二、《漫水》人物的二元對立
《漫水》在塑造鄉土理想世界的同時,對現代化進程中都市文明進行了深刻的審美現代性批判,這種批判深入反思了現代化對人性、道德和靈魂等精神領域的影響,《漫水》中既表達了對真善美的余公公和慧娘娘的贊美,也表達了對造謠生事的秋玉婆和人性扭曲、利欲熏心的強坨的不滿。
秋玉婆是漫水村出了名的長舌婦,以搬弄是非為樂,她的狹隘和愚蠢使她成為村民眼中的“討死萬人嫌”。村民們常說,“講是非多的人遭雷打”。她最終在喝酒時突發疾病,遭雷擊而亡。在現代化進程中,人們雖享受物質進步,卻也被異化為金錢的奴隸。強坨懶惰、不思進取,與外人合伙偷走并賣掉龍頭杠,因貪婪而背叛了村民的信仰,破壞了傳統。作者批判了強坨為私利賣掉傳統龍頭杠的行為,展現了他因受現代物質文明影響而道德淪喪。
余公公是作者塑造的一位理想人物,德高望重,多才多藝,深受村民敬仰。他寬容對待愛散播謠言的秋玉婆,秋玉婆逝世時他毫不猶豫地鋸下自己屋內的木材,通宵為她割一副老屋,還不收取工錢。他正直堅定,毫不畏懼權勢,面對“綠干部”的非議與強勢,勇敢地與其對抗,上去呵責:“我們不犯王法,你那家伙就是坨爛鐵!”他無私而公正,是非分明,當聽說摯友的兒子強坨打算出售全村代代相傳的龍頭杠時,他義憤填膺,面對強坨堅持要賣龍頭杠并提出以十副龍頭杠的價錢來賠償時,他怒火中燒,揚起手就要打強坨。余公公在當地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展現了湘西大地熏陶下淳樸民性的柔韌和剛健,體現了共通的道德品質,蘊含了深厚的民間智慧。
慧娘娘是作者塑造的另一位理想人物,她美麗、賢惠、勤勞、忠誠,雖曾遭遇不幸,但內心依然善良。她嫁入漫水村后,以堅韌和熱情服務村民,既是接生婆也是送終者。她的善行體現了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和高尚境界。在她無女送終之時,眾多受她恩惠的婦女悲痛哭泣。她去世時,山頂的七彩祥云和火紅飛龍象征著她的靈魂升天,反映了她生前的善良與崇高品質。慧娘娘有著一顆滾燙愛人的心,她平凡又偉大的舉動無不閃爍著中國傳統女性的賢良品德和崇高的境界。
余公公和慧娘娘無私無悔的奉獻滲透著人性美好的光輝,他們的行為彰顯了中國文化傳統所具備的價值理念,他們的善行與重利輕義的強坨等人形成鮮明的對比,凸顯了道德底線和情感紐帶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他們的存在,作家才能夠在作品中寄托對愛與美的生命理想,并將這種美好精神傳達給讀者。
三、《漫水》背景的二元對立
《漫水》刻畫了現代文明沖擊下的中國傳統農村——漫水村,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和倫理秩序經歷了深刻的變遷,作者在構建理想化的鄉村生活圖景的同時,展現了城鄉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緊張關系,并表達了對鄉村文明遭受侵蝕的深切憂慮。隨著新式磚房的興起、老木屋的逐漸消失,建設新農村的年輕勞動力的大量外流,以及鄉村的倫理和秩序維護者——如慧娘娘的逝世和余公公的老去,傳統鄉村的存續和守護問題成為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議題:傳統鄉村的家園應當如何保護?
自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的城鎮化步伐顯著加速,并日益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之中。進入21世紀,鄉土文學以更為尖銳的筆觸揭示了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中國鄉村面臨的現實困境。漫水村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經歷了土地改革、市場經濟改革等一系列事件,這些事件在塑造漫水村的歷史發展軌跡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特別是作為傳統和權力象征的龍頭杠的丟失,不僅象征著漫水村鄉村文明的危機,而且暗示了本土文明的脆弱性。在漫水村民心中,龍頭杠是民俗文化的精髓,維系著村莊的傳統命脈,而強坨偷龍頭杠這一細節意味著漫水的本土文明正岌岌可危,即便表面上村民生活似乎無憂無慮、自由自在,但漫水村仍難以抵擋現代化浪潮的沖擊。漫水村詩意地映射出一個文明世界,同時揭示了人才流失和貧困的嚴峻現實。隨著科技進步、城鎮化和全球化的沖擊,鄉村生活方式、傳統價值觀和社區凝聚力面臨空前的挑戰。例如:強坨妻子的出走象征著鄉村青年和勞動力的外流,以及鄉村居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強坨每天在窯上替人做磚,掙取微薄的收入,常常早出晚歸,卻還是連替他父母造棺材的能力都沒有,揭示了經濟困境對鄉村居民的影響。就連漫水村的外觀也日益現代化,在田壟中的村子里,所有的房屋都是兩三層的磚屋。余公公回憶過去,每家每戶都是木屋,能看見“炊煙慢慢升到天上去”。而現在,隨著現代城市的帶動,村莊迅速變遷,由傳統的木屋逐漸演變為現代化的磚屋,家家戶戶都換成了現代磚屋,漫水村景觀的現代化轉變進一步標志著鄉村傳統文化的衰落。余公公對自己木屋的堅守,以及鄉村日常生活的變化,如“村子不像往日熱鬧,青壯年都出遠門掙活錢”,反映了現代城市發展對鄉村文化和傳統的沖擊。慧娘娘的孫輩也離開村莊到南方工作,這些現象共同指向一個現實:隨著年輕人的離去,鄉村的凝聚力和傳統價值觀正逐漸消解。
總之,不論是龍頭杠的失蹤、慧娘娘的去世還是余公公的日益衰老,均映射出漫水村理想化的田園生活背后的悲劇。這些事件不僅揭示了漫水村代表的鄉村文明難以抵抗現代文明的侵蝕,而且表明了鄉土倫理所蘊含的淳樸和集體主義價值觀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衰退。這些變化預示著鄉土世界在現代化力量的沖擊下,正面臨著分裂和解體的
宿命。
四、結語
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分析法對于深入分析《漫水》的深層意義具有重要作用,《漫水》通過“二元對立”的結構展現了生與死、善與惡、傳統與現代等主題沖突,突出了余公公和慧娘娘等人樸實的信念與處世原則,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價值理念和美好品質,這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轉型至關重要。盡管結構主義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但它為文本解讀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有效工具。
(貴州民族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楊洋(1998—),女,布依族,貴州黔南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責任編輯 ? 黃蕾
——評《中國現代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