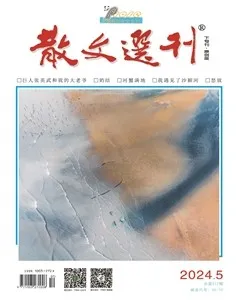摸魚蟲的女人
泥馬度
天已經冷了。北海和頤和園的水或已結了冰。那個女人還在河里摸魚蟲。她也不知道這水為何不封凌。她摸過一座座橋底,頭頂上的車流人流如水。
她摸著這微微流動的大河的底部,就像家鄉犁鏵插入泥底,掀起小小的波瀾,土浪或水花。在河流里,難道只有人和魚蟲沒有冬眠?河水最深處不能沒過一個女人的膝蓋。流水不能淹過一個女人的手臂,時間悄無聲息地流過她的指尖。她手掌沒有一條魚會醒來。這是一條正在死去或正在誕生的河流,仿佛萬物流淌如斯。
水就像夏天大雨下在地面上的車轍那樣深淺。這仿佛是從黑夜下來的雨水,幾年前它的氣味,就像一位焦黑高燒的老頭,暴躁得不讓人近前。塵土布滿水面,就像夕陽鋪在河面上一樣。
這夜皮色的水,遙遙大運河的開頭部分。她摸的是魚蟲嗎?岸上沒有人的眼會看見。魚蟲,只有小小金魚的眼,在岸上才能瞅見。她把摸到的魚蟲賣給養金魚的人,金魚和她都得以溫飽。她像在丈量流水和每一寸的河流仍然隱含的心底。
她坐在水里休息,就像坐于田間地頭歇一會兒。她看不見泥土。她在這樣的深處,平地很高了。她摸不著一片溫暖的泥土。磚和石板穿嚴了河身。光滑而不會下陷的河,平靜而不會激情四溢的河。一條汁水枯萎的河,晃過正值生育高峰期的女人,這是它所見的生,她的影子像一條娃娃魚,游得很慢,在她的旁邊。
平靜的水流,像一種漫長的憂傷,她永不會摸到它的盡頭。一位母親摸著孩子發燒而黑枯的額頭,把她喚回人間。一條再也不會暴怒的河,但它的眸里有太多的陰影,像黑夜無月的心地。她在期待著魚蟲。河流用魚蟲在期待著她。河流仍在哺育著她。
你看岸多么高遠。你看大地就是高原。那一塊大磚石砌的河床,就是水家族的墻,多么像敦煌。一個女人在夜色中,白天已被摸到了盡頭。她坐在水中恍若入夢。
敲開一塊大磚的門,里邊的好像都是人家或仙家、水族的家園。水的女兒在舞蹈,白龍在戀愛,有水族河家的寶貝在閃閃發光。這不是一條通向美麗的南方,流向東海之濱的大河嗎?它把北方游玩到南方,又把南方運到北地。這汪沛的水,神奇的水,流到哪里哪里亮。把村莊流成都市,把都市連成流水。水中漂過多少美人、花朵與春風和雪花。
多少次她站在岸上,高高的地平線讓她陡生要縱身或失身跳落下去的念頭,而今她能緩緩地,甚至是拾階而下,來到河深的盡頭,而又能沿級而上,回到人間。
夜幕已落下,一個女人還沒有上岸。她像一條魚尾人坐在河里,在河中彎腰,就像詩經時代刈麥的女人。現在生命和果實只有微粒樣魚蟲觸摸她的雙手和心靈。
白天她把生活帶入河中,黑了又要把它背上去。現在她坐于水中,任黑暗漫過臉頰。生活被擱在上邊了。
地像閃開一道漫長的深縫,把她接納在里面。這是不是接近地獄的深處?
有過多少船沉在她坐的地方?有多少財貨像黑魚潛入泥底?有多少人命在岸邊拉纖——那些和瓊花一樣漂亮的少男少女。激情與狂暴的河流。暴漲的時間與人性和物性的波濤駭地。現在它就像一連串的傷口綿延。財富和游樂另有道路。
河底的石磚像狹長的棺蓋,蓋住了地口和往事。那個像金魚一樣可愛的小妹妹,不就在一個夏天里落入這條河再也沒有回來嗎?現在她在哪里了呢?河流像瘋狂的車道,帶走無數人的生命。寸草不生的河底,冰冷的河底,遮住了生也擋住了死。她摸不到一道縫隙。她不知道掀開一塊石板,會摸到什么,什么會出現。一個洞穴?一條魚的骨架?一條蛇的言語?
她仿佛聽到一種凄愴的聲音在喊——河水開門,河水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