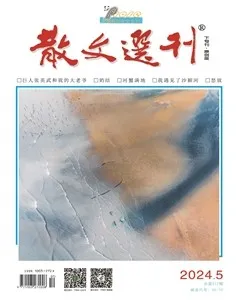迎婿日
孔慶貴

大年初二,是一個重要日子,被稱為“迎婿日”。在這一天,已婚的女兒會帶著丈夫和孩子們,拎著豐厚的禮物,回娘家拜年。
妻子的老家離我們工作、生活的城市約有110 公里的路程,得用2 個時辰才能抵達。這一路程包括兩段:一段是從我們工作的城市到妻子家的縣城,約95 公里;另一段15 公里就是從縣城到妻子老家,確實很遠。
初二的清晨,天剛蒙蒙亮,我和妻子便早早起床,拎著大包小包的禮物,在家屬院的門口上了一輛人力三輪車。蹬三輪車的是位年齡稍長的大爺,和他講好1 元錢的車費,就直奔汽車總站而去。要不是我們帶的東西多,不到三里地的路程,我連1 元錢也不舍得花,直接跑步過去。三輪車由于承載著我和妻子還有一大堆禮物,有種負重前行的感覺,大爺的雙腳輪換用力向下踏去一次,車身就會發出“咯吱咯吱”的響動,像要散架,痛苦地呻吟著。
到達汽車總站,偌大的大廳內乘客不多,在去往妻子老家的進站口排有五六個人,其他幾個站口也大抵如此,檢票員一臉嚴肅狀,周圍等車人的身邊和我們一樣,放著大包小包的禮物,看來也像是回娘家的。檢票、上車,一切安排停當,司機就開始啟動汽車。檢票員再次檢查了一遍車上乘客的車票,就示意司機師傅可以出發了。
汽車開出站時,早晨的第一縷陽光已經灑滿了大地,照在車上,透過車窗,讓人暖暖的,難以形容的好心情。十幾分鐘后,客車便駛離了城區,此時的郊外一片荒涼,光禿禿的樹木,滿眼的耕地,耕地里泛綠的禾苗、溝溝隴隴上殘留的雪片,村莊上飄著的炊煙,讓這幅村景圖有了些許生機。汽車一路向東北方向駛去,中途路過一座縣城停留了約10 分鐘,又歷經1 個多小時的顛簸,才抵達妻子老家的縣城汽車站。
下車后,我和妻子又上了一輛“三蹦子”。三蹦子蹦蹦蹦地把我們拉到妻子村莊東頭的大堤上,就繼續去送其他客人。大堤離妻子家還有三四里路。這段不長的路程卻讓我和妻子走得很艱難,我左手拎著用麻繩捆扎好十字花的一箱白酒,右手提著兩箱精裝水果;妻子右手拎著一塊包裝好的五花肉,左手提著裝有糖果、小食品的提包,小心翼翼地下了大堤,又歪歪斜斜,走走停停地向家走去。望著眼前村莊上升騰的炊煙,我的心里倒有點忐忑起來,我可以想象出來,妻子的家人們正在為我們的到來忙碌著、期盼著……
“四姐,四姐夫來了!”四叔家的堂兄弟一邊沖著我岳父家大聲喊著,一邊接過我手里的酒和水果。
我岳父家在村子里胡同的最西邊,東邊緊挨的就是四叔家。四叔家的大門朝南,我岳父家大門朝東。堂兄弟可能估摸我們也快到家了,就出門去我岳父家,正好碰見有些疲憊的我和他四姐。岳父家的門樓像一頂兩頭翹起的破氈帽,兩扇大門就像兩個懶漢一樣,一個斜靠在東屋的南墻,一個斜靠在前排人家的后墻上,看來是有些年頭了。進大門院子里正對著的是一個不大的羊圈,一只老羊和一只小羊正在圈里悠閑地踱步,嘴里還不停地咀嚼著食物。羊圈旁有一棵棗樹,光禿禿的枝丫上站立著一只大公雞。西墻上還趴著兩只老母雞,見我們進院,堂屋里又有親戚出來迎接,便也站立起來,“咯咯咯”地叫著向北慢悠悠走去;受驚嚇的那只大公雞,一躍而起,撲棱棱地飛上了堂屋的屋頂,“喔喔喔”地叫著,好似用最高的禮節歡迎我們。
岳父正在東屋廚房里炒著菜,岳母往爐膛里添著柴火,見我們進屋,岳父放下炒菜的鍋鏟子,拉著我的手說:“路上還挺順利吧?”我說:“挺順。”“你爸媽身體好吧?”“挺好的。”
岳母說:“你倆上堂屋去吧,這兒煙挺嗆的。你大爺炒完這個菜就讓他過去。”
妻子說:“咱這兒的規矩,你給你大爺你大娘(當地對岳父岳母的稱呼)磕個頭吧。”來時,妻子給我說了磕頭的事,可我沒想到是在廚房里給二老磕頭,顯得有點不太正式,出乎了我的預料。
我跪下時,岳父忙拉我一把,說著:“有那回事就行,快起來吧。”我略微起身又接著給岳母磕了個頭,妻子拉起我,陪我回了堂屋。
今天陪我的人還真不少,有四叔、堂兄弟、二連襟、三連襟,還有妻子的大姨哥、表兄弟。我的大連襟在東營油田上班,離老家遠一些、孩子也小,沒有趕回來。聽妻子說過,每到年根,大姐只要不能回來就給家里寄來過年的錢,彌補不能回娘家的遺憾與愧疚;妻子有好幾個姨兄弟和表兄弟,逢年過節,他們就輪流串親戚,年復一年。今年輪到了大姨哥和二表弟來我岳父家,恰巧趕上我第一次陪妻子回娘家過年,立馬就認了兩門子親戚。
岳父家的正屋有三十幾個平方米。進門是客廳,約有十幾個平方;北墻根有一張八仙桌子、兩把木椅,桌子上放著喝茶的茶具和一包紙包的茶葉。八仙桌上方墻上貼著一幅童男童女的寶寶貼畫,笑得特別開心,很是喜慶。客廳東邊有一張木床,看來是家里來客人住時,用一道布簾拉上就與客廳隔開了。客廳西邊是火炕,是岳父岳母的臥室,進臥室的門也是用花布簾遮擋,簡易簡陋。
當岳父把最后一道菜端上來時,時間已到中午。太陽明亮地照進屋子里,暖洋洋的,一掃我來時的疲憊。說句實話,瞧著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氤氳的香氣,我還真感覺有點餓了。我對岳父說:“大爺,喊我大娘過來一起吃吧。”
岳父說:“不用了。她和你二姐三姐四妮她們在廚房吃就行了。”
我的二連襟接著說:“咱們吃吧,大娘從來不上酒桌吃飯。”二連襟的話,在以后我們年節回來時得到了驗證。
因為我是新姑爺回門,按妻子老家規矩,我坐在了朝屋門的主位,正午的陽光特別關照了我。堂兄弟還對我說:“你不先叨菜,桌上人不動筷子;你不先喝酒,大家都不端酒。”可在岳父和四叔兩位長輩面前,我讓他們先吃,可得到的還是那句話“你先叨吧”。我不再客氣,說著“吃吧”就先叨了起來。
喝酒用的都是小酒盅,大約有五六錢,可以一口喝清。我第一盅喝完后,看了一下其他人的酒盅,只有三連襟、大姨哥、表兄弟的酒盅喝清了,其他酒盅里只是輕輕地被喝了一點點。憑我喝酒的經驗,這么小的盅子,第一杯沒喝完的話,基本上都是不能喝酒的人。我這時候心中就有數了,按我平日里喝酒的酒量,兩三個人和我論酒問題不大。
堂兄弟今天是大忙人,去東屋廚房拿筷子、拎熱水壺、端菜等都是他的活。酒桌上倒水倒酒也是他干。新姑爺的特殊待遇,只管吃喝就行。三連襟的酒量我聽妻子說過,喜歡喝,酒量也就那樣,多半是逢酒必暈。我和他有一點不一同,雖然也喜歡喝,但很少暈場,屬于那種熟暈型的,耐力大。我聽母親說過,我的酒量是遺傳了我姥爺的基因。我姥爺是個伐木工人,在東北的冰天雪地里伐木,他能喝一斤多60度的白干酒,不耽誤伐木。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話題就敞開了。原來大姨哥是我妻子三姨家的大公子,身高體壯,在縣城電廠干臨時工,閑來就喜歡喝點小酒,看他那體魄,屬于實力派;表兄弟是我妻子大舅家的二公子,高挑清瘦,在家務農,也喜歡喝點小酒,可是幾盅酒下肚臉就像屋頂上公雞的紅冠子,但也不能小覷。喝著喝著,屋里的氣氛就濃郁了起來,沒有了開始時的拘謹,說笑喝酒也隨意起來。我也不知道喝了多少盅了,推杯換盞,有求必應。大姨哥說:“看你的酒量,我們都喝不過你。之前,就數三姐夫能喝了,今天一看,他也喝不過你。”
大姨哥可能是看我喝酒痛快,盅盅不拖泥帶水,給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酒量大,豪爽、能喝。喝酒的氣勢上我占了上風,主動和我喝酒的就有所顧慮了,說話的時間也就拉長了。
太陽慢慢西移,已經移出了屋子,屋子里變得有些陰涼,菜也有些涼了。岳父看我三連襟、大姨哥和二表弟喝得差不多了,就說:“喝得差不多就行了,你們還得趕路,天黑了路不好走,別摔著了。”接著又對著我說,“你這一天也累了,一會兒你去東屋床上休息一下,晚上你大娘燒好湯再喊你。”
二姐三姐也都上來幫腔:“以后有的是時間讓你們哥幾個在一起喝酒,今天喝這些就行了。”最后三姐又補充了一句,“看你們幾個喝得都帶樣了,說話啰里啰唆,含糊不清了,就四妹妹家像沒喝酒一樣,說話還有板有眼。”三姐是小學語文老師,說話在本。
岳父起身熱了一下桌子上涼了的菜,又端來一小筐饅頭,大家就開始吃了起來。此時,大年初二“迎婿日”的宴席基本上告一段落。
喝了一杯茶水,吸了一根煙的工夫,我便把親戚們送出岳父家的路口,目送著他們,依依不舍地揮手說著:“騎車子慢點,小心路上不好走!”
回到屋里,岳母已經把桌子上拾掇干凈了。兩杯剛剛新沏的茶水,縷縷升騰著芳香,這是家里才有的味道與溫馨。
岳父催我去東屋休息,我突然感覺緊緊張張的一天,放松后還真是有點累了。進東屋迎面便是鍋灶,鍋灶南兩三米處有一張木床,被褥鋪得整齊一新,夕陽透過窗戶,曬得被褥暖暖的,我帶著這種溫暖很快進入了夢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