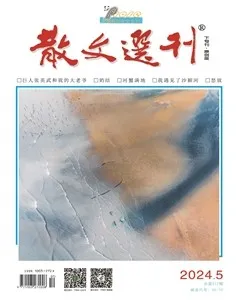翻地
郭平

十多年前,表哥在市郊農村買了套住房,退休后,圍繞房前屋后種點兒果樹、養些雞鴨,過著愜意的生活。表哥脾氣好,為人謙和,見人就笑,與周邊鄰里相處融洽,一戶村民送給他三分地,他辛勤耕耘,樂此不疲。每年收獲時節,都給親戚朋友送點兒山芋、土豆、辣椒什么的。去年,他身體不適,力不從心,打電話告訴我,想不想打理這三分地。我心生歡喜,欣然答應。
翌日,我與愛人及大舅哥開車前往。表哥早就在村頭等候。我們到他家拿了工具,便來到地頭。這塊地位于山坳間,四周被雜樹、野草包圍,有點兒密不透風。由于是耕地,少有雜草。我們觀望一會兒,表哥勸我們趕緊干活兒,否則就要錯過午飯時間。我數了一下,這塊地上有九個土壟。表哥說,我和你大舅哥承包六壟,你們夫妻包干三壟,看誰先完工。
打山芋壟,我沒有干過,表哥隨即示范。看后,我覺得與一般翻地無異。所謂“翻地”,在江南就是鍬、鎬翻松土地。我問愛人行不行,她說沒問題。愛人屬于“女漢子”,手腳麻利。上班那會兒,商業單位經常搞技能比武,她常獲頭名,拿過不少紀念品回家,我沒有理由懷疑她。
在耕地的中間,我先后平行踩下兩鐵鍬,把下面的土翻作表層,然后,順勢把挖松的土左、右各平鏟幾鍬,堆入中間,形成中間高、兩邊底的長行土堆。我干得急,挖得深,用力猛,不到十分鐘就氣喘吁吁。我手拄著鐵鍬,站著一邊休息一邊觀望。愛人雖說挖得不太標準,但一鍬一個坑,不知疲倦,都說“女人的耐力比男人強”。表哥和大舅哥像個老農民,不時朝自己手心噴吐唾沫,一鍬挖到底、不緊不慢翻著土,氣不喘、汗不流,地壟翻得筆直又規整。我自嘆弗如。
于是,我低下頭,彎著腰,學著表哥的樣子翻地,確實輕松許多,進度也快了不少。突然,右手一陣撕心裂肺的疼痛,我停下來一看,虎口處磨了一個水泡破了,露出殷紅的皮肉。表哥見狀,回家拿來創可貼,囑咐我別干了。我貼好傷口,心想“多大事”,便又繼續耕作。
平靜的山坳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原來都在這里干活兒”,大舅哥兒子一家四口興沖沖趕來。內侄是一名醫生,他看看我的手說,別感染了。我說,都是老皮,沒大礙。
醫生的女兒叫小妞,十二歲,平時我倆最親近,看到我的手受傷了,難過的小臉露出痛苦的表情,說:“姑爹,疼嗎?我幫你吹吹吧。”我說:“破點兒皮,沒事,人要勇敢點兒。”她點點頭,跑開了。
醫生的兒子是二寶,平時大人們就喊他小二子,比姐姐小三歲。他是愛人家的長孫,爺爺奶奶都寵著他,好吃的、好玩兒的都讓他先來,所以長得胖、好生氣、喜歡哭。對他這些壞毛病,我從不吝嗇嚴厲,他見到我時,顯得畢恭畢敬,不敢造次。古人不是說“窮養小子,富養閨女”嘛,但是在大舅哥家里,這種古訓似乎被遺忘。小二子來到地頭,挺著個肚子,背著小手,像個“小監工”,不往地里挪動半步,生怕泥土弄臟了手腳。我和顏悅色地說:“小二子,你也來像姑爹這樣翻地吧。”也許懾于威嚴,也許出于新鮮,他竟爽快答應。表哥回家,找了把小平口鍬。
小妞回來,叫我坐在地上,從小手里拿出一把帶軟刺的植物果子,然后,在我的胸前一個一個黏上,形成一個“心”字。我問她這是什么意思,她說:“姑爹手好疼,我的心就有多痛。”一句話說得我竟有些酸楚,多么惹人愛憐的孩子!
六月的江南,氣候濕潤、悶熱,小二子脫掉汗衫、長褲,在地里學著大人模樣翻地。他人小,虛胖,沒力氣,只把鍬踩入土里,鍬面一斜就完事,翻的地如同狗啃,但我仍給他鼓勁,說他干得好。現在的小學生很少有這樣的勞動,對我來說過程比結果更重要。他聽后,勁頭更足,干得更歡。不一會兒,就大汗淋漓,臉上、渾身都沾滿泥土。我問他,要不要洗洗,他說不要。大舅哥心疼,幾次想過來幫忙,我都示意他別插手。
突然,小二子大叫一聲,我趕忙上前,只見地里露出一條粗蚯蚓。大舅哥慌不擇路地跑過來,我告訴他,是一條蚯蚓,別大驚小怪。他說當心嚇著他。我回懟:他沒嚇著反而把你嚇著了。我揮揮手,讓他離開。我笑著把小二子喊到蚯蚓旁邊,用手把它從地里拿出來,告訴他,蚯蚓是小動物,它可以挖洞松土、使土壤呼吸空氣,它的肉是珍貴藥物,能治療多種疾病,也可以供大人們釣魚、釣黃鱔等用。聽后,他說蚯蚓是好動物,要保護它。我們用手一起拿起它,然后,他一個人捧在手心,炫耀地說:“爺爺,你看!”
一個多小時后,山芋地壟就翻挖好了。表哥說,接下來是挖坑、施底肥和栽苗,這幾天沒有雨,不適合種苗。
挖坑就是在地壟上刨個小的坑,碗口大,間距三四十厘米。它看似簡單,實則是技術活兒。地的主人見來人多,也過來湊熱鬧。她從家里拿來把鋤頭,輕輕一刨、往懷里一拽、向前一推,一個小坑就完成,很輕松。我嘗試幾下,費了老鼻子勁,挖得坑大小、深淺不一,難看極了。現場只有兩把鋤頭,表哥和大舅哥各持一把,其他人就地觀摩、休息,我找來一把小鏟子,和小二子一起干。我挖坑,他把挖起來稍大的土塊捏碎。挖了不到一壟的坑,小二子已成泥人。
施肥是個臟活兒,表哥在地頭早已準備好了兩大麻袋干雞糞,打開袋口,一股難聞刺鼻的味道撲面而來。表哥把麻袋里的雞糞分別倒入一個個小塑料袋,男人們拎著塑料袋,抓一把雞糞放入一個坑,如此循環。我綁定小二子,兩人共牽一個塑料袋,我另一只手戴著手套抓放雞糞。他嫌味大,一手捂住鼻子,另一只手慢慢松開袋子。我停下腳步,問他:“為什么捂鼻子?”他說:“味道好難聞。”我說:“紅燒肉味道可好聞?”他答道:“好香。”又問:“豬糞可香?”他答:“好臭。”我說,養豬的伯伯每天喂豬食、鏟豬糞、掃豬圈,難道他就不嫌臭嗎?很早以前的老伯伯說過,沒有大糞臭哪來五谷香呢?小二子聽罷,放下捂著鼻子的手:“姑爹,我來抓雞糞吧。”我露出欣慰的笑容。
沒過多時,翻地活兒就干完了。來到表哥家,大伙兒洗洗手、擦擦臉,我問小二子,要不要洗個冷水澡,他高興得直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