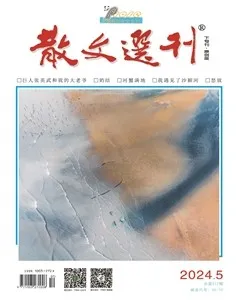宋王臺懷古
顧宗周

香港,如此繁華。曾到過九龍馬頭涌的人,想來,誰都看見過宋皇臺花園。
宋皇臺花園門口,四根花崗巖砌成的石柱,如同華表般矗立,讓花園充滿著復古的東方色彩。走進去十余步,見到左右各立著二龍戲珠圖案的石碑,用中、英文記述著宋王臺的前世今生,七百余字的碑文沒有句讀,讀下去需要很大的耐心。走到花園最里面,才到了宋王臺巨石前。這塊淡黃色巨石呈長方形,橫刻“宋王臺”三字,頗具古意,但是繁體“臺”字寫得不規范,古碑帖中也不曾有這樣的寫法。宋王臺的題字涂朱已淡,加之筆勁柔弱,不禁讓人回想起南宋積弱的國運,引發起無限的思古幽情。
花園所在的地方原是水田,往東南百余米是九龍灣畔,那里原有一座叫圣山的小山,才是宋王臺原本所在。
香港日據時期,日軍欲滅香港歷史,卑劣地將圣山和宋王臺巨石炸毀。戰后,港英政府擴建啟德機場,最終將圣山夷平,將殘存的宋王臺刻石切割成長方形,移置于新建的宋皇臺花園。現在所見到的宋王臺巨石不復昔日景象,殘存面積不及原來的三分之一。面對圣山被夷平、宋王臺巨石被炸毀,時人難掩悲痛:“匈奴未滅千秋恨,官富難容百尺臺。”前些年,香港修港鐵沙中線,在圣山原址附近出土大量宋元遺存。地鐵站內的“圣山遺萃”,展出宋代古井、蓮瓣紋青瓷盤、宋元通寶銅錢、蓮瓣紋瓦當、八卦紋青瓷香爐等宋元器皿,與宋王臺巨石一道,靜靜地告訴著熙來攘往的人們,香港有著深厚的中華歷史文化根源。
徜徉于宋皇臺花園,追尋著宋末皇帝南來的史跡,思緒萬千。宋王臺這方巨石,熔鑄了宋亡七百多年的歷史滄桑和國家興亡、民族氣節。翻開史志,我們可以知道,香港地區原屬東莞縣、新安縣管轄,北宋初年朝廷就在這里設立“官富場”鹽場,并非不毛之地。1273 年,元軍攻破襄陽城,次年宋度宗因酒色過度而死,年僅四歲的宋恭帝繼位。1276 年元軍攻破臨安,宋恭帝投降。宋度宗的另外兩個兒子昰、昺,在陸秀夫、張世杰、文天祥等人護送下出逃福建,昰被擁立為帝,是為宋端宗,昺被封為衛王,經海路南播廣東,1277 年農歷四月到官富場(九龍城一帶),六月到古瑾(馬頭圍一帶),十二月到淺灣(荃灣)。端宗和衛王昺駐蹕九龍的史實,饒宗頤先生在《九龍與宋季史料》一文中考證甚詳。
不過,《新安縣志》所載“昔帝昺駐蹕于此”,大概是口口相傳,因為衛王昺是到廣東化州的碙州,端宗死后才被擁立為帝的。陳仲微《二王本末》記載端宗在厓山時尚有二十萬軍民,可以推測駐蹕九龍時人數也不少。1278 年,元兵追到九龍,端宗和衛王昺退據虎門、香山、化州,想必有不少軍民留在九龍,成為這段歷史記憶的承載者。然而,經清初禁海令,香港等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這里荒蕪殘敗十余年之久,復界后人口十不還一。由此,宋王臺的記憶,與宋行宮舊址、二王殿村、金夫人墓、北帝廟一道,漸漸湮沒于無情的歷史之中。
1916 年,陳伯陶以敬祝南宋遺民詩人趙秋曉生日為由,召集寓港前清文人聚集宋王臺舉行祭拜,題詩酬唱,輯錄成《宋臺秋唱》《宋臺圖詠》,逐漸將宋王臺建立為緬懷清朝、寄望復辟的符號。詞人蘇選樓《自題宋王臺秋唱圖》“離離禾黍故宮秋,羞見降幡出石頭。終古難消亡國恨,怒濤嗚咽向東流”,寫得沉郁悲慨,就是這樣一種心跡。
自此之后,在香港,沒有哪一個景觀能夠像宋王臺這樣,吸引眾多的文人雅士參觀拜謁、登高吟詠。辛亥革命后的大半個世紀里,寓港文人圍繞著宋王臺的詩詞創作和紀念活動從未停歇。他們借宋王臺之酒澆灌心中塊壘,當然,每個人的立場、心態不同,憑吊抒發的情志也不同。民國初年,自詡前清遺民的文人,他們表達的是清滅亡后的黍離悲情。到了民族危難之際,南來文人登宋王臺吟詠,抒發的又是愛國守土、抗擊日寇、寧死不屈、抵抗到底的精神。三度訪港的郭沫若,借宋王臺寫下多首詩作,“遙望宋王臺,煙云了不開”“寇焰愈猖狂,我情愈悲壯”,表達了匡時救世、抗日救國的豪情壯志。
隨著香港回歸祖國懷抱,香港被英人割占的民族屈辱一洗而光,宋王臺的歷史記憶演變成更為復雜多元的情愫。《龍壁懷古》這首歌寫的“誰曾在此處痛失家國在悲叫,無奈情景遠逝,時人在歡笑,消失的一個朝代,竟不知誰曾憑吊。幾多飛機過頂上,問有幾架路過陳橋。它身邊訪眾千萬,但有幾個住腳靜瞄。香江的一塊古石,在這個海角漸已無聊”,正是一個注腳。
在這里,既見到宋王臺石刻,又見到宋皇臺道、宋皇臺花園,讓很多人不解。其實,王、皇二字都已無關宏旨,所謂的正統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話語,畢竟年僅十歲的端宗和八歲的衛王昺到九龍,那是亡國逃命。他們從宋度宗、宋恭帝那里繼承的皇位,已經是被元軍攻陷臨安、亡了國的江山。而荒淫的宋度宗作為南宋滅亡前最后一個成年的皇帝,他所接過的江山,在昏庸的宋理宗那里已經腐朽不堪、搖搖欲墜,即王夫之《宋論》說的“宋迨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再往前則在靖康之難后、宋高宗趙構偏安一隅時,“天下之大勢,十已去其八九”。以文治天下的南宋,滿朝文武想必都讀過《阿房宮賦》,但是那時“靖康恥,猶未雪”,卻沒有誰能挽狂瀾于既倒。
南宋末年學者黃震痛陳當時社會的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四大弊,以士大夫無恥為甚,他們既貪且慊,上貪國家,致使財匱,下剝百姓,致使民窮,統率軍隊,懦弱無能,委印棄城,避難偷生,將熊兵弱。南宋“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最后丟給趙昰、趙昺兩個孩子,他們除了在朝臣簇擁下逃命,又能做什么呢?只怪歷朝歷代有太多的秦檜、賈似道,太少的岳飛、文天祥,終究沒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只是“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圣山已被夷平,宋王臺巨石也被切割置于宋皇臺花園之中,可是宋王臺所蘊含著的國家治亂興衰、民族尊嚴氣節,卻深深地刻印在香港的歷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