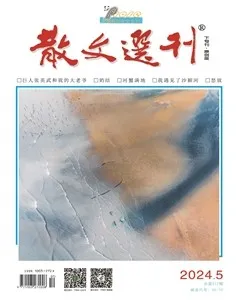給愛美的母親理個發
于路
聽到母親病重消息,我從溫暖如春的海南三亞飛到積雪半人高的威海。
母親見到我和從各地飛回的兒孫,先后圍到她的床前,臉上露出淺淺的笑。她知道我們每個人是誰,三言兩語回答了我們的問話,全然沒有以往她見到至親時的興奮勁兒。
少許,她聲不高卻鄭重地對我說:“我去見你爸的衣服,要穿得好看些。”她用手指了指衣柜的頂層。我早就知道父親病故后,母親就為自己縫制了件紅花緞面襖,說留著送老穿。又說:“找個照相館,加洗一張照片留老了用。”
聽說加洗制框要一周完成,她懨懨地說:“這么長時間!”
父母對我這個長女的信賴超過弟弟,家里家外每逢大事,他們更重視我的意見,沒有那種重男輕女的老舊觀念。
母親的生命恍如進入倒計時。她閉著眼,睜開時眼神直直的,腦袋像一邊耷拉著,臉色發暗,半張的嘴,含著一口氣,沒力氣吐出,也沒氣力咽下。
我迅速往她嘴里塞了幾粒速效救心丸,約莫二十多分鐘后,她的生命體征又慢慢回生。清醒時,她一句半句地說著兒時在膠東家鄉的往事:她七八歲時,地下黨員的姥爺曾教她怎樣裝啞巴與掃蕩村莊的日本鬼子周旋,掩護了兩個八路軍文工團員。革命勝利后,她還看到文工團員寫給老家的來信。說這話時,母親的臉上似拂過一縷春風。
我趴在她的臉邊,從含混不清的吐字中,知道她在說我父親當兵時的通訊員濟萬叔叔晚年的不幸,他的大兒子在工作中不慎遭遇鋼水包脫落,活活跌入鋼水中被燙死了。她咕嚕咕嚕說了兩遍。
她對坐骨神經痛的感知降低了,以往每一個寂靜的深夜她發出的時高時低的呻吟聲,如今突然消失了。半清醒時,她的手到處亂找,直到抓住我或者弟弟的手,便安穩了。清醒時,我們和她對話,她回答得很輕很輕,吐字像綣著舌頭。
一天上午,母親的侄子利來看她,大聲問:“你是幾月幾日的生日?”“四月,”母親想了想又說:“五月。”侄子又問,“四月幾日?”她眨了眨眼,“三日。”93 歲的老媽,腦子一直門清的她,第一次記不得自己是四月二日的生日了。
我擔心她隨時會走,想請小區附近“名格”理發店的小秦師傅為她理發。小秦在省城名店干過,他技術精湛,修剪細心。夏天來威探望母親,我總是帶著老人在他的理發店給老媽修剪,他知道母親喜歡的是近似叫“上海青年式”的一種發型。
“媽媽,我叫小秦師傅給您理理發。”
她點點頭,表情木然,臉蠟黃,慢慢地從一塊白色的圍裙里伸出她的手,抓著我的手。
前幾天,她精神和神志清楚時,一個勁兒對弟弟說:“你姐吃飯了嗎?你姐身體不好,叫你姐到另一間屋休息,你晚上值夜。”我在外屋聽到了,鼻子酸酸的。弟弟對我說,媽媽常告訴他,記著你姐對你們的幫助,什么時候都別忘了你姐。
母親已沒有力氣,像以往一樣,一剪頭,就對理發師說:“別剪短了,別剪短了,太短不好看。”她沒有力氣看一眼照相館放大的照片,那是她選中的要和天堂的父親團聚的照片。
照片中,她三十多歲,扎著一對大辮子,和父親在蚌埠機關大院的合影,說是今生照得最漂亮的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