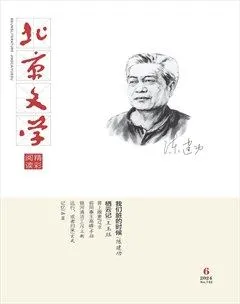會飛的腰條肉(小小說一組)
學校食堂后門正對著羅師傅家的大門。羅師傅每次偷著攜帶腰條肉回家,都是走的這條通道:食堂后門到自家大門。久而久之,已成習慣。
這天,他侄兒結婚,喜豬是在他家里殺的。殺完豬,他照樣很嫻熟地切了一掛腰條肉裹在圍裙里,往后門而去。他以為還在學校食堂里。他家的后門正對著黃老師家的大門。他把腰條肉放在桌上就走。黃老師的老婆江嫂正在房里看電視,聽得響動,出來看時,只看到了羅師傅的背影。心里忖道:羅師傅為何給我家送腰條肉呢?開始有點納悶,隨后便是暗喜,將肉收了。家里好久沒有開過葷了,這正如雪中送炭,下午一家人美美地吃了頓。
來日,江嫂遇見羅師傅一邊甩媚眼,一邊扭腰肢,弄得羅師傅踉蹌了幾下,渾身麻酥酥的。知是腰條肉起了作用。那天送了腰條肉后,回到家中,恍然大悟,知道弄錯了,又不便追討,也不敢吱聲,只好認了。想不到竟有這般奇效。
羅師傅仗著校長關星是他老婆族內侄兒,所以敢大著膽子往家里帶腰條肉的,加上他是大廚兼領班,菜燒得好,人望很高。雖說是避人眼目的,怎奈人多眼雜被人覷著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都不敢說。一般人無所謂,羅師傅最忌憚的是關星,雖說沾親帶故,但關星原則性強,鐵面無私,有人給他取了個綽號叫關鐵。
隨后的一些日子,羅師傅只要有機會,就想方設法把腰條肉送到江嫂手上。這種反常現象,引起了羅師傅的另一半——關嫂的注意。
關嫂其實很糾結的。一則她喜歡腰條肉,同時她又擔心羅師傅的行為被人發現,丟了自己的面子,也丟了關星的面子。當初是她找關星把羅師傅安排到廚房去的。她就是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中期盼著,可是羅師傅多日不往家里帶肉了。這不能不引起她的懷疑。關嫂是個精明人,很快不費吹灰之力就弄明了真相。
話說這關嫂和江嫂都屬于中年婦女。關嫂大江嫂兩歲。娘家只隔一條河,打小熟悉,江嫂是個風騷的女人,而且為了利益不擇手段。有天,關嫂路遇江嫂,故意問道,喲,大妹子,這幾日不見,人怎么長得又白又胖了?江嫂腦瓜子靈活,隨口道,嗐,這人啦,沒得事做,又不操心,困豬養肉,當然就胖。再說,江嫂朝自身打量一眼,我這也還好,不算胖。
胖了胖了,絕對胖了,我問你,是不是吃腰條肉長胖的呀?
關嫂這話點了穴。江嫂臉騰地紅了,哪來的腰條肉吃喲!我們連肉星子都看不到。說著,扭頭走了。
看來,事情已經敗露了,都怪這個羅師傅做事不慎,幸好還沒跟他那個,這如何是好?
一天, 江嫂遇到關嫂,主動搭訕,嫂子呀!你上次說我吃了腰條肉,我確實吃了腰條肉,我向你坦白。
關嫂笑了笑,風輕云淡地說,上次一句玩笑話,你還當真了啊!
江嫂說,沒有,沒有,我想告訴你一個辦法,可以吃到腰條肉,信不信?關嫂說,我不信,哪有這么好的事?江嫂附在關嫂耳邊如此這般說了一通,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也為了討好關嫂,她把羅師傅賣了。末了,還說,把你家羅師傅看緊點啰!
次日上午十點,關嫂按江嫂說的辦法,來到學校圍墻外面的一塊菜地。這菜地正好對著學校食堂后園的一個側門,后園有片小樹林,很少有人到這里來。關嫂在圍墻外等候了約十分鐘,就聽得墻內有響動,接著聽到羅師傅連咳三聲,關嫂對這聲音再熟悉不過了。接應著拍了三下手。隨即,嗖的一聲,一掛腰條肉從圍墻上飛過來,落到菜地里……
晚上,羅師傅回家看見桌上有盤沒吃完的蘿卜燒肉,就問,今天你去買肉了?
關嫂不陰不陽地說,沒買,是撿的。在圍墻外面的菜地撿的。
羅師傅面紅耳熱。從此,恨透了江嫂。兩人相遇,互不搭理。
此后,羅師傅老老實實地把腰條肉帶回了家,但關嫂總是一邊指責埋怨,一邊喜滋滋地照收不誤。關嫂甚至提醒說,這樣你遲早會被人發現的。干脆,改天我再到菜地那邊接應,到時候,你把腰條肉扔過圍墻就行了。
羅師傅點點頭。一切如舊。
這天,羅師傅扔完腰條肉回到廚房不久,校長關星進來了。大伙見校長進了廚房,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都睜大眼睛盯著校長。關星繃著臉將一掛腰條肉放到案板上,輕描淡寫地說,這是剛才我在圍墻外的菜地里撿到的,希望大家以后不要這樣浪費了,我們的師生一個星期吃一次肉不容易。誰丟的這掛肉,誰就回家去。別在這里混了。
原來剛才關嫂在菜地里拿到腰條肉正要回家時,轉身見關星站在身后,瞬間涼了半截,手足無措,恨不得鉆到地下去。
關星冷冷地問,姑姑,您這腰條肉哪里來的?
關嫂明知露了餡,瞞不過,只好照實說了。
奇怪的是羅師傅辭職回家后,江嫂卻到食堂上了班。
后來羅師傅到公社一家養雞場喂雞去了,每次回家,總要從口袋里掏出三五只雞蛋來,邊掏邊不好意思地說,習慣了,沒法。
關嫂說,你像這樣搞,連這點差事都要搞掉的。邊說,喜滋滋地收了雞蛋。
特殊保安
我是來應聘保安員的。朱真走進物業管理處,站在旭光小區物業經理劉成前面,黧黑的臉顯得很平靜。
劉成愣愣地看著這個瘸了右腿的人,有點糾結地說,好像不太合適。
我原先當過保安,追趕小偷時摔傷了一條腿,但這并不妨礙我奔跑擒拿。朱真依然平靜地說著,做了個擒拿的姿勢。
小區保安昨天有人因家庭原因辭職了,急需用人。劉成再次打量著眼前的這個中年人,態度有所轉變,按你的身體條件,說實話不能當保安,按國家有關政策,可以考慮安排你上崗試試,我是說可以試用一段時間。
幾天后,朱真穿上了保安服,走進了紅光小區門衛室。門衛室里還有一位叫田戰的保安員,五十多歲了,是個獨眼龍,俗稱乓子。據說是在老山前線負的傷。
自從這兩個人上崗后,小區的居民就議論紛紛,說七說八的都有。
一個乓子,一個掰子,這兩個保安員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怎么能保證小區安寧呢?住在這里一點安全感都沒有。
這哪能叫保安室,這簡直就是療養室。
劉成聽在耳里,放在心里。
小區不大,只有六七百戶居民。但樹木蔥蘢,花草叢茂,環境優美。小區只有一個朝北的出口,對著一條橫跨東西的馬路,約十五米寬,兩側是進出的車道及人行道。門衛室居中,扼其咽喉,對進出的人員及車輛進行監督管控。
有天晚上九點多鐘,小區內忽然有人喊:抓小偷啊!抓小偷啊!有人偷電動車呀!
此時在門衛室值班的正好是朱真和田戰。兩人幾乎同時沖出了保安室。田戰向左,朱真往右。
朱真沖出來時,正好見一人騎電動車從人行通道躥出了小區。這時候,小區的人行通道尚未關閉。按小區規定,晚十點以后關閉人行通道,人員刷卡刷臉才能進出。
朱真沒有半點猶豫,撒腿就追,平時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很慢,可這時他像一陣旋風卷過去,離電動車還有一兩米遠的距離時,朱真騰空而起,縱身一躍,將人車一起撲倒,但小偷身手敏捷,一個鯉魚打挺消失在了夜幕中。朱真的一只手卡在電動車輪轂上折斷了一根手指,鮮血直流。
劉成很快趕到了現場,將朱真急送醫院。醫生說斷指可以接上,但需要三千元醫療費。劉成拍著胸脯說,費用沒問題,我們物業出。可是朱真不肯,斷了就斷了,不礙事。他黧黑的臉顯得很平靜。從此,朱真又少了半截手指。
再說田戰從西邊通道沖出后,剛好看見馬路上有個人騎電動車經過,以為是小偷,便不問青紅皂白地猛撲過去,將人車一起撲倒,結果鬧了一場誤會。致人輕傷,賠禮道歉不說,還賠了幾百元醫療費。
過了一段時間,也是夜里九點多鐘,小區內忽然響起了“嗚笛——嗚笛——”的電動車報警聲。朱真和田戰迅速趕到報警點,報警聲停了。
兩人在周邊觀察一陣,沒見異常,回到門衛室。
老田,這電動車報警,我感覺有點蹊蹺,是不是又有小偷進來了?朱真黧黑的臉顯得不那么平靜。
田戰應和著,我也有這個懷疑,我們再過去看看。我往西邊轉過去,你往東邊轉過去,我們來個合圍。
兩人從林陰遮蔽的小路上躡手躡腳地會合到剛才電動車報警的地方,發現有個黑影蹲在地上,“鬼鬼祟祟”地想撬鎖,兩人如同鷹拿燕雀,同時撲將過去,將其擒住,反剪雙手,押往物業管理處。
劉成早已等在門口。看見兩個保安滿頭大汗地押著小偷過來,說,兩位師傅辛苦了!
那小偷一邊哎喲哎喲地叫喚,一邊埋怨,哥,這兩位保安大哥好大的勁啦!把我的骨頭都快折斷了,快讓他們放開!原來此人是劉成的弟弟——劉威。
讓小弟受委屈了。劉成伸手在劉威的肩頭安慰性地拍了拍。
沒事。哥,這兩位保安是好樣的。我先故意觸動了電動車的報警裝置,見他倆趕過來,我便隱身樹林中,我以為他們沒有發現異常就會不了了之。哪想到他們還是殺了回馬槍,把我抓了現行。
哈哈哈……劉成和劉威放聲大笑。
朱真黧黑的臉依然顯得很平靜,他和田戰面面相覷,隨后兩人開心地大笑起來。
雀吃餅
湖草鄉鄉長楊鐵到以大棚蔬菜聞名的綠華村去檢查指導工作。吃了晚飯,決定不回鄉里,在村里住一宿,和群眾打成一片。
村支書吳小偉知道楊鐵喜歡打麻將,就安排了三個人作陪,他自己一個,村主任周大剛一個,還有一個就是隨楊鐵來檢查工作的鄉人事干事蔣超。蔣超是自告奮勇來的,因為他是這里人,還在村里干過書記,想借機回來看看。前兩年,他通過關系調到鄉里去了,還把他老婆趙翠姑弄到縣農業局機關食堂當廚師。可是蔣超打了兩圈,他老母親發病了,要送醫院,于是向楊鐵請了假。吳小偉就安排村通訊員兼司機周列兵上場。楊鐵也頷首同意了。按說,一個通訊員怎么能陪鄉長打牌呢,可是當時的確沒有合適人選,情急之下,只好拉夫湊數。周列兵坐在楊鐵上首,這家伙賊精賊精的,盡量給楊鐵提供方便,楊鐵需要的牌,他會毫不猶豫地打出來。這盤楊鐵已經停和了,丁壹雀。此時,周列兵打出一個壹餅,楊鐵說,和了。說著,把壹餅拿過來,跟自己的壹雀放在一起。吳小偉和周列兵都笑而不語。周大剛卻直言不諱地說,楊鄉長,您和錯了吧,您丁壹雀,別人打壹雀您才能和,您怎么和了個壹餅呢?楊鐵一臉不屑地把牌一推,說,怎么不能和呢?這叫雀吃餅。你連這也不懂啊!周大剛無語,干咳了兩聲,像吞了個毛毛蟲。三人把錢匯了。
再一盤。桌上早已打出四個七餅。楊鐵還和邊七餅,他趁人不備在桌上撿了個七餅,說,和了。這周大剛明明知道楊鐵是個握云攜雨之人,卻還是不識趣地說,楊鄉長,桌上早已打出了四個七餅,您哪里摸來的一個七餅,難道這副牌有五個七餅不成?
楊鐵頓時拉下臉,不悅道,我不管你打了幾個七餅,我摸到七餅和了這是事實。你問問他們倆,看是不是我摸的七餅。他指指吳小偉和周列兵。吳小偉模棱兩可地點點頭,依舊笑而不語。周列兵則厚顏無恥一本正經地道,原先桌上只有三個七餅,周主任你是不是看錯了?我親眼看見楊鄉長是從牌堆上摸的七餅。又一盤,周大剛停和了,也是丁壹雀。楊鐵在上首打出一個壹餅,周大剛拿出一個壹雀,說,和了。說著模仿楊鐵把壹餅拿過來與壹雀放在一起。楊鐵板著臉說,你不能和。周大剛不服,犟頭捏頸地說,一樣的牌,為什么您能和,我就不能和呢?楊鐵針鋒相對地說,是的。我能和你就不能和。我講個道理你聽,你想想,這個壹雀剛才已經吃過餅了。這么大的餅一個就能把壹雀給撐住,還怎么能吃第二個餅呢?你說是不是?周大剛很尷尬,點頭也不是,搖頭也不是。吳小偉抿住嘴暗自好笑。周列兵則豎起大拇指向楊鐵做了個贊許的手勢。
雀吃餅的故事很快傳開,大伙私下里議論紛紛,當著楊鐵的面大氣都不敢出。
不久,周列兵被調到鄉里給楊鐵當司機。
又兩年,楊鐵要調到縣農業局當局長,決定把周列兵帶到農業局去。 據了解,農業局還有一個工勤編制,但是工齡必須滿十年才行。而周列兵的工齡才五年,于是楊鐵就給周列兵出了個主意,讓他找蔣超把工齡加到十年。
周列兵提著兩條好煙去找蔣超。一進門就殷勤地連聲叫著超哥超哥,同時把煙往蔣超柜子里塞。
蔣超把煙推到一邊,說,周師傅,不用客氣。
周列兵笑瞇瞇地說,我是來開介紹信的。
蔣超爽朗說,開呀,我知道你要進城了。
周列兵壓低聲音說,就是有點要求,請你幫個忙。
蔣超問,幫什么忙?有話直說。
周列兵說,超哥,我們是鄉親。我就直說了,我的工齡只有五年,農業局那邊的工勤編制要十年的工齡,你給我開介紹信時,把工齡加到十年,行不行?說完,眼巴巴地望著蔣超。
蔣超瞪大眼睛一臉歉意地道,這恐怕不行。這不是讓我造假嗎?你明明只有五年工齡,我怎么能憑空加到十年呢!
周列兵央求道,超哥,我們都是一個村的人。這個事就是你的筆頭子歪一下的事。這次你幫了我這個忙,我一輩子都記得你的好。
蔣超把頭擺了又擺回道,不行,不行,這是個原則問題,事關重大,我沒有這個膽量給你加工齡。
……
僵持了一會兒,周列兵見蔣超油鹽不進,沒有商量余地,便提著兩條煙灰溜溜地走了。
次日一早,蔣超剛上班,楊鐵的電話就來了。楊鐵說,蔣干事,我聽說你老婆在農業局機關當廚師,怎么這么巧呢?我這回可是有口福啦!
蔣超趕忙說,是啊,是啊,以后還要您多照顧的!
楊鐵嘿嘿地笑了兩聲說,這個沒問題的。頓了頓,說,小周的介紹信開了嗎?這次他有點機遇,但是要有十年工齡才行。如果你能通融一下,他會很感激你的。
蔣超說,楊局長,您說的我理解,可是……周列兵工齡只有五年,昨晚我還專門查了他的檔案,只有五年……
蔣超的話還沒說完,就被楊鐵打斷了,楊鐵笑著說,檔案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蔣超也有些按捺不住了,就大膽地說,楊局長,實話對您說吧,周列兵這人比較狡猾。我給您舉個例子吧!有一次我和村主任,還有周列兵三人在縣城辦了事,中午在一個叫兩廣餐館的地方吃飯,吃了七十五元,我嫌貴了,找老板論理,正討價還價時,周列兵過來把我一拉,說,算了,算了,七十五元不貴。說著分文不少地把賬結了。我當時很惱火,劈頭蓋臉地問他,你家里有好多錢?你像蠻有錢的樣子!到了車上,周列兵從懷里往外掏出一包東西來,說,你們看——他把報紙攤開,是包鹵牛肉。我們都很驚訝,問他哪來的。他說,你們與餐館老板在前面討價還價,我趁機溜進廚房把他鹵牛肉卷了一包,光這包牛肉就值七十五元……您看,他是這種人!您要我給他加工齡,我怎么加呢?再說以后別人查出來了,這責任我擔不起呀!蔣超帶著哭腔說。
楊鐵停頓了一下,半嗔半笑地說,蔣干事,我們都來自農村,誰年輕時不干點荒唐事,不怕你笑話,我小時候也偷過生產隊的瓜,還偷過五保戶的雞……你能說我不是好干部嗎?再說吧,這個工齡,你加了,它就是十年,你不加,它就只有五年,也沒人知道,事情就是這么簡單,你看著辦吧!楊鐵說完,啪地掛了電話。
蔣超哭笑不得,進退兩難。正在長吁短嘆、愁悶不已之時,抬頭卻看見老婆趙翠姑背著包,提著行李站在門前,便驚訝地問,你怎么回來了?
趙翠姑伶俐回道,周列兵逼我回來替他說情,并說楊局長會幫他打招呼的。你給我講過雀吃餅的故事,我不想讓這個故事在你身上發生,就把工作辭了,回村承包大棚去。我聽村里人說,承包大棚的收入也不錯!
蔣超望著眼前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凄然一笑。笑容里有幾分欣慰,也有幾分堅毅與悲壯。
收禮只收朱生的禮
年底,在鄉人大會上,二十八歲的朱生當選為鄉人民政府副鄉長。他有些喜出望外,過后細細沉思,自己出身農家,無關系無后臺,卻年紀輕輕能夠走上鄉領導的崗位,離不開鄉黨委于書記像父親一樣的關愛和栽培。他在信封里裝上十張鈔票,要當面去感謝這個人。
朱生走進于書記的辦公室,畢恭畢敬地站在辦公桌前,待于書記抬起頭時,真誠致謝道,于書記,我這次能被選進班子,感謝您的關懷和培養!
于書記憨厚地笑了笑,指正道,你能當上副鄉長,靠的是你自己努力,靠的是組織器重,路還長著咧,你得繼續加油!朱生看到,于書記的眼里充滿了希冀和期待。
朱生堅定地表態道,我一定繼續努力,不辜負您的信任!說完,他摸了摸大腦袋,嘴里囁嚅著咕嚕了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然后急慌慌地從褲兜里掏出一個信封,放在桌上,逃也似的離開了。
我不收禮!于書記追身喊道。本想趕出門去,把信封退還給他。可年輕人已跑得無影無蹤。
春節前那段時間,朱生聽說陸陸續續有班子成員以及鄉直部門的頭頭腦腦們來送禮,都被于書記一一謝絕了。在外人眼里,于書記從不收禮,是出了名的清官。別人打不開的豁口,朱生卻打開了,這讓他喜不自禁。
又一年年底,朱生升任黨委副書記,于是在春節到來之際,他如法炮制,又特意來到于書記辦公室,進門不再是站著,而是選擇坐到了木椅子上。于書記見朱生來了,笑道,坐沙發,坐沙發,干嗎坐在椅子上?朱生一語雙關道,坐椅子也蠻好的,這椅子還不是您給我坐的。不然的話,我連坐椅子的資格都沒有。于書記給朱生倒了一杯水,贊許道,這次組織提拔你當副書記,是你表現突出。八月份,鄉里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洪水,湖草鄉沒潰口,不破防,確保了幾萬畝農田的豐收,防汛的四十多個日日夜夜,你是風里來雨里去,輕傷不下火線,給基層干部做了很好的表率。朱生摸了摸大腦袋,靦腆地笑道,哪里哪里,還不是您領導有方,指揮得當。這功勞應該記在您身上……春節到了,沒什么好表達我心意的……說著把一個鼓囊囊的信封塞到于書記的抽屜里,轉身要走。于書記說,朱生,請留步!你知道我是不收禮的。說著拿起信封,塞到朱生手里。朱生趕緊把信封再次塞進抽屜,小跑著沖向門外,于書記無奈地搖搖頭,妥協地喊道,既然這樣,我就暫且替你保管著!朱生當然明白,這只是領導們的冠冕堂皇之詞。不管怎么樣,于書記只收他的禮,說明他與于書記的關系已經非同一般,這既成了他干事的動力,也讓他感到背后似乎有一根“撐棍”,工作起來無比踏實。
又過了一年,朱生升任該鄉鄉長。春節前,他到于書記辦公室匯報工作,進門就直接坐到沙發上。于書記趕忙站起身來,朱生看到于書記起身時右手按壓在肝部,似有不適。便勸道,于書記,您日日夜夜為鄉里操勞,這幾年,把一個落后的湖草鄉,搞得有聲有色,不容易。您也在湖草鄉工作了十幾年,該考慮動一動了。
于書記故作輕松地走到朱生身邊坐下。問,上級組織沒有考慮,怎么動?朱生摸摸大腦袋,提醒道,縣里的頭頭腦腦,您該走動的走動,現在興這個。于書記搖了搖頭。話不投機。朱生點明來意,春節了,來看看您。您不沾煙,又不能喝酒,我只能用這個表達心意了。邊說邊把一個鼓鼓囊囊的信封塞到于書記的抽屜里。
于書記看著朱生,柔光在他的眼里聚集。他很平靜地說,朱鄉長,你和我是同志加兄弟的關系,湖草鄉的進步,是大家努力的結果,也有你的一份功勞。其實,是我應該感謝你對我工作的支持才對!他的音色透著疲憊。
朱生趕忙說,沒有您給我踩油門,就沒有我朱生的今天。
于書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這樣吧,禮金我暫且替你保管著。
朱生沒有去品咂這話中的意味,這種堂而皇之的話,雖然很假,但朱生樂意聽到。他臉上洋溢著從內心深處沁出的欣悅。臨走,他再次勸告道,于書記,親戚在于走動,官場在于活動,為了您的身體,您得與時俱進,該跑動的一定要去跑動。于書記微笑以對,自言自語道,我一個農民的兒子,能為湖草鄉的群眾做點事,已經很知足了,要我去送禮,我實在做不出來。神情里充滿堅毅。朱生走出于書記辦公室,很為他惋惜,也為他不值,既然你能收我的禮,你也可以去送禮呀,為什么要把自己困在這鄉里一輩子呢?
又一年,縣委調朱生到朱場鎮當一把手。
一日,朱生聽說于書記身染重疾住進了縣人民醫院。放下手頭工作,他火急火燎地去看望于書記。等他趕到醫院時,為時已晚……來到于書記的悼念現場,于書記的老伴拿出一個大信封交給朱生,交代道,小朱,這個信封,是老于臨終前囑托我,一定要親手交給你。
朱生接過沉甸甸的大信封,打開一看,是一摞摞用別針別好的現金,還有一張紙條,紙條上列出了他送禮的時間及金額,后面附著這樣兩句話:收禮只收朱生的禮,今天全部退給你。
仿佛有種突襲而至的震撼把8SJYcahr2uN/jhxs+06ZTfLmg3xbKpwof6EK7WWRgJo=朱生穿透了,他的身體有些微戰栗,隨即,他悲催地大叫一聲:于書記——!便撲通一聲跪倒在于書記靈前,淚如雨下……
撞餐
中午,縣紀監委常委、黨風建設辦公室主任張成執行公務回來,過了飯點,機關食堂無飯可吃了。他轉到街道上,走進一家名叫宏遠的餐館,想隨便弄點吃的。
餐館很冷清。張成順手推開一個包間,卻見里面坐著兩個人,一個是稅務局的田副局長,一個是做無紡布的陳老板。看樣子是在等菜。
因為都熟悉,張成首先打了招呼,喲,怎么在這里撞到兩位了!
張主任,是來吃飯、飯的吧,來同、同我們一塊兒吃、吃。田副局長知道張成是專查吃喝的,不由自主地哆嗦著站起身來,倉皇中舌頭都沒有捋直。
張成本來是來吃飯的,但礙于自己的身份和有關規定,便忖了忖,搖搖頭道,不用,不用,我已經在機關食堂吃過了。我是來……
沒等張成的話說完,陳老板似乎明白了什么,忙解釋道,張主任,是這樣的,我公司涉及一筆出口退稅業務,今天特地約了田局長,幫我到武漢海關做工作去的。本來很早就要走的,無奈瑣事纏身,拖到現在。我們準備吃個工作餐就往武漢趕的。說完,有所期許地望著張成。
最近,對公職人員吃喝查得很緊。他希望張成能理解。這是事出有因。他自己沒事,主要是怕連累田副局長。
張成其實也很糾結的。他與兩位不期而遇,又不好意思加入;同時,他的職責又是查吃喝的,而田副局長就在眼前,陳老板這番話他將信將疑,他令人捉摸不定地笑了笑說,陳老板的意思我明白,但是……
正說著,服務員端著一盤菜推門而入。
田副局長似乎意識到了什么,敏感地瞥眼手表,一拍手說,呀,不能吃了,時間來不及了,下午四點我還要趕回來參加局里的一個會議。說著,朝張成尷尬地笑了笑,便起身往外走。陳老板是個靈活人,也迅速夾起包,湊到服務員耳邊咕噥了兩句,也出門去了。留下張成獨自佇在那里。
很明顯,這兩個人是怕自己查他們,才倉皇撤離的。如果上了高速,就沒有飯吃了。張成抬腕看眼手表,一點半鐘,估摸著這兩個人應該還會回來的。不如自己干脆在這里等著他們,剛才偶遇,事情來龍去脈沒有弄明白,不好明確表態,現在看來,這兩位在這兒吃飯的確事出有因,這不算違規。自己不也是錯過了飯點來吃飯的嗎?他靈機一動趕忙喊來服務員道,馬上給我準備四菜一湯。服務員遞過菜單,張成點了菜,對服務員吩咐道,馬上去做。不一會兒,四菜一湯就上桌了。
再說田副局長和陳老板上車后,直奔高速公路而去。在接近高速路口時,田副局長早已餓得肚轉腸鳴,面色蒼白,冷汗涔涔。陳老板瞥了他一眼,關切地問,不會是被嚇病了吧?
我有低血糖。田副局長如實告知道,邊說從包里摳出一顆糖,塞進嘴里。
要是上了高速,得一個多小時才有吃的,咱們得打轉。陳老板掉轉車頭,自吹自擂道,我有先見之明,早讓服務員準備好了,咱們直接過去吃。這會兒那個姓張的應該走了。
小車又停在了宏遠餐館門前,兩人走進餐廳,推開包間的門,看到張成還在包間里,而且桌上已擺好幾個熱氣騰騰的菜,一時蒙圈了。田副局長雙腿發軟,唯愿有地縫可鉆。真是倒了八輩子血霉了,吃個午飯竟然兩次與姓張的撞餐,太他媽的不幸了。正欲撤退,卻被張成一臉笑容地攔住了去路。
張成打趣地道,還想跑啊?這回你們跑不掉了。你們知道,我確實是查吃喝的,你們這種情況,我不但不查,還要支持你們。說著,轉過身,指著桌上幾個熱氣騰騰的菜說,這是我準備的四菜一湯。單我已經買了。我自己也沒吃,我想邀你們一起吃。不知兩位肯不肯給這個面子?
張成的話像輕拂的春風,吹散了兩人心頭的霧霾。兩人內心涌過一陣喜悅的波瀾,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搓手挪足,頭顛尾顛,不知所措。
張成連拉帶拽地把他們弄進包間,給他們斟了茶,說,吃吧,放心大膽地吃吧,還愣啥哩!
兩人這才如釋重負地相視一笑,同時舉起茶杯,對張成說,我們敬你!
咣當,三只茶杯撞到了一起。
責任編輯 丁莉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