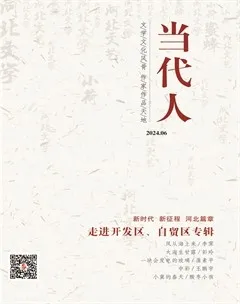落村
一對甲蟲,在木槿花上持久地交尾,兩只蝴蝶,在它們周圍翩躚,閃著金光,仿佛時間被凝固成一坨金子。它們的背后,有片紫云英,正熱烈地呈獻出紫與綠。它們歸于自己的世界,繁殖,只是我們給它們的定義,或許,還有更轟轟烈烈的。
一陣風吹過來,木槿花翻起一陣波浪,兩只甲蟲搖晃起來,蝴蝶順勢往低處飛。我摘了一片木槿葉子,蓋在甲蟲身上,你們繼續。
我張望了一下,沒人,眼前的幾間房子都關著門,也聽不到嬰兒的啼哭。有一間房子的窗前貼著紅雙喜,可院子只有一只大公雞與三只母雞,它們在樹底下打盹。
可能,我又摸錯路了。我騎上自行車,原路返回。
路,是村里的機耕路,中間高,兩邊低,原先應該鋪過一些碎石頭,拖拉機跑得久了,一半嵌入了泥里,一半險靈靈地露著,變成了三角頑石,我努力避讓,車把被我左擰右拽,還是顛得屁股生疼。
我從車上下來,走了幾步,痛得齜牙咧嘴,一邊把腳高高抬起,仿佛自行車長了一只腳。上次我去老家,見母親在地里忙活,幫她種了一些菜,因穿的鞋子過于正式,再加上天熱,干脆赤腳,不小心被一枚很細的荊棘刺了一下,因沒流血,也沒上心,沒把那枚刺拔出來,結果長成了雞眼,平時倒沒什么大礙,一旦碰到它,那痛簡直鉆心。剛才一顆小石頭仿佛驚醒了它,四周的神經瞬時活躍起來。我貼過很多雞眼膏,每次都能掉下來一些白色的腐肉,意欲把那枚刺給清出來,可它非常頑固,一直躲在里面。
等腳后跟的痛慢慢收攏,過去,我朝四周看了看,右側有一條泥路,雖然窄了些,但騎自行車沒問題。那條泥路蜿蜒著去前面一個村莊,也可能串連前面的前面。村里的路,大多是活路,眼看著沒有路,拐個彎,又出現一條,好像是村莊的根須。
產婦的婆婆說,從醫院里出來,順著橫路,到底后右拐,有一座石橋,她家就在石橋的對面。產婦的婆婆說這話時還跟我比畫著,兩只手忽上忽下,中間還來個一橫。
我騎上自行車,咔噠咔噠往前,拆線用的血管鉗與剪刀,在飯盒里嘩啦嘩啦。初夏的風,往我臉上拂,也往我褲管里流,天上還有一朵白云悠悠地浮著。
童醫生曾告訴我,如果實在找不到,可以去找一下村里的婦女主任。也是,她們對產婦的情況知根知底,甚至男女青年有戀情開始,就一次次地家訪,宣傳非法同居不可取,未婚先孕不可取。婦女主任確實不容易,門難進也要進,臉難看也要看,沒有潑辣與干練,還真難勝任,尤其肚量要大,容得下來自各張嘴巴的議論。
那天,我也是找不到產婦的家,再加上天熱,心里很煩,便向一位老婆婆打聽婦女主任的家。結果,那位老婆婆立馬拉下臉來,說是不曉得,然后用很嫌棄的神情剜了我一眼,一邊捉起掃帚嘩啦啦地掃地,塵土沒頭沒腦地朝我撲來。我趕緊推上自行車,再不走,我也成了垃圾。背后跟過來一陣罵聲,罵得有些戳心戳肺。我著實窘迫極了,在她的罵聲里幾乎有點陷進去了。好半天,我才明白她罵的是一條狗,似乎那條狗踩臟了她曬的干菜,又好像說的是狗善惡不分。狗哪來的善惡,于它只有忠心與否。我心里嘀咕著,腳可一點也不嘀咕,拼命地往前踏。
西醫有望、問、叩、觸、聽,這五門手藝我用來落村。望,我看嬰兒的尿布,門口有萬國旗一樣地掛滿了尿布,家里自然有產婦,無論今天是不是這家產婦拆線,都不要緊,她肯定來醫院做過產檢,即使我記不住她,她也會認得我,農村有句話,叫弄不過熟。問,是主動打探。母親說過,嘴巴活絡,苦頭不吃。聽,我是聽嬰兒的哭聲,月子里的嬰兒,哭聲頻繁,音頻短促,因為他更多的是用嘴巴在哭,像一只破簸箕,裝進長輩們的無限期待與祝福,也盛進世間的苦與樂。
我進入村莊后,看到一位老婆婆在河埠頭洗衣服,我喊了聲“阿婆”,她抬起頭,狐疑中帶著慈祥。我問她這里是石步村嗎。她笑了,臉上的褶子像核桃一樣展開,說石步在前面。顯然,我把豎路走成了橫路。產婦婆婆說的橫路,是她眼里的橫路,從醫院出來,于我應該是豎的,我不需要拐彎。
我出來時一只狗跟了上來,心里一陣發怵,情急之中蹬快了自行車。結果,狗也跑了起來,還狂吠幾聲。我拼命地踏,只要踏出村莊,它就不會跟了。這是狗的德行,看家護村是它一輩子的使命。真應了那句老話:性越急柴越濕。拆線飯盒從后座松了下來,啪的一聲,掉在了地上。我想也沒想,剎住了自行車。狗,停步不前,跟我對視著,尾巴一點點翹起來,越來越直。我知道這是狗在表達敵意。我一點點從自行車下來,盡量動作輕緩,就像平時給人做手術一樣,此刻,我是給狗的目光做手術,努力祛除它的寒光。
我曉得人與獸之間只要不發生沖突,傷害是可以避免的,何況狗還通人性的。我慢慢俯下身子,它轉了一下腦袋,可能調整著同我對視的角度,我伸手去摸飯盒,狗往后退了幾步。我盡量控制著自己的動作,至少看起來很從容的樣子。
突然,不知從哪里鉆出來另一只狗,驚得我簡直花容失色,一只狗讓我緊張了,它們聯合起來,這讓我情何以堪。我一只腳踮在地上,另一腳踩在腳板上,拆線飯盒被我放進前面的車籃子里,準備以最快的速度沖出一條路來。
那只狗看看我,又看看它,卷了一下舌頭,掉頭就走,很快,與我對峙中的狗,屁顛屁顛跟了過去,一場危機完美化解。
有時,產婦的老公也會來帶我,可我除了一時逞強外,還有一層意思,覺得難為情,跟著一個陌生人,心里很別扭,碰上熱心的產婦老公非得讓我坐他的自行車,讓我更加尷尬,可能他們不覺得什么,我無非是替他老婆拆線的婦產科醫生,可我心里不這么想,坐異性的自行車后座,可得是特定的對象。
套用魯迅先生的話:世上本無路,走得多了便成了路。我是走得熟了便有了路,就像臨床經驗一樣,靠多次的操作才能熟練,熟練后才是屬于自己的技術。如果往宏大處說,人生是需要一次次的硬碰硬,哪怕明信片上寫的人生寄語多深刻,不自己去摸索,寄語不過是小語。
應該說,我落村的能力還行,打退堂鼓的事還沒有發生。
不過,曾遇到過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那天我去一個叫半岙的村子,有兩條路,一條是山路,另一條是平路,前者相對近,平路遠一些,我去的時候,走的是平路,回來的時候,突然心血來潮,自行車車頭一拐,拐進了山路。我慢慢地踏著,一邊騰出視線,看看山景,那是初秋的光景,山上的樹木接應著時序,像翻牌一樣翻出了五顏六色,在或左或右、忽前忽后地簇擁著我的視線,感覺挺愜意的。
后背有點熱,便停了下來,想吹吹山風。我站在一棵樹底下,樹上還纏著一根粗壯的藤,藤上開著一朵紫色的花,花蕊特別白,花瓣上還長著一圈圈的黑點,我詫異的同時又有一種不祥的感覺,到底哪里不對勁,卻一時說不出來,總覺得目光在那些黑點點上抽不出來,有一種眩暈,開始有些恍惚,像打瞌睡似的,小腿處有一縷陰陰的風蕩來蕩去,仿佛有一種怪力推著自行車,我分明感到自行車正往路下面的蓬草滑去。我又有一半清醒,告誡自己必須從那朵花上抽出目光。也不知哪來的激靈,我拼命地打鈴,叮鈴鈴……大約持續了幾分鐘,額頭冒出一陣汗,人開始慢慢輕松起來,身上也有了力氣。我趕緊踏上自行車,一邊打著鈴,往山下騎去。
到了醫院后,晚飯也沒吃,只覺得很困,半夜醒來,人有點迷糊,身上軟綿綿的。我摸摸額頭,好像燒了,摸索著起來倒了杯白開水。第二天,我勉強起來,坐在診室也是一陣陣地犯困,差點給一位病人開錯藥,好在病人拿著處方又回來,問我這是吃的還是用的。我一看,才知自己犯錯誤了。病人走后我知道自己今天是沒辦法坐診了。好幾天我都處于這種迷糊的狀態,量量溫度,略比正常高一點點,除了犯困,其它沒什么不適,也就是不需要用藥,或者是達不到用藥的標準。
閑時,我跟中藥房的麗姨說起那天的事,她瞪大眼睛,用怪異的眼光看著我,然后掐掐我的內關。她囑咐我喝碗紅糖水,晚上早點睡覺,就像開了一張醫囑。我完全遵循,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自己感到虛弱,一陣陣的冷意,從腳踝處漫上來。
那晚我睡得很安穩,也沒有夢,是被上班的鈴聲催醒的。我一骨碌起來,飛快穿衣,飛快下樓,照常落村,但那個山路,我再也沒去過。甚至,連紫色的花,我都不愿意再看。
我騎了一刻鐘,總算找到了產婦的家。產婦的婆婆綻開笑臉,在門口迎接我,一邊還說,路挺好摸的吧,筆筆直。我心里嘀咕著哪來的筆筆直,現在只希望產婦的切口愈合也能筆筆直。
我拆線的時候,心里挺緊張,擔心產婦的側切口愈合不好。這也是我非常抵觸產婦提前出院的原因。我心里也清楚我們接生用的產包與器械,在消毒方面有點不達標,放在高壓鍋里消毒后再在太陽底下曬一曬;消毒水的沖兌比例,也是毛估估的,根本沒有量杯去測量。產婦做了側切術后我一般會用三天的抗生素,外加每天的護理,以防切口感染。她們提前出院,我最擔心的是切口愈合不好。這樣的例子不是沒有,無論是產婦本人受到創傷,還是我自己的聲譽,都是非常苦惱的。
我每剪一根線,心里總會沉一下,擔心它會裂開,這種也不是沒碰到過。童醫生碰到過,我也碰到過。這多數是因為感染引起的,如果不是很嚴重,只能加強平時的護理,用點抗生素,讓切口慢慢愈合。否則,我得給產婦重新縫合。其實,這個風險更大,產婦的疼痛也會更重,你得清創,那些長不好的肉全部切除,這時候的疼痛更清晰,分娩時產婦的注意力在生孩子的事上,事外的疼痛,一般不是很劇烈。因此,我如果做了側切術,在縫合前會用幾支維生素C與抗生素沖洗一下,保持創面干凈。
產婦的婆婆一直在旁邊盯著,問我怎么樣。其實,她不問也看得很清楚。縫合的針腳不是特別平,最后一針還有一點點鼓起,不過,倒也無礙,十天半個月后基本會消失。嚴格來說,這不是我理想中的愈合。我在心里選擇著詞語,斟酌再三,說是挺好的,需要每天碘酒消毒一次,這樣會長得更好。產婦的婆婆不住地點頭,還說,我們把風管得牢牢的,不讓她下床,伺候得好好的。
我說適當的時候可以開開窗,室內空氣好一些,也不一定每天躺在床上,現在大醫院流行產后第一天就下床活動。產婦的婆婆連連擺手,這怎么行,坐月子是老一輩子傳下來的,不能洗頭,不能洗澡,吃飯都在床上。老人家一口氣說了很多規矩。我也不好跟她辯解,農村有農村的習俗,這個話語權是在老一輩人身上,就像時間熬出來的湯藥,良藥必是苦口吧。
從產婦家出來,我看到一本《讀者》雜志,被一只大公雞踩在爪子底下,頁角翻得跟卷發似的,封面上污穢不堪。我著實心疼了許久。
我落腳在鎮上,對于鎮上的許多老規矩,還是空白,并非說要接受它們,但總歸要適應與了解。就像落村,起初我聽不明白,世上只有村落,哪有落村。時間一長,越來越覺得落村的落字充滿了張力,如同一片落葉,無論飄蕩多久,總歸要墜于村莊的土壤。那一年我十九歲。
(干亞群,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見于《上海文學》《天涯》《青年文學》《散文》《散文選刊》《作家》《花城》等。著有散文集《給燕子留個門》《梯子的眼睛》《指上的村莊》等。)
特約編輯:劉亞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