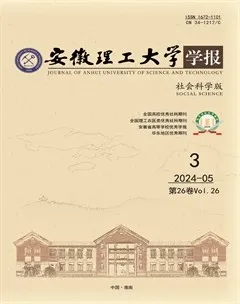《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的后田園詩
王婷婷 張奇才
摘 要:文章基于后殖民生態批評理論框架,從后田園詩角度分析《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小說中,英美等殖民國家以各種形式壓迫著特立尼達,而這種壓迫與對自然的壓迫緊密相連。受到英美等殖民國家的影響,特立尼達人民的思想和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同化,他們也加入到掠奪自然的進程中。然而擁有能動性的自然會抵抗人類的意愿,通過巨大的力量向人類示威和報復。自然給人類帶來死亡,也孕育著新生。自然的偉大讓人類敬畏,而這種敬畏的態度也就成為人類放棄人類中心主義和改善人與自然關系的起點。
關鍵詞:《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后殖民生態批評; 后田園詩; 自然; 敬畏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2-1101(2024)03-0043-06
收稿日期:2022-06-24
基金項目: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托妮莫里森小說中的生存美學研究(AHSKY2020D129);淮南師范學院2023年度校級科學研究項目:高校“四新”建設背景下大學英語教學中大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研究——以淮南師范學院為例(542023XJYB022)
作者簡介:王婷婷(1983-),女,湖北隨州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Post-pastoral in A House for Mr.Biswas
WANG Tingting1,ZHANG Qicai2,3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Huainan,Anhui? 232038,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3.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Anhui 23200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A House for Mr.Bisw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pastoral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In this novel,in the post-colonial era,colonist countries are oppressing Trinidad in various ways.The mindset of the people in Trinidad is then assimilat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and the oppressed Trinidadians join them in exploiting nature.Nature,with its unique agency,resists mens oppression and avenges itself.It is true that nature may inflict death upon men,but death is just one of the many facets of nature.Nature is in a balance of fluidity between death and birth,growth and aging.Nature instills awe,which may count as the start of a new era where anthropocentricity may be abandon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is likely to be radically transformed.
Key words:A House for Mr.Biswas;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post-pastoral; nature; awe
印度裔英國作家奈保爾(V.S.Naipaul)被認為是21世紀最無爭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59,其代表作《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以下簡稱《房》)被許多讀者視作他最具影響力的作品[2]3,受到學者廣泛關注。許多學者從后殖民主義視角探討了作品中離散所導致的身份認同危機[3-5]。也有學者對《房》中的自然予以了深切關注,如布魯斯·金(Bruce King)就關注到了《房》中自然的暴力,但是他主要著眼于小說中自然的象征意義,認為自然的暴力象征著具有破壞性的空虛和無序[6]41-57。還有學者關注到《房》所反映出的生態危機[7],但是未能分析生態危機產生的深層次原因。綜合來看,已有相關研究的關注點要么是后殖民語境下人的困境,要么是生態危機,要么是自然的暴力,較為狹隘和片面。后殖民生態批評理論框架下的后田園詩研究將人的困境、生態危機以及自然的能動性共同納入關注視野,因此從后田園詩角度探究《房》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有助于彌補以往研究的不足。
一、田園詩、反田園詩、后田園詩
田園詩也稱牧歌,通常描繪鄉村、田園優美的自然風光與牧民的生活與生產活動。作為文類,它是一種詩歌形式,歌頌鄉村生活的簡樸、純潔、與自然的和諧,以及農牧民生活的快樂和單純。作為一種歌頌鄉村生活、自然環境的文學模式,它可以出現在詩歌中,也可能出現在小說、戲劇等其他文類中[8]84。但是,田園詩本質上是對鄉村生活的一種虛構的或者理想化的模仿,在面對社會不公時表現出了麻木和膽怯,包藏了遁世和逃避的態度,根本無法成為變革根深蒂固的社會體制的催化劑[9]83。
與之相對,“反田園詩(anti-pastoral)則是對田園詩的這種理想化和浪漫化傾向的質疑,是對鄉村生活的更加現實主義的呈現,是一種關于鄉村的去理想化和去浪漫化的寫作”[8]88。但是反田園詩在認識架構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狹隘性。“在現代社會的認識架構下的生態批評,關注的不僅僅是‘鄉村和‘風景,更多關注的是環境。我們在知識、態度和意識形態方面都取得了進步,這個我們否認不了。”[10]147一種對“成熟的環境美學”(matur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的追求應運而生,這種新的嘗試能夠跳出田園詩、反田園詩的圈囿,有助于我們從整體上把握自然世界[10]148。吉福德(Terry Gifford) 把追求這種“成熟的環境美學”的文學作品命名為“后田園詩”(post-pastoral)[10]150。
吉福德在1999年出版的專著《田園詩》(Pastoral)中歸納了后田園詩作品呈現的主要特點:對于自然的敬畏;我們所處的自然世界具有創造性和毀滅性,在生死、死亡和重生、生長與腐朽的流動性中處于平衡狀態;我們的內心狀態受外部世界影響,內心也映射了外部的自然;自然與文化密不可分;逐漸提高的生態意識可以提高生態良知;對于自然的掠奪與對于弱勢群體的壓迫、剝削密切勾連,要改善人和自然的關系,人類需調和自身內部矛盾。
二、弱勢群體和自然受到的壓迫
吉福德關于“后田園詩”的論述得到了其他學者的呼應。哈根(Graham Huggan)和蒂芬(Helen Tiffin)將“后田園詩”闡釋為:堅持生態原則的后田園詩反映了環境正義和社會正義之間的共生關系,這種關系不僅僅體現在局域層面,還體現在更高更寬廣的層面[9]115。這種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與環境種族主義相通。環境種族主義強調“種族與環境在理論和實踐中的緊密關系,對一方的壓迫與對另一方的壓迫相連,對一方的壓迫會強化對另一方的壓迫”[11]145。《房》中特立尼達的遭遇印證了這種觀點,西方殖民國家從過去到現在持續地壓迫著特立尼達人民和自然,而且對兩者的壓迫之間還存在著密切聯系。
有研究者認為“我們在小說(《房》)中看不到殖民者的身影,也很難尋繹到什么宗主國與殖民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緊張的對立與沖突的痕跡”[4]43,但事實上小說對于英美等國的殖民行為存在著濃墨重彩的描述。首先,殖民行為以軍事存在的形式出現。當圖爾斯家族在矮山暫住時,美國人也來到村子里并打算在那里修建一個營地。軍用卡車不分晝夜地穿過矮山,當卡車數量不夠時,他們還租用了W.C.卡特爾的卡車[12]328。為了方便運輸,美國人在西班牙港外修建了“平整光滑的美國高速路”,美國營地里“有戴著頭盔拿著步槍的美國士兵站崗”[12]403。其次,英美等國操縱了特立尼達的行政管理乃至法律。隨著美國人在特立尼達的人數增長,為美國人工作的非法移民也越來越多。為了保證有足夠的勞動力,美國不僅迫使特立尼達接收這些來自其他島嶼的非法移民,還迫使特立尼達頒布法律“禁止像莎瑪以前那樣無故驅逐房客”[12]348。
《房》中,英美等殖民國家在特立尼達維持著大量軍事存在,操控著特立尼達的行政管理以及法律,并以此為基礎將特立尼達轉變為經濟作物種植地和工業產品傾銷地,造成特立尼達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首先,特立尼達的農業經濟結構嚴重失衡。文中,作者筆下的特立尼達無垠的土地上幾乎盡是甘蔗和稻谷,其他農作物非常少見。特立尼達人民選擇這種單一的農業經濟結構,除了是其較為契合特立尼達獨特的地理特征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殖民統治的影響。西方殖民者一旦完成了入侵,建立了行政架構,他們會刻意地引入外來的植物、動物,對當地的生態系統造成巨大的影響[9]6。殖民者利用加勒比地區優越的自然條件、肥沃的土地和從非洲販賣來的黑奴大辦甘蔗、咖啡等經濟作物種植園,而特立尼達則成為宗主國的“種植園”“大農場”。二戰結束后,加勒比地區的一些島嶼雖然注意到農業的多樣化,擴大了糧食作物的生產,但經濟作物仍是農業部門的主體[13]14。畸形的單一經濟結構使加勒比地區長期處于貧困和落后狀態,使得加勒比地區必須依靠經濟作物換取殖民國家的工業品和糧食[13]16。文中,港口的起重機不停地裝運著進口來的面粉,裝運任務是如此繁重,以致于忙中出錯,面粉“從高空落下,不幸砸死了原來的船務記者”[12]263。從這個細節可看出這個國家的面粉生產不夠充足,必須依賴進口。可即便進口了面粉,“在店鋪里,爭奪儲存的生滿象鼻蟲的面粉的糾紛時有發生”[12]304,面粉的供應仍然是供不應求。其次,特立尼達嚴重依賴英美殖民國家工業產品。英美汽車經銷商在特立尼達的生意很是火爆,為了擴大影響,他們把宣傳廣告印制在日歷上。文中,就連主人公畢司沃斯購買的也是一輛英國產的普萊福克特車。除了這種表面正當的、冠冕堂皇的工業品輸入,文中還描寫了非正當的工業品輸入。當畢司沃斯登上南美洲旅行路線的美國船時,“船上的廚子邀請他加入走私相機鎂光燈的團伙”[12]263。這些英美工業品的大行其道,表明特立尼達的工業發展嚴重不足,工業品市場已被資本主義大國侵占[14]25。
一方面,殖民國家通過在特立尼達的軍事存在、對行政管理和法律的掌控實現了對特立尼達人民的剝削;另一方面,殖民國家大肆攫取特立尼達的自然資源,破壞了特立尼達的生態環境。此外,殖民國家對特立尼達生態環境的破壞不僅進一步加劇了對特立尼達人民的控制,也加劇了特立尼達人民的文化身份認同危機。
當成年的畢司沃斯回到幼時待過的地方時,他看到的是林立的石油鉆塔和布滿油污的泵,兒時的水塘已被抽干,“那個他曾經在里面看見黑色小魚的小溪已經被水壩截住,變成了一個水庫”[12]24。英美殖民國家參與和掌控的油井[15]、水壩[16]等大型現代化工程,如同那些種植了經濟作物的田地一般,占據了畢司沃斯和外祖母的故居和自然的領地,改變了特立尼達的生態環境。石油鉆塔和水壩的修建,不但導致數以萬計的當地人民被迫從故土搬離,給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不可逆的影響,而且也給特立尼達人民帶來了隱性的危害。在發展中國家,水壩的建造總是會涉及到官僚政客、水壩承建方和作為國際資本載體的世界銀行等諸多角色之間的勾聯[17]3。雖然有來自于世界銀行的貸款扶持,但興建大壩的巨額造價必然會將如印度、特立尼達這樣的(前)殖民地國家更進一步地推向債務包袱之中[17]35。因此,與世界銀行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英美殖民國家對特立尼達的掌控也勢必會加劇。大型工程興建的隱性危害還表現在特立尼達人民的文化身份認同危機上。自然和文化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土地定義我們,而不是我們給土地下定義。”[18]175興建水壩和石油鉆塔改變了特立尼達的自然環境,包括特立尼達在內的加勒比地區成為“世界上地貌被人為改動程度最大的地方。”[19]64自然環境的改變也必然會給特立尼達人民的文化身份認同帶來影響。“外祖母的房子也消失了”[12]24,水壩和油井等人類工程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特立尼達人民與歷史和傳統的聯系。畢司沃斯的臍帶曾經被埋在土地里,象征著人與土地的連接,但是如今埋在土地里的臍帶消失了[12]24,意味著當地人與土地的親密聯系也被割斷。以往土地具有的“不規則”[12]24性、特殊性被規則性和“整齊劃一”[12]24所取代,土地不再是生活體驗記憶的載體,土地被抽象化為沒有歷史意義的幾何空間,喪失了神性;而土地屬性的統一化也映射了個人屬性的特殊性的喪失,如象征畢司沃斯個性的被埋掉的第六根手指“已經化作塵土”[12]24。
三、弱勢群體對自然的壓迫
英美等殖民國家通過引入單一的經濟作物、興建大型工程改變了特立尼達的生態系統以及特立尼達人民和土地關聯的生活理念和文化,造成了包括來自印度的移民在內的特立尼達人民的文化身份認同危機,當地人民的文化和傳統的多樣性逐漸被西方文化的統一性所替代,當地人民的心理逐漸被西方同化。例如,在圖爾斯家族中,圣誕節被當作重要的節日度過,而印度特有的宗教節日則逐漸式微,墻上的宗教掛畫已經被英美汽車經銷商分發的日歷以及一副巨大的象征著消費主義的印度女影星的照片擠沒了[12]190。他們向往著宗主國優良的教育,急于將自己的孩子送往英國和美國。當留學英國的奧華德要從英國回來時,圖爾斯家族的每個人都興奮不已,認為他具有“非同凡響,甚至超乎常人的理解”[12]419。他們把英美雜志編輯給出的寫作建議奉為至寶;他們聆聽的是美國歌曲“你永遠在我心中”[12]397;他們把擁有一套莫里斯家具當作是身份的象征;他們為了能夠獲得更多的健康知識閱讀的是美國雜志《你的身體》;他們的孩子們也覺得給美國人工作是體面的。由于英美等殖民者給居住在特立尼達的這些印度人在宗教、教育、音樂、就業選擇、生活方式和健康意識等方面的意識形態上的影響極其深遠,他們會錯誤地把宗主國當作天堂。當阿南德在英國抑郁不得志時,畢司沃斯還給他郵寄了一本由兩名美國女性心理學家編著的《以智慧克服緊張》[12]468,心甘情愿地讓美國人控制著自己和兒子的心理和思想。
在心理和思想被英美等殖民國家控制以后,特立尼達人民效仿英美等殖民者肆意掠奪自然的作法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殖民國家進行全球范圍的征服和統治的過程中,其他民族被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可以像動物一樣處置;其他民族也被同化并接受他們對待自然的觀念。”[9]6
在《魯濱遜漂流記》中,當魯濱遜因為輪船失事而漂流到偏遠的小島上以后,他即刻在島上勘察地形,接著開始圈占土地,種植農作物,飼養動物。他自己手工制做面包和各種陶器,他解救了黑人“星期五”并和星期五建立了主奴關系。魯濱遜在小島的經歷被看作是資本主義擴張的典型代表。而當圖爾斯家族舉家搬遷到矮山之后,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重復了魯濱遜壓迫自然的殖民過程。矮山這塊土地像是一塊“處女地”,在這里他們發現了“克里斯托弗·哥倫布路”的指路牌[12]321。即便學界對于哥倫布是否為發現美洲大陸的第一位歐洲探險家仍然存有爭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哥倫布成為了殖民主義“發現”(discovery)的代名詞。“發現”可以和殖民的暴力聯系起來[9]116。圖爾斯家族在矮山發現的哥倫布的指路牌,一方面可以理解為特立尼達所承載的慘痛的殖民創傷記憶,另一方面也預示了被西方文化洗腦、同化了的特立尼達人民將重復殖民者的作法,給這片土地帶來新的暴力。
圖爾斯家族到達矮山以后,開始對矮山周圍進行觀察、凝視,而隨之產生的是強烈的剝削自然的欲望。可可樹、咖啡樹、豆類植物均是經濟作物,他們可以由此獲利;飼養牛、羊可以給他們帶來經濟回報,騎馬讓他們享受了奴役動物的優越感;在他們眼中,各種樹木的功能僅僅在于可以變成木板,樹木只是貨幣的符號而已。當圖爾斯太太看到藤蔓時,她說“就像繩子那樣結實,孩子們可以用來跳繩”[12]322。當看到荒廢的花園時,她說“這是蓋禮拜堂的好地方”[12]322。自然在他們眼中只是可以利用的客體和他者而已,這種想法是源于工具理性的生態擴張主義的典型表現[20]25。他們帶著這種目光看待自然,破壞自然的種種行為與殖民者如出一轍。
他們不僅具有剝削自然的欲望,還已然具備了剝削自然的能力,并且以擁有此種能力沾沾自喜。生火是人類的一個重要技能,它使得人類可以吃上熟食、更好地保護自身安全。此外,生火的技能也讓人類擁有了更大的破壞自然的能力。在矮山居住時,圖爾斯家族中的人就表現出了他們對于生火能力的集體無意識的自豪感。“孩子們向往放火燒林子如同向往一個慶典。”[12]342他們不滿足于小規模的火焰,于是找來當燈油的柏油充當助燃物,把柏油隨意澆在灌木叢上點著。當火勢變大時,“他們議論著火苗不同的顏色,他們心滿意足地傾聽著火焰燃燒時發出的噼啪作響的聲音”[12]344。使用火的能力如同魯濱遜的火槍一般,讓人類在與自然的遭遇中所向披靡。
受到欲望的驅使,他們用自己不斷增加的技能武裝自己,開始了對自然的蠶食鯨吞。圖爾斯家族在矮山嘗試了各種利用自然的方式,這些方式也成為了人類不同產業的縮影,每種產業都以自然的損害為代價。他們開辟了土地,成功地種植了南瓜。塔特爾砍倒了十幾棵雪松,雇傭黑人塞爾菲爾為他制作家具。他們生產了書架、桌子、衣柜。制作家具成為人類手工業的象征,加工對象則是自然界中的樹木。而雇傭黑人同歐美殖民國家在資本原始擴張時期依靠黑人勞動力的作法有著巨大的相似之處。塔特爾賣了一棵又一棵的雪松,“格溫德賣了一卡車又一卡車的橙子、番木瓜、鱷梨、酸橙、西柚和可可豆以及豆子”[12]328。他們的買賣行為成為商業活動的象征,但是他們獲取商品的手段卻是只看中眼前利益、無計劃非可持續性的濫砍濫伐和肆意采摘。塔特爾販賣木板積累了資金以后買了一輛卡車出租給美國人,格溫德販賣水果后西裝革履“開出租車招徠美國人的生意”[12]353。他們成為第三產業從業者的代表,服務了利用和剝削特立尼達自然和人民的美國人,而結果就是自然會間接地受到更多破壞,特立尼達人民會受到更多壓迫。更為嚴重的是,塔特爾在矮山開辦了象征著開采業的采石場,甚至還售賣土地。他對自然的剝削變本加厲,牟利的對象演化成萬物賴以生存的土地本身。
四、讓人敬畏的自然
在許多文學作品中,自然都表現出了自主能動性。如,《古舟子詠》中的老水手射殺了信天翁之后,他和其他水手就遭遇種種怪異和災難。在長詩的最后,全船所有的水手,除了老水手,都以死亡告終。在水手冒犯自然和遭受毀滅性的災難之間,可以明顯地看到自然復仇的能動性。《貝奧武夫》(Beowulf) 第三部分巨龍攻擊耶阿特人[21]102以及《白鯨》中大白鯨毀滅皮闊德號捕鯨船和亞哈船長的做法都體現了自然復仇的能動性。哈拉維(Donna Haraway)使用“狐狼”(coyote)一詞指稱具有能動性的自然,這一稱謂充分表現了自然的詭計和狡詐[22]161。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房》中,在英美等殖民國家和特立尼達人民的壓迫下,自然表現出了讓人敬畏的能動性和多面性。
首先,《房》中的自然拒絕配合人類,它抗拒人類的愿望。童年的畢司沃斯企圖和小牛建立良好的溝通。他想喂給小牛各種各樣的青草,“但卻無法理解為什么小牛不情愿從一個地方被領到另一個地方”[12]10。畢司沃斯把小牛帶到小溪邊,想讓小牛嘗試水中的竹葉,“而小牛懶洋洋地悲哀地站在他的旁邊,對竹葉沒有一點興趣”[12]11。圖爾斯家族來到矮山,想要在那里飼養牛和羊。但是“母牛們沖破了板球場上的圍欄。綿羊們四散逃竄,沖破了竹樁,把樹苗啃得精光”[12]327。家族中的寡婦們想要在這里辦一個養雞場,但“雞躲到樹叢里去,學會飛到高處,并把雞蛋下在寡婦們找不到的地方”[12]337。
其次,《房》中的自然是丑陋的自然,抵抗著人類的審美訴求。一直以來,人們大多習慣于華茲華斯筆下那美麗、給人心靈帶來慰藉的自然。在他的筆下,自然“有一些力量能使我們的心受感染”[23]73,自然“會用寧靜和美打動”[23]31人們,能“引導我們從歡樂走向歡樂”[23]191。而《房》中的自然卻呈現不同的樣態。畢司沃斯見證的自然界往往是“錯綜復雜的灌木”與“枯朽的滋生著蚊蟲的叢林”[12]142。畢司沃斯看到的樹木似乎“都在茂盛的同時枯萎……沒有生命的光彩”[12]161。就連海水散發的都是“陳腐的咸腥味”[12]248。自然展現的是荒涼與雜亂,壓抑人心,無法給人類帶來審美的愉悅。畢司沃斯心灰意冷地發現,在“這片每天被太陽灼烤的單調乏味的綠色土地上絕無浪漫可言”[12]53。
最后,《房》中的自然威力巨大,在遭受人類壓迫時并非一味地逆來順受,而是會報復人類。《房》通過狂風和暴雨顯示了自然的巨大威力。“大雨真正落下來之前先帶來狂風的咆哮,預示著大雨的降臨:風的咆哮是風卷過樹林,瓢潑大雨橫掃過遠方的樹林的咆哮。然后就是急驟的敲打屋頂的雨聲,隨之雨聲淹沒在好似千軍萬馬齊奔之中,聲音是如此之響。”[12]228“雨點敲打著濕透的地面,濺起一道道白光。”[12]229“屋頂一陣晃動,一聲嘎吱響,接著是延續的噪聲,阿南德知道一張瓦楞鐵皮被風扯掉了。”[12]231“一陣怒號席卷了他們……雨像鞭子一樣抽打進來。”[12]232《房》中的自然的暴力比起李爾王遭遇的狂風驟雨有過之而無不及,它不僅摧毀了畢司沃斯剛剛建好的房子,也擊垮了他的精神。此外,隨著圖爾斯家族在矮山對自然的瘋狂掠奪,自然開始有意識地報復圖爾斯家族。“吉祥、德行都已經從這個家庭里消失了。”[12]336“一連串的死亡接踵而來。一個叫沙門的采橙子并送孩子們去上學的女婿在一個下雨的早晨,從長著苔蘚的橙子樹枝上滑下來,摔斷了脖子。他幾乎立刻就斃命了。”[12]333接著哈瑞死了,然后是帕德瑪。如同拉圖爾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行動者一般,自然具有了自主行動的能力,給圖爾斯家族帶來了巨大的災禍。
自然的威力和報復造成的死亡讓人敬畏,但死亡畢竟是自然眾多面孔中的一副。具有后田園詩特點的文學作品讓我們“認識到我們所處的自然世界具有創造性和毀滅性,在生死、死亡和重生、生長與腐朽的流動性中處于平衡狀態”[10]153。畢司沃斯出生時,他的外公處于一種“老不中用”和“等死”的狀態,認識到“我們無法改變命運”[12]1。畢司沃斯彌留之際已經無力償還房子貸款時,女兒賽薇回來了,她找到了一份薪水豐厚的工作,此時一切都有了轉機。“一切都水到渠成,畢司沃斯先生剛剛停付薪水賽薇就開始工作了。”[12]470在他衰老彌留之際,新的一代風華正茂。畢司沃斯給兒子寫信說:“在這之后你怎么能還不相信上帝呢?”[12]470或許我們可以把“上帝”和“命運”理解成一種抽象意義上的理念和原則,在成長與衰老、死亡與重生的轉化中,“上帝”和“命運”象征著自然那種具有張力和辯證的平衡。這種認識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人類中心主義,它促使我們認識到自己的渺小,敬畏自然。而敬畏自然這種生態意識也是改善生態良知的重要前提[10]163。
五、結束語
《房》中,英美等殖民國家或國際資本在殖民地國家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們以各種形式壓迫著殖民地國家,這種壓迫與對自然的壓迫緊密聯系。受到英美等殖民國家的影響,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思想和心理一定程度上也被西方同化,他們加入到掠奪自然的進程中。而自然并非一位地被動,它擁有能動性,會抵抗人類想當然的意愿,并通過巨大的力量向人類示威和報復。自然是多面的、流動的,它給人類帶來死亡,也孕育著新生,死亡與新生、衰老和成長在自然中不斷轉化。自然的偉大讓我們敬畏,而這種敬畏的態度也成為人類放棄人類中心主義和改善人與自然關系的起點。
《房》中,特立尼達人民意識到自然是讓人敬畏的,但是他們還未能清晰地認識到自身對于土地和自然的責任,也未能采取具體的措施和行動來彌補人與土地、自然之間破裂的關系。在《大河灣》《抵達之謎》以及“印度三部曲”(《幽暗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等作品中,奈保爾以非洲、英國與印度等地域為考察對象,繼續著后田園詩書寫,保持著他對后殖民語境下人民與自然關系的關注。在這些作品中,人與自然的關系、人的生態意識均有變化和發展,因而對于奈保爾作品的后田園詩研究仍有巨大發掘空間。
參考文獻:
[1] 明皓.《非洲的假面劇》中的非洲真相[J].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5(3):59-63.
[2] ROB NIXON.London Calling[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 張德明.懸置于“林勃”中的幽靈:解讀《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J].外國文學研究,2003(1):81-86,174-175.
[4] 胡志明.《畢司瓦斯先生的房子》:一個自我反諷的后殖民寓言[J].外國文學評論,2003(4):42-52.
[5] ZHOU MIN.Postcolonial Identities: A Study of V.S.Naipaul's Major Novel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6] BRUCE KING.V.S.Naipaul[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3.
[7] 張奇才,王婷婷.《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生態解讀[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8,39(1):109-111.
[8] 張劍.田園詩[J].外國文學,2017(2):83-92.
[9] GRAHAM HUGGAN,HELEN TIFFIN.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M].New York:Routledge,2010.
[10] TERRY GIFFORD.Pastoral[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9.
[11] DEANE CURTIN.Environmental Ethics for a Postcolonial World[M].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2005.
[12] 奈保爾.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M].余珺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13] 學時.關于加勒比地區的農業發展[J].拉丁美洲研究,1987(5):14-19.
[14] 江時學.加勒比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歷程[J].拉丁美洲叢刊,1983(6):25-29.
[15] 梅心.特立尼達和多巴哥[J].世界知識,1966(Z1):30-31.
[16] HOLLIS RESERVOIR.Wikipedia[DB/OL].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llis_Reservoir.
[17] ARUNDHATI ROY.The Cost of Living[M].London:HarperCollins,1999.
[18] JIM CHENEY.Nature/Theory/Difference[A].Warren,Karen J.Ecological? Feminism[C].London:Routledge,1994.
[19] ELIZABETH DELOUGHREY.Quantum Landscapes[J].Interventions,2007(1): 62-83.
[20] 朱新福,張慧榮.后殖民生態批評述略[J].當代外國文學,2011,32(4):24-30.
[21] LAWRENCE BUELL.Some Emerging Trends[J].Qui Parle,2011(2):87-115.
[22] TIMOTHY CLARK.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23] 華茲華斯.華茲華斯抒情詩選[M].黃杲炘,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責任編輯:吳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