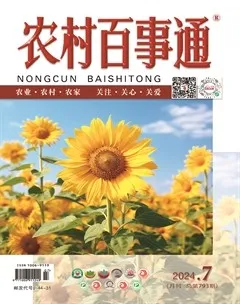大山里種出好咖啡
巍峨的高黎貢山,奔騰的怒江,高海拔、好生態,造就了云南省保山市小粒咖啡的獨特品質。這個種咖啡的好地方,也是怒江雪林農產品種植專業合作社負責人胡樹林的家鄉。
胡樹林,云南省保山市隆陽區芒寬彝族傣族鄉人,2009年中專畢業后,回到家鄉創業,從賣咖啡豆、制咖啡豆再到種咖啡豆,見證了當地咖啡產業的發展。眼下,他正積極探索從生產大眾咖啡豆到生產精品咖啡豆的轉型之路。
賣豆
2009年,胡樹林中專畢業后決定返鄉創業。父親胡躍華得知后,堅決反對,他希望胡樹林趁著年輕,應該先去外面歷練一番。胡樹林對父親說:“咱保山實現咖啡產業化這么早,何愁干不成一番事業?”此后,胡樹林跟著父親,在家里近20畝的咖啡豆地里一年到頭地忙活著。“種咖啡豆,父親更有經驗。但賣咖啡豆,我有想法,也敢闖蕩。”胡樹林聯系當時收購咖啡豆的貿易公司,自薦成為咖啡豆收購代理。當時市場上“一豆難求”,聽說胡樹林能收來咖啡豆,貿易公司答應預支貨款請他代為收購咖啡豆。
第一單,胡樹林轉手了300噸咖啡豆,每公斤賺了一兩元的差價,賺到了“第一桶金”。但隨后幾年不斷腰斬的咖啡豆期貨價格,很快讓他沒了脾氣。2013年后,伴隨國際咖啡主產區種植面積的迅速擴大,咖啡豆價格暴跌。收來的咖啡豆賣不出去,胡樹林虧損嚴重。
在父親的安慰之下,胡樹林牽頭成立合作社,拉著鄉親抱團取暖。“父親告訴我,面對價格漲跌,要把目光放長遠些。”胡樹林說。
在咖啡豆價格谷底苦苦支撐了6年后,國際咖啡豆期貨價格再次起飛。隨著國內咖啡連鎖門店逐漸向更多城市延伸,越來越多的人有了品飲咖啡的習慣,胡樹林牽頭的合作社咖啡豆的銷售開始好了起來。
制豆
長期以來,云南咖啡豆價格跟著國際市場走。云南的咖啡豆種植成本相對較高,當咖啡豆期貨價格低時,國際采購商傾向于采購種植成本更低的大產區咖啡豆。胡樹林想到了一條新路子:外貿公司不收,咱就內銷。
掛耳咖啡、速溶咖啡、精品咖啡……如今合作社的主要收入來源,已經不再是轉售咖啡生豆了。
這樣的轉變,最初卻是無奈之舉——從農戶手里收來的生咖啡豆賣不出去,時間稍長就會發霉。為了延長保存期限,胡樹林買來烘焙設備,自己烤咖啡豆。
最初的客戶,主要是咖農。家中來了客人,咖農會給客人煮上一杯自己種的咖啡,臨走時再給客人送上幾袋咖啡。慢慢地,上門要貨的咖農越來越多,胡樹林順勢印制包裝,靠著熟人傳播,加工的咖啡豆慢慢有了穩定的客源。
看到希望后,胡樹林先是帶著產品去趕集,后來又到商場、超市去推廣。為了推銷自己的產品,他現磨咖啡豆請商超工作人員品嘗,“支持下本地咖啡吧,只要店里擺上我們的產品,賣完了再付款都行”。剛開始每家店每月只能賣出三四包咖啡,現在已是成箱成箱地賣。“最期盼的就是接到補貨的電話,我巴不得天天出去送貨!”胡樹林說。隨著怒江沿線旅游開發不斷推進,合作社的咖啡還成為特色旅游產品,被更多游客帶到了大山之外。
經過市場的潮起潮落,如今的胡樹林格外冷靜。他說,周邊客戶數量有限,要想不再受制于人,必須不斷拓展市場;而要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要么靠價格優勢,要么靠產品品質。
“保山小粒咖啡的畝產量相對較低,如果做成普通商品豆出售,難以獲得市場競爭優勢,出路一定是做精品豆。”胡樹林分析,“小產區的精品咖啡豆能單獨定價,從而降低國際咖啡期貨價格波動帶來的影響。”
種豆
要想做精品咖啡豆,必須從源頭把關。不善于種咖啡豆的胡樹林,2020年開始再次回歸咖啡豆種植園,除草、施肥、試種新品種,重新學習種豆。
要做自己的精品咖啡,首先要確保原材料供給。胡樹林說:“認準了這個行業,我就想長期干下去。沒有一定面積的自有基地,就沒法保證高品質的原料;沒有足夠的高品質咖啡,就沒法打開精品咖啡的市場。”
胡樹林知道,大眾咖啡豆銷售主要靠批發,而精品咖啡豆則要做零售,更加注重品質。“好品質的第一關,就是好品種。”胡樹林把自己流轉來的土地作為試驗田,試種瑰夏、鐵皮卡、黃波旁等更加小眾的咖啡豆品種。
試種品種中,價格最高的是瑰夏,有的小產區一公斤瑰夏咖啡豆能賣好幾千元。胡樹林在海拔超過1600米的地方種了幾畝,“能不能種出來?烤出來還是不是原來的風味?能不能賣上高價?”胡樹林當時也很忐忑。
早期試種的鐵皮卡、黃波旁逐漸掛果,有些感興趣的咖農上門要苗,胡樹林二話不說就贈送。胡樹林依托合作社加強對咖農種植環節的培訓,盡可能幫助大家降低種植風險。如今,合作社已有咖農103人,種植面積超過1500畝,銷售額達到600萬元。
對于未來,胡樹林信心滿滿:“只要種得好,就不怕合作社發展不好!”
(摘編自《人民日報》 作者:楊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