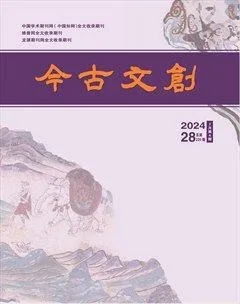哲學內容與形式的對立及統一
【摘要】《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在《〈科隆日報〉第179號的社論》中指出德國哲學似乎具有偏離現實的傾向。德國哲學抽象的形式和思辨的內容受到當時人民的指摘,但事實上真正的哲學是時代和人民的產物,哲學始終是對現實世界作出的帶有自身特色的反映。馬克思看到德國哲學所面臨的困境——具體內容與抽象形式間的對立,并指出德國哲學形成如此的局面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馬克思在對海爾梅斯的批判回應中,為德國哲學面臨的困境找到合適的出路——世界哲學化與哲學世界化。
【關鍵詞】哲學;《科隆日報》;馬克思;德國哲學困境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8-006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22
1842年,《科隆日報》的編輯卡爾·海爾梅斯(Karl Hermes),作為一位保守的天主教徒和政府代理人,他在該報第179號上撰寫了一篇社論向政府告密,指責《萊茵報》和《科尼斯日報》非法刊登一些青年黑格爾學派的文章,質疑這些報刊的政治立場,認為他們存有攻擊基督教和普魯士政權的嫌疑。對此,馬克思于1842年6月28日至7月3日寫下《〈科隆日報〉第179號的社論》(以下簡稱《社論》)對海爾梅斯作出回應,揭露《科隆日報》的虛偽面貌。馬克思在反駁海爾梅斯的同時,表露出對哲學與時代問題的獨特思考和集中探討。盡管整篇文章的字數不多,但馬克思在其中展現了德國哲學遇到的二律背反問題:一方面,哲學不同于宗教神學,始終接觸時代,是現世的智慧;但另一方面,哲學本身保持著自身的歷史特點,具有不可忽視的思辨性和抽象性。面對哲學具體內容與抽象形式的對立,馬克思堅定維護哲學的話語權,提倡人民自由的理性。
一、哲學內容與形式的對立展現
在《社論》這篇短作中,馬克思論及了兩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是:哲學是否應在報紙的文章里探討有關宗教事務的內容?針對這一問題,馬克思指出只有批判了這個問題,才能得出答案,而在批判此問題的過程中,馬克思闡述了自己對于哲學本性的理解以及哲學與世界關系的看法。馬克思在探討國家與宗教的關系時,看到了德國哲學(實際上指代更確切意義上的德國古典哲學)所面臨的問題。當哲學受到時代的非議和來自報刊的否定時,馬克思堅定地拿起理論的武器,對哲學真正內容和具體形式的關系展開了探析。
馬克思指出德國哲學存在著脫離現實的傾向。首先,德國哲學具備其自身特色,即追求體系的完滿。正如康德、黑格爾等德國古典哲學家,他們一味強調要構建龐大圓滿的哲學體系,致力于理性法則的自我展現。長期抽象的哲學討論中貫徹著脫離現實的形而上概念和晦澀難懂的哲學概念關系,德國古典哲學家所探討的似乎總是形而上的內容,他們對現實世界的構造和體系總是抱持一種高高在上的不屑態度。因此,德國哲學基本不參與討論現實政治,始終以一種旁觀的目光注視社會。其次,德國哲學按照其體系的發展進步來看,始終是晦澀難懂的,因為哲學所討論和使用的概念內容似乎總是超脫于現實之外的形而上學。如此一來,哲學自身的演進變化對于普通人來說似乎總是不切實際的,“就像一個巫師,煞有介事地念著咒語,誰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1]219。
哲學自身的抽象性質使得人們對此常常退避三舍,而德國哲學愈演愈烈的思辨性也將哲學與人們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并且,哲學始終也沒有嘗試把“禁欲主義的教師長袍”變成和報紙一樣的輕便服裝,他們摒棄膚淺簡單的言論,著力于采取喃喃自語的方式去闡述真理,哲學始終拒斥輕便的方式講述內容,因為哲學本身的內容正是如此的晦澀和抽象,一旦采取極為下里巴人的論述形式,那么哲學探討的內容就很難敘述清楚。哲學探討的抽象內容規定了哲學的論述方式亦是如此,馬克思也為之辯護道,哲學本身,一定不會如報紙一般如此迅速且充滿激昂地討論時事,海爾梅斯以報刊的方式去要求哲學改變路徑顯然是不合理的。
然而,盡管德國哲學有些固守傳統,但其哲學始終是時代和現實的產物。馬克思看到了哲學的本性,指出哲學的現實性,哲學是和現實相互作用的。哲學是對現實的反映,盡管不是對現實簡單直接的反映。哲學不是懸置在世界外部,它所觀照的正是這個現實世界。只不過不同于其他領域,哲學是理論展現早于實踐活動。馬克思強調哲學并不是人們所誤解的那樣,好似漂浮于世界現實之外,哲學擁有其現實性,不能因為哲學與宗教神學或其他學科采取的敘述方式不一致就斷然否定其現實性。顯然,馬克思在這里偶爾跳出了黑格爾的哲學視野,黑格爾關注哲學的反思性和后發性,而馬克思則偵察到哲學作為一種理論對于現實世界的引導性,哲學作為一種時代精神的精華,立足于現實,也同樣對現實具有批判的反作用。馬克思闡述哲學具體內容與現實的不可分割性,因為哲學總是透視時代脈搏,抓住時代中各種運動和事件的集中表現,從而對時代現實進行整體性的把握。哲學的具體內容與抽象形式是不可對立而語的,二者是統一、相互尊重的,正是其思辨的內容規定了抽象的形式,而思辨內容的實質是對具體世界本身的超越性探析。回到馬克思在《社論》中所研究的這個問題,馬克思強調哲學是由于時代的要求而進入世界的,哲學當然擁有在報紙上對于此岸世界內容的發言權,這是源自哲學對于現實的深切觀照和體察。
至此,哲學的具體內容與抽象形式間的矛盾便昭然若現。一方面,以往的德國哲學始終帶著濃厚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而顯得高高在上;另一方面,哲學的內容本性要求哲學必須對現實世界做出反應。由于黑格爾本人和青年黑格爾派始終保持哲學的晦澀特性,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進行純粹理論的批判運動,加之當時普魯士政府對于思想自由的強烈限制和打擊,當時的哲學家不得不采取更為晦澀的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思想以免受到政府的攻擊。如此一來,德國哲學的內容便愈加晦澀抽象,在人們眼中的哲學似乎始終是一種彼岸的思想,那么人們對哲學形成的誤解和責難便情有可原,其晦澀抽象的形式使人們很難理解并把握其核心的思想要旨,只是淺于表面便斷然拋棄。何況由于當時公眾對宗教神學思想采取的是極為堅定的信仰態度,以至于哲學更被棄之邊緣角落。但德國哲學形成如此的困境是當時社會的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彼時公眾對于哲學的態度也是當時歷史背景和現實根源所導致的。
二、哲學內容與形式的對立源頭
馬克思對哲學的話語權問題十分重視,但哲學之所以在當時的公眾面前被束之高閣,除了哲學自身孤寂和晦澀的特點之外,也有時代背景的因素。回到《萊茵報》時期的社會環境,德國落后的社會狀況以致對哲學自由發言的打壓,神學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性對哲學的威脅,德國官方政治對共產主義新思潮的極致性管控,種種因素導致德國哲學受到人們的摒棄和責難,德國哲學繼續發展的道路極其艱巨。馬克思犀利地發現哲學具體內容與抽象形式間的對立問題,并試圖對此進行調解、找尋二者統一的路徑。但找尋問題的解決之路必須要回到問題的發生之中,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哲學之所以出現如此的困境,是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和思想環境息息相關的。
首先,德國在19世紀40年代時期的經濟政治狀況是十分落后的。1840年前后,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結束,工業革命之風迅速向整個歐洲大陸傳播。然而當時的德國是一個不統一的國家,屬于各種分散的城邦,工業革命面對極大的挑戰,并未形成龐大的規模。德國在19世紀初期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社會,大工業生產沒有統一的國內市場,并且在國際貿易上也受到大西洋沿岸國家的排擠。而19世紀30-4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雖然有了較快的發展,但資產階級力量非常之小,不僅受到封建統治勢力的打壓,也受到無產階級的挑戰。總體上,當時德國的國內經濟發展狀況并不如意。而新的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0年登基,這位頗為保守的國王屢屢鎮壓自由新興的改革,并且強烈抵制資產階級的新興力量,試圖進行歷史的復辟。這對于當時的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是種無比巨大的阻礙。實際上德國的保守主義派仍然把握德國主要的話語權,他們始終強調社會內在穩定不變的固定秩序,很大程度地限制資產階級和新興思想的發展,國家陷入專制主義的死亡喘息之中。德國的資產階級勢力對抗不了封建傳統的保守派,統治權力大部分始終是為保守派所把持,而為了讓沉重腐朽的國家繼續茍延殘喘,保守派禁錮自由思想的發展,企圖以基督教控制人民大眾的思想。正如《社論》中海爾梅斯站在基督教會的立場上,反對《萊茵報》討論宗教和哲學問題。
其次,在19世紀40年代,哲學,尤其是德國哲學所參與的主要輿論內容就是神學,因為宗教是當時人們生活方式的核心內容,而“神學塑造了人們最深層的信仰體系與人們在這個世界中的存在方式”[2]。在當時的德國,幾乎無法將宗教與政治完全地分離開,哲學不可避免地會討論宗教與神學,而對于公眾而言,正如馬克思所言,當時的宗教神學領域是處于“和物質需要的體系幾乎具有同等價值的唯一的思想領域”[3]221。因此,馬克思無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宗教神學的言論,但馬克思始終是為哲學正名,強調哲學生于時代和人民之中,它雖然保持原本的抽象思辨性質,但是對現實問題,哲學并不會一直保持沉默,哲學是哲學家對于時代精神的深刻把握,這種哲學成果帶有必然的思辨性,盡管不是遠離人民和時代的思辨性,但這種不可避免的思辨性在公眾眼里就是無法觸及的內容。而相反,宗教抓住人民的溫情心理,利用這種可悲的心理去發展自身思想,給予人們來世的安慰。這樣一來,在不了解哲學本質的思想背景下,為了追求未來天堂的或者將來人間的享受,大多數無知的公眾都會選擇臣服于教會的長袍。神學教會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在人們心中的崇高地位,勢必會普遍地將利爪指向其敵人——哲學。于是,當社會的目光都固定在宗教神學之上,那么哲學這個無比思辨的內容就被置于冷板凳之上。
除此以外,德國當時處于新舊交替的時代,各種社會思潮在德國思想界瘋狂蔓延。1830年左右,法國共產主義思想傳入德國,盡管一直處于十分邊緣的狀態。因為此時的德國依然沉浸在虔誠主義復興中,他們陷入對新約和福音書的激烈論戰,施特勞斯和鮑威爾關于耶穌形象的爭論激化了當時宗教與政治的矛盾,德國內部的意識形態出現紛爭。但與此同時,圣西門主義、傅立葉主義不斷傳入德國,而赫斯對于德國哲學與法國社會主義理論聯系的推進也深深影響了當時的青年黑格爾派。除此以外,《萊茵報》時期,盧格和費爾巴哈的思想著作對于馬克思關注現實政治以及轉向唯物主義世界觀都有著催化作用。馬克思在《社論》中多次提到費爾巴哈,馬克思指出人們當時對于費爾巴哈的責難更多的是源于費爾巴哈哲學思想中的宗教方面,強調當時人們反對哲學的原因并不具備合理性。盡管此時的馬克思大部分是處在黑格爾理性主義思想的籠罩下,但早期共產主義思想和費爾巴哈等人對其的影響也展露在《社論》的一些觀點中。比如馬克思始終站在哲學的角度,指出當哲學“以世界公民的姿態出現在世界上”時,哲學首先反對的就是宗教,因為宗教本身是非理性的異化。馬克思對于宗教的批判指責,以及對于無神論者費爾巴哈和施特勞斯的維護,也側面展現出當時馬克思思想所受的多重影響。
因此,德國哲學之所以出現具體內容與抽象形式的對立困境,與當時具體的時代背景和思想環境具有極大的關聯,德國民眾對于宗教神學的大肆信仰,德國資本工業經濟的嚴重落后,德國政治國家對于宗教的官方推崇,德國資產階級力量的弱小以及法國共產主義等等對馬克思思想的影響,這些共同致使馬克思察覺到德國哲學所面臨的困境。面對德國哲學出現的困境,在當時《社論》的社會背景中:黑格爾總體性哲學體系的崩塌,青年黑格爾派內部的演進,以及政治官方對于哲學言論自由的管控,社會各種思潮的交織等等,馬克思試圖為德國哲學的困境尋找一條出路,探析哲學與現實的本質關系,強調哲學與現實的統一。
三、德國哲學困境的出路
受當時具體時代環境的影響,德國哲學受到無數來自人們和報刊的誤解和責難,海爾梅斯就此指責哲學不應該甚至沒有合法權利在報刊上探討有關宗教的事務,并認為青年黑格爾學派的哲學觀點極易造成社會的混亂。馬克思在對海爾梅斯的回應中,辨明了德國哲學本身的對立問題,并深化其博士論文中的思想和觀點,試圖對德國哲學內容與形式的對立找尋統一的路徑。
面對德國哲學具體內容與抽象形式的對立,馬克思指出了德國哲學的出路,即世界哲學化和哲學世界化。馬克思早在《博士論文》中就提到了哲學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并指出哲學世界化與世界哲學化。馬克思強調哲學必定會走向現實,因為哲學作為一種理論,首先就是批判。理論闡述的是一種規范性的原則體系,但現實往往不符合規范性的設想原則,兩者之間必定存在鴻溝和差異。但馬克思堅定地強調,“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不僅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而且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4]220。哲學在確定一種規范性的維度之后,必定會向現實過渡。哲學在與世界的接觸中,哲學會影響世界甚至會變成當代世界的哲學,因為哲學作為一種理論的內在之光,它必定要滲透到外部世界之中,去吞噬一切不合理的成分,哲學通過把原則貫徹到外部現象事物之中去實現自身。但正如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所闡述的那樣,“哲學的實現同時也就是它的喪失”[5]76。在哲學與世界的接觸過程中,哲學喪失了其自身的抽象性,其作為純粹思辨理論的特色隨之喪失。因為在哲學未與世界結合之前,哲學本身是極為抽象的。哲學唯一消除自身內在缺陷的方式就是與現實世界發生作用,如此一來,哲學不得不完善自身,其自身原本的自我滿足和完整性就將被打破,喪失自身的抽象性。而通過哲學的世界化,使得人們易于透過哲學的晦澀和孤僻的形式,而看到哲學內容中包含的時代特性和規律特性,以此不再對哲學產生畏懼心理。不同于黑格爾的哲學體系,其是一個抽象的思辨總體,強調一種內在于世界之中的支配性原則即理性的力量。然而黑格爾的哲學始終是漂浮于現實世界之上,馬克思則強調反思的力量,看到理論體系與現實狀況的差異。因為按照理想性的原則,哲學與世界是統一的,但現實情況并未如此,只有當哲學進入現實之中,才能夠消除其自身與世界不統一的缺陷。所以黑格爾學派解體之后的自由派和實證派無非只是抓住了黑格爾哲學的某一個方面,而忽視哲學與世界的統一關系,割裂了實踐與理論的一致性,最終造成自我意識的分裂。
哲學的出場是在敵人的叫喊聲中被迫顯露,因為哲學的本性仍然是站在在理性自主的前提上審視現實,這表明哲學在與現實進行結合的過程中,盡管會喪失自身的抽象本性,但并不是說要拋棄自身的本性。在《社論》中,馬克思尤其強調“當代的真正哲學并不因為自己的這種命運而與過去的真正哲學有所不同”[3]221。哲學在抓住實現的同時始終保有其特色,它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思辨性不能被徹底拋棄,雖然長久以來德國哲學采取沉默的方式面對報刊的膚淺語調,但哲學曾經拒絕對報紙的使用是因為報紙不符合哲學本身的特征,而以往的哲學家喜歡寧靜和冷靜的自我審視,他們厭惡世俗的自吹自擂,追求思想的嚴格推理。所以即使哲學在與世界進行接觸之時,哲學喪失自身的同時也不會徹底與世俗其他學科同流。因為哲學是哲學家對于時代和現實的苦思冥想、耗盡心力的成果。哲學的研究內容和形式要求決定了哲學的成果始終具有孤僻性和晦澀性,但這不是代表哲學將遠離時代和人民,哲學的思辨和抽象只是形式的必然,哲學雖然從未考慮過拋棄自身的形式特征,但哲學始終是關注時代和人民的,哲學試圖立足現實構建理性的法則,并以哲學成果去指導世界。
馬克思對德國哲學面臨問題的展開以及解決路徑的闡述C4C1l4/5W49K1m3/O5hOEw==回應了當時人們對哲學所形成的誤解,使人們明晰了哲學的真正內涵。哲學始終是觀照現實的,以現實內容作為反思的對象,盡管采取抽象的形式,但這正是哲學本身不同于報刊等簡易理論的最大特征。哲學晦澀的形式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就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哲學就始終高高在上,只論及超出現實世界以上的形而上學問題,相反,哲學只是以一種獨有的方式和概念上升性地討論現實世界的種種問題。
《〈科隆日報〉第179號的社論》是馬克思從書齋進入塵世的政論性文章之一,彼時馬克思還深受黑格爾法哲學觀點的濃厚影響,其思想處處彰顯著黑格爾的印記。在這篇文章中,當馬克思談及國家與宗教的關系時,仍舊是在黑格爾理性主義國家觀的籠罩下的成果。然而馬克思早在博士論文時期,就已經展露出不同于黑格爾的部分哲學觀點,這表現在馬克思提出了“哲學的世界化”與“世界的哲學化”,馬克思后期在《萊茵報》時期正是深化了其博士論文時期對于哲學與世界關系的看法觀點,超脫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思想局限。除此以外,黑格爾主張國家的合理性依據,認為哲學不應在報紙上談論和發表觀點,因為在他看來,哲學本身的獨特性要求哲學的論述方式就不同于報刊。但不同于黑格爾,馬克思指出哲學與世界的相關性,揭示哲學的真正本質,提出哲學應回歸現實生活,實現哲學的世界化,而我們對世界本身的探討也不應拘泥于具體時代和現實問題,必須要上升到理論高度,去發現和總結規律,實現世界哲學化。當然,哲學在下降到現實世界時,始終秉持其抽象的形式特點,這是因為哲學本身就不同于報刊等行業,哲學談及的內容本身就是以形而上的形式所呈現,對此的責難是對哲學本質的誤解。
總之,長久以來,德國哲學始終以其抽象思辨性著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曲解,認為德國哲學存在著脫離現實的傾向。為此,海爾梅斯對《萊茵報》上刊登青年黑格爾派哲學思想文章的行為十分不滿,指責哲學不應該在報刊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利用此次契機,馬克思通過對海爾梅斯的回應和反擊,捍衛了哲學的言論自由權利,明確指出哲學的現實性和當代性。但針對德國哲學所面臨的抽象形式與具體內容之間的對立問題,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馬克思尋找到德國哲學的出路,即世界哲學化與哲學世界化:哲學始終是對現實做出的帶有自身思辨特征的反映,哲學體系也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規范性原則。為實現哲學與世界的統一,必須以哲學的方式干預和影響現實,并在實現哲學自身的同時喪失其抽象性,最終實現二者的統一。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9.
[2](澳)羅蘭·玻爾.塵世的批判——論馬克思、恩格斯與神學[M].陳影,李洋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49.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1.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0.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6.
作者簡介:
江燕君,女,河南南陽人,鄭州大學哲學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