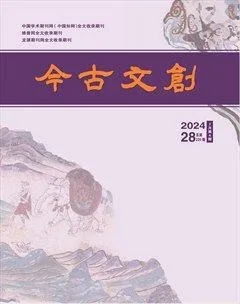青年網絡“圈層化” 現象的立體透視與反思糾偏
【摘要】青年網絡“圈層化”現象是指青年群體在網絡場域中因特定興趣領域形成小團體,并呈現出共同價值觀、話語模式和行為規范等現象。本文從青年網絡“圈層化”的現實表征出發,基于弗洛姆《逃避自由》的視角,從內在、外在因素兩方面對青年網絡“圈層化”背后的心理根源和社會動因進行剖析,并從宏觀上探討這一現象的糾偏機制。
【關鍵詞】《逃避自由》;青年;圈層化
【中圖分類號】B08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8-0079-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25
弗洛姆是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綜合起來,形成了社會心理學。《逃避自由》是弗洛姆社會心理學的奠基之作。弗洛姆關注的問題是“什么讓一個社會群體以相似的方式思考、感受和行動”[1],并在這本著作中給出了答案,這對于剖析當代青年群體網絡“圈層化”現象具有較強的解釋力。
近年來,網絡上圈層文化在青年人中空前發展,而現實中青年又出現“社恐”“emo”等心理狀態,構成了“網絡狂歡”與“現實孤單”的鮮明對比。目前,傳播學、社會學、教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學界從不同視角出發,結合學科特點展開研究。其中,傳播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研究內容多是網絡“圈層化”的衍生現象——輿論傳播、群體極化等,探究其生成機理、現實困惑和價值引導;教育學和馬克思主義學界多致力于解決教育“失語”的問題展開研究。弗洛姆“逃避自由說”關注個人心理的動態過程和社會的動態過程,以人的理性和愛的潛能的自由發展為旨歸,為探究青年網絡“圈層化”生成的心理根源和社會動因提供理論視閾。因此,本文將基于這一理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研究青年網絡“圈層化”現象。
一、青年網絡“圈層化”現象的現實表征
圈層不是網絡時代獨有的現象。圈層現象自人類社會產生起就存在,在過去的熟人社會中聯結圈層成員的主要根據是親緣和地緣,這種“社會圈子”是“富于地方性的”[2]。在網絡的催化下,圈層的覆蓋面拓展到虛擬空間中,圈層關系的形成依據由親疏遠近轉變為以興趣愛好為主導。網絡的時效性使圈層內部聯結更為緊密,圈層文化對青年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凸顯。網絡“圈層”是指“以興趣、愛好、利益等為關系構成的網絡社群連接”[3]。“圈層化”的“化”則表明這一現象是不斷變化的、動態的、漸進的形成過程。因此,要以變化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一現象。從當前網絡“圈層化”的發展來看,其現實表征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一)現實自由的擴大
網絡的匿名性和網絡交往的不在場性,給予了青年更多選擇、塑造形象、興趣表達的空間。具體來說:首先,圈層選擇自由。對于青年而言,相較于現實社會中社群的復雜性,網絡“圈層”的選擇是更為自主的。從復雜的現實強聯系中剝離,興趣愛好、價值取向成為青年在網絡圈層選擇上主要考慮的因素,滿足自身需求成為青年在網絡圈層選擇上的根本目的。青年可以依托個人判斷采取行動,“混圈”與否、參與深淺、投入大小都不必受外界強制性因素的控制,青年群體向往的選擇自由在此過程中得以充分滿足。也正是由于選擇的自主性,青年對自己選擇的網絡圈層有著更高的依賴度與信任感。這種網絡圈層選擇自由帶來的吸引力,成為越來越多青年人主動加入其中的重要原因;其次,形象塑造自由。網絡的虛擬數字實踐解構著主體自我意識同一性的和諧狀態。網絡作為現實的延伸,其匿名性可以給青年自由感,允許青年嘗試以不同于現實的方式展現自己。青年在其所屬的網絡圈層中,通過“碎片化”地表現自我,塑造一個理想的數字自我。虛擬世界塑造形象的自主性,同時暗含著真實自我和數字自我的分離;最后,表達興趣自由。這種因趣緣凝結成的網絡圈層往往也是松散的,自發主觀因素多、外在行為約束少,圈層內人員處于相對平等的地位,每個人都能在圈內自由表達和交流,成為所屬圈層的參與者和建設者。所屬圈層文化的單一性給予了青年展現自我的回應和呼聲,這讓青年主觀地認為找到了精神世界的歸屬。但同時青年也面臨著迷失自我的風險與挑戰。
(二)圈層內外的分離
文化是多元的,但圈層文化具有獨特性和排他性,“小眾文化是青年網絡圈層形成的前提和基礎”[4]。圈層文化的傳播和更新只在圈層內部進行,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現“文化孤島”的情況,圈層內外出現了分離的樣態。具體來說,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方面,從不同網絡圈層的隔閡來看,“網絡空間本身構成了一個大的場域,其內部又有不同的小場域”[5]。青年往往只關注自己所屬“小場域”的動態。因此,圈層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文化壁壘”,不同圈層成員之間難以理解彼此的情感傾向,也難以有共同的興趣話題。另一方面,從網絡與現實的分裂來看,首先是代際溝通的分裂。青年人作為數字原住民,發展出各類網絡亞文化,形成了獨具時代特色的網絡圈層,如“二次元圈”“電競圈”“飯圈”等。這些網絡亞文化的發展與傳播離不開網絡技術發展的“推波助瀾”。但年長一代對于時代技術的革新大多處于被動適應的狀態,而老年人更是出現“數字失能”的問題,他們無法把握網絡的文化潮流,更不會深入圈層內部。因此,代際溝通的空間和共知的意義內容被壓縮。其次是青年群體與現實的分離。長期對網絡圈層的沉迷,可能會使青年與現實脫節,甚至產生對現實問題的抵觸情緒。
(三)消費主義的膨脹
“社會的變遷導致了人類心理內部的轉化。”[6]在泛娛樂化、享樂主義等網絡亞文化的耦合驅動下,青年作為“時代最靈敏的晴雨表”[7],他們的消費心理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轉變。商品的使用價值弱化,而商品外在、情感、符號價值的重要性突顯。圈層文化打造的消費熱點,滿足了青年消費的需求變化。一方面,圈層的封閉性加劇消費主義的擴張。攀比心理、炫耀心理等不良消費心理在價值觀尚未定型的青年群體中彌散開來。另一方面,圈層青年表達情感和文化認同的方式集中在消費上。青年人散布在網絡的各大小圈層中,盡管在圈層的文化基礎上各不相同,但是青年表達文化認同的方式卻主要集中在消費上,即青年人常說的“氪金”。以典型的“娃圈”為例,青年沉迷于購買和收藏各類玩偶和玩偶的衣服與配飾,構成了現代社會的消費“景觀”。據一名“娃圈”愛好者坦言,在圈內,最厲害的那些畫手和最有錢的一批金主不斷推高價格,普通人仍然愿意隨波逐流。[8]同樣的情況在“飯圈”也處處可見,比如偶像能否出道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粉絲“打投” ①的能力。顯而易見,消費主義在網絡圈層中已靡然成風。某一圈層的凝聚力和文化認同越強,其消費能力越強。文化認同在網絡圈層中異化為消費主義。
二、青年網絡“圈層化”現象的心理根源
青年網絡圈層是對現實自由的擴大,出現內外分離的樣態以及消費主義的膨脹等現實表征,實質上顯示出青年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個體孤獨、脫離現實、情感消費等現實困境和傾向。借助弗洛姆“逃避自由說”,可以更加深入地剖析青年網絡“圈層化”背后的心理根源。
(一)個體化進程:青年個體孤獨的現實處境
圈層的生成從表層看是青年由于各自不同的興趣而凝結形成的,深入來看實則是青年對現實自由的無所適從,向圈層內尋找安全感。
在弗洛姆看來,人對安全感的需求是一個被動接受到主動尋求的過程。從人的生命歷史來看,嬰兒獨立于母體的標志是聯結母子的臍帶被割斷,但這只是粗淺意義上的獨立。人在成長早期通過器質性的“始發紐帶”與外界相連,這個生命的安全區使其獲得了安全感和歸屬感,找到了“生命的根”[9]15。在“始發紐帶”的作用下,一切都是確定的,人不會有孤獨和疑慮,并且會得到歸屬感,但自我意識的缺失,會使其以一個群體、社會或部落的一分子,而非作為一個人去認識自己。因此弗洛姆總結道,“這些始發紐帶屏蔽了人的全面發展,是人的理性及批判能力發展的絆腳石”[9]22。
一旦人的自我意識覺醒,就會出現“首次自由行為”[9]22,和諧和安全的狀態被打破,開始與原始群體分離,人變成了“個人”,自我的力量得到彰顯,原始的安全紐帶也因此斷裂。在自我意識還未萌芽的時期,人在“始發紐帶”的庇佑下,沒有所謂的自由和獨立,但是卻能獲得安全和歸屬;在自我意識萌芽并增長的時期,人渴望擺脫“始發紐帶”的束縛,獲得獨立自主的權利。
青年在擺脫“始發紐帶”的過程中,進入個體化進程,但個體化進程是具有兩面性的,造成了青年“自由卻孤獨”的現狀。弗洛姆剖析了個體化進程的辯證特征,一方面是“肉體、情感和精神上越發強壯,各方面的強度和活動都在增加”,即“自我力量的增長”;另一方面是“孤獨日益加深”。[9]18在成長早期隨著年齡的增長,自我意識增強,“達到斷絕始發紐帶的程度越高,渴望自由與獨立的愿望就越強烈 ”[9]18。認識個體化進程的辯證特征是理解人渴望自由的愿望的前提。
因此,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青少年階段,人的自我意識開始萌芽并不斷增長,對社會和世界的認識增強,積蓄了徹底割斷“始發紐帶”的力量,開始謀求自由和獨立。伴隨著身心的不斷成長和發展,其出現了矛盾心理,一面渴望得到自身的獨立和外界的尊重,抗拒并且想掙脫外界的管束,一面又離不開父母,渴望被對方理解和關懷。但是由于受到社會變革,青年一代和年長一代的社會環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因此父母們在很大程度上難以真正地理解青年們的興趣和需求。因此,青年們開始向虛擬世界尋求安全感和歸屬感,眾多趣味相投的青年聚集于網絡圈層中,構建起了一個龐大的烏托邦的世界。
(二)受虐傾向:青年尋找新的安全和歸屬
弗洛姆在第五章分析了逃避自由心理機制的不同的表現形式,指出受虐傾向是權威主義性格的一個方面,受虐傾向有兩種表現形式。其中,一種表現形式是,個人過分地俯視自我,貶低和輕視自我,這種貶低自我的行為的目的是為了克服孤獨和不安全感;另一種表現形式是通過依附權威,放棄個人的完整性,這一權威在外在形式上表現為某一機構、某個人、某個國家等具有凝聚力的整體力量。當個人發現自己“孤獨一人面對一個被異化了的敵對世界”,于是開始“尋求某人或某物,將自己與之相連,他再也無法忍受他自己的個人自我,瘋狂地企圖除掉它,通過除掉這個負擔——自我,重新感到安全”[9]100。個人想要除掉自我,從本質上來講,是要除掉自由的負擔。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也分析了現代人這種異化的生活狀態,“靠別人恩典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從屬的存在物”[10]。由此便找到了“繼發紐帶”——受虐紐帶,試圖重新獲得安全。
弗洛姆又指出,繼發紐帶根本不同于始發紐帶。始發紐帶能讓個人知道真正的歸屬,是真正的安全;而繼發紐帶是一種逃避。人在個人自我狀態下,卻未能實現自由,由此生發孤獨與無能為力感。因此試圖在繼發紐帶下尋求安全感,可能是一種自我安慰的心理,主觀上感覺到安全,但從“根本上仍是一個淹沒在自我之中苦苦掙扎的一個無力的原子”[9]104。
青年們以原子的狀態在網絡空間和現實生活中,在享受個人自我狀態的同時,也飽受著從傳統共同體中脫離出來而產生的精神孤獨和存在焦慮,因此產生了在網絡中尋找自我認同和保持存在的需要。青年人依附于網絡圈層的表現,實質上是由于自身的孤獨和不安全感而試圖使自己成為自身以外的網絡圈層的一部分,成為網絡圈層的參與者、管理者,使自己不再是一個現實中的孤獨的自我,而是一個獲得了新的安全和尊嚴的自我。但現實與網絡的割裂感,如果長期得不到彌合,青年們根本不能將自我從這種孤獨的困境中解脫出來,仍然扮演著“無力的原子”的角色。
(三)迎合傾向:青年逐漸向圈內趨同
弗洛姆梳理了逃避機制的三種表現形式,他認為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機械趨同,即迎合傾向。這是為大多數現代人所采用的一種方式。機械趨同是指,由于懼怕孤立,害怕對我們的生命、自由及舒適的更直接威脅,我們與別人的期望和要求保持一致。[9]132偽活動取代思想、感覺和愿望的原始活動,最終導致偽自我取代原始自我。[9]135我們可以看到,飯圈、二次元圈、電競圈等各種娛樂性的網絡圈層充斥著虛擬世界,并在網絡平臺資本的支配下蓬勃生發。青年人融入網絡圈層的出發點本是去尋求個人興趣所帶來的精神愉悅感,但網絡圈層的封閉性和圈層內容的同質性,會使青年忽視外界環境批判的聲音,無法看清事物的真實本質。因此,即使圈層內出現了錯誤的傾向,圈層成員也會不由自主地去迎合圈層內的潮流,久而久之,價值觀得不到主流文化的滋養逐漸扭曲。以飯圈為例,每個偶像在微博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支持者,這些支持者們為了吹捧自己的偶像,經常出現粉絲群體引戰、廣場狂歡,為了黑而黑所謂的競爭對手或合作對象,惡意p圖,傳播黑圖,編造謠言,使其陷入從天而降的污名中,無法脫身。粉絲群體中不乏不服從之流,為了維護自己在圈層內所塑造的形象,迎合圈內的任務,也會加入一場場的紛爭中,成為群體引戰中的一分子。
三、青年網絡“圈層化”現象的社會動因
弗洛姆在從人的生命歷史的角度分析了現代人的性格結構之后,又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剖析了社會進程對于個人性格塑造的影響。而“人的性格結構不但決定了人的思想和感覺,而且還決定了其行為”[9]189。
(一)平臺資本的宰制
弗洛姆認為,社會進程通過決定人的生活模式,即與他人及勞動的關系,塑造了他的性格結構。[9]68除了有青年群體自身特征的因素外,現代社會的發展也為“圈層”的生成提供了滋養環境。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智能手機的普及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用戶行為發生了質的變化。流量經濟大行其道,吸引了一眾資本注入互聯網的浪潮中。平臺資本利用算法推薦機制將用戶分流,為用戶搭建了一個“信息繭房”,網絡用戶收到越來越多能滿足興趣的同質化內容。作為數字原住民的當代青年與互聯網的聯系,無疑是最為緊密的。因此,青年人的個體孤獨是其向圈層逃避的內在原因,資本宰制與算法技術是催生圈層形成不可缺乏的社會條件。內外因素的合力作用為青年群體打造了一個個性化的信息世界,當青年們在圈層中發表看法時,迎來的幾乎都是同類回響,造成了“回音室效應”。
(二)數字勞動的隱蔽
弗洛姆肯定了資本主義把人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積極意義,但同時也指出,人隱蔽地成為實現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目的的勞動者。人的命運便是促進經濟制度的進步,幫助積累資本,這并非為了自己的幸福或得救,而把它當做目的本身,人成了巨大經濟機器上的一個齒輪。[9]73個人臣服于經濟目的,成為實現它的一種手段。[9]74在泛娛樂化的時代,體量不一、各不相同的圈層內嵌了使資本積累的數字勞動。以飯圈為例,在娛樂明星的微博評論區,以互動次數為標準區分鐵粉、金粉、鉆粉;在明星的超話中,同樣以每日簽到、發帖量、評論量等為標準確定超話等級,級別越高難度越大。如果在某一天超話斷簽,需要通過充值VIP獲得補簽卡,否則就難以升級。在資本的運作下,青年粉絲對偶像的迷戀被捆綁到日復一日的數字勞動中,青年與圈層的聯系越來越緊密。
(三)消費景觀的建構
弗洛姆批判了現代廣告對人的批判思維能力的弱化。他指出,大部分現在廣告并不訴諸理性,而是情感,像其他任何一種催眠暗示一樣。他先著力在情感上征服對方,然后再讓他們在理智上投降。廣告宣傳根本與商品的質量無關,像電影一樣具有白日夢的特點,能滿足顧客的某種需求,但同時增加了他們渺小感與無能為力感。[9]85“誰懂得了令群體想象力深刻的藝術,誰就掌握了駕馭他們的藝術。”[11]在網絡圈層中的青年們無一不是某一類商品的潛在消費者。這些商品的宣傳海報或宣傳廣告,從根本上脫離了使用者對于商品使用價值的訴求。而是通過高價聘請流量明星做代言人,通過圈層的力量促進消費。又或者是,通過科技的手段賦予虛擬的動漫人物,以人的特性創設夢幻的情境促進消費。在圈層中消費景觀的建構使青年對人的迷戀有了物化的實體。
四、青年網絡“圈層化”現象的引導糾偏
青年網絡圈層化的生成既受青年群體內在性格結構的影響,也受到社會發展變化的影響。網絡圈層的封閉性,加深了圈內文化對青年群體的影響。文化的好壞,影響著青年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如果長期沉浸于某一種文化中,青年可能主動或被動地排斥主流文化,無法與外界正常交流,自以為是、作繭自縛,嚴重危害其成長。因此,需要對青年網絡圈層化現象加以規訓。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與《愛的藝術》中略窺一二。
(一)注重愛的非對象性
弗洛姆認為人們對自由的肯定來源于人們愛的能力。這里的“愛”不是對某個特殊人的關系,而是一種態度、一種決定。愛是肯定所愛之人是根本人性的化身,愛一個人也意味著愛人類。如果只愛某一個人,“對其他同胞漠不關心,那么這不是真正的愛,而是共生性的依附,或是擴大了的自我主義”[12]57。青年網絡圈層的運作模式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實質上是一種共生性的依附,又或說是一種群體自我主義。從某種程度上說,圈層因不同的興趣而分門別類,這既是個性的彰顯,也是個性的喪失。一方面,圈層為青年提供了彰顯個性和紓解孤獨的入口;另一方面,圈層創造了一個“小世界”,“參加者為了使自己屬于這一組人而失去了大部分個性”[12]16。因此,真正地尋求自由是獲得真正的愛的能力,即,由愛一人而“愛所有人,愛這個世界,愛生活”[12]57,又或者說是獲得積極生活的態度。
(二)回到現實的創造性勞動
創造性勞動是青年自我實現的現實途徑。弗洛姆認為實現積極自由需要我們“自發地在愛與勞動中與世界相連”[9]92。這告誡廣大青年,要用自發勞動聯結世界。首先,自發勞動意味著勞動要與人的類本質相符合。馬克思提出,“異化勞動,由于使自然界同人相異化,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動機能,使他的生命活動同人相異化”[13]56,也就是說,勞動要有益于身心成長,凡被資本裹挾與誘導的,要以資本規定的數字勞動表現自我的不能被稱為自發勞動。其次,回到現實世界中。青年作為“現實的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3]135。青年要實現積極自由最終要回到現實世界中,因此,要注重判斷現實世界和網絡場域的必要性與非必要性、根本性與附生性,以免在網絡中失去自我,陷入更深層次的虛無與孤獨中。
(三)積極實現自我超越
自由和超越往往是密不可分的,自由意味著自發地實現自我,而超越意味著質變,到達實現自我的彼岸,是自我實現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弗洛姆認為,人類所真正追求的是積極自由——自由地發展,而非消極意義上的自由。追求自由是個體化進程的必然結果,也是文化進步的必然結果。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之辯實際是質與量之辯。因此,弗洛姆提出:“自由不僅僅是個量的問題,而且是個質的問題,我們不但要保存和擴大傳統的自由,而且要贏得一種新自由,它能使我們認識到屬于自己的個人自我,可以使我們對這個自我及生活充滿信心。”[9]70也就是說,一方面,青年要保有自我思考、自我選擇、接受結果的傳統自由;另一方面,青年要培養遠見與格局,有面對人生困惑的智慧和能力,超越一切既定關系的束縛,不逃避、不依附,認識自己、成為自己,達成自我“質”的飛躍。
總之,“逃避自由-順應群體-成為工具-瘋狂失控-走向毀滅,這不僅是社會理論的邏輯演繹,更是人類歷史的真實展現”[14]。青年從獨立自我到順應網絡圈層群體,在多重勢力的交織影響下,存在著擺脫良性發展、走向瘋狂失控的隱患。面對網絡圈層的現實困境,青年要關注現實世界,在愛與勞動中實現積極自由。
注釋:
①“打投”指的是“打榜”+“投票”,在一些選秀成團真人秀節目中,票數最高的幾位選手可以“成團出道”。通常是粉絲被拉入一個群以后,用手機不斷為明星投票。
參考文獻:
[1]賴納·豐克,王琦琪.弗洛姆《逃避自由》一書的出版及其意義[J].國外理論動態,2021,(03):56-62.
[2]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6-7.
[3]涂凌波,鄭石,蔡雨.構建美美與共的網絡文化景觀[N].光明日報,2020-12-04(11).
[4]羅琳.青年網絡“圈層化”的時代特征、生成機制與風險防控[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22,41(03):75-83.
[5]劉勝枝.值得關注的95后群體文化圈層化、封閉化現象[J].人民論壇,2020,(Z2):131-133.
[6](德)韓炳哲.倦怠社會[M].王一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65.
[7]習近平:青年是標志時代的最靈敏的晴雨表[EB/OL].http://www.qstheory.cn/2019-04/29/c_1124432366.htm,2019-04-29.
[8]從“繪圈”到“娃圈”都“圈錢”[EB/OL].http://zjnews.china.com.cn/jrzj/2021-11-09/311159.html,2021-11-09.
[9](美)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劉林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
[10]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9.
[11](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群體心理研究[M].張源譯.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63
[12](美)艾·弗洛姆.愛的藝術[M].李健鳴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1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甘紹平.對“逃避自由”的倫理審視[J].道德與文明,2019,(04):11-20.
作者簡介:
冉嘉怡,北京聯合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