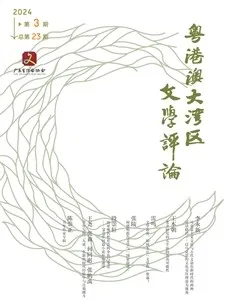鄉土中國的“內”與“外”:當文學面對鄉村與農民
摘要:“鄉土中國”影響下的中國鄉土小說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革命對趙樹理及當代作家莫言、賀享雍都有深切的影響。而西方作家則可能由于缺乏革命一維而對鄉村和農民高度忽視,如巴爾扎克把鄉村貴族化和財富化。賀享雍小說中的鄉村類似趙樹理,始終強調生存為上,愛情和生育都以此為準則;或者可以說莫言的鄉村提供了當代作家面對鄉村的復雜參照。
關鍵詞:賀享雍;巴爾扎克;莫言;鄉土;生存
人類始終離不了農業,是因為人類的生存離不開糧食。不管人類的政治怎么發展,糧食生產都是必須要保證的,這意味著鄉村或者農民生存的土地永遠是不可替代的——至少幾百年內還應該如此,人類還沒有能力完全人工合成糧食。這也意味著人類離不開鄉村,而且人類的文明也是從鄉村開始,在今天鄉村仍然是文明的焦點之一。文學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鄉村文學也同樣是文學的中心之一。鄉村有著其特殊性,雖然對人類的生存及延續至關重要且不可替代,但其在經濟體系中卻一直處于低位,當人類文明進入大工業時代更突顯了這一問題,即農業的低產出低效益越來越削弱農業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鄉村作為農業生產的場所出現在小說中也面臨同一問題,生活在鄉村并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在鄉村文學中也同樣,很多作家難以掩飾或者毫不掩飾對鄉村和農民的輕視,這是城市化進程中很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和文學問題。
中國鄉村文學最鮮明的特色,是由于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中國當代作家面對鄉村時會有一種馬克思主義式的關注,特別是毛澤東的“大眾化”寫作理論,如到群眾中去和知識分子面對鄉村的“自我改造”,給中國作家形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中國革命的特殊經歷也是其他國家的作家不具備的,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在今天的環境下也不可低估。中國的作家對鄉村特殊情感也源于此,總能在儒家的仁義之外加上超現代的“公共意識”,這個“公共意識”又與道家的“無我”和“無名”混合在一起。這也是其他國家的作家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具備的,包括世界第一大社會主義國家蘇聯。
賀享雍的小說同樣有著“后革命”特色,他雖然不是有意而為,但他作為新中國第二代作家,經歷了“大躍進”的尾聲、“文革”、聯產承包及改革開放,受毛澤東式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非常深遠。賀享雍的鄉村類似趙樹理的鄉村,充滿了儒家式的悲憫,同時對鄉村本體的細致入微的再現也與趙樹理相似,特別是對鄉村倫理下人們的生存細節的描述尤其接近趙樹理的日常化鄉村;同時,莫言式對權力的幻滅也時有表現,但賀享雍更多的還是著眼于權力之下鄉村的存在,批判性經常讓位于道家式的忍耐。從某方面來說,賀享雍的小說是對當代農村文學的重要補充,特別是精致入微的細節描寫,把鄉村、鄉村的權力及農民的生存狀態作了獨具特色的內部展示。
一
西方的文化傳統從文藝復興以來一直是重個體、重現代主體性,西方現代小說產生于文藝復興之后,更是以個體為重,所以他們對農民的思考也是以個體為中心,重人性、重人道。而中國不是,中國在個體之上還有一個儒家式的集體,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著終極價值,輔之以無所不在的道家。進入現代社會,道家成了隱藏的又是根本性的文化積淀,以集體無意識的方式發揮作用。了解這種中西文化的差異,就會發現中西文學面對鄉村和農民時的差異。如波蘭作家萊蒙特192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就是《農民們》,或譯成《農夫》,這應該是西方最接近農民作品之一,其寫作是現實主義式的,視點也是單一視點,敘述人基本是隱含作者的化身,其身份基本是一個西方的啟蒙知識分子。他的鄉村立場和后來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小說相似,如茅盾、丁玲和周立波等人的小說,即其敘事建構更多的是外在于鄉村的。托爾斯泰的《復活》同樣如此,貴族地主聶赫留朵夫主動分地給農民,很自然且完整地實現了托爾斯泰這樣一個貴族地主的想象及其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同時這也是他自我救贖以“復活”的重要行動之一。但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分地只是他的個人行為,并沒有其他地主響應或學習他的行為,主動把土地分給農民。因為當時的大環境并不具備“解放”式平等的諸多條件,特別是人們沒有社會主義式的公有意識,不會想到也不會接受把財富無償地分給窮人。而且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也決定了他不會去發動其他貴族響應他的號召。托爾斯泰只能也始終在鄉村之“外”。
巴爾扎克也寫過很多次鄉村,但他的沒落貴族立場決定了他的作品不會真正描寫貧苦農民。果然,即使命名為《農民》那部小說,寫的也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農民階級,而是鄉村的權力階層,貴族地主。畢竟那時只是19世紀前半葉,馬克思主義還未在全球造成影響。具體分析一下巴爾扎克的鄉村場景,就能明白巴爾扎克的意旨所在,如《農民》一開始就是典型的現代風景描寫:
從這兩幢人去樓空,布滿灰塵的小樓開始,有一條漂亮的林蔭大道,夾道兩排百年老榆,樹頂如華蓋,交相掩覆,形成一只長長的,壯麗的搖籃。道上長滿了草,雙輪車走過的轍痕依稀可見。那榆樹的高齡、大道兩側邊道的寬度、兩座小樓令人肅然起敬的氣派,還有那墻基石塊的棕色,處處都使人一望而知王侯府第離此不遠了。
小樓的柵欄位于一塊高地,我們愛虛榮的法國人稱之為山,下面是驛車終點站庫什村。我在到達那柵欄之前,望見了艾格莊狹長的山谷,大路就在峽谷盡頭拐彎,直奔法耶市,我們的朋友德·呂卜克斯的侄子就在那里當土皇帝。在一條河邊的丘陵上,一大片參天古木俯瞰著這富饒的山谷,遠處群山環抱,那山名叫摩凡山,是屬于小國瑞士的。這片茂密的森林屬艾格莊、龍克羅爾侯爵和蘇朗日伯爵共有。登高遠眺,那別墅、園林、村落,真像柔美的布律蓋爾筆下神奇的風景畫。
這個風景與寫實、抒情與欲望緊密結合的敘事片段不是個案,而是廣泛存在于巴爾扎克的作品之中。只要涉及鄉村,巴爾扎克的風景可能就是同樣的狀態,如《老姑娘》和《攪水女人》,同樣是充滿誘惑的莊園。“登高遠眺,那別墅、園林、村落,真像柔美的布律蓋爾筆下神奇的風景畫”,如此美妙的地方,帶來的不是東方的恬淡和閑適,而是勾起了所有的人的占有欲。而前一句則交代了這片風景的“主人”:“這片茂密的森林屬艾格莊、龍克羅爾侯爵和蘇朗日伯爵共有”。在巴爾扎克看來,這些誘人的風景是貴族們的神圣財產。無邊的風景,實際是貴族們的莊園。而莊園是鄉村財富和權力的集中地,是成功的符號,是貴族的標志。所以,雖然是風景描寫,但滲透了對財富的欲望。在一般的小說中,此段的功能在于第一人稱的敘述人或“類說書人”向接受者或聽眾介紹故事空間的一些環境要素,但對于巴爾扎克的經典批判現實主義小說,那個“我”或者“我們”卻更多地投射了那個真理化的隱含作者的欲望。而巴爾扎克對這些欲望是沒有感覺或者沒有反省的。雖然在上面的片斷中,巴爾扎克似乎自嘲為“我們虛榮的法國人”,但在實際上,他很為自己是“法國人”而驕傲,因為他家在巴黎——1814年十五歲時隨父親遷入巴黎,而且此時他已經是巴黎有名的大作家,他覺得自己不再是出生于法國中部圖都爾市的“外省人”,他很滿意“巴黎人”這個稱號或者命名,因為“巴黎”代表著“法國”; 所以上文的“虛榮”在修辭上是反向的,并非貶義,而是得意。這與他對財富的渴望息息相關。他的所有行為,包括寫作本身及愛情、他的社交,都是為了金錢,為了投機和還債,他的欲望無法掩飾,因為他沒機會掩飾,他必須生存,他必須出人頭地,他必須有體面的人生。這種俗世的欲望正是巴爾扎克一生的軟肋——可以說是生于斯,死于斯。
而賀享雍不同,下面是《土地之癢》第一章中的風景描寫:
清晨濕漉漉的露水打在賀世龍一雙赤腳上,令他覺得十分清爽。他來到牛草灣那塊過去曾經屬于父親、現在歸在他和世鳳、世海三弟兄名下的祖業地邊,天已經開始大亮了。擂鼓山后面,太陽早早撒開了一片像是膏脂的紅顏色,又像是要把天給燃起來似的。賀世龍聽別人日白說,太陽和月亮是一對兄妹,太陽是哥哥,月亮是妹妹。這會兒西邊跑馬梁天上的月亮,似乎看不慣哥哥這副愛出風頭、張狂的樣子,歪著臉在一邊慪氣。過了一會曉得自己慪氣也是白慪,干脆把自己所有的光,都收了起來,躲到跑馬梁的后面去,眼不見心不煩,讓你個毛頭毛腦的去發羊角瘋吧!
賀世龍跳到地里,這塊地朝南,又處在一個背陰的灣里,盡管那太陽迫不及待地在東邊擂鼓山頭發出了光芒,但灣里還是有些麻雜雜的。不過,地里的景色已經能看得分明了。這塊地上季種的是清一色的高粱。現在高粱收了,連高粱稈也早挖了。高粱收獲早,距種小春作物還有差不多兩個多月時間。在這個時間里,賀世龍本來還可以種一季早蘿卜,等賣了咸菜蘿卜種小麥正合適。
賀享雍小說中的風景描寫不多——巴爾扎克類似的細節描寫倒比比皆是,他的小說中即使有風景描寫,似乎也不代表隱含作者的情感注入,而是與人物結合在一起的,既是人物生活在其中的風景,也是人物視角中的風景。上段就投射了“聯產承包”之后農民賀世龍終于分到自己的土地后的喜悅,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太陽和月亮都帶上了俏皮的色彩。這樣的描寫,用柄谷行人的“風景”分析,仍然能歸于現代主體性得以發生的“裝置”,因為賀享雍生活在當代,現代意識早已成為中國作家的共識,風景描寫在此處是作家特意通過環境來襯托農民得到土地后的喜悅的,而改革開放之下的農民其目的也是要走向“現代”,從作家到角色,都有現代訴求,所以這段風景描寫可能至少承載了雙重的現代。但在這個敘事片斷中,卻看不到巴爾扎克那種資產階級式的欲望,不是攫取,不是占有,風景描寫之后就是賀世龍生龍活虎地“跳到地里”準備干活。一定要明白一個前提,鄉村的農民這種面對土地的勞作是低效率的,達不到巴爾扎克那種“資本”的高度,更談不上奢華的欲望,與后工業時代的量子經濟更是風馬牛不相及,賀世龍需要的只有一個:活著。就是說,賀世龍作為一個中國鄉村農民的代表,他明知自己的勞作的辛苦與低效,他仍然要非常歡喜地去勞動,就是因為他背后是一個最基本的人類問題IUDkgI0PfqjTwgS5DunhiA==:生存。
一個重在奢華和財富,一個重在生存,雖然不能從對錯和高下方面進行價值判斷,但其差異性卻是天壤之別。巴爾扎克熱衷的是貴族式的財富及金錢堆成的優雅,賀享雍看到的是農民的艱難的生存,或者可以說,巴爾扎克是無所謂悲憫的,而賀享雍則充滿了對農民的同情,那是來自儒家的仁義與革命的“解放”意識相結合的悲憫。所以,對于賀享雍,他的立場與趙樹理高度一致:革命之后,農民需要的是休養生息和基本的生存,而不是“發展”。賀享雍小說中的農民的絕大多數都不需要資產階級式的體面,金錢的欲望也沒那么強,他們要的是一個純粹的生存化的農民。賀享雍作為一個鄉村作家,則是一個鄉村的講故事者,一個鄉村的詩人。
二
把賀享雍和巴爾扎克的關于鄉村的同等敘事場景做對比之后,就會發現社會主義革命與道家結合的巨大力量,巴爾扎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處于急速發展且尚未成熟時期的知識分子,對鄉村的態度是何等的單一。再看鄉村的愛情,作為人類永恒的主題、生殖本能的文明化裝飾,它在賀享雍、莫言、巴爾扎克、趙樹理的小說中都有非常精彩的描述,他們的處理方式明顯有很大差異。比如莫言《天堂蒜薹之歌》里面的高馬和方金菊,趙樹理的《登記》里的晚晚和小艾,賀享雍《蒼涼后土》里的余文富和孫玉秀,這些人的愛情就有各自不同的走向。趙樹理的《登記》是最完美的解決,青年們皆大歡喜。但在莫言和賀享雍那兒就未必了。
賀享雍《蒼涼后土》里面寫了一對被物質拆散的青年人余文富和孫玉秀,父親孫學禮貪財,逼女兒退婚余文富嫁給一個經商的混混,因為商大于農,經商向來是純農業收益的數倍乃至百倍,有能力給孫家的彩禮更多。在此,隱含作者的安排意圖非常明顯,不提及生存,因為此時已經聯產承包,大家都能吃上飯,生存不再是問題。敘述人明顯把它歸于道德問題,即貪婪,且沒把一點同情給那個黑心的父親孫學禮,倒是給孫玉秀的母親劉澤榮很多善意,母親愿意女兒幸福,但父親不同意,而且鄉村的家庭是絕對男權,母親沒有話語權,直接導致女兒的不幸。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之中的高馬和方金菊愛情悲劇的起因類似,他們的愛情阻礙明顯也是金錢,和農村的生存化婚姻一致,即婚姻能否給女方家庭帶來物質回報。在此莫言設置了一個復雜的三家換親,方劉曹三家農戶各有一個病殘的兒子,又恰好都有一個女兒,三家簽“協議”轉著換親,方家女兒嫁劉家兒子,曹家女兒嫁方家兒子,劉家女兒嫁曹家兒子。高馬能夠給金菊帶來基本的幸福,因為他們都是健全的,但他不能給金菊的哥哥帶來幸福,實際上方家父母考慮的是家庭和家族的未來,因為金菊的殘疾哥哥沒有辦法(實際是沒錢)正常娶親,所以他母親只能依賴金菊去換親,高馬帶來的自由戀愛破壞了農民的這一生存鏈條,當然要受到重重阻礙,金菊的父親方四叔也曾說過,高馬要娶金菊就拿一萬塊錢來,背后的含義實際是有一萬塊錢金菊的殘疾哥哥就能娶到媳婦了,但在那個一只雞蛋幾分錢的1980年代,一個農民怎么可能有一萬塊錢。所以,高馬和金菊的執拗的愛情最后變成了一個大悲劇:金菊退親后曹家兒子娶媳無望自殺,金菊與高馬私奔被捉回毒打,金菊懷著孩子自殺身亡,死后還要被三家換親之一的曹家買尸給兒子配陰親。這種婚姻悲劇一方面是鄉村生存倫理起作用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男權本位起作用的結果。對于鄉村,婚姻的第一原則是生存,第二原則是要生男傳家,女性隨時可以被犧牲。
在賀享雍的小說里的愛情結局一般沒有那么悲慘,如上述農民余文富和孫玉秀之間的愛情,雖然最初被建構成悲劇,孫玉秀被父親逼迫嫁給了不喜歡的人,但最終卻成了正果,得以和不良人離婚,與余文富破鏡重圓。這種安排,也是作家或隱含作者心存善念的表現,他似乎不忍心讓自己的人物過得過于悲慘,所以讓他們經歷了很多的苦難之后,還是給了他們一個大團圓的結局。總體上看,莫言的愛情悲劇更殘酷,他對人性之陰暗似乎非常不樂觀。大小人物都在金錢和權力之下死于非命,愛情也僅是死亡之途的曇花一現。另一方面,莫言在冷靜展示的背后更強調生存。金菊的父母親雖然非常殘酷,寧愿女兒死也不愿她婚姻幸福,但作者的著力點并不像張愛玲在《金鎖記》中所表現的那樣,男權的千年壓迫導致女性的奴性與變態,更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性扭曲,而是農民在鄉村生存倫理之下所做的必然選擇。莫言作為一個鄉村出身的男作家,明了生存為中國鄉村的第一倫理規則,他從未低估它對農民行為的巨大影響。趙樹理的小說中的婚姻也是面臨著鄉村的生存問題,但趙樹理弱化了生存一維。作為一生為農民思考的作家,他敢于弱化生存的自信在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解放區農民已經獲得了土地,生存已經不再是問題,他相信政策會一直穩定地持續下去,所以那個時候的農民面臨的就不再是生存問題,而是新制度和舊傳統的矛盾。因此,《登記》中青年的婚姻受到老一代阻礙之后,在政策的影響下得以完美解決,表面看是革命的勝利,實際也是鄉村新倫理的勝利。
論述過革命影響下的中國作家之后,再對比一下巴爾扎克這樣的“前革命”時代的西方大作家,可能仍然會有較大的發現。在巴爾扎克的小說中也有一個關于鄉村女性愛情和婚姻的故事,即《攪水女人》。它實際上是一個巴爾扎克版的灰姑娘的故事,“攪水女人”本是一個貧窮的農民,但她超乎尋常的美貌改變了她的命運。她12歲時被70多歲的鄉村地主羅杰醫生看中,于是她憑著自己的驚人的美貌得到了一個貴族的垂青,不但獲得了豐富的物質生活,掌管了大量的財產,還能夠找到自己愛的人。但巴爾扎克卻把她處理成了圖謀主人/恩人財產且性觀念混亂的窮人出身的小丑。為什么非是出身貧窮農民的攪水女人覬覦貴族的財富?關于貴族與資產階級的財產之爭,為什么必須有一個丑惡的下層人來攪起波瀾?為什么一個窮人家的孩子就不能像灰姑娘一樣嫁給王子過上幸福的生活?
很明顯巴爾扎克犯了馬克思所說的那個錯誤,即站錯了階級隊伍,巴爾扎克自己本為上升中的資產階級,但他的情感卻在屬于舊時代的封建貴族一邊。他同情和羨慕的是貴族的“氣質”,實際他潛意識中更想要的是資產階級的財富和自由。再者,資產階級立場和貴族立場都是精英立場,兩種立場都是貧窮的農民階級的奴役者和壓迫者。所以巴爾扎克站在精英立場角度丑化下層勞動人民是正常的,面對窮人的復雜態度更不可能出現。巴爾扎克的強烈的批判性在于他把當時的法國看成一個高度利益化的社會,在他那兒完全不存在純潔的個體,都是利益下的蟲蟻,毫無文明可言。從這點上看,巴爾扎克的批判現實主義在一個農家姑娘那兒也得到夸張的體現,于是她利用她美麗的肉體掌控一切,包括財富和男人,如巴黎的那些貴婦和女演員一樣成為資本主義下最丑惡的現象之一。總而言之,不是說農民就沒有“壞人”,也不是說農村女性的愛情就不能有陰暗,而是巴爾扎克的選擇意味著他從來沒有真正融入鄉村,他關心的只是鄉村中的資本和財富,而不是農民的生存和農民群體的復雜。
而賀享雍則在此種描寫中充滿了對農民的同情。正常的愛情就不說了,即使寫到農村婦女的“墮落”,他也極盡善意。如《村醫之家》中的蘇孝芳,外出打工被一個老板包養生了私生子,敘述人并未作什么價值判斷,而是借村醫之口罵幾句不懂事了事,還幫她撫養私生子。賀冬梅同樣外出打工,卻做了“小姐”,并得了性病,隱含作者并未對她譴責,而是借敘述人之口強調她是不得不如此,她母親生病花了幾萬塊錢,她做“小姐”是為了給母親還債。作為反例,對心不在鄉村的農民后代,盡管沒多少錯,賀享雍卻毫不留情。如《盛世小民》中賀世躍的兒子賀松的女朋友吳嫻,同樣出身鄉村,到賀松家卻對農民的衛生及環境大加指責,在外面打了幾天工就拿城市標準要求鄉村,在小說中被塑造成年輕無知且盲目羨慕城市的典型。整個敘述過程中敘述人明顯站在農民一邊:鄉村不需要城市的那些多余的規則。再后來兩人分手了事,這也是新世紀處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女性的正常的“雙向選擇”。“分手”的情節安排意義相當重大,“分手”解決了農民的兒子與傾向城市的女友之間的矛盾,也解決了農民賀世躍與兒媳之間的城鄉意識差異造成的矛盾;同時,“分手”也解決了賀享雍的矛盾,在他看來,一個心中沒有鄉村的女性是無法和農民家庭融合的,鄉村的立場使得他不得不在文學世界解決各種城鄉的沖突。城市代表著過多的欲望,而鄉村代表著生存和閑適。欲望的膨脹總是弊大于利。如同人類社會一樣,宇宙規則在任何角落都發生作用,大自然的平衡力量隨時會到來,沉湎于過多的欲望,必然被欲望反噬。巴爾扎克的金錢欲望,他對貴族身份的期待,他對資產階級的財富的向往,導致了一生的悲慘,50歲才得以娶了一個極富有的貴族,伯爵夫人甘斯卡婭,幾個月后就貧病交加與世長辭。從文學上講,欲望的指向也決定了他小說的復雜向度,這個復雜,卻獨獨缺少了對鄉村的關懷。因為在對金錢充滿野心的巴爾扎克那兒鄉村是無用的。
而這正是從趙樹理到賀享雍和莫言面對鄉村的長處或優勢所在。馬克思主義帶來的階級思路及解放全人類的理想,使革命時代和后革命時代的中國作家不管身處何種處境都有底層關懷的可能。
三
除了生存與愛情,生育同樣是鄉村的大事。國家的生育政策會對生育行為產生重大影響,鄉村更是如此。歷史證明,鄉村的相對貧窮使農民更易于生育盡可能多的后代來緩解物質的匱乏,因為后代意味著勞動力。但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相應而變的國家政策卻未必支持此種生育策略。中國人口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是計劃生育在1982年被確定為全新的“基本國策”,此項政策的背景是人口的過度增長。而鄉村之中,生育非常重要,關系到整個家族的繁衍和臉面。
賀享雍《盛世小民》中賀世躍妻子逃避計劃生育,作者也充滿了同情,甚至沒有一點指責,這點與莫言的《蛙》有很大區別。賀享雍在小說中給出了農民寧死也要“超生”的重要原因:
你知道世祿哥在賀家灣自覺矮人一截,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這原因也是賀家灣人根深蒂固的傳統,那就是只要你沒有兒子,不管你品德有多么高尚,能力有多么突出,對村里的事業有多少熱心,人們有紅白喜事或鄰里糾紛調解什么的,也不會來請你去幫忙或說理,更不會把你拉到上席就坐。活躍在賀家灣紅白喜事上的,總是那些有兒有女、兒孫齊全、人丁興旺的“大家子”代表。
這確實是農村的常態,沒有兒子的家庭是備受歧視的,一切都被邊緣化,給農民家庭帶來巨大的壓抑和恥辱。不是農民生來就如此固執,而是父系系統造成的男權社會的深遠影響:男人才是真正的完整的“人”,而女人永遠都不“完整”。
賀享雍在同情之下,運用隱含作者的上帝之手解決了賀世躍的重大人生價值問題,他超生了一個兒子,且在相關基層行政人員的監視和“追捕”之下把孩子偷生在路邊的草垛下:
這天晚上,你就陪著產婦和新生的嬰兒擁著這條毯子坐到了天亮。你一邊坐等黎明,一邊給嬰兒想了一個名字:草生。草生在他母親的懷里香甜地睡著,小鼻子發出均勻的呼吸,月光在他的小臉上像是上了一層光滑而輕柔的釉。天亮以后,你看見鄉上那兩個監視你們的漢子從屋后小路回去了,等他們走遠以后,你才一手扶著產婦,一手抱著草生回家去了。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淡淡的晨霧在賀家灣的土地上四處氤氳,空氣中散發著一股青草特有的香甜的氣味,這氣味有些像是年輕女人洗浴過后身上散發的味道。你的臉上泛著紫紅色的光芒,昂首挺胸,完全是一副凱旋而歸的樣子。
有了兒子,賀世躍的生命全亮了,面對監視的基層干部,他即使和妻子兒子顛沛流離也欣喜若狂,以致居無定所也整天昂首挺胸,一副“凱旋而歸”的樣子。賀享雍的隱含作者在此仍然堅定地站在農民這邊,在他那兒鄉村傳統就是人間鐵律。但歷史和現實中的“計劃生育”背后的東西非常復雜。莫言在《蛙》中討論了這個問題。計劃生育政策推出之前,有過人口的大起大落,五六十年代社會環境由于戰爭的結束顯得十分穩定,人口出生率大大增加,不久后的三年(1959-1961)經濟困難,人口大減,《蛙》中直接寫道:“因為饑餓,女人們沒了例假;因為饑餓,男人們成了太監。”政策性的糾偏之后,1960年代的中國,爆發了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蛙》中又直接寫出了農民對政府的感激:“‘地瓜小孩’出生時,家長去公社落戶口,可以領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兩斤豆油。生了雙胞胎的可以獲得加倍的獎勵。家長們看著那些金黃色的豆油,捻著散發出油墨香氣的布票,一個個眼睛潮濕,心懷感激。還是新社會好啊!生了孩子還給東西,我母親說:國家缺人呢,國家等著用人呢,國家珍貴人呢。人民群眾心懷感激的同時,都暗暗地下了決心,一定要多生孩子,報答國家的恩情。”但人口急速增長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人口的暴增,土地的相對稀少,人與自然的矛盾加劇,政府為資源最大化地合理分配只能宏觀上做出“計劃生育”的重大決定。但是在中國香火不斷子嗣延綿的生育傳統之下,人們努力維護“生育權”。小說《蛙》中計劃生育的執行者是敘述人“蝌蚪”的姑姑,——鄉村婦產科醫生萬心,她曾經是萬人敬仰的革命后代和最優秀的婦產科醫生,“計劃生育”時代她由于“鐵血”般的計生手段被人們加上各種詛咒,如“紅色木頭”“黨忠實的走狗”。恨則恨,但怎么看都是雙方都有各自的道理。“超生”者是為了自己的后代,執法者是執行國家的政令。
因此,計劃生育雖然被西方國家多次指責為“反人道”,但對于當時的中國確實很有必要。《蛙》的日譯本封皮上有這樣一句話:打胎則生命與希望消失;出生則世界必陷入饑餓。1《蛙》最開始出現的孩子吃煤事件就暗示了當時資源匱乏的大環境,它來自莫言的親身經歷2,所以控制“人種繁衍”也迫在眉睫。《蛙》中的敘述人“我”對這一歷史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某種看法:
歷史是只看結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們只看到中國的萬里長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許多偉大建筑,而看不到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在過去幾十年,我國以一種極端的手段去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客觀上來講,這不僅僅是為了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是為全人類作貢獻。
第一人稱敘述人“我”的觀點當然不能等同于莫言本人的觀點,莫言在小說中全方位地表現各種人對此政策的觀點,對他們的所為并不做錯與對的評判。莫言一向如此,對各種人都是理解為先,讓其自然地“呈現”其存在狀態。再看賀享雍對計劃生育個案的最終處理,先是巨額的“超生”罰款在村干部暗中幫助下,到鄉政府幾次鬧事之后被取消了,然后最重要的結果是兒子安全又茁壯地成長,作者很有意思地安排了一個小插曲,“超生”的兒子不知道父親生下他會經歷那么多生死磨難,“草生”之名正是對“生于草垛下”的人生磨難的紀念,稍懂事后居然不滿意父親給他取的名字:
你看見兒子淚水橫流的樣子,心又一下軟了,急忙過去抱住他,摸著他的頭說:“好,好,兒子,不管你叫什么,老子都一定要讓你過上好日子!”說完又指了后面的房屋,繼續對他說:“你看,老子給你修新房子了,等你討婆娘時,老子一定給你修一座全灣最漂亮的樓房,你快點跟老子長大吧!”
你說那番話時,聲音之高亢,語氣之堅決,仿佛在對全世界發表宣言一般。
賀享雍對計劃生育的后果和影響的處理明顯與莫言不同。“超生”的兒子給了農民揚眉吐氣的感覺,從村民到村干部都在他這一邊,他們一點也不擔心人口過多會造成什么問題,他們只要解決自己的傳宗接代的個人之事,和政府斗智斗勇他們也不認為有什么錯,反而認為自己這樣做就是“好人”應為之舉。或者這算是計劃生育的悖論之一。畢竟已經是過去時。作家寫作時計劃生育仍然很嚴格,但已經準許生了女兒的農民生二胎,作家在整個過程中,對計劃生育沒做任何評價,但同情全在農民一邊。而《蛙》中的隱含作者莫言則未站在任何一方,他是“超人類”的。“超生”者受盡磨難,如陳眉的毀容到代孕到變瘋,計劃生育的執行者也面臨心靈的折磨,姑姑萬心晚年陷入扼殺數千生命的自責與贖罪的躁郁幻覺之中,不能生育的敘述人“我”在代孕后也陷入對代孕者陳眉的歉疚之中,形成了整本書的“救贖”基調。而莫言作為隱含作者,則跳出“三界”之外,冷靜地展示著蕓蕓眾生的各種悲歡離合的表演。
賀享雍的處理當然與他的立場有關。他和趙樹理一樣始終在鄉村之“內”。趙樹理如果此時還健在,應該也不太會贊同嚴苛的計劃生育制度。除了身份與趙樹理非常相似,賀享雍面對的時代遠比趙樹理的時代更復雜,趙樹理面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鄉村,啟蒙是遠距離的小劑量吸收,而在賀鄉雍的時代,知識分子群體啟蒙權威話語仍然是主流,否定傳統成為一種定勢,經濟倫理掌控一切,后現代消費文化甚囂塵上,人群越來越松散成原子化個體,這都使人的群體思維越來越難以融合。進一步說,賀享雍在鄉村之“內”并非就是全面“正確”,此立場同樣面臨眾多的難題。只從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鄉村怎么都是“發展”的“負效益”,只是關注農民的生存似乎很難獲得大工業時代的大眾的支持;如果不關注,鄉村又確實是弱勢,有違作家的精神高位和理想主義追求。關注的話又不知從哪個方面入手。所以對于賀享雍,個人、主體、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都很難再有一個堅定不移的、固定的理想或想象標準。未來的走向是高度不確定的。這實際是人類文明中的“現代”或者“超現代”走向何方的問題。不管如何想象,都可能被人類飛速發展的步伐否定,甚至變成笑柄,這是人類自身的難題,反映在作家那兒,就是理想的破碎,再難以有人類高度或超人類高度的永遠閃亮的精神光環。
對于這個后工業時代或量子時代,莫言的處理方式則非常有道家色彩,他用后現代的方式、以中國的道家為核心整合了所有的思想,最終是跳出人類的局限,在人類之外從宇宙視點以超人類的廣大存在為參照,從點、線、面、體到超三維事物等人類無法認識的層面進行量子宇宙式的觀照。所以莫言會時而在鄉村之“內”,時而在鄉村之“外”,而且莫言之“內”非“內”,其“外”也非“外”,其時時表現出神出鬼沒的超越性,幾乎無人可解。
從一個優秀作家的標準來看,不但要有優良的敘事能力、深刻的思考和敏銳的洞察力,還要有對人類的無區別意義的悲憫,特別是對弱勢的同情和理解。前一點需要更多的才華和天賦,并非想達到就能如愿的。對于后一點,即立于鄉村之“內”真正地關懷農村和農民,中國的作家多數能做到,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中國革命的影響,賀享雍也很好地做到了后一點。巴爾扎克作為一個資產階級作家,他卻沒有做到,因為他一生都在鄉村之“外”,但他卻相當完美地做到了前一點。不管怎么說,巴爾扎克都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欲望的泛濫、他的虛榮的矛盾、他對金錢和財富的羨慕與渴望,與他的高超文學才華一起,都造就了他文學的復雜和難以企及的深度。賀享雍在很多方面與巴爾扎克類似,十本《鄉村志》系列與《人間喜劇》一樣形成了多場景的交錯式宏大布局,在技巧方面,人物的前景與背景的轉換、對各種場景的極其細膩的描寫和主題結構方面的真理化關注等,都無意中與巴爾扎克相似1。賀享雍的不足在于場景的內涵,與巴爾扎克相比,賀享雍的鄉村在主題結構方面過于單一,或者這也是革命留下的思維模式的影響,從單一的革命到單一的批判,容易忽視人類社會的真實存在的復雜性。復雜,或者正是賀享雍今后努力的方向。中國有一個超越人類的復雜性的道家,時刻有“混沌”之“無”的存在,就能不忘宇宙的復雜,注入文學,就是超越人類自我的文學。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