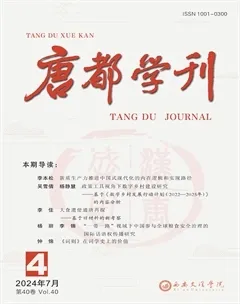國內社會科學視域下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一個文獻綜述
摘 要:人工智能治理是社會科學語境下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方向。梳理CSSCI來源文獻,首先,圍繞人工智能的界定。梳理了主要的五種歧見,分析歧見產生原因,并對關于人工智能界定的共識進行了概括。其次,圍繞人工智能的治理。針對人工智能進行治理的動因、難題及方略,概述了學界的主要觀點。再次,圍繞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針對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的效能、難題、障礙和對策建議,整理了學界的重要看法。最后,對人工智能治理研究的前景進行了展望,包括對深化人工智能治理的相關機制研究、強化人工智能治理的案例研究、定量研究和實證性研究、加強人工治理的合作研究,等等。
關鍵詞: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治理;研究;述評;展望
中圖分類號:TP1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0300(2024)04-0020-08
收稿日期:2024-03-05
基金項目: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大學生創新創業勝任力測度評價與提升的話語互動模型研究”(23JYD005)
作者簡介:王仕軍,男,山東高密人,法學博士,南京工程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主要從事馬克主義基本理論、社會治理研究。
自1956年約翰·麥卡錫在美國達特茅斯會議上正式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以來,人工智能歷經60多年的艱辛探索,一路迤邐跌宕,終于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與第二個十年的交替之際迎來了爆發式增長的黃金時期。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熱潮翻滾、澎湃向前。得益于大數據、深度學習技術的迅速發展及核心算法的突破,以2017年AlphaGo戰勝世界排名第一的棋手柯潔為標志,人工智能不斷從概念走向現實,從科技研發走向行業應用,深刻改變著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乃至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方式,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未來已來,伴隨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智能革命大幕拉啟,“人工智能已然成為定義這個時代的‘關鍵詞’之一”[1]。作為引領未來的戰略性、顛覆性、通用性技術,人工智能研究無可爭議地成為國際競爭的新焦點,既是科技研究的關鍵場域,亦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課題。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16年以來,人工智能治理逐漸引發我國社會科學領域專家學者的關注,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本文梳理了國內社會科學領域權威的CSSCI來源文獻,對相關研究熱點進行綜述,并對未來研究的前景進行展望,以期對后來者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關于人工智能的界定
對于人工智能,學術界有不同的認識,這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
(一)何為人工智能:歧見紛紜
人工智能治理研究的前提和關鍵是清晰界定人工智能。關于人工智能的概念主要有五大類說法,分別是:
其一,“機器智能”說。“機器智能”說認為,人工智能是不同于人類“天然智能”的、通過計算機或軟件實現的一種“機器智能”。龐金友認為,人工智能是指“通過軟硬件的結合使機器具有一定程度的類人智慧、思維和行為”[2]。著名的“圖靈測試”強調的就是這一點:“如果一臺機器能夠與人類展開對話而不能被辨別出其機器身份,那么稱這臺機器具有智能。”[3]更有學者指出,人工智能亦稱機器智能,是指“由人制造出來的機器所展現出來的智能”[4]。安維復對“人工智能就是機器智能的說法”提出異議,指出“人工智能不是物,而是人的物化”[5]23,在本質上是人的能力的延展和放大,不是“機器智能”[5]25,而是“人的機器智能”[5]25。這種延展和放大,與人類在歷史上曾經借用石器、機械力等并無二致。
其二,“顛覆性科技”說。此說認為,人工智能本質上是一場科技創新和科技革命,它是引領未來的顛覆性技術,也是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的通用性技術。在賈開等看來,當前的人工智能“是建立在現代算法基礎上,以歷史數據為支撐,而形成的具有感知、推理、學習、決策等思維活動并能夠按照一定目標完成相應行為的計算系統”[6]。楊虎濤認為,人工智能是一種拓展自動化、機械化和標準化的技術體系,是一場“可替代人類體力乃至腦力勞動的技術革命”[7]。王仕軍等依據埃里克·布萊恩約弗森和安德魯·麥卡菲提出的“第二次機器革命”理論,指出當前的人工智能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發展到新階段的產物。在這一過程中,人工智能發展既助推了人類由“第一次機器革命”時代向“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的跨越,也為自己的未來發展奠定了新的基礎,成為“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的通用技術。[8]
其三,“生物工藝學”說。此說認為,人工智能不是簡單的信息通訊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它關涉人腦的問題,是人類走向后人類的“生物工藝學”問題。唐代興指出:“生物工藝學是特指探討人如何完全控制自己的肉體、重構自己的生物本性、生物結構、生物功能的規律、原理、方法、手段的學問。”[9]112人工智能不能膚淺地被看作是“分析人類使用的知識和判斷力并用之于電腦上的技術”,它所指涉的對象是人腦,“是以人的生物腦為研究對象,借助計算機基本理論、以計算機為運算工具來模擬、延伸、擴展人腦工作原理的技術方式和方法系統”[9]112。
其四,“意識形態”說。此說認為,人工智能作為現代科技發展的前沿成果,具有“意識形態”屬性,必將成為智能時代的意識形態。此類說法,源自法蘭克福學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學者關于“技術是隱性意識形態”的理論解說。在沈江平看來,人工智能終歸是科學技術發展演化的產物,作為“一種復合型、集成型的技術深度融合,其既有‘集權的單一技術’特性,又具有‘民主的綜合技術’的特征”,從而成為一種“‘非政治化’的意識形態”[10]。
其五,“多視角界定”說。此說認為人工智能涉及學科眾多、表現形式多樣、功能作用多重,因此需要從多個視角進行界定。李曉方的看法是,對人工智能的概念至少可以從三個視角進行再界定:一是技術視角,認為人工智能本質是一種工程和科學知識,呈現日益多元和場景化的特征;二是市場的視角,認為人工智能是一種產品和行業的形式;三是政治視角,人工智能是一種價值分配的工具,關涉“權利、價值以及責任的再分配”[11]等政治場域的問題。
(二)歧見成因:三種說法
何為人工智能,人們遠未達成共識,學者們見仁見智、歧見紛紜,代表性的看法有如下幾種:
其一,“人工智能迷霧說”。在李恒威等人看來,人們對“人工智能”概念本身的理解相當多樣和含混,頗如一團迷霧。原因有三:一是從內涵上看,“人工智能”概念與最初誕生時相比已出現了根本差異。“人工智能”概念最早是約翰·麥卡錫于1956年在美國達特茅斯會議上正式提出來的,指的是通過軟硬件來實現與人類智能相媲美的智能體。但從現實看,當前的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還相距甚遠,實際不過是機器學習而已。不少人使用時并沒有區分這些概念,甚至將它們混為一談。二是從外延上看,“人工智能”概念在某種意義上是自相矛盾的。這種矛盾被稱作“人工智能效應”,即“只要某個問題被人工智能成功解決,那么該問題就不再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三是企業、媒體以及文學作品的誤導性解讀或宣傳。“它們因其內在的行為方式或各自利益的考慮,都或多或少地夸大或扭曲了人工智能實際能力,并想當然地賦予人工智能一些未經論證的特征和屬性。”[12]
其二,“思想與現實錯位說”。吳彤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將經歷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個發展階段,每一階段的人工智能的技術能力和愿景目標是不同的。[13]人類當前身處弱人工智能階段,而思想已經飛躍到第三階段,即超級人工智能階段,想象著這種強大無比的人工智能是否會取代人類,或奴役人類。這種思想和現實的錯位,導致人們對人工智能的理解和治理的諸多爭論。
其三,“智能理解歧見說”。按照王治東的看法,“準確定義人工智能,困難不在于定義‘人工’,而在于‘智能’一詞在概念上的模糊性”[14]。關于智能的概念,有功能主義、行為主義、演進主義等多種視角,由此帶來關于智能理解的眾多歧見。他認為,由于人類是唯一公認的智能體,智能界定離不開與人類智能的對比,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相比有兩大明顯界限:其一,人類智能具有“知、行、情、意”四大特征有機整合的特點;其二,人類智能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是高度統一的。
(三)人工智能界定:基本的共識
從文獻審讀情況看,盡管對于人工智能的界定學界歧見甚多,達成一致共識亦有難度,但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識:
一是從本質特征看,人工智能是人工物,是人的智能在機器上的體現,它是人為的也是要為人的。二是從地位作用看,人工智能是綜合性、交叉性科技,涉及計算機、醫學、哲學、倫理學等眾多學科,具體表現形式有知識、產品(裝置、程序等)、產業,等等,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標志性技術,是國際科技競爭的新焦點。三是從基本功能看,人工智能的功能是多重的,既包括功能領域的多重如生產功能、賦權功能、治理功能等,也包括功能性質的多重如正功能、負功能、顯功能、潛功能等。四是從技術界限看,人工智能不是無所不能的,人工智能所能達到的技術水平取決于算力、算法和數據三大因素。
二、作為治理對象的人工智能:對人工智能進行治理
人工智能之于治理,首先是作為對象存在,即人們首先要治理好人工智能。
(一)對人工智能進行治理的動因
之所以要對人工智能進行治理,主要的看法如下:
一是技術“自主—失控”說。持此說的學者認為,人工智能作為現代科技,本身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存在“失控”的風險,因此必須進行治理。張成崗認為,現代技術社會始終貫穿著三重邏輯悖逆,即“主奴悖論”“不均衡悖論”“工具與目的悖論”。[15]43此三重邏輯悖逆正持續延展到信息社會中。“由于樣本空間大小的限制,人類的經驗認知容易收斂于局部最優,大數據科學的發展及機器學習能力的躍升有可能突破人類認知的局限性”[15]48;“能否和如何保持對人工智能的控制無疑是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基礎性問題,人類在高度發展的人工智能面前可能沒有反復試錯的機會”[15]48。人工智能失控的結果可能帶來諸多風險甚至災難。
二是“風險技術—技術風險”說。持此說的學者認為,人工智能的風險源自技術的不確定性。從技術本身看,人工智能就是風險性技術;從技術后果看,人工智能的運用就會帶來人工智能風險。鄭容坤指出,風險技術是人工智能的風險因子,技術風險是人工智能的風險后果。[16]112-113風險技術“源于技術理性的認知局限、人類主體的主觀利益、類人自主的它者欲望等技術性缺陷”[16]108。技術風險乃“風險技術的后果顯影,指涉人工智能風險表層波及面的廣博性以及深層次的工具性與價值性兩種動態風險情形”[16]108。風險技術與技術風險互為因果、相互糾纏,使得人工智能風險成為風險社會的獨特險種,由此生成智能時代鮮明的治理議題。
三是“重大風險挑戰”說。持此說的學者認為,任何重大的科技創新的效應都是雙重的,既有正效應,也有負效應;既有“天使”面相,亦有“魔鬼”面相。作為21世紀人類的重大科技創新,人工智能既可為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力,帶來魔幻般無限美好的可能,也可能帶來諸多不確定性乃至顛覆性的風險挑戰。強化對人工智能的治理,有效應對其帶來的顛覆性風險挑戰勢在必行。陳小平認為從理論上看,人工智能存在四種風險:“技術失控、技術誤用、應用風險、管理失誤”[17]。梅立潤基于主體維度和時限維度將人工智能風險劃分為四大類型:“國家主體在短期時限內面臨的失業風險、國家主體在長期時限內面臨的消權風險、社會主體在短期時限內面臨的隱私風險、社會主體在長期時限內面臨的意義風險。”[18]王東等認為人工智能的風險挑戰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即勞動過程人的本質的異化、全球化進程中的資本邏輯與技術壟斷、傳統倫理形態的嬗變與解構、主體規范缺失與定位不明等。[19]何哲將人工智能的社會風險概括為十個方面,即“隱私泄露、勞動競爭、主體多元、邊界模糊、能力溢出、懲罰無效、倫理沖突、暴力擴張、種群替代和文明異化”[20]2。
還有一些學者如閆坤如、董青嶺、姚萬勤、吳河江、孫會巖、闕天舒、趙寶軍、張愛軍等專門撰文討論了人工智能的設計風險、道德風險、法律風險、教育風險、政黨的政治安全風險、國家安全風險、意識形態操控風險、算法權力風險,等等。2022年、2023年元宇宙與ChatGPT橫空出世,夏佳雯、趙精武、高奇琦等圍繞元宇宙、ChatGPT的治理,包括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等進行了初步討論。
(二)人工智能進行治理面臨的難題
對人工智能進行治理的任務艱巨復雜,面臨一系列的困難或者障礙,包括:
其一,技術難題。人工智能的研發和運行高度依賴算法和數據。治理人工智能,從技術本身看,集中在算法治理和數據治理兩個方面。算法治理涉及算法的制定權及相應的監督程序問題,面臨“不可解釋隱憂、自我強化困境與主體性難題”[21]等;數據治理涉及個人隱私的保護、數據價值的分配、數據安全等議題,面臨數據孤島、數據鴻溝、數據非中性等難題。
其二,風險難題。風險應對是治理人工智能的關鍵環節。由于人工智能的技術復雜性、超前性、自主性以及人工智能研發所具有的秘密性、分散性、不連續性及不透明性等特點,使得人工智能帶來的風險具有前所未見的新特征。有學者認為人工智能風險具有三大特征:“技術與社會共生的復雜性”、“當代與未來貫通的長期性”、“全球性與區域性結合的跨界性”。[15]47還有學者指明人工智能風險具有“客觀現實性、主觀建構性、技術非人化”[16]108等特點。從風險應對的角度看,治理人工智能面臨的兩大難題是“事前的風險識別和預防難題”和“風險發生的不可預知性難題”。[22]50
其三,體制難題。治理人工智能是技術治理問題,就是對技術進行治理的問題。傳統的技術治理體制面對人工智能這一新技術的沖擊,面臨諸多不適:其一,人工智能快速應用所造成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凸顯傳統科層治理結構的僵化與低效。其二,“外在的事后規范性治理”,無法解決人工智能的不確定性。其三,人工智能的研發及運用超出了傳統技術治理體制的治理范圍,帶來諸多“治理空場”問題。[23]
其四,法律難題。法律規制是治理人工智能的重要方式。面對加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法律規制存在三大難題或困境:一是“人工智能的不可控性導致的監管兩難”,二是“人工智能風險主體的多元性和不可預知性問題導致了對其監管的法律困惑”,三是“人工智能法律主體的難題”。[22]51
其五,利益難題。人工智能的研發和運用涉及國家、政府、科技企業、研發機構、使用者等眾多利益相關者。他們“都存在于具體的文化社會背景中,多樣性的價值觀念、思維習慣、行為方式和知識背景等構成的社會文化語境必然會傳遞到人工智能技術的各個環節和方面,造成復雜的價值矛盾”[24]和利益糾葛。治理人工智能必然涉及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分配,由此引發復雜的利益爭奪和利益博弈。
(三)對人工智能進行治理的方略
如何高效地治理人工智能,確保人工智能發展的安全、可靠、可控,學者們提出了諸多富有啟發的思路和設想,主要有:
風險應對的思路。針對人工智能研發和運用某一領域的風險,如設計風險、隱私風險、法律風險、教育風險、安全風險、存在性風險等,提出相應的治理對策。如閆坤如針對人工智能的設計風險提出的治理要點是:其一,設計的目的應彰顯“善”的理念;其二,設計過程中應關注正義與公平;其三,應強調設計者的責任意識等。[25]
構建風險善治體系的設想。就是運用風險治理理論,提出治理人工智能的總體性設想。唐鈞[26]指出,必須通過“社會多元主體的共治”,著力構建“可控的應用環境、可靠的安全屬性、合理的責任機制”。為此,必須明確“透明、超前、人本、系統的善治原則”,遵循“本質安全、發展優先、公平公正、統籌兼顧的善治方針”,建立健全“責任到位、聯動、連帶、兜底的善治機制”。鄭容坤認為,治理人工智能的著力點包括:治理理念上,“審視人工智能迭代中技術邊界與人類底線的關聯性”[16]115;治理結構上,“構筑人工智能風險化解的協同治理格局”[16]115;治理工具上,“優化人工智能風險治理的多樣載體”[16]116。
建立健全全球治理體系構想。人工智能技術方興未艾,發展一日千里。考慮到人工智能潛在的高風險性以及一國治理人工智能存在的局限性,必須構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體系。何哲提出的構想是:其一,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風險共識”[20]12;其二,共同推進人工智能的“透明性和可解讀性研究”[20]12;其三,推動人工智能的“全球科研共同體盡快形成人工智能研究自我倫理體系”[20]12構建;其四,推動各國完善人工智能“國內立法”[20]12;其五,推進“全球合作立法和共同監督機制”[20]13建立。
三、作為治理手段的人工智能: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
根據現代治理理論,任何先進科技都是治理對象與治理手段的統一。作為治理對象,它需被治理,以確保科技向“善”;作為治理手段,它又可以被嵌入國家(社會)治理體系之中成為治理手段,成為推動國家(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利器。人工智能亦不例外。這里的人工智能治理指的就是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我國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就明確指出:要“圍繞行政管理、司法管理、城市管理、環境保護等社會治理的熱點難點問題,促進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
(一)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的效能
國家治理層面,梅立潤[27]從信息基礎、政策運行和組織協同三個維度分析了人工智能嵌入國家治理的“有意義的前景”。其一,“增強國家治理信息基礎的完整性、準確性和新鮮性”;其二,“增強國家治理政策制定的科學性、政策執行的有效性、政策評估的準確性”;其三,“增強國家治理的央地、部門和政社之間的協同性”。張愛軍認為人工智能為國家治理提供了新契機,作用體現在“四個推動”:推動了國家對輿論的治理、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的效率化和國家治理的智慧化。[28]
政府治理層面,陳鵬認為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可以有效控制政府規模、提高行政決策質量、優化行政運行流程、推動政府治理精細化、增進政府與公眾的互動。[29]27李曉夏等把“生態”的概念運用到政府治理中,認為人工智能將推動政府治理在四個層面的優化:治理結構“生態網絡”的系統性拓寬、治理體制向“生態交互”的信息化轉變、治理模式向“生態智能”的過程性透明、治理成本向“生態節約”的云端化實現。[30]
社會治理層面,李韻指出人工智能可以推動社會治理方式變革,還可以提升社會治理服務水平和社會治理效率。[31]文習明認為,人工智能給社會治理帶來新機遇,能為社會熱點難點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案,精準預測公共需求,助推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進而全面提升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水平。[32]
城市治理層面,高奇琦等在區分智慧城市和智能城市的基礎上,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在政務、交通、醫療、安全和教育等方面推動城市治理的智能轉型,有效解決城市治理面臨的一系列難題。[33]王楊認為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提升城市公共治理的行政效率、提升城市公共資源的配置績效、促進城市公共決策的民意參與、促進城市公共空間的記憶營造。[34]
此外,王曉斐、張文博等還對人工智能在健康治理、環境治理中的效能進行了分析。朱婉菁、高奇琦等對元宇宙和ChatGPT賦能國家和社會治理進行了一些探討。
(二)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的風險
國家治理的人性化式微。張愛軍認為,人工智能嵌入國家治理的過程中,人工智能的技術化與國家治理的人性化極易發生矛盾和沖突,由此導致國家治理的人性化式微,集中表現在“技術理性取代價值理性、國家治理‘一刀切’、助長官員的懶政濫政、影響官員的人性化關懷、侵犯個人隱私”[28]1等方面。
滑向“技術利維坦”。王小芳等指出人工智能嵌入社會治理可能推動社會治理呈現治理主體機器化、治理體系算法化、治理手段技術化等轉場特征,存在滑向“技術利維坦”的潛在風險,即“人工智能技術賦權與約束的非對稱性潛含著加劇寡頭統治的危險;人工智能嵌入后的行政吸納具有有限性特征,傳統官僚制結構很難主動促進算法和數據的開放性;人工智能時代社會政治力量之間的張力與不確定性可能會加劇社會碎裂”[35]。
智能反治理。劉永謀認為,人工智能作為新技術治理手段,“智能治理并非敵托邦科幻文藝想象得那么簡單、有效和粗暴”[36]32,存在著智能反治理的問題,這構成影響治理效果的風險因素,包括“智能低效、技術怠工、智能破壞、官僚主義智能化和過度治理”[36]29等。
價值悖論。在譚九生等看來,人工智能治理是由“‘數據+算法+算力’所定義的全新治理范式”[37]29。政府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在實現政府治理的價值同時,也存在著“安全、民主、自主、責任、公正”[37]31等價值異化問題;存在五大價值悖論:“安全悖論”[37]31——秩序維護與隱私侵犯,“民主悖論”[37]31——公眾參與與社會極化,“自主悖論”[37]32——決策優化與技術依賴,“責任悖論”[37]32——清晰治理與責任迷離,“公正悖論”[37]33——公正增量與公正減損。
還有學者討論了政府的“去中心化”風險、行政倫理風險、政府信息安全風險和精準治理的“內卷化”困境等。
(三)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的障礙
當前將人工智能嵌入國家和社會治理還存在諸多困難和障礙,制約了國家和社會治理智能化步伐和治理效率的提升,學者們的主要看法是:
體制性羈絆。傳統的國家(社會)治理體制是典型的科層制行政組織體制,特點是縱向層級多、橫向分工細,缺點是難以及時高效地回應公民訴求和應對突發公共事件。“人工智能吁求的是適應性強和高度靈活性的體制模式,其發展和應用呼喚的是政府治理過程的扁平化與網絡化,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各主體之間的協同配合與互動互通,這是人工智能的應用實現最優化的基本前提,同時也恰是傳統的科層制模式難以支撐和實現的。”[29]31
“數據孤島”難題。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高度依賴算法和數據。數據是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資源,開放共享是數據的天性。由于體制、利益、法規等因素的糾葛,我國在數據使用上存在著數據被割據或壟斷于單位、部門、組織、平臺之內,以至于形成了開放性差、共享性不足的數據孤島難題。以政務數據為例,“當下政務大數據在開放與共享過程中仍然存在著技術短板、部門利益、安全陷阱、問責壓力與產權糾結等主要障礙和壁壘,影響著政務大數據的充分開發和利用,增大了行政成本、制度成本和協調成本。”[38]
人才和技術瓶頸。人才和技術是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的關鍵環節。“目前國內的人工智能專業性人才,主要還是面向企業治理和電子商務等層面展開技術研發……直接針對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不足”[39]83,推進國家(社會)治理的智能化缺乏有力的人才和技術支撐,對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大型科技企業的依賴程度較高。
(四)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的政策建議
人工智能嵌入國家和社會治理是技術與政治、技術與社會、技術與文化等雙向互塑的、艱巨曲折的進程。針對人工智能嵌入國家(社會)治理,提升國家和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學者們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政策建議,主要有:
其一,必須以“善智”為基本前提。就是持續加強和改進對人工智能的治理,確保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即實現“善智”,這是人工智能嵌入國家和社會治理,實現國家和社會治理“善治”的前提性的工作。[40]
其二,完善與人工智能相契合的政府治理結構。就是通過革新政府治理理念、優化政府組織形式、強化相關制度建設、加強行政文化建設等舉措,建立和完善與人工智能相契合的政府治理結構。
其三,建立和完善以人工智能為核心載體的政府善治機制。[39]85通過建構和形成針對政府治理的智能化處理系統、創新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政府治理流程、建構政企間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深度合作機制、建構政府人工智能應用狀況的科學評估機制等途徑,建立和完善以人工智能為核心載體的政府善治機制。
此外,還有很多學者針對人工智能嵌入具體領域的治理,如健康治理、公共安全治理、教育治理、意識形態治理、社區治理等也都提出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政策建議。
四、國內社會科學視域下人工智能治理研究的前景展望
2016年以來,在社會科學語境下,我國人工智能治理的研究進展迅猛,涌現了不少富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一些學者和學術平臺的影響持續擴大,這主要得益于:其一,人工智能“第三次浪潮”的興起;其二,我國關于推進國家(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籌劃;其三,對人工智能進行治理和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的實踐探索不斷深化。總的看來,這一領域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核心作者群還未形成,重大的突破性成果還未出現,這主要與三個“進行時”有關,即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進行時”、對人工智能進行治理實踐的“進行時”和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實踐的“進行時”。從研究文獻梳理的情況看,這一領域的研究存在“三多三少”的特點:理論演繹研究多、案例和實證性研究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單一學科研究多、跨學科研究少,尤其是跨計算機、腦科學、科技哲學、公共管理學科的研究少。未來的研究亟需在如下三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深化對人工智能治理的相關機制的研究。比如人工智能嵌入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機制,就要把為什么要嵌入、為什么能嵌入、嵌入到哪里(嵌入界限)、如何嵌入等這些基礎問題搞清楚、搞系統。當前的研究在此方面還需深入。
二是強化人工智能治理的案例研究、定量研究和實證性研究。跟蹤人工智能技術前進的步伐,密切關注對人工智能進行治理和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治理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強化案例研究、定量研究和實證性研究,突出問題導向和精準導向,既把“論文寫在大地上”,又充分體現科學研究“第四范式”的時代特點。
三是加強人工治理的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科技是綜合性科技,人工智能學科是交叉性學科,人工智能科技的功能和影響復雜而多重。社會科學語境下人工智能治理研究要打破學術、學科的藩籬,加強自然、人文、社會科學等各學科以及學術界、科技界、實踐界的合作研究,既要提升研究的系統性,又要優化研究成果的可用性。
參考文獻:
[1] 吳冠軍.告別“對抗性模型”:關于人工智能的后人類主義思考[J].江海學刊,2020(1):134.
[2] 龐金友.AI治理:人工智能時代的秩序困境與治理原則[J].學術前沿,2018(05下):7.
[3] 盧克·多梅爾.人工智能:改變世界,重建未來[M].賽迪研究院專家組,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4.
[4]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人工智能發展的現狀與前景[J].人民論壇,2018(02下):12.
[5] 安維復.人工智能的社會后果及其思想治理:沿著馬克思的思路[J].思想理論教育,2017(11).
[6] 賈開,蔣余浩.人工智能治理的三個基本問題:技術邏輯、風險挑戰與公共政策選擇[J].中國行政管理,2017(10):41.
[7] 楊虎濤.人工智能、奇點時代與中國機遇[J].財經問題研究,2018(12):12.
[8] 王仕軍,趙利群,胡志彬.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與中國應對:基于“第二次機器革命”的角度[J].電子政務,2020(4):60.
[9] 唐代興.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人類向后人類演進的不可逆風險與危機[J].江海學刊,2020(3).
[10]沈江平.人工智能:一種意識形態的視角[J].東南學術,2019(2):70.
[11]李曉方.人工智能概念的再界定與政府的治理回應:基于技術、市場和政治視角的分析[J].電子政務,2019(3):4.
[12]李恒威,吳昊晟.人工智能威脅論溯因:技術奇點理論和對它的駁斥[J].浙江學刊,2019(2):55.
[13]吳彤.關于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的若干哲學思考[J].學術前沿,2018(05下):23.
[14]王治東.人工智能風險性芻議[J].哲學分析,2017(5):37.
[15]張成崗.人工智能時代:技術發展、風險挑戰與秩序重構[J].南京社會科學,2018(5).
[16]鄭容坤.人工智能風險的意蘊生成與治理路徑[J].黨政研究,2020(2).
[17]陳小平.封閉性場景:人工智能的產業化路徑[J].文化縱橫,2020(2):40.
[18]梅立潤.人工智能到底存在什么風險:一種類型學的劃分[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119.
[19]王東,張振.人工智能的時代意涵:基于技術變革的風險及規避的視角[J].江海學刊,2020(4):124-125.
[20]何哲.人工智能技術的社會風險與治理[J].電子政務,2020(9).
[21]賈開.人工智能與算法治理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9(1):17.
[22]陳偉光.關于人工智能治理問題的若干思考[J].學術前沿,2017(10下).
[23]程海東,王以梁,侯沐辰.人工智能的不確定性及其治理探究[J].自然辯證法研究,2020(2):38.
[24]賈璐萌,程海東,王鈺.人工智能的價值矛盾與應對路徑探究[J].自然辯證法通訊,2020(8):79-80.
[25]閆坤如.人工智能的設計風險及其規避[J].理論探索,2018(5):22.
[26]唐鈞.人工智能的風險善治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9(4):46.
[27]梅立潤.人工智能如何影響國家治理:一項預判性分析[J].湖北社會科學,2018(8):28.
[28]張愛軍.人工智能:國家治理的契機、挑戰與應對[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
[29]陳鵬.人工智能時代的政府治理:適應與轉變[J].電子政務,2019(3).
[30]李曉夏,趙秀鳳.人工智能時代的“政府生態”治理現代化[J].電子政務,2019(10):91-92.
[31]李韻.借助人工智能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J].人民論壇,2018(08上):112.
[32]文習明.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治理:機遇、挑戰與總體框架設計[J].嶺南學刊,2019(3):83.
[33]高奇琦,劉洋.人工智能時代的城市治理[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9(2):35-37.
[34]王楊.人工智能、城市治理與空間正義重構[J].現代城市研究,2019(12):82.
[35]王小芳,王磊.“技術利維坦”:人工智能嵌入社會治理的潛在風險與政府應對[J].電子政務,2019(5):86.
[36]劉永謀.技術治理、反治理與再治理:以智能治理為例[J].云南社會科學,2019(2).
[37]譚九生,楊建武.智能時代技術治理的價值悖論及其消解[J].電子政務,2020(9).
[38]陳潭.政務大數據壁壘的生成與消解[J].求索,2016(12):14.
[39]胡洪彬.人工智能時代政府治理模式的變革與創新[J].學術界,2018(4).
[40]顏佳華,王張華.以“善智”實現善治:人工智能助推國家治理的邏輯進路[J].探索,2019(6):87.
[責任編輯 賈馬燕 馬力佳]
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sin China:A Literature Review
WANG Shiju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article reviews authoritative CSSCI source literature of AI governance in China. Firstly, it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AI, summarizes the five main types of ambiguities,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m, and concludes the consensus on the definition of AI;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main viewpoint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motivation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AI governance; Thirdly,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AI for governance, it summaries the important opinions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effectiveness, challenges,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using AI in governance; Finally, the prospects of AI governanc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which include further research on its mechanisms, case studies, quantitative and empirical studies,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on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governance; research; review; prosp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