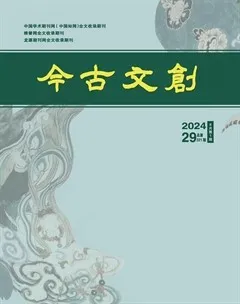梁曉聲小說中的知青 “ 還鄉 ” 書寫研究
【摘要】“還鄉”這一行為是梁曉聲小說敘述的矛盾起點,在“還鄉”書寫中,知青們為了生存逐漸舍棄北大荒知青身份,以城市創業者的身份開始新生活。通過網狀敘事結構展現知青完成群體分化的過程:以知青身份構建復雜的人物關系網,在倒敘和插敘、現實與回憶的交錯敘事時間中逐漸分割過去與現在,不同敘事空間的個體選擇呈現群體分化結局。梁曉聲開辟了“還鄉”書寫新模式,以知青的“故鄉錯位”關注一代青年的奮斗經歷,寄寓了作家對知青的深厚情誼。
【關鍵詞】知青小說;“還鄉”書寫;梁曉聲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9-006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18
“還鄉”是中國文學中一個具有古老淵源的母題,也是中國人情感表達和精神寄托的常見意象。對“還鄉”母題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原始蒙昧時代的神話和早期文學文本《詩經》《楚辭》中。有學者關于中國文學“還鄉”母題原型研究發現,從發生學的角度看,“還鄉”的心理訴求來源于人們對生命的體驗和思考——從對誕生到死亡的生命過程的驚顫,對肉體和靈魂分離、歸棲的生命構成的想象。①知青群體在歷史轉型時期所經歷的不僅是身份的轉變,還有生存困境和內心惶惑導致故鄉錯位帶來的精神重建。“還鄉”行為背后承載著知青共同體意識逐漸削弱的結果,“還鄉”的游子失去“游人”集體認同,也未能被城市完全接受,他們是在時代飛速進步中強行適應的一批人,既從心理上離開了城市,又在距離上離開了承載的理想的精神故鄉。“還鄉”后的“再離鄉”不僅意味著知青群體的分化和再造,還體現了青年實現自我價值的認知變化和國家發展路線的轉向。趙青曾從心理學角度剖析知青們生存的困境和人生的惶惑:“對于知青來講,他們作為一個群體,被迫完成了兩次生存空間的遷移……他們不僅在生存空間上有無法消除的焦慮感,甚至精神空間上,這種焦慮感變得更為沉重,因此‘家歸何處’‘魂歸何處’就成了知青作家群為完成自我構建而想要探討的問題之一。” ②“還鄉者”與故鄉格格不入是中國現代文學文本中常見的話語模式,梁曉聲書寫了特定歷史時期從鄉村返回城市的一代青年人如何更換身份和理想的過程。通過敘事策略逐步實現知青集體的分化,在失去集體身份之后,這批還鄉者們帶著焦慮完成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離鄉。
一、知青還鄉后的身份變化
對知青們而言,回到故鄉恰是與故鄉疏離的開始zs4V8/qQl+loNO5tkcVqbw==,身在北大荒時城市是寄托溫暖向往的避風港,回到城市卻發現故鄉殘酷冷漠的一面。“家”這一最后堡壘對待業知青而言形同于無,甚至成為壓力與尷尬的一種來源。③他們被迫以外來者的身份重新爭奪城市生存的權利,而他們身上揮之不去的北大荒經歷又成為知青在城市抱團立足的唯一憑借,青年們的掙扎與迷茫來源于身份重建過程中無序的探索。
(一)“還鄉者”的窘迫處境
長期分別致使知青們回到家鄉后還來不及修補薄弱的家庭關系,就要為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發愁的困境。返城知青大都到了成家立業的年紀,生存所需的物質基礎亟須滿足。但是他們在北大荒的工作經驗在城市一文不值,想要在城市找工作維持生活都要依靠父母的社會關系。《雪城》借鐵路局領導之口說:“要接父母班的人很多啊……許多當父母的為了早點讓返程待業的孩子有個工作,不到五十歲就打報告申請退休哇!” ④對大部分返城知青來說,對家人的歉疚和對城市的怨懟成為他們沉重的心理壓力。“他們感到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匱乏帶來的窘迫,而更多的是一種從高尚的身份跌落到卑微者的無所適從。巨大的反差讓他們不得不在現實面前自慚形穢……他們可以忍受貧困,卻難以忍受這種來自精神上的折磨。” ⑤少時熱烈的理想精神被北大荒的風雪消磨,更深層的是對自我選擇的懷疑。姚守義想要報考師范學院的師資進修班,可是他母親道出了實情:“十來年你連念過的中學課本都沒再摸過一次。”知青們當年是先進思想和知識文化的攜帶者,現在卻是落后的弱勢話語方,這種位置的倒轉使他們萌生巨大的疏離感。
(二)“外來者”的強勢融入
數十萬返城知青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壓力的雙重圍堵之下,每個人都尋找機會宣泄著內心的悲憤與不滿。他們因為知青身份被城市排斥,也以知青身份為號召,個體抗爭最終形成集體抗爭。《雪城》中返城知青們在音樂廳外為劉大文組織了一場特殊的音樂會,引起歌唱家對劉大文的關注;師范學院招教事件內幕公開后知青們大鬧考場,致使包括郭立強在內的多人入獄,郭立強獄中去世直接點燃了知青怒火,引發知青大游行。《返城年代》中林超然賣餃子被工商部門查抄,大量知青聚集到看守所門口靜坐要求釋放林超然。有學者認為:“巨大的心理情結與感情依戀使他總是難以割舍和否定集體強大溫暖的懷抱,但梁曉聲努力地從感情的控制下掙脫,去檢視過度的集體觀念潛在的危險性。” ⑥
(三)“創業者”的艱難困頓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轉型的關鍵時期,大多數知青的人生轉折都與開放市場經濟脫不開關系,返城知青們因人數眾多無法加入城市原有的工作體制內,造成大批待業青年就業難問題。長期下鄉導致知青們不熟悉城市規則,在創業中屢次受限。《返城年代》中林超然和張繼紅曾將舊自行車配件組裝成新的“無牌自行車”售賣,但是遭到市場監管部門的阻攔。后來林超然又組織知青們在冬天賣水餃,經歷風波后辦下了營業執照,正式開始個體經營。《雪城》中嚴曉東抓住機遇,拉關系做個體戶存下了十四萬元,徐淑芳則經歷了艱難的資本積累最終建立了自己的“女兒國”百花玩具工廠。知青在初返城市時,是一個被夾在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一個既獨立又不穩定的特殊階層 ⑦,他們在身份上是城市居民,但對于城市的規范和制度并不清晰,甚至多因誤會而被粗暴對待。創業幫助知青們保留城市生存條件,但卻進一步造成知青集體的分解,創業成功之后小家庭的建立也是致使知青群體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網狀敘事策略去知青化
梁曉聲的長篇小說擅長把握宏觀歷史事件下多人物的刻畫,通過關注個人命運表現時代發展,兩部以知青返城為主題的小說用高度相似的敘事策略書寫了返城知青“去知青化”的全過程。知青群體在城市家庭生活中被分解成單獨的個體,個人意志隨著現實和記憶的插敘回溯逐漸確立新的方向,篇末人物的不同命運也暗示了改革開放背景下知青底色進一步消逝。
(一)復雜的人物關系
梁曉聲在小說開篇以縱橫交錯的人物關系組建出一副緊密聯結的知青關系網。《雪城》以姚玉慧展開,圍繞在她身邊的人物有同兵團的劉大文、徐淑芳,又在這二人之下引出劉大文的妻子袁梅,徐淑芳的男友王志松、現任丈夫郭志強以及嚴曉東、姚守義、吳茵、郭立偉、曲秀娟等人。《返城年代》則圍繞知青夫婦林超然、何凝之,以及他們的家人林嵐、何慧之、何靜之與兵團知青楊一凡、羅一民等人展開敘述。知青身份構建的關系網絡相互交錯,甚至隨著時間的延續增加或變換交點,使得故事矛盾集中發生在讀者視野。由于知青經歷遺留的社會關系也必然造就他們之間命運互通,然而隨著個人選擇不斷分化,大多數人在擺脫知青群體影響后通過個人奮斗獲得新的社會身份,知青關系網解體。
(二)交錯的敘事時間
在“還鄉”這一動作下的小說敘事離不開關于回憶的倒敘,以及補充人物命運的插敘。《返程年代》中林超然對弟弟林超越的回憶是分幾次補充完整的,由一開始想起就會覺得痛苦,抱著深切懷念小心翼翼地隱瞞死訊,到后來與父親說起弟弟生前好笑的事,甚至將弟弟與戀人的相處講給家人。從林超然的變化上可以感受到北大荒記憶前后的分別,林超然接受了弟弟離去的事實,牢牢記住弟弟生前鮮活有趣的面貌,不再將生離死別看作和弟弟最深刻的記憶片段。閃回、閃前的運用豐富了人物形象,在《雪城》中徐淑芳經歷了四次情感,性格也由一開始的柔弱猶豫變成后期的有膽有謀,小說通過寫北大荒時期——返程初期——丈夫去世——創業成為廠長幾個時期的前后事件,詳細解釋了徐淑芳性格形成的契機與原因。但在實際敘述中,作家并沒有按照順敘的時間順序,而是穿插跳躍,增強了人物的陌生化。
(三)多重敘事空間
梁曉聲構建了許多家庭空間,知青“返鄉”前后最大的空間樣態變化就是由北大荒的集體空間回歸到城市故鄉的個體空間。北大荒作為知青集體空間,在小說敘述中也存在著高度一致的傾向,尤其是荒原的廣闊與城市的擁擠、北大荒人的淳樸和城市人的市儈、大展拳腳的理想主義高揚和處處受限無處施展的現實困境,在知青心里形成對立的兩種空間印象。在小說的后半部分,知青群體完成分化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通過對不同知青家庭的敘寫,更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壁壘。《雪城》在結尾徐淑芳的婚禮上對知青現狀進行了總體觀照,王志松和吳茵來之不易的婚姻已經名存實亡,曾經是知青中心的指導員姚玉慧找借口缺席,其余人也各懷心事,將婚禮當作社交場合擴大自己的社會關系。小說開篇因知青身份緊密聯系的眾人,在城市空間中已經因其各自的新身份失去了統一立場。
三、知青“還鄉”的現代性錯位
城市和鄉村在文學中一直是常見的兩種文化符號。樸婕關注到梁曉聲作品中的城市意義:“城市的意義在此是多重的,它首先是知青生長和獲得知識的土壤。” ⑧北大荒的意義也可以對應著進行定義,它是知青實現理想的載體,也是知青理想事業的見證;返城時期它是知青記憶中的精神故鄉。現代小說還鄉母題是基于游子身上他鄉烙印造成回到故鄉產生滄桑感和陌生感,在知青返城事件中具備這樣的因素,知青群體是城市的“鄉下人”,雙重身份使他們對“故鄉”認定產生錯位。
(一)城市潛規則的掣肘與熟稔
在物理空間上,城市是不容置喙的故鄉,也是知青們在遠行歸來后產生撕裂的痛苦的家園。而在價值觀念的文化身份上,他們則更為熟悉北大荒的生存法則。有學者直言:“在人格形成的最關鍵時期,知青們接受了以理想主義和集體主義為主體的價值體系的熏陶和導向,十一年的北大荒生活后重返城市,時間與空間的雙重變化背后是異質價值準則的交鋒碰撞。” ⑨首先,知青在北大荒形成的集體意識是不便于在城市這種擁擠生存空間下以個人家庭為組成單位的空間生存的。在《返城年代》中林超然從搬運工變成路邊工,因急需賺錢但工作機會少,沒有聯系一同失業的兵團工友,被人當面叱罵。另外,城市對于“托關系走后門”等灰色手段的運用也比北大荒更為直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雪城》中沒下過鄉的郭立偉為了哥哥回城的機會設局與區知青專管蓋章的家伙認識,威逼利誘獲得了蓋過章的病返申請書。從北大荒回來的哥哥郭立強在監獄里隱忍著無端的挑釁,卻被騙拿起鐵鍬,被當作暴動分子擊斃。徐淑芳創業之初在廠房置換過程中艱難疏通關系,還為此賣掉了自己的城市戶口,收到的錢卻被公社扣留,最終拿到手的只是賣戶口的兩萬元錢。而在成為玩具廠長之后,她深諳此中關竅,不僅將事業做得風生水起,還用自己的婚姻一舉化解了被羅織的罪名。
(二)北大荒記憶的沉湎與揚棄
在傳統歸鄉母題定義中,“故鄉之‘鄉’是生命出發之‘鄉’,也是與都市相對的鄉村之‘鄉’,與異域文化相對之本土文化之‘鄉’,與道德淪喪、人性衰退、精神荒蕪相對的道德人倫醇美、人性自然、精神健康之‘鄉’。” ⑩從這一意味上看,北大荒似乎是更為合格的理想故鄉,大多數知識青年都在內心保留著北大荒精神家園的一席之地。從還鄉者的角度來看,跨越千里接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特別是在這種體系中獲得過極高榮譽和地位的人,猛然失去這種身份對于他們來說是不小的打擊,一定程度上壓抑著其對故鄉的認同。極為明顯地表現在《雪城》中姚玉慧的身上,她是所有人中最看重北大荒經歷的人,她不斷沉浸在北大荒記憶中,為躲避難以融入的現實生活頻頻向精神故鄉求援。隨著北大荒倉庫管保員的“女兒”扯掉她美好回憶的最后一層遮羞布,對北大荒的回憶分裂成兩種不同立場的講述,姚玉慧主動斬斷了與社會的聯系,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與她形成鮮明對比的另一女性徐淑芳,從知青經歷中汲取了吃苦耐勞的頑強精神,在城市生活中學會新的生存技巧,變成姚玉慧艷羨的對象。
無論是還鄉和離鄉,“此處”和“別處”的距離總是無法得到消弭。返城知青們遭到物理空間城市故鄉的排擠和厭棄,心理上與現實故鄉產生間隙;知青集體身份認同弱化和群體分化后,北大荒精神故鄉也與他們漸行漸遠。去知青化導致一代青年們曾寄托理想的精神家園落空,知青還鄉后感受到的是與精神故鄉的地理距離感和與物理故鄉的文化距離感。梁曉聲以飽含真情的筆觸道出了知青返鄉后的迷茫與蛻變,為“返鄉”題材增添了新的寫作范式。
注釋:
①何平:《中國文學“還鄉”母題原型研究》,《民族藝術研究》2004年第3期。
②趙青:《生存的困境與人生的惶惑》,河北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
③徐曉東:《〈雪城〉:徘/Sz0wpjK/OvozUamuY/K+jY3/7TGmMwtpXjl+6TDrj8=徊在理想與世俗之間的精神殉葬之作》,《理論與創作》2004年第3期,第69-75頁。
④梁曉聲:《雪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版。
⑤黃昕:《艱難的回歸之路——讀梁曉聲〈雪城〉》,《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年第8期,第62-67頁。
⑥徐曉東:《〈雪城〉:徘徊在理想與世俗之間的精神殉葬之作》,《理論與創作》2004年第3期,第69-75頁。
⑦劉明明、盛昕:《社會融入與身份認同:后知青時代的集體記憶》,《新疆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第147-156+159頁。
⑧樸婕:《論梁曉聲的小說創作》,《小說評論》2019年第5期。
⑨徐曉東:《〈雪城〉:徘徊在理想與世俗之間的精神殉葬之作》,《理論與創作》2004年第3期,第69-75頁。
⑩何平:《現代中國小說還鄉母題的“轉換”和“安置”》,《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
參考文獻:
[1]何平.中國文學“還鄉”母題原型研究[J].民族藝術研究,2004,(03).
[2]趙青.生存的困境與人生的惶惑——知青文學的空間焦慮研究[D].河北大學,2019.
[3]徐曉東.《雪城》:徘徊在理想與世俗之間的精神殉葬之作[J].理論與創作,2004,(03):69-75.
[4]梁曉聲.雪城[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
[5]黃昕.艱難的回歸之路——讀梁曉聲《雪城》[J].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8(06):62-67.
[6]劉明明,盛昕.社會融入與身份認同:后知青時代的集體記憶[J].新疆社會科學,2019,(06).
[7]樸婕.論梁曉聲的小說創作[J].小說評論,2019,(05).
[8]何平.現代中國小說還鄉母題的“轉換”和“安置”[J]. 江蘇社會科學,2012,(06).
作者簡介:
趙奇薇,女,漢族,河南安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